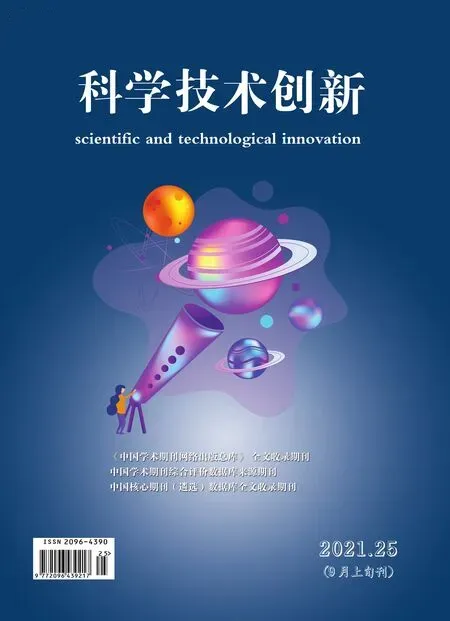百分位數在倒春寒氣象指標研究中的應用
盧 堯 沈 陽 楊瓊瓊 姜 麟
(1、蕪湖氣象局,安徽 蕪湖 241000 2、江蘇省氣象臺,江蘇 南京 210008)
“倒春寒”是一種冷空氣引發的春季低溫凍害[1-2]。相關研究表明,春季持續低溫可對多種農作物生長,甚至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影響[3-15]。鑒于倒春寒的破壞作用,相關研究基于溫度距平和最低氣溫提出了多種監測標準[16-18]。倒春寒作為一種春季異常低溫現象,每次過程持續時間和最低溫度的數值各不相同,因此嚴重程度有所區別。百分位數[19]在研究氣象災害嚴重性方面有著廣泛的應用,但現有成果主要涉及極端天氣氣候事件[20-26],鮮有針對倒春寒的研究。鑒于目前江蘇省氣象部門無業務化的倒春寒氣象指標,研發基于百分位數的,適用于江蘇地區的倒春寒指標,對于監測春季低溫凍害,做好防災減災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1 資料和方法
1.1 資料和倒春寒定義
本文選取了江蘇13 市(南京、徐州、連云港、宿遷、鹽城、淮安、泰州、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和南通)氣象觀測站,1981-2020 年(共40 年)2-5 月日最低氣溫(20 時-20 時)和日平均氣溫(20 時-20 時)記錄。
參考已有研究[27-28],本文對倒春寒的定義為:每年入春至4月30 日,至少連續3 天日平均氣溫<10℃時,則第1 天為倒春寒起始日;由于4 月日平均溫度較3 月有顯著上升,故4 月倒春寒開始條件放寬為至少連續2 天日平均氣溫<10℃時,則第1天為倒春寒起始日;無論在3 月還是4 月,至少連續3 天日平均氣溫≥10℃時,則第1 天為倒春寒結束日。其中入春日期的判定參照《氣候季節劃分》[29]。
1.2 分析方法
根據倒春寒起始日期,定義起始日至結束日的持續天數為過程“持續日數D”(單位:日)。由于結束日當天日平均溫度通常有一定程度回升,故定義倒春寒起始日至結束日前1 天日最低溫度的平均值為“過程平均最低溫度Tmin”(單位:℃)。例如:某次倒春寒過程自3 月15 日開始,至3 月20 日結束,則持續日數D為6 日,平均最低溫度Tmin等于15-19 日每日最低氣溫的算術平均。
將統計后得到的各測站D 按升序排列,Tmin按降序排列,各取2 個百分位數作為閾值,將D 序列和Tmin序列各自劃分為輕度、中度和重度3 個區間,根據D 和Tmin兩個因子的嚴重程度,綜合判定倒春寒等級,判定方法詳見表1。

表1 倒春寒等級判定
2 結果與分析
2.1 入春日期
如前文所述,倒春寒是發生于春季的異常低溫事件。故統計倒春寒事件的首要步驟,是確定入春日期。參照《氣候季節劃分》[29],1980-2020 年江蘇13 市最早入春日期大多位于3 月2 候,個別地區可提前至2 月4 候(南京、蘇州);最晚入春日期大多位于4 月2 候,個別地區可推遲至4 月4 候(連云港、鹽城)。平均而言,長江以南地區入春日期為3 月4-5 候,長江以北地區入春日期為3 月5-6 候。
2.2 倒春寒起始時間
將全省13 市劃分為淮北(徐州、連云港、宿遷和淮安)、江淮之間(鹽城、泰州、揚州和南通)和江南(南京、鎮江、常州、無錫和蘇州)三個地區。以候為時間跨度,3-4 月全省分區倒春寒起始時間分布各有其特點(圖略)。淮北地區和江淮之間地區呈現單峰結構,兩個地區倒春寒均在4 月1 候出現最為頻繁,分別達34 次和31 次;而江南地區呈現雙峰結構,倒春寒在3 月5 候和4 月1 候出現最為頻繁,兩個峰值分別為33 次和35 次,極為接近。需要注意的是,4 月5-6 候從未發生過倒春寒,因為該時段冷空氣強度和活動顯著減弱,日平均氣溫難以維持2 天以上低于10℃狀態;這也是1.1 節將倒春寒時段限定為“3-4”月的重要原因。
2.3 倒春寒時空分布特征
2.3.1 總體分布
由圖1a 可知,1981-2020 年,倒春寒多發生于江南地區,鎮江、常州和無錫各存在一個大值中心;緯度較高的淮北地區反而倒春寒頻次較少。全省13 市中,揚州倒春寒總頻次最少,40年間僅23 次;鎮江最多,達34 次。就全省平均狀況而言,各市年均發生倒春寒0.7 次,泰州、鎮江、常州和無錫共4 市年均頻次高于全省平均值圖1b。

圖1 江蘇1981-2020 年倒春寒累計頻次(a)和年均頻次(b)
分區平均后,淮北地區倒春寒年均頻次為0.7 次,江淮之間地區為0.6 次,江南地區最高,達0.8 次。由上文可知倒春寒年均頻次高于全省平均值的4 市中,有3 個位于江南地區,故倒春寒在江南地區最為頻繁。
全省逐年倒春寒總頻次(圖2)表明,1981-2020 年,年總頻次最高為28 次(2013 年),最低為0 次(1986、1991、1992、2002、2007、2012 年),年均頻次為9 次。40 年中,有19(18)年總頻次高(低)于平均值,如圖2。

圖2 江蘇逐年倒春寒總頻次和年均頻次
從年總頻次的峰值看,1981-2003 年期間,峰值均小于15次,最多為14 次(1981 年、1990 年);而2004-2020 年期間,峰值均大于等于15 次,其中有4 次峰值達20 次以上(2004、2010、2013、2018 年),最多為28 次(2013 年),是2004 年之前的2 倍。綜上,全省各年倒春寒總頻次的峰值,自2004 年起發生了顯著增長的現象,其中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
2.3.2 百分位數閾值的確定
如1.2 節所述,本文使用“持續日數D”(單位:日)和“過程平均最低溫度Tmin”(單位:℃)作為判定倒春寒天氣過程強度的2個因子。參照相關研究所用方法[17-23],選定第80 百分位數和第50 百分位數作為閾值,將上述2 個指標劃分為輕、中、重三個區間。由于相同百分位數對應不同站點的數值亦不相同,為統一監測標準,本文采用平均值方案,全省平均和區域平均的對比結果如表2 所示。
因子D 的80%分位數均值為6,標準差為0.6,占均值比例10。00%;50%分位數均值為4,標準差為0。因子Tmin的80%分位數均值為3.9,標準差為0.5,占均值比例12.82%;50%分位數均值為4.8,標準差為0.4,占均值比例8.33%。
結合其他百分位數(表略)可知,因子D 和因子Tmin的標準差均隨百分位的增加呈上升趨勢,其中因子D 的標準差增幅更為顯著。說明百分位數越高,各地區對應的數值分布愈加混亂,故不宜采用全省均值方案。
若采用分區方案,因子D 的80%分位數中,淮北地區標準差和全省標準差均為0.6,但淮北地區均值升為7,標準差和均值比例降為8.57%;江淮之間地區、江南地區和全省均值均為6,但2 個分區標準差降均降至0.5,標準差和均值比例亦降為8.33%。因子D 的50%分位數中,各分區和全省相比無變化,均值(標準差)均為4.0(0.0)。
因子Tmin的80%分位數中,淮北、江淮之間和江南地區的標準差(0.3、0.3、0.4)較全省標準差(0.5)均明顯下降;淮北地區均值(3.3)較全省(3.9)減小,其他2 個分區(4.0、4.3)則上升;計算結果表明,分區的標準差和均值比例(9.10%、7.50%、9.30%)較全省(12.82%)顯著降低。因子Tmin的50%分位數分區均值較全省均值的變化與80%分位數完全一致,3 個分區的標準差和均值比例(4.55%、6.12%、5.88%)亦較全省(8.33%)顯著降低。
綜上,從標準差和均值之比看,采用分區均值方案確定百分位數作為倒春寒強度劃分閾值,相較采用全省均值方案更為合理。故本文最終確定的江蘇省分區倒春寒因子D 和因子Tmin的強度閾值如表3 所示。
2.3.3 不同強度倒春寒時間分布
圖3 表明,1981-2020 年期間,輕度倒春寒年頻次隨時間波動較大,3 個峰值分別出現在1981 年(12 次)、1997 年(12 次)和2013 年(16 次)。中度倒春寒年頻次在1988-1990 年出現一組峰值(8 次)后,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自2009 年至2013 年,峰值又迅速增長至12 次,之后再次逐年下降。中度倒春寒年頻次波動較為劇烈,相鄰年份頻次差值最大可達12 次(2012 年和2013年)。重度倒春寒在1992 年之前較為少發,年頻次最多僅1 次;1993-1995 年頻次開始增多,之后至2000 年不再發生;2001 年之后雖然亦存在連續數年不發生的情況,但總體上進入多發期,年頻次峰值出現在2018 年(9 次)。

圖3 江蘇逐年倒春寒分級頻次統計

表2“持續日數D”(單位:日)和“過程平均最低溫度Tmin”(單位:℃)百分位數分布

表3“D”(單位:日)和“Tmin”(單位:℃)分區分級閾值
三種程度的倒春寒事件年頻次變化趨勢各有其特點。如1993-1999 年,輕度倒春寒年頻次呈現逐年增長趨勢,但中度和重度倒春寒年頻次則逐年下降。又如2010 年之后,中度倒春寒年頻次呈逐年下降趨勢,但重度倒春寒則呈增長趨勢。從服務角度而言,應更多關注重度倒春寒頻次的未來演變。
2.3.4 不同強度倒春寒空間分布
1981-2020 年輕度倒春寒累計頻次(圖略)分布表明,輕度倒春寒頻發區位于南通(17 次)、常州(20 次)、無錫(17 次)和蘇州(21 次)一帶,淮北地區中連云港(17 次)和淮安(17 次)最為頻發,其他地區頻次則相對較少。
中度倒春寒(圖4a)高發區則位于揚州(13 次)、常州(13 次)和無錫(11 次)地區,連云港(7 次)、淮安(6 次)、鹽城(6 次)和南通(5 次)地區最為少發。重度倒春寒(圖4b)分布亦有顯著變化,高發區位于江蘇西部地區和無錫(5 次)、蘇州(4 次)一帶,南京頻次最多(7 次),常州頻次最少(1 次)。
綜上,輕度倒春寒中心位于江蘇東南部地區,中度倒春寒中心向江蘇中部轉移,而重度倒春寒中心則位于江蘇西部地區。隨著倒春寒嚴重程度加深,其頻發區向西、向北轉移的特征十分顯著,如圖4。

圖4 江蘇1981-2020 年中度(a)和重度(b)倒春寒累計頻次
不同等級倒春寒的區域平均頻次(表4)表明,江南地區平均頻次在所有等級上均高于其他地區,與圖1 結論一致;輕度和重度倒春寒中淮北地區平均頻次高于江淮之間地區;而中度倒春寒則是江淮之間地區平均頻次高于淮北地區。
以重度倒春寒事件為例,淮北地區平均頻次為0.10 次/(站年),江淮之間地區平均頻次為0.08 次/(站年),江南之間地區平均頻次為0.11 次/(站年)。由表1 可知,若達到重度倒春寒,則因子D 和因子Tmin中至少有一個達到重度等級。經統計(表略),淮北地區16 次重度倒春寒事件中,重度D 和Tmin分別為12 次和7 次;江淮之間地區12 次重度倒春寒事件中,重度D 和Tmin分別為5 次和7 次;江南地區22 次重度倒春寒事件中,重度D 和Tmin分別為10 次和15 次,如表4。

表4 江蘇分級倒春寒區域平均頻次(單位:次/(站年))
而對于中度倒春寒事件而言,淮北、江淮之間和江南地區平均頻次分別為0.20、0.21 和0.25 次/(站年)。類似的,由表1 可知因子D 和因子Tmin中至少有一個達到中度及以上等級時,方可達成中度倒春寒事件。統計結果(表略)表明,淮北、江淮之間和江南地區中度倒春寒頻次分別達32、34 和50 次,其中符合要求的因子D頻次分別為17、22 和27 次,而因子Tmin頻次分別為26、21和37 次。綜上,在影響重度倒春寒的2 個因子中,淮北地區因子D作用更大,而江淮之間和江南地區則是因子Tmin更為重要。對中度倒春寒而言,淮北和江南地區因子Tmin作用更大,江淮之間地區則是兩者作用相當。可見,造成不同等級倒春寒事件的2 個因子相對重要性存在地區差異;江南地區一致性最高,中度和重度倒春寒均需要重點關注因子Tmin能否達到所需等級。
3 歷史事件檢驗
《中國氣象災害大典(江蘇卷)》[3(0]以下簡稱《大典》)中記錄了2000 年之前發生的影響較為嚴重的低溫凍害事件,考慮到本文所述倒春寒指“入春”之后的低溫天氣,故《大典》中記載的發生于1994 年和1995 年的2 場入春后全省范圍低溫事件可用來檢驗前文所述倒春寒指標的適用性。這兩場倒春寒事件發生時,連云港、宿遷、淮安、鹽城、泰州和南通尚未入春,其他地區統計結果詳見表5。
由表5 可知,在兩場全省范圍倒春寒天氣過程中,有效記錄站點均為7。其中1994 年個例中,D等級均為中度及以上,Tmin等級有3 站為中度及以上,綜合判定4 站發生中度及以上倒春寒。其中徐州1 站達重度倒春寒。《大典》中只查詢到徐州地區受災情況,說明徐州災情最為嚴重,這與文中指標判定結果完全一致。1995 年個例中,D等級中度及以上有2 站,Tmin等級重度則高達5 站,綜合判定5 站發生中度及以上倒春寒。其中無錫1 站達重度倒春寒。《大典》中亦只記錄了無錫地區受災情況,從側面說明無錫災情最為嚴重,這亦與文中指標判定結果完全一致。綜上,以《大典》記錄的倒春寒天氣過程為參考依據,本文所設計的倒春寒指標從范圍和強度兩方面均能很好地反映真實情況,充分證明了該指標在江蘇地區具備完善的合理性和可用性。

表5 倒春寒歷史事件檢驗
4 結論
本文利用1981-2020 年3-4 月日平均溫度和日最低溫度,設計了一套基于百分位數的江蘇分區倒春寒指標,研究結論如下:
4.1 現有倒春寒國標在江蘇地區應用結果存在事件頻次過高的現象,而根據文中提出的指標方案,江蘇各市倒春寒頻次更具合理性;1981-2020 年,揚州倒春寒總頻次最少,鎮江最多;泰州、鎮江、常州和無錫共4 個地區年均倒春寒頻次高于全省平均值;江南地區倒春寒最為頻繁。
4.2 采用“持續日數D”和“過程平均最低溫度Tmin”2 個因子的第50、80 百分位數,將倒春寒分為輕、中、重3 級;隨著其嚴重程度加深,相應等級倒春寒頻發區自江蘇東南部地區向西、向北轉移的特征十分顯著;江南地區所有等級倒春寒頻次均顯著高于其他地區,影響不同地區不同等級倒春寒的因子相對重要性存在差別,未來應更多關注重度倒春寒頻次的演變趨勢。
4.3 本文所設計的分區倒春寒指標判定的事件范圍和等級,尤其是重度倒春寒地區,與《大典》記錄的倒春寒事件完全一致,充分證明了該指標在江蘇地區具備完善的合理性和可用性。
受篇幅所限,文中一些問題未得到充分討論,如2004 年后全省倒春寒頻次顯著增多原因,倒春寒前期信號及預報關鍵點等,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