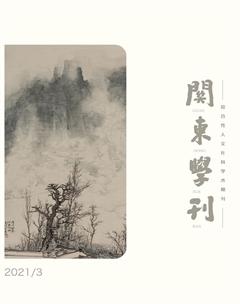徒勞的出走與無(wú)奈的回歸
[摘 要]文人的日常生活與日常交往,鑒于其特殊身份很容易與創(chuàng)作、學(xué)術(shù)研究等職業(yè)活動(dòng)混在一起。日常生活中的瑣碎小事,在普通人看來(lái)不過(guò)是沒(méi)有意義的單調(diào)和重復(fù),卻能觸動(dòng)文人內(nèi)心甚至引發(fā)其創(chuàng)作和學(xué)術(shù)研究沖動(dòng)。就吳虞而言,他“五四”之前蟄伏于四川期間的日常生活特別是與父親的矛盾,對(duì)其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反封建意識(shí)和付諸行動(dòng)起到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他到北大后的日常生活、日常交往與教學(xué)、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也一直是相互影響、互為表里,最終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促成他返回四川。他從沖出四川到回歸四川的過(guò)程,就是他反抗傳統(tǒng)思想和道德規(guī)范并最終無(wú)奈退縮的過(guò)程——盡管這種退縮并非完全倒退和投降。吳虞和魯迅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前后的思想軌跡有較多相似,魯迅終能從彷徨中走出并繼續(xù)前行而吳虞不能,兩人命運(yùn)之異同值得深思。
[關(guān)鍵詞]吳虞;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日常生活
[作者簡(jiǎn)介]劉克敵(1956-),男,文學(xué)博士,杭州師范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教授(杭州 311121)。
以往人們提及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的代表性人物時(shí),大都以定性方式先確定某人的政治文化態(tài)度,例如是贊同新文化還是持反對(duì)立場(chǎng),然后論述其具體觀點(diǎn)以及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的地位和影響,至于這些人物的其他方面往往語(yǔ)焉不詳甚至有意忽略。例如陳獨(dú)秀等人在北大的教學(xué)和工作究竟怎樣,他與北大同事的私交如何?更不會(huì)談?wù)撍麄兊幕橐鰫?ài)情以及其他日常生活內(nèi)容。對(duì)此,美國(guó)學(xué)者福爾索姆的這樣一段話(huà)可謂定評(píng):在中國(guó)史研究中,歷史事件、制度和人物太多地散發(fā)著一種冷冰冰、沒(méi)有人情味的氣息。中國(guó)人的濃烈的溫情和仁愛(ài)消失在職官名稱(chēng)、章奏和上諭的一片混雜之中。……通常缺乏私人生活的記載。……只有把從私人信函、日記和奏折中搜集來(lái)的點(diǎn)滴材料拼湊在一起,研究者才能開(kāi)始看到既有弱點(diǎn)又有力量、既有欲望又有嫌惡的活生生的中國(guó)人形象。
是的,這些歷史人物并未生活在真空中,導(dǎo)致他們走向倡導(dǎo)或反對(duì)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原因可能很復(fù)雜,而來(lái)自日常生活的一些具體因素也不可忽視。陳獨(dú)秀如果不是因?yàn)樗氡贝蠛笠廊簧孀泔L(fēng)月場(chǎng)所而授人以柄的話(huà),可能就不會(huì)在1919年離開(kāi)北大,也就可能不會(huì)有《新青年》同人的內(nèi)部分裂,或者說(shuō)即便有分裂也不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情形。由此可見(jiàn),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細(xì)小事有可能成為改變其人生經(jīng)歷的重要因素,而文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觸發(fā)之個(gè)人感觸和待人接物細(xì)節(jié)等,也常常展示出內(nèi)心情感的深邃復(fù)雜,本文要討論的吳虞就是很好的例證。
一、從反“魔鬼”父親到反孔
被胡適贊譽(yù)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吳虞,一直是作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論述和被塑造。特別是他來(lái)自當(dāng)時(shí)相對(duì)封閉的四川,更可以藉此說(shuō)明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廣泛性和深入人心。從吳虞公開(kāi)發(fā)表文章中看到的確實(shí)是一個(gè)反孔的吳虞、一個(gè)贊同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吳虞,以及一個(gè)和胡適、陳獨(dú)秀、魯迅等并肩作戰(zhàn)的吳虞。可是,如果看吳虞的日記及其詩(shī)詞,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吳虞殘存濃郁的封建士大夫情調(diào)和思想,日記詩(shī)文中散發(fā)出古代文人特有的酸腐氣息——他其實(shí)是一個(gè)說(shuō)新卻舊、說(shuō)舊卻新的人物。只有這兩方面結(jié)合起來(lái)才能看到一個(gè)思想復(fù)雜的吳虞,一個(gè)符合“圓形人物”概念的吳虞。
現(xiàn)存《吳虞日記》從1911年開(kāi)始到1947年結(jié)束,中有少數(shù)缺失,共六十冊(cè)。其時(shí)間跨度之長(zhǎng)、材料之詳盡在那個(gè)時(shí)代的文人日記中極為罕見(jiàn)。據(jù)此,本文將以吳虞日記為主,輔之以書(shū)信以及同時(shí)代人回憶等,以求還原一個(gè)真實(shí)而復(fù)雜的吳虞形象。
打開(kāi)吳虞日記,會(huì)發(fā)現(xiàn)他第一個(gè)抨擊的對(duì)象是他的父親,他對(duì)父親的稱(chēng)呼竟然是“魔鬼”或“老魔”,且看他以怎樣的文字描述父親:
魔鬼一早下鄉(xiāng),心術(shù)之壞如此,亦孔教之力使然也。(1911年12月5日)
本書(shū)所引用之《吳虞日記》,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只標(biāo)明頁(yè)碼或日期,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這一段很有意思,首先是吳虞對(duì)其父親的態(tài)度,其次是把父親如此之壞的緣由歸根于孔教。正是源于對(duì)父親的深仇大恨,吳虞后來(lái)才會(huì)喊出“打到孔家店”的口號(hào)罷。吳虞本來(lái)在父母感情糾葛中傾向于母親而與父親關(guān)系不好,后來(lái)父親為納妾將家產(chǎn)幾乎揮霍一空而把剛成家的吳虞趕回老家,更使得父子關(guān)系趨于破裂,并為爭(zhēng)奪家產(chǎn)訴訟經(jīng)年,最終父子成為仇敵。當(dāng)吳虞勝訴后在日記中這樣發(fā)泄:“大吉大利,老魔遷出,月給二十元。”“余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孫也!”更有甚者,吳虞在其父死后竟然寫(xiě)信給兩個(gè)女兒,“告以老魔徑赴陰司告狀去矣!”
不過(guò)吳虞官司雖然打贏,也為此付出沉痛的代價(jià)。在那個(gè)時(shí)代,與親生父親打官司理所當(dāng)然被認(rèn)為是大逆不道,當(dāng)時(shí)的四川教育總會(huì)會(huì)長(zhǎng)徐炯為此召開(kāi)會(huì)議將他逐出教育界,以致長(zhǎng)達(dá)八年之久整個(gè)四川沒(méi)有學(xué)校聘用他。也正因如此,在這一時(shí)期吳虞的日記中我們看到他除了對(duì)父親的詛咒外,就是對(duì)人生多艱、世事不平的哀嘆以及對(duì)大難將至的擔(dān)憂(yōu):
天冷如冬,一人枯坐,真不知生人之趣,然后知老莊楊墨所以不并立之故,而中國(guó)之天下所以?xún)H成一治一亂之局者,皆儒教之為害也。(《吳虞日記》上冊(cè),第4頁(yè)。)
胡文忠云:天下之將亂也,必先無(wú)真是非。近日法律不加于多數(shù),刑罰惟施于個(gè)人,世衰道喪,恐大禍未已也。(《吳虞日記》上冊(cè),第5頁(yè)。)
盡管吳虞更多是由于個(gè)人境遇不佳才有如此悲觀感受,但他對(duì)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動(dòng)蕩和時(shí)局的看法還是很有遠(yuǎn)見(jiàn)。其實(shí),那時(shí)的魯迅其心境也正與吳虞相同,所以日后他們?cè)谂険舳Y教“吃人”一點(diǎn)上有驚人的一致也就毫不奇怪。且看魯迅剛到北京后的日記:
晨九時(shí)至下午四時(shí)半至教育部視事,枯坐終日,極無(wú)聊賴(lài)。(1912年5月10日)
當(dāng)然,導(dǎo)致吳虞走上批判封建禮教的原因不只是父子之間的財(cái)產(chǎn)糾紛。從吳虞日記中可以發(fā)現(xiàn)其內(nèi)心深處的諸多矛盾以及對(duì)個(gè)人命運(yùn)與性格的深刻分析。不了解這些就無(wú)法理解地處西南一隅的吳虞如何能夠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產(chǎn)生之初,與北京的《新青年》同人有著強(qiáng)烈的共鳴并成為“五四”時(shí)期四川知識(shí)分子的杰出代表。
首先,從日記中可知,吳虞的反孔意識(shí)在“五四”之前很久就已孕育,并不時(shí)有所表現(xiàn)。按他自己的說(shuō)法,早在1906年他留學(xué)日本時(shí)所寫(xiě)的《中夜不寐偶成八首》中,就表現(xiàn)出明顯的反孔傾向:
扣角悲長(zhǎng)夜,迷陽(yáng)發(fā)短吟。英雄欺世慣,賢圣誤人深。
地獄誰(shuí)真入,神州竟陸沉。始知稱(chēng)盜跖,微意費(fèi)推尋。
萬(wàn)物為芻狗,無(wú)知憫眾生。孔尼空好禮,摩罕獨(dú)能兵。
遘禍庸奴少,違時(shí)處士輕。最憐平等義,耶佛墨同情。
其中如“圣賢誤人深”“孔尼空好禮”等句被認(rèn)為具有鮮明的反孔思想,但整體看那時(shí)的吳虞其思想意識(shí)還是與康梁等改良派相同,并非自覺(jué)有意識(shí)的思想批判。當(dāng)然,其日記中攻擊儒教的文字自然多見(jiàn):
孔教專(zhuān)制野蠻國(guó)民——余之生日也。
家國(guó)涂炭如此,孔教之力大矣。(《吳虞日記》上冊(cè),第13頁(yè)。)
中國(guó)人束于儒教之迷信,往往于人情世故糊涂不堪,宜其衰弱至此也。為之三嘆。(《吳虞日記》上冊(cè),第33頁(yè)。)
其次,吳虞認(rèn)為反對(duì)孔子之說(shuō),至少在四川應(yīng)與他首先提倡有關(guān),顯示出比較自負(fù)的一面:
《公論日?qǐng)?bào)》今日登孫逸仙“孔教批”及“如是我聞”一段,反對(duì)孔丘,實(shí)獲我心。四川反對(duì)孔子,殆自余倡之也。(《吳虞日記》上冊(cè),第36頁(yè)。)
對(duì)于封建體制得以維系的重要支柱——中國(guó)的家族制度,吳虞也認(rèn)為很有必要摧毀,并能從一些社會(huì)新聞中發(fā)見(jiàn)家族制度衰落的征兆:
成都一瘋子毆死其父,擬辦永遠(yuǎn)監(jiān)禁。法部駁下謂精神病者無(wú)罪。此家族制將消滅之征也。(《吳虞日記》上冊(cè),第66頁(yè)。)
再次,吳虞長(zhǎng)期以來(lái),由于家庭矛盾和經(jīng)濟(jì)狀況不佳,一方面對(duì)經(jīng)濟(jì)收入和物價(jià)漲跌極為敏感,一方面對(duì)人生艱難和世態(tài)炎涼多有感觸,這些在日記中構(gòu)成了重要內(nèi)容,而且很多都是首先有感于社會(huì)動(dòng)蕩和家庭矛盾的難以解決,然后引發(fā)對(duì)人生艱難的感慨。所有這些,其實(shí)都為吳虞走向反孔、反禮教提供了思想資源和支撐:
余自去歲(指1911年,引者注)歸來(lái),訴訟憂(yōu)勞,罕有寧日。稍得寸晷,讀書(shū)作報(bào),冀獲微資,精力漸衰,疲倦思睡。而社會(huì)之傾陷排斥,家人之污蔑凌藉,初無(wú)已時(shí)。惟恃家庭,略尋生趣。然諸女驕縱,讀書(shū)操作,毫無(wú)進(jìn)境。……諸女鬧擾不休,絕無(wú)戒飭,徒事優(yōu)容,使余憂(yōu)患勞生。在此家庭,現(xiàn)在將來(lái)皆無(wú)可樂(lè),但見(jiàn)擾累之日增耳。(《吳虞日記》上冊(cè),第50頁(yè)。)
念余年二十,先母去世,即受家庭慘酷,同香祖奔波勞碌勤苦已二十年。外遭社會(huì)之陷害,內(nèi)被尊長(zhǎng)之毒螫。年逾四十,人世艱危辛苦,既已備嘗。子死無(wú)后,惟遺數(shù)女,又不受教,來(lái)日方長(zhǎng),真未知稅駕之所,心中為之慘淡久之。(《吳虞日記》上冊(cè),第83頁(yè)。)
為日常生活之煩憂(yōu)困擾的吳虞,自然對(duì)時(shí)間的流逝特別敏感,并很自然地選擇走向老莊,這幾乎是數(shù)千年來(lái)中國(guó)文人不約而同的思想歸宿。在之后的日記中,多次出現(xiàn)了吳虞讀《莊子》的記載,并對(duì)《列子·楊朱》篇,深有共鳴。楊朱學(xué)說(shuō)在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曾獨(dú)樹(shù)一幟,與儒、墨學(xué)派相抗衡,但其實(shí)思想近乎道家,故后為道教所吸收容納。至于《楊朱》一文,結(jié)合吳虞當(dāng)日日記,估計(jì)最能引起吳虞同感的應(yīng)為下面感慨人生短暫的一段:“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wú)一焉。設(shè)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jué)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yōu)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dāng)?shù)年之中,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shí)之中爾。”此段大致意思為:人能活百年的一千人當(dāng)中挑不出一個(gè)。假設(shè)有人能活百歲,那么他處在幼年和衰老的時(shí)間也要占據(jù)一生的一半。睡眠以及白天浪費(fèi)的時(shí)間又幾乎占據(jù)了剩余的一半。至于疾病哀苦憂(yōu)傷懼怕,幾乎又占據(jù)了一半剩下的時(shí)間。剩下那十幾年,能夠舒適自得、無(wú)牽無(wú)掛的日子,恐怕連一天也沒(méi)有。
有意思的是,1914年吳虞為妻子曾蘭所寫(xiě)白話(huà)小說(shuō)《孽緣》進(jìn)行修改定稿后,小說(shuō)發(fā)表在上海出版的《小說(shuō)月報(bào)》上,開(kāi)頭部分幾乎就是對(duì)上文所引《楊朱》一文的復(fù)述,說(shuō)明吳虞對(duì)該文宣揚(yáng)觀點(diǎn)一直持欣賞贊同態(tài)度。
如果吳虞真的能夠讀懂老莊,理解楊朱之學(xué),他就不會(huì)成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的一員大將。吳虞曾留學(xué)日本,雖然學(xué)習(xí)的是法律,但耳聞目睹間也接觸了解了很多西方近代文化思想,這些對(duì)其強(qiáng)化思想意識(shí)中的反封建因素,自然起到正面誘導(dǎo)和激勵(lì)作用。而吳虞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不幸或者平庸,對(duì)于個(gè)性倔強(qiáng)甚至有些頑固的他來(lái)說(shuō)反而激發(fā)他走向不惜與社會(huì)對(duì)抗、與傳統(tǒng)決裂的道路。至于《新青年》的出版以及陳獨(dú)秀、胡適等人對(duì)他的推薦和重視,不過(guò)是誘發(fā)的外因而已。吳虞的“天時(shí)”之運(yùn)極好,他趕上了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之前所有的理論和實(shí)踐的積累正好遇到最佳的表現(xiàn)機(jī)會(huì)。在這個(gè)意義上可以說(shuō)不是他主動(dòng)參與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而是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成全了他。
“西馬”代表人物之一的赫勒,在其《日常生活》一書(shū)中曾這樣論述“時(shí)間”因素在日常生活中的特殊重要性:
日常時(shí)間概念的特殊性,在于倒轉(zhuǎn)的進(jìn)程也可以起作用。……作為概念,不可逆轉(zhuǎn)性在日常思維中不起作用,但是不可逆轉(zhuǎn)的事實(shí)是日常知識(shí)的有機(jī)組成部分。只要想一想錯(cuò)過(guò)機(jī)遇時(shí)我們的感受就足夠了。誰(shuí)在日常生活的過(guò)程中不曾一遍一遍想過(guò):“就是那樣,它決不會(huì)再發(fā)生”,或者“已發(fā)生之事業(yè)已發(fā)生,對(duì)它沒(méi)什么辦法”,等等。同時(shí),雖然我們?cè)谌粘I钪袆e無(wú)選擇,只能接受不可逆轉(zhuǎn)性的事實(shí),但我們不能總是屈服于它。我們禁不住沉思默想不可逆轉(zhuǎn)的過(guò)去,演練其可能性:“假如我……該多好”,“假如……會(huì)是什么情形”。一個(gè)人的生活越是無(wú)望,他愈不容易自覺(jué)地接受已經(jīng)發(fā)生的不可逆轉(zhuǎn)的事實(shí)。
[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259頁(yè)。
就吳虞而言,長(zhǎng)達(dá)八年之久被四川教育界排斥而不能從事教學(xué)的經(jīng)歷以及從20歲開(kāi)始就承受父親的長(zhǎng)期壓制以及后來(lái)爆發(fā)的訴訟,自然對(duì)吳虞的思想情感產(chǎn)生重要影響,也是他常常感到人生無(wú)常無(wú)趣的原因之一。不過(guò),總是不甘心屈服于命運(yùn)安排,更不愿意與時(shí)間妥協(xié),也就等于向生命有限這一絕對(duì)的事實(shí)提出反抗。就日常生活而言,再?zèng)]有比那種日復(fù)一日年復(fù)一年的單調(diào)瑣細(xì)生活能夠消磨生命的了,一切對(duì)人生意義有深刻思考者必然會(huì)對(duì)這樣的生活格外警惕并試圖走出它的束縛。吳虞對(duì)父親的各種反抗乃至憤怒,對(duì)家人的不滿(mǎn)以及對(duì)社會(huì)種種黑暗現(xiàn)象的詛咒,其實(shí)都可以從這一點(diǎn)給予說(shuō)明。
總之,吳虞的聰明或者說(shuō)睿智之處在于,盡管他處于一個(gè)對(duì)自己很不利的生活環(huán)境之中,但目光所及并不總是看到黑暗,而是盡力搜集一些或者說(shuō)從思想上尋找讓自己樂(lè)觀向上的因素,甚至連外來(lái)的基督教也可以成為積極因素:
從前消極主義不可用,須改為積極主義,……孔教既不足法,信仰耶穌亦足為道德之標(biāo)準(zhǔn)。余甚以為然。(《吳虞日記》上冊(cè),第82頁(yè)。)
在這方面,吳虞有意無(wú)意所采取的方式還有許多,例如在經(jīng)濟(jì)上不僅爭(zhēng)取自立,而且力求家境富裕,所以才會(huì)在自己購(gòu)買(mǎi)住宅后有如此感到欣慰的感慨:
二十年來(lái)寄人籬下,中心耿耿。今年始自置此宅,了一件心愿,于恨海中生一線(xiàn)光明也。(《吳虞日記》上冊(cè),第51頁(yè)。)
之后,日記中出現(xiàn)了為有專(zhuān)門(mén)的書(shū)房而欣慰的記載以及連買(mǎi)房紀(jì)念日也特地記入等。此外就是把他人對(duì)自己的評(píng)價(jià)作為激勵(lì)和肯定自己的最好方式,在這方面吳虞甚至表現(xiàn)得有些病態(tài)。如將柳亞子、陳獨(dú)秀等人的第一次來(lái)信全文照錄入日記,并為自己的文章被《新青年》發(fā)表欣喜萬(wàn)分,甚至有“余之非儒及攻家族制兩種學(xué)說(shuō),今得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的自吹自擂說(shuō)法。
更加荒唐的是,吳虞竟然把自己被《新青年》同人承認(rèn)及名聲漸起,與購(gòu)買(mǎi)住宅事聯(lián)系起來(lái),說(shuō)明他骨子里依然是傳統(tǒng)文人的思維方式:
章行嚴(yán)非東南名士所及,陳獨(dú)秀蜀中名宿大名家,柳亞子詩(shī)界革命數(shù)龔定庵、馬君武、吳又陵三人諸評(píng)語(yǔ),皆由余買(mǎi)得此宅已后乃能得,此宅之關(guān)系于余大矣哉。(《吳虞日記》上冊(cè),第311頁(yè)。)
綜上所述,吳虞與陳獨(dú)秀、胡適及周氏兄弟等人,在思想觀念以及對(duì)中西文化認(rèn)知的深度和廣度上一直有較大差異。他從來(lái)不是一個(gè)真正的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倡導(dǎo)者,充其量只是一個(gè)鼓吹者,而鼓吹的原因與他的個(gè)人經(jīng)歷、家庭背景以及長(zhǎng)期單調(diào)乏味和相對(duì)閉塞的日常生活環(huán)境有著密切聯(lián)系。只是歷史的因緣際會(huì),吳虞在反對(duì)儒教的家族制度方面與他們有著共同立場(chǎng)而已。
當(dāng)代學(xué)者冉云飛在其著作《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guó)時(shí)代》中
此處內(nèi)容可參看冉云飛的《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guó)時(shí)代》中“對(duì)吳虞的心理學(xué)分析”一章,該書(shū)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曾從心理分析角度對(duì)吳虞彼時(shí)的心理狀態(tài)給予這樣的概括。他認(rèn)為有五個(gè)方面的因素影響了吳虞,一個(gè)是長(zhǎng)期以來(lái)受到的來(lái)自父親和社會(huì)黑暗勢(shì)力方面的壓抑;其次是因與父親的財(cái)產(chǎn)訴訟導(dǎo)致社會(huì)對(duì)他的道德歧視,使他長(zhǎng)期蒙受一種被強(qiáng)加的“負(fù)罪感”;第三是吳虞一直存在著個(gè)人身份和價(jià)值的“認(rèn)同危機(jī)”,他在長(zhǎng)期受到壓抑迫害的過(guò)程中,比一般人更加需要得到外界的肯定和贊揚(yáng),這也是他把柳亞子、章行嚴(yán)和陳獨(dú)秀等人給他的較高評(píng)價(jià)多次記入日記的原因——他需要這些;第四就是他生性敏感多疑,所以對(duì)外界的反應(yīng)常常過(guò)度,即便對(duì)多年的老友和親屬也不例外,這方面與魯迅倒有幾分類(lèi)似;第五就是上述幾點(diǎn)導(dǎo)致吳虞的內(nèi)心深處一直缺少安全感,因此他才會(huì)急于購(gòu)買(mǎi)住宅,同時(shí)對(duì)經(jīng)濟(jì)收入斤斤計(jì)較。
冉云飛的分析準(zhǔn)確到位,這里稍作補(bǔ)充的是,吳虞任何心理上的矛盾或者說(shuō)看似扭曲變形的心理都與他的個(gè)性和性格傾向有關(guān),更與他所處的具體生活環(huán)境有關(guān)。四川在那個(gè)時(shí)代本就是一個(gè)相對(duì)封閉的地區(qū),而吳虞所處的具體小環(huán)境(無(wú)論是家庭還是他身在其中的教育界)又不能給他這種特殊而敏感的性格以適當(dāng)?shù)陌l(fā)泄和排遣管道,如此長(zhǎng)期受到壓抑的他,必然會(huì)有一個(gè)火山爆發(fā)式的反抗。對(duì)此如果把在四川成都困居八年之久的吳虞,與民國(guó)初年到“五四”時(shí)期一直處于蟄伏狀態(tài)的魯迅進(jìn)行比較分析,會(huì)是很有意義的話(huà)題。
二、沖出四川與回歸寧?kù)o
依仗在《新青年》等刊物發(fā)表的幾篇文章以及陳獨(dú)秀和胡適等人對(duì)他的贊美,吳虞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終于揚(yáng)眉吐氣,成為一個(gè)“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也正是彼時(shí)他獲得的好名聲,為他進(jìn)入北大提供了最好的政治資本。關(guān)于吳虞如何進(jìn)入北大以及到北大后的教學(xué)生活情況等,冉云飛等學(xué)者已有詳盡分析。本文所著重分析的是吳虞進(jìn)北大后心理上的變化,以及來(lái)北大后的日常生活對(duì)他思想情感方面產(chǎn)生的細(xì)微瑣細(xì)卻是長(zhǎng)期復(fù)雜的影響——也許正是這些因素,促成了他的離開(kāi)北大返回四川,最終帶著所謂的“英雄遲暮”之感,完結(jié)其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1925年8月6日吳虞乘火車(chē)離開(kāi)北京,結(jié)束了他在北大任教的生涯,由于戰(zhàn)亂等原因,他直到9月12日才回到成都的家,而家給他的感覺(jué)竟然是:
予歸,至枕頭被褥俱無(wú)多者,家中物件殘缺散失,污穢不堪,真有棲流所之現(xiàn)象,殊可悲嘆也。(《吳虞日記》下冊(cè),第279頁(yè)。)
多年沒(méi)有回家的吳虞居然沒(méi)有一絲快樂(lè)興奮,反而明顯流露出心情不佳,這自然與其多少有些灰溜溜地從北京返鄉(xiāng)有關(guān),與當(dāng)年意氣風(fēng)發(fā)的出川到北大任教,形成了鮮明對(duì)比:1921年5月7日他剛到北京當(dāng)天就與很多北大同事見(jiàn)面,并且不顧旅途勞累與友人一起去中山公園觀賞牡丹。
其實(shí),吳虞進(jìn)北大任教是其一生中最風(fēng)光最得意之時(shí),可惜吳虞自己才學(xué)有限,思想雖激進(jìn)卻并不深刻,個(gè)人言行又極不檢點(diǎn),不僅愛(ài)去風(fēng)月場(chǎng)所,更是將嫖娼寫(xiě)成詩(shī)歌發(fā)表,與“反封建老英雄”形象反差太大,遂激起社會(huì)輿論,導(dǎo)致北大不再續(xù)聘,只得離京返鄉(xiāng)。
殘存于吳虞內(nèi)心那些封建士大夫的情結(jié)和陳舊思想,本來(lái)在北大特殊的環(huán)境中受到很大壓抑,吳虞本人也有意進(jìn)行控制。但一方面長(zhǎng)期客居在外,一方面吳虞的任教隨著時(shí)間和頭上光環(huán)的退去逐漸不再受到學(xué)生歡迎,也促使吳虞想通過(guò)其他方式排遣郁悶,那些被壓抑的情感思想遂得以泛濫。吳虞用其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太光彩的經(jīng)歷證明,他這個(gè)“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骨子里也還是一個(gè)老學(xué)究、一個(gè)與他批判過(guò)的那些封建文人沒(méi)有多少差別的老夫子。
如果詳細(xì)分析吳虞從準(zhǔn)備去北大一直到最后離開(kāi)北大的心理歷程,可以分為這樣一些階段:
從盼望離開(kāi)四川這個(gè)封閉保守的環(huán)境到確定可以入北大的欣喜。
據(jù)冉云飛考證,
冉云飛:《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guó)時(shí)代》,第298-301頁(yè)。吳虞早在其堂弟吳君毅1917年9月從日本留學(xué)回國(guó)入北大任教后就萌生去北大的想法,不過(guò)當(dāng)時(shí)吳君毅自己尚立足未穩(wěn),此事暫時(shí)無(wú)法操作。等到1919年8月后,吳虞之名因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被廣為人知,吳虞本人也與陳獨(dú)秀等人有了書(shū)信往來(lái),且吳君毅也在北大站穩(wěn)腳跟,吳虞入北大事方正式展開(kāi)。吳虞能入北大應(yīng)該說(shuō)吳君毅功不可沒(méi),也與胡適等人的推薦以及馬幼漁等人的具體操作有直接關(guān)系。此處只看吳虞的數(shù)則日記,以見(jiàn)其對(duì)入北大的極度向往和能否如愿的忐忑不安:
爾純,劉士志之子,清華學(xué)校畢業(yè),言胡適以英文譯《孟子》得博士。(《吳虞日記》上冊(cè),第450頁(yè)。)
對(duì)于這樣顯然是誤傳的信息吳虞竟然記入日記,說(shuō)明一方面他開(kāi)始對(duì)北大教師特別是可能與其日后進(jìn)入北大有關(guān)之人給予關(guān)注,同時(shí)對(duì)胡適獲得博士學(xué)位事的關(guān)注,其實(shí)說(shuō)明他對(duì)自己沒(méi)有拿到博士學(xué)位事有些不安,潛意識(shí)中在擔(dān)心是否會(huì)影響自己進(jìn)入北大。
朱伯韓有《書(shū)歐陽(yáng)永叔答尹師魯書(shū)后》文,予因擬國(guó)文題為《書(shū)蔡鶴卿答林琴南書(shū)后》。(《吳虞日記》上冊(cè),第458頁(yè)。)
1919年4月1日,蔡元培給林紓的回信被公開(kāi)發(fā)表在《公言報(bào)》上,而當(dāng)月22日,吳虞就以此作為國(guó)文測(cè)試的題目,這不僅說(shuō)明他對(duì)當(dāng)時(shí)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發(fā)展以及反對(duì)派的攻擊非常熟悉,而且說(shuō)明他對(duì)蔡元培這位北大校長(zhǎng)極為關(guān)注,因?yàn)榇巳伺c他將來(lái)入北大有很大關(guān)系。下面一則日記內(nèi)容,也是如此:
北京十六日來(lái)電,陳獨(dú)秀已釋放。上海十八日來(lái)電,蔡元培二十一日北大開(kāi)校已入校視事。此二消息皆令人欣喜不置。(《吳虞日記》上冊(cè),第486頁(yè)。)
本年六月陳獨(dú)秀被捕吳虞日記中曾有記錄,故此處得知陳氏被釋放,蔡元培重新回到北大視事,則自己進(jìn)北大事大概不會(huì)受到影響,所以吳虞才會(huì)欣喜異常罷。
初到北大的興奮以及由于師生仰慕其反孔老英雄之名而給予的尊敬,其內(nèi)心的得意與滿(mǎn)足。
經(jīng)過(guò)北大胡適、馬幼漁諸人及其堂弟吳君毅的操作后,吳虞終于如愿以?xún)敚?920年12月吳君毅寫(xiě)信給吳虞,告知北大已經(jīng)決定聘其為教授,1921年5月7日吳虞到達(dá)北京。以下數(shù)則日記較為詳細(xì)的披露了吳虞確定來(lái)京及動(dòng)身前后的心情:
和迥來(lái)書(shū)云,養(yǎng)生以多喜為要訣,而予居家中,趣味極少。安能多喜耶。又言,北京為吾國(guó)第一可住地方,弟絕嗜之,吾兄來(lái)此,即知其妙。(《吳虞日記》上冊(cè),第579頁(yè)。)
此段日記寫(xiě)于1921年2月3日,之前吳虞已經(jīng)回信給北大馬幼漁,答應(yīng)去北大任教,故此段中流露出對(duì)北京生活的向往之情。
飯后,唐百川、少坡、沈靖卿、楊哺谷來(lái)談久之,百川長(zhǎng)君擬入北大文科,托問(wèn)旁聽(tīng)規(guī)則。交靖卿水精小印二方,刻吳虞又陵四字。(《吳虞日記》上冊(cè),第583頁(yè)。)
此段文字的背景是北大校方已同意聘任吳虞為教授,且吳虞已經(jīng)收到聘書(shū),連路費(fèi)也由校方支付,赴北大任教事完全落實(shí)。故吳虞不僅對(duì)有人進(jìn)北大旁聽(tīng)事熱心關(guān)注,而且求人刻制名章,急不可待擺出要北上的架子,其得意和興奮之情字里行間非常明顯。
接下來(lái)重點(diǎn)要分析的是吳虞到北京第一天(1921年5月7日)的日記,因重要故全文錄之:
早,六點(diǎn)二十三分到北京前門(mén)。同諸生到西城宗帽二條十號(hào)。楊廉、席文光、倪平歐、梅真如同來(lái)招待黃、敖、聶諸人,君毅留諸人早飯而去。術(shù)伯交予銀四十元,遂過(guò)源利通。晤姚作賓、王弘實(shí)。休息少頃,同君毅往中央公園來(lái)今雨軒看牡丹。晤馬幼漁、馬寅初、蔣夢(mèng)麟茗飲久之。幼漁、夢(mèng)麟意見(jiàn)極反,而外面周旋,仍絲毫不露,足見(jiàn)江浙人之有心也。夜同君毅談久之乃寢。在公園晤鄧慕魯。予歸后,慕魯以電話(huà)約明日晚餐。
此段日記明顯看出吳虞初到北京的興奮、忙碌及對(duì)未來(lái)執(zhí)教生活的期待。首先他對(duì)到京時(shí)間的記錄竟然精確到“分”,在那個(gè)時(shí)代可謂不多見(jiàn),說(shuō)明他對(duì)這次赴京的意義看得很重。其次到京第一天他就去山西的老票號(hào)源利通,應(yīng)該是將術(shù)伯給他的四十元銀票兌換為現(xiàn)金,也是先要做好資金方面的準(zhǔn)備。第三,就是與北大同事的見(jiàn)面,其中當(dāng)然以與馬幼漁、馬寅初和蔣夢(mèng)麟的會(huì)面最為重要,時(shí)間也長(zhǎng)以致他用“茗飲久之”來(lái)形容。至于和堂弟吳君毅近乎徹夜的長(zhǎng)談,更明顯是吳君毅在向吳虞交代來(lái)北大后應(yīng)注意的事項(xiàng)。最后,該日日記將白天與鄧慕魯?shù)臅?huì)面放在最后寫(xiě),而鄧慕魯與吳虞會(huì)面時(shí)沒(méi)有請(qǐng)飯,反而在事后又電話(huà)邀請(qǐng),多少有些蹊蹺?不過(guò)也許僅僅是當(dāng)時(shí)無(wú)法確定?總之,吳虞初到北京必然忙碌,最重要的就是拜見(jiàn)各路諸侯特別是北大的同事及老鄉(xiāng),再次驗(yàn)證了即便是吳虞這樣喊出“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也還是擺脫不掉中國(guó)傳統(tǒng)文人到一個(gè)新地方就要拜碼頭見(jiàn)老鄉(xiāng)、盡快創(chuàng)建自己人際交往圈子的老做法。在這一點(diǎn)上,他無(wú)法做到讓自己保持一種高傲的孤獨(dú)狀態(tài)而拒絕與外人來(lái)往。實(shí)際上之后一個(gè)多月吳虞一直忙于見(jiàn)人和吃飯,也正是在不停的與同事、同鄉(xiāng)的交往中吳虞逐漸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慢慢克服了初來(lái)陌生之地的不習(xí)慣。從他人對(duì)自己的尊敬中,吳虞的個(gè)人感覺(jué)開(kāi)始好起來(lái),終于可以為自己在北大的教學(xué)進(jìn)行準(zhǔn)備,開(kāi)始習(xí)慣北大的教學(xué)生活并建立自己在京的人際交往圈子,心理上進(jìn)入相對(duì)安穩(wěn)狀態(tài)。
吳虞一直耿耿于懷的是自己沒(méi)有兒子,到京之后不久吳虞就聽(tīng)信他人之言開(kāi)始留須,讓人覺(jué)得十分可笑:
十一點(diǎn)半過(guò)鄭淡成公館,淡成言予為木火形人,宜早留須,方可早得子。(《吳虞日記》上冊(cè),第598頁(yè)。)
很難想象吳虞會(huì)信這樣的說(shuō)法,但他一周之后真的開(kāi)始留須,讓人覺(jué)得這似乎不是吳虞這樣的反封建戰(zhàn)士所為——其實(shí)這才是真實(shí)的吳虞,說(shuō)明吳虞確實(shí)想進(jìn)入自己人生的一個(gè)穩(wěn)定狀態(tài),不僅在事業(yè)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免除所謂的后顧之憂(yōu)罷。就在這同一段日記中,吳虞還記錄了友人如何借助所謂的“采陰補(bǔ)陽(yáng)”方法以求延年益壽,分析此段文字,看不出吳虞有任何嘲諷之意,而詳盡的記錄本身說(shuō)明吳虞對(duì)此至少是半信半疑。
晨雇車(chē)過(guò)看馬幼漁。又坐車(chē)過(guò)君毅家,給燕生糖一匣。午餐后同聶燦霄訪胡適之,還《札移》一部。借《崔東壁遺書(shū)》一部,此翻幾輔先哲叢書(shū)本也。又借日人《漢籍解題》一本。適之因作《跋水滸考證》付印,故予文序尚未作。訪陳幼孳不值,送渠《秋水集》一本,留一片。至燦霄公寓一視而歸。(《吳虞日記》上冊(cè),第605頁(yè)。)
這是吳虞1921年6月5日一天的活動(dòng),不可謂不忙碌,也看出吳虞為盡快建立自己在京交往圈子的努力。吳虞先拜訪對(duì)自己在北大任教起到關(guān)鍵作用且自己也最為感激的馬幼漁,然后是因?yàn)樘玫軈蔷阋呀?jīng)出國(guó),所以要到他家看看。第三個(gè)活動(dòng)是拜訪胡適,目的自然是詢(xún)問(wèn)胡適為吳虞文集所作序言是否寫(xiě)好,順便借書(shū)還書(shū)。這里有必要說(shuō)明的是,文人之間的書(shū)籍借還活動(dòng)本來(lái)很正常,但畢竟很多文人不愿意借書(shū)于外人,特別是被視為珍本秘籍之類(lèi)的書(shū)。因此文人愿意借書(shū)于外人,說(shuō)明他對(duì)借書(shū)者比較信任且關(guān)系較為密切。最后吳虞所拜訪的陳幼孳值得一提,陳幼孳,名陳廷杰,四川巴縣人。他1901年中庚子辛丑并科舉人,畢業(yè)于兩廣法政學(xué)堂。曾任兩廣總督署文案、廣西巡撫署文案及四川省寧遠(yuǎn)府知府等。1913年2月任四川省川西觀察使。同年9月任四川民政長(zhǎng),后民政長(zhǎng)改稱(chēng)巡按使,他繼續(xù)任四川巡按使。1915年5月被調(diào)到北京,曾遭彈劾被捕,后獲釋。1920年9月任蒙藏院副總裁。由上述簡(jiǎn)歷可見(jiàn)吳虞拜訪他只因此人是四川老鄉(xiāng),且在政界有較大影響而已。
至于在北大的教學(xué),由于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名聲大振,吳虞一開(kāi)始是受到北大學(xué)生歡迎的,對(duì)此他日記中不乏此類(lèi)記錄:
八時(shí),至北大第六教室上課。聽(tīng)講百余人,有女生一人,室為之滿(mǎn),無(wú)座位,有數(shù)人立聽(tīng)。第二時(shí)雜文,予為介紹當(dāng)讀之書(shū)二十余部,一一為詳言之。(《吳虞日記》上冊(cè),第645頁(yè)。)
字里行間吳虞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特別是吳虞竟然能在百余學(xué)生中發(fā)現(xiàn)有一名女生,可見(jiàn)其觀察力之敏銳,也說(shuō)明在那個(gè)時(shí)代女生能上北大者確實(shí)寥寥無(wú)幾,無(wú)怪乎吳虞要鄭重其事地寫(xiě)入日記。
七時(shí)半,過(guò)北大講《荀子》,約一百五六十人,教師為滿(mǎn)。師自怡言四十一教室,為第一院最大之教室,此外則第三院大禮堂矣,予在北大授課,已滿(mǎn)半月,現(xiàn)象如此,尤不可不勉也。(《吳虞日記》上冊(cè),第651頁(yè)。)
第二教室在二層樓,較四十一教室為大,乃胡適之先生講中國(guó)哲學(xué)史之教室也。第一院以第二教室為最大,四十一教室次之,予之功課乃兼此二教室矣,此為北大國(guó)文系向來(lái)所無(wú)有者也。(《吳虞日記》上冊(cè),第654頁(yè)。)
在吳虞看來(lái),自己來(lái)北大僅僅兩個(gè)月,教學(xué)效果已經(jīng)可以和胡適相媲美甚至超過(guò)了胡適——因?yàn)樗呀?jīng)在北大兩個(gè)最大的教室上課而胡適只在其中一個(gè)上課而已。可以說(shuō)此時(shí)的吳虞,內(nèi)心的成就感和自豪感達(dá)到了頂峰。吳虞沒(méi)有想到的是聽(tīng)課人數(shù)之所以多,還是由于他的反封建老英雄的名聲而不是執(zhí)教水平。假以一定時(shí)間,一旦學(xué)生熟悉其教學(xué)套路和多少有些陳舊的教學(xué)內(nèi)容,很快就會(huì)引起向來(lái)挑剔之北大學(xué)生的厭倦。
由于教學(xué)效果不佳,授課逐漸受到冷落以及學(xué)校欠薪、身體欠佳和嬌玉事引起眾人非議,吳虞內(nèi)心逐漸萌生退意,最終決意離開(kāi):
七時(shí)起,八時(shí)至校,上教室人數(shù)尚不多。(《吳虞日記》下冊(cè),第4頁(yè)。)
十二時(shí)下課。學(xué)生謂予引申過(guò)多,蓋全不知學(xué)之豎子耳。(《吳虞日記》下冊(cè),第6頁(yè)。)
以上兩則日記寫(xiě)于1922年1月,吳虞大概沒(méi)有想到,不到一個(gè)學(xué)期學(xué)生對(duì)自己的課已經(jīng)沒(méi)有了興趣,不僅聽(tīng)課人數(shù)日少,而且居然會(huì)對(duì)吳虞上課內(nèi)容和方式提出意見(jiàn)。學(xué)生所謂“引申過(guò)多”,其實(shí)不過(guò)是表示不滿(mǎn)的一種說(shuō)法而已。當(dāng)年陳寅恪一首唐詩(shī)可以講幾個(gè)星期,肯定會(huì)有很多引申之處,但學(xué)生沒(méi)有意見(jiàn),因?yàn)閷W(xué)生知道陳氏確實(shí)知識(shí)淵博且見(jiàn)解過(guò)人,其引申之處都是大有深意,所以樂(lè)得聽(tīng)其幾乎無(wú)限的引申。而吳虞講課引申過(guò)多但缺少個(gè)人創(chuàng)見(jiàn),自然遭到學(xué)生質(zhì)疑。
對(duì)此可以從其文章中覓得佐證。吳虞最有名的文章當(dāng)屬那篇與魯迅的《狂人日記》呼應(yīng)的《吃人與禮教》。這樣一篇使其爆得大名的文章,認(rèn)真分析一下其實(shí)比較膚淺,全文不過(guò)是從歷史上找了幾個(gè)古代“食人”的例證,然后對(duì)此進(jìn)行分析,所得結(jié)論不過(guò)是驗(yàn)證了魯迅的“禮教吃人”而已。按說(shuō)魯迅寫(xiě)的是小說(shuō),只要把“禮教吃人”用生動(dòng)的故事演繹出來(lái),喚起讀者對(duì)“禮教吃人”的思考和批判,就是小說(shuō)的最大成功。而吳虞所寫(xiě)為思辨性論文,理應(yīng)從對(duì)魯迅小說(shuō)的褒獎(jiǎng)引申開(kāi)來(lái),進(jìn)一步分析為何中國(guó)古代有如此虛偽而殘酷的“禮教吃人”現(xiàn)象,以及引導(dǎo)讀者在今天如何對(duì)其進(jìn)行批判和破除此種愚昧觀念等等。但吳虞在列舉幾個(gè)事例后就以這樣的文字結(jié)束全文:
我們不是為君主而生的!不是為圣賢而生的!也不是為綱常禮教而生的!什么“文節(jié)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設(shè)的圈套來(lái)誆騙我們的!我們?nèi)缃駪?yīng)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趙清、鄭城編:《吳虞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頁(yè)。
此段文字及其全文,給人感覺(jué)就是對(duì)魯迅小說(shuō)進(jìn)行說(shuō)明舉例,不僅思想深度沒(méi)有超過(guò)魯迅,藝術(shù)感染力和引導(dǎo)讀者思考方面更是無(wú)法與魯迅小說(shuō)相比。
其實(shí)吳虞對(duì)于自己的見(jiàn)識(shí)有限和思想淺薄,可能有自知之明。就在他發(fā)現(xiàn)學(xué)生聽(tīng)課人數(shù)日漸減少后,其日記中有了如下文字,似乎是借龔自珍來(lái)表述自己的感慨,或者可以認(rèn)為他就是在為自己上課效果日差而辯護(hù)吧:
龔自珍解“月無(wú)忘去其所能”曰:
人之所以自忘其能者,有二病:一則見(jiàn)異思遷,新近所見(jiàn)所聞益多,則昔年得力之地,以精力不能兼顧而遺忘之,此賢者之過(guò)也。一則暮年頹唐,新亦無(wú)所聞見(jiàn),而舊時(shí)所得與精力而俱謝,此愚不肖之不及也。(《吳虞日記》下冊(cè),第4頁(yè)。)
除了聽(tīng)課人數(shù)減少外,吳虞在北大所遇到的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就是學(xué)校的欠薪,這其實(shí)是那個(gè)時(shí)代幾乎所有教師都曾面臨的問(wèn)題,魯迅在其日記中對(duì)此也有很多記錄。不過(guò),相比魯迅的兼職北大,吳虞可是全部經(jīng)濟(jì)來(lái)源都仰仗學(xué)校,每次北大欠薪吳虞都特別緊張,因?yàn)樗粌H要養(yǎng)活自己還要盡可能支援家人。遭遇欠薪次數(shù)多了,吳虞開(kāi)始萌生辭職回鄉(xiāng)念頭。且長(zhǎng)期客居北京,年齡和身體因素也不時(shí)讓吳虞萌生退意。且看其日記中有關(guān)記錄:
北大前月發(fā)八十四元,今又月余,尚分文未發(fā)。磨骨養(yǎng)腸殊乏趣味,歸歟之感愈覺(jué)其深矣。(《吳虞日記》下冊(cè),第249-250頁(yè)。)
吳虞一開(kāi)始并未想徹底離開(kāi)北大,只是想利用假期回鄉(xiāng)探親兼處理一些雜事。其萌生回家念頭見(jiàn)諸日記者,似乎為1923年,且看該年1月1日日記:
明年秋間,或后年三月,當(dāng)歸蜀,此后書(shū)籍物件,概可勿買(mǎi)。(《吳虞日記》下冊(cè),第76頁(yè)。)
予擬明年二月返里,而教育現(xiàn)狀頗不安,且待至五月再看,若經(jīng)費(fèi)無(wú)著,則當(dāng)請(qǐng)假也。(《吳虞日記》下冊(cè),第115頁(yè)。)
課畢,同幼漁談,予詢(xún)?nèi)粲杌卮ǎV星酚柚剑骱无k法。幼漁云,路費(fèi)三幾百元,校中自然可籌給,至所欠多數(shù),亦止有領(lǐng)得經(jīng)費(fèi)、再行匯川耳。予又詢(xún)?cè)O(shè)予依任叔永例,請(qǐng)假休息一年半載,將來(lái)如再到校時(shí),然后銷(xiāo)假,假中自不支薪,能否。幼漁云,此當(dāng)然可能,不成問(wèn)題也。(《吳虞日記》下冊(cè),第119頁(yè)。)
吳虞長(zhǎng)期客居異地,思鄉(xiāng)之情難免不時(shí)襲來(lái),加上不時(shí)耳聞目睹同事友人去世,聯(lián)想到自己身體欠佳,自然加深返鄉(xiāng)之念:
今日?qǐng)?bào):駱繼漢突然去世,年四十四歲,遺一子年六歲,頗有積蓄。辛苦經(jīng)營(yíng),有何益哉,可以恍然矣。(《吳虞日記》下冊(cè),第162頁(yè)。)
七時(shí)起,頭暈極欲嘔,莫名其故。因念年逾五十,孤身遠(yuǎn)客,萬(wàn)一患病不堪設(shè)想,暑假?zèng)Q歸,所有衣物、書(shū)籍暇即逐漸寄回,勿再留戀矣。(《吳虞日記》下冊(cè),第243頁(yè)。)
此外,影響吳虞最終決定離開(kāi)北大回鄉(xiāng)者,還有那個(gè)當(dāng)時(shí)鬧得紛紛揚(yáng)揚(yáng)的“嬌玉”事件。吳虞當(dāng)時(shí)孤身一人客居北京,家眷仍在四川,寂寞之時(shí)免不了眠花宿柳,結(jié)果和一名叫嬌玉的妓女打得火熱,還給嬌玉寫(xiě)了不少詩(shī)。本來(lái)這在那個(gè)時(shí)代不算什么,但吳虞竟然將這些艷詩(shī)公開(kāi)發(fā)表在報(bào)上,自然引起社會(huì)上一些人的不滿(mǎn)。果然在1924年4月29日就有化名“XY”的人在北京《晨報(bào)》發(fā)表文章《孔家店里的老伙計(jì)》,諷刺吳虞有如此言行,不僅不是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而且該是孔家店里的“老伙計(jì)”。至于那些為嬌玉作的幾十首詩(shī)都是“肉麻的歪詩(shī)”,“淫穢不堪”。這自然引起吳虞的憤怒,他考慮給予反擊。在征求同事如周作人等人意見(jiàn)后,吳虞將八條回復(fù)在5月2日的《晨報(bào)》上公開(kāi)發(fā)表。此事見(jiàn)于他1924年4月29日的日記:
今日《晨報(bào)》,又有一篇,由詩(shī)單而攻擊《文錄》與《朝華詞》,語(yǔ)多誣詆輕薄,而實(shí)不學(xué)無(wú)術(shù)之狂吠也。因書(shū)八條復(fù)之,示周作人、馬夷初、沈士遠(yuǎn),作人、士遠(yuǎn)言可答復(fù)一次,以后即當(dāng)置之不理,不然終無(wú)說(shuō)清之一日;夷初則以為此等少年,可以不理。予用作人、士遠(yuǎn)之說(shuō),將八條寄孫伏園,并聲明不再答復(fù)。(《吳虞日記》下冊(cè),第178頁(yè)。)
不過(guò),吳虞也深知“人言可畏”之理,此事既然引起社會(huì)對(duì)其不利輿論,吳虞遂決定對(duì)此事不再聲張,即便再與嬌玉聯(lián)系,也是要單獨(dú)行動(dòng):
嬌玉處皆一人去最好,不再約人同往。(《吳虞日記》下冊(cè),第178頁(yè)。)
此后無(wú)論對(duì)于何人,皆勿再言嬌玉……。(《吳虞日記》下冊(cè),第179頁(yè)。)
由于當(dāng)時(shí)傳言化名寫(xiě)文章責(zé)罵吳虞者為錢(qián)玄同,吳虞之后的日記中不乏對(duì)錢(qián)玄同的辱罵貶斥之辭,盡管他沒(méi)有直接證據(jù)證明是錢(qián)玄同所寫(xiě),而且之前兩人關(guān)系還算不錯(cuò)。且看他日記中的錢(qián)玄同,其形象簡(jiǎn)直成為一個(gè)文壇流氓無(wú)賴(lài)了:
昨夷乘言,幼漁、公鐸、兼士皆與玄同沖突過(guò)。公鐸罵其卑鄙,陳介石罵其曲學(xué)阿世,孟壽椿言其出身微賤,傅斯年言其音韻學(xué)最使人頭痛,潘立山言其前諂事黃侃,后痛詆黃侃,又諂事陳獨(dú)秀、胡適之。玄同常到蔡孑民處,當(dāng)時(shí)人譏之曰:又到蔡先生處去阿一下,其人格尚可言哉!(《吳虞日記》下冊(cè),第180頁(yè)。)
顯而易見(jiàn),這些對(duì)錢(qián)玄同的評(píng)價(jià)不可能都正確,但吳虞卻全當(dāng)作事實(shí)。吳虞大概認(rèn)為既然很多同事對(duì)錢(qián)玄同有負(fù)面評(píng)價(jià),此人又寫(xiě)文章詆毀自己,自己當(dāng)然可以予以還擊:
十時(shí)至十二時(shí),在北大上課,向?qū)W生陳述事實(shí),約一點(diǎn)半鐘,并痛罵錢(qián)玄同,不欲示弱也。(《吳虞日記》下冊(cè),第180頁(yè)。)
按說(shuō)吳虞不該利用上課時(shí)間對(duì)學(xué)生講述此類(lèi)事情,但他竟然用長(zhǎng)達(dá)一個(gè)半小時(shí)時(shí)間為自己辯護(hù)并詆毀辱罵錢(qián)玄同,其心理之變態(tài)和陰暗由此可見(jiàn)一斑。從另一方面說(shuō),吳虞對(duì)于錢(qián)玄同這樣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的同道者,為了一己名聲不惜大肆辱罵詆毀,也就等于斷絕了他繼續(xù)與北大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提倡者圈子繼續(xù)交往的可能——盡管胡適、蔡元培等人不會(huì)因此事怪罪于他。但既然連陳獨(dú)秀也因此類(lèi)事不得不離開(kāi)北大,則吳虞在北大的命運(yùn)也就只有離開(kāi)。果然,據(jù)其日記,1925年4月30日北大教職工開(kāi)會(huì)商議對(duì)付章士釗合并八所學(xué)校事,吳虞竟然在事后才知曉,這應(yīng)該看作是北大不會(huì)再續(xù)聘他的一個(gè)信號(hào)。之后吳虞日記中出現(xiàn)了北大聘幾位四川人為教授的文字,是否吳虞已經(jīng)預(yù)感到不會(huì)被續(xù)聘了呢:
張真如來(lái),言北大又聘李又椿、楊季璠、曹四勿任教授,皆川人。(《吳虞日記》下冊(cè),第270頁(yè)。)
吳虞無(wú)論怎樣自負(fù),對(duì)于自己在北大的命運(yùn)還是有所預(yù)感,他在1925年初實(shí)際上已經(jīng)決定返回四川,而且不是暫時(shí)請(qǐng)假,是徹底離開(kāi)北大。只是由于當(dāng)年年初四川一直戰(zhàn)亂不止,吳虞歸家才一再被拖延,直到七月才得以動(dòng)身。對(duì)此吳虞也特別感慨,似乎連老天爺沒(méi)有給他以特別的眷顧:
自初二至今,雨竟不止,予生平行事,每多坎坷,極少順?biāo)臁=衲昊卮ǎ瑒t戰(zhàn)事不解,又值天旱米荒;方定行期,而雨水連綿不已,必使人不快,不知何故也。(《吳虞日記》下冊(cè),第273頁(yè)。)
決定動(dòng)身回川的吳虞陋習(xí)不改,在離京前三天還要再去一次風(fēng)月場(chǎng)所,以給洋二元的價(jià)格選得一年僅十五女子。后路經(jīng)昔日常常留戀之處,看到舊時(shí)相識(shí)“花憶情牌已下”,而自己馬上就要告老返鄉(xiāng),多少還是有些感慨吧:
經(jīng)春艷院,花憶情牌已下,養(yǎng)子之說(shuō)不誣,人海滄桑,曷勝感慨。(《吳虞日記》下冊(cè),第275頁(yè)。)
自吳虞1925年8月6日離京,歷經(jīng)月余至9月12日他才回到成都家中,然后直到當(dāng)年10月25日,吳虞日記中沒(méi)有一次出現(xiàn)過(guò)“北大”或北大同事名字,即便是在10月25日再次提到“北大”,也無(wú)非是因?yàn)橛讶藖?lái)信告知北大已經(jīng)發(fā)過(guò)兩次薪水,所以吳虞才寫(xiě)信給朋友囑托代問(wèn)北大欠薪事。看來(lái),數(shù)年的北大執(zhí)教生涯吳虞似乎不愿再提甚至不愿回憶,這一階段吳虞的日記相比之前字?jǐn)?shù)少得可憐。吳虞似乎確實(shí)對(duì)執(zhí)教厭倦了,或者該說(shuō)北大數(shù)年確實(shí)傷透了吳虞的心?之后即便郁達(dá)夫兩次寫(xiě)信邀請(qǐng)赴武漢大學(xué)任教,吳虞還是拒絕,這其中的復(fù)雜內(nèi)心從其這一時(shí)期日記中已經(jīng)很難尋覓。也許最終使得吳虞拒絕再次出山的理由,僅僅是他覺(jué)得自己真的老了罷。
吳虞僅僅比魯迅大九歲,兩人都曾留學(xué)日本,“五四”之前都有過(guò)長(zhǎng)期的思想苦悶時(shí)期,都是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因他人的推動(dòng)而參與其中,也都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退潮后感到彷徨。但前者最終回到四川也就等于再次回歸之前的生活,而魯迅在短暫的彷徨后卻終能清醒,堅(jiān)定走向新的道路,這其中有很多值得反思之處。不過(guò)從日常生活交往方面看,魯迅比吳虞幸運(yùn)的是在遭到《新青年》同人分裂、兄弟反目等重大人生挫折時(shí),許廣平及時(shí)走到他身邊,愛(ài)情最終拯救了魯迅。盡管導(dǎo)致二人不同命運(yùn)者還有其他原因——例如他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方面的差異,但不同的日常生活與日常交往狀況,可能成為他們走向不同道路的重要因素。至于這些日常瑣事的發(fā)生出自偶然還是必然,恐怕很難說(shu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