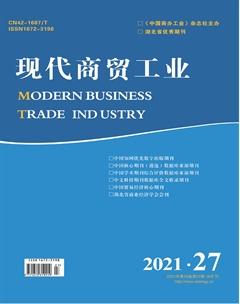17世紀中國沿海海盜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走私貿易研究
廖梓蔚
摘 要:17世紀20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與中國政府求商不成的情況下,被迫依靠沿海的海盜開展對華走私貿易。而這些海盜對公司經營的走私貿易既有合作也有制約,雙方關系十分復雜。
關鍵詞:荷蘭東印度公司;走私貿易;中國海盜
中圖分類號:F74 ? ? 文獻標識碼:A ? ?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27.014
關于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以下簡稱為“荷印公司”)與中國海盜的關系,上世紀的研究在明代海洋貿易的框架內將海盜定位為商人,考察荷人在框架內的角色,如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李金明《明代海外貿易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他們都強調了荷蘭人的海盜行徑對中國沿海貿易的破壞。進入21世紀,有學者研究明末荷人與中國東南海盜的交往歷史,如徐曉望《晚明在臺灣活動的閩粵海盜》(《臺灣研究》2003年第3期)、陳思《論1622-1625年間福建大海商李旦與荷蘭殖民者的關系》(《閩臺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也有關注料羅灣海戰中荷人與中國海盜的動態,如任志宏《從料羅灣海戰看十七世紀中西方海軍實力的差距》(《國家航海》2011年第1期)、甘穎軒《中國海盜與料羅灣海戰》(《海洋史研究》第九輯2016年7月)等。另外陳博翼在《月港到安海——泛海寇秩序與西荷沖突背景下的港口轉移》(《全球史評論》2017年第01期)荷人與中國海盜的互動中探討海港地位的升降問題。
海外研究則有美國學者歐陽泰的論文《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海盜》(《海洋史研究》(第七輯)2015年版)探討荷人在明末如何處理與中國海盜的關系,其著作《1661,決戰熱蘭遮》(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聚焦于鄭成功攻臺事件;在Pepper,Guns and Parleys: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62-168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衛思韓(John E.Wills,jr.)研究清朝與荷蘭在面對共同敵人——鄭氏家族期間的談判,從中探討十七世紀由戰爭與商業連接的國際關系;另還有鄭維中的WAR,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BRILL,2013)關注明末鄭氏海商集團為維持海上商貿利益游走于各方之間的歷史。
本文將利用《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總督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巴達維亞城日記》等中譯荷蘭檔案考察中國海盜在荷蘭人經營的對華走私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
1 明末中國沿海的海盜勢力
1622年4月,受高額利潤的刺激,荷印公司派遣雷爾松艦隊從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以下簡稱巴城)出發,赴華開展中國商務。
1622年10月雷爾松艦隊首輪對華貿易談判失敗,荷人不被納入漳州月港的合法貿易中,商務開展十分困難。一方面,當時的東亞貿易格局擁有強大的慣性,中國商船前往馬尼拉和日本貿易由來已久,獲利豐厚,即使荷人的收購價高于一般市場價格,仍無法輕易改變舊有格局。另一方面,荷人在通商談判失敗后實施的武力手段使自己臭名昭著。曾于荷人交涉過的中國使者就稱荷人“不過是海盜而已,來此地并不是要通商交易,只是要來……沿海搶劫,……不過是既沒有金錢又沒有貨物的窮乞丐。”一般商人憚其聲名,更不敢輕易與荷人接觸不過,當時沿海猖獗的走私貿易卻能幫助荷人開展商務。
一般認為,明中后期的倭亂與走私與明朝的海禁政策有關,但即使月港在1567年后被確定為私人海外貿易港口,走私活動仍然嚴重。實際上月港只是在全國“海禁”的框架下開辟的有限對外港口。月港貿易排除漳、泉以外地區的商人,目的是將對外貿易限制在相對封閉且偏僻的閩南地區,減少因貿易開放而對內地的影響。而江浙等經濟發達地區的商人不滿貿易被閩人壟斷,便憑借區域資源優勢參與海外貿易,走私貿易大規模興起,所謂“人輒違禁私下海,或假借縣給買殺捕魚之引,竟走遠夷。”
明末由于地區秩序和社會經濟的雙重崩壞,大量破產流民沖破海禁政策,下海謀生,以致荷人驚嘆“中國沿海人口密度之高,令人難以相信,人與船遍地都是。”他們游離于地方政府的控制之外,其身份亦寇亦商,根據情況可相互調整,“因為中國人很多借口出海變成海盜,搶劫沿海縣份。由此沿岸有很多中國海盜。”雖然在海盜問題上,荷人與明廷面對同樣的問題:不受管束,破壞海上貿易。但當時的海盜勢力尚處于分合狀態,并未產生擁有絕對優勢的唯一勢力,故荷人可以靈活地處理與海盜的關系,從中選擇盟友,有些盟友甚至“懸掛親王旗和旒旛旗,以公司或荷蘭人的名義去[搶劫]的”,“公司按照……約定的辦法,取得[打劫到的東西]的半數”。這是這類人群為荷人的貨物供應提供幫助。
2 荷印公司與海盜的合作
海盜盟友幫助荷人走私中國商品,巴城總督卡本提耳對這種走私貿易寄予厚望:“備幾艘快船占領大員灣,并保留相當數量的資金吸引冒險商,泊至的人定會與日俱增,因為其中有些人已與我們貿易而相互結識。”但由于明朝政府的嚴格限制以及荷人在沿海掠奪造成的惡劣影響,走私得來的貨物從質量到交付日期都不穩定,無法滿足荷人的需求,正如在1624年2月那批收購自海盜后送抵巴城的“1000件次等質量的錦緞及6擔生絲”。為了壟斷中國貿易,荷人在澎湖和大員(今臺南安平)都曾通過高額收購價吸引冒險商,從而培養自身的貿易網絡,但收效甚微。不夠大員當地有走私商和日本朱印船主經營的為貿易網幫了荷人。從事中日走私貿易的李旦主動向荷人能提供了幫助。
在1624年明軍對澎湖紅毛城的圍困中,李旦便與荷人建立密切聯系,“在使者如此往還之間,……此時成為中國人甲必丹即日本華僑頭人,從臺窩(安平)前來澎湖島,……而聲言愿為我方與中國人之間盡力斡旋。”李旦作為管理在日華商群體的甲必丹,活躍于中日走私貿易,能為荷人提供一定商業資源。因其非法走私行為,《明史》稱其為“海寇”。荷人在大員落腳后,李旦成為大員的重要供貨商,荷人通過間接貿易的方式向李旦收購絲貨,“……中國甲必丹[李旦]……離開日本航來大員了,但我們還沒聽到他們來。真希望他已經到達那里,來償還(我方的人交給他的)負債[指運來用預付款訂購的貨物];……他[李旦]去年在中國留下很多貸款[預付款],把人質和那些人[指收取預付款的人]的保證書留在我們這里,用以[保證]在他不在[大員]的期間,那些人會為我們收購絲和絲貨來償還那些預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