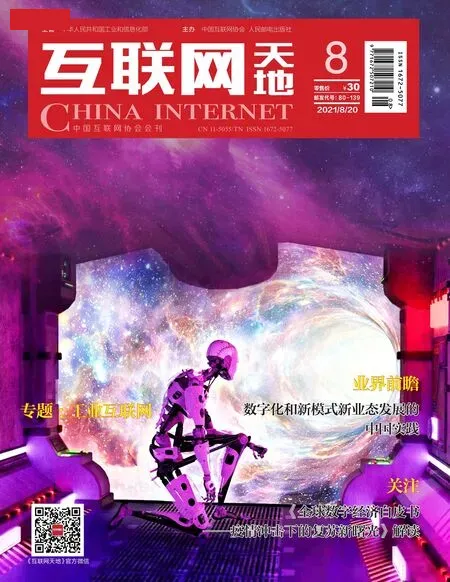工業軟件發展趨勢與機遇研究
□ 文 云夢妍 賈 斐
0 引言
隨著制造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變革的加快和深入,工業軟件的戰略意義愈加凸顯。“十四五”期間,工信部在關鍵基礎材料、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先進基礎工業、產業技術基礎等傳統工業“四基”的基礎上,又追加了工業基礎軟件,構成了產業基礎再造工程的“新五基”。因此,有必要把握工業軟件的特征和發展趨勢,研判工業軟件市場競爭格局,找到我國工業軟件發展的機遇與路徑。
1 工業軟件分類與特征
1.1 工業軟件分類
工業軟件為智能制造提供了關鍵支撐,可以說是現代工業的“大腦”和“靈魂”。工業軟件是工業技術軟件化的產物,本質是將工業技術和經驗知識以軟件工具的形式封裝和沉淀下來,以解決工業場景下的特定問題。
工信部在《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統計調查制度》中將工業軟件劃分為產品研發設計類軟件、生產控制類軟件和業務管理類軟件。其中,產品研發設計類軟件用于提升企業在產品研發工作領域的能力和效率,包括3D虛擬仿真系統、計算機輔助設計(CAD)、計算機輔助工程(CAE)、計算機輔助制造(CAM)等;生產控制類軟件用于提高制造過程中的管控水平,改善生產設備的效率和利用率,包括工業控制系統、制造執行系統(MES)、先進控制系統(APC)等;業務管理類軟件用于提升企業的管理治理水平和運營效率,包括企業資源計劃(ERP)、供應鏈管理(SCM)、客戶關系管理(CRM)等。
1.2 工業軟件特征
工業軟件賦能工業轉型升級。一方面,工業軟件通過數字化手段變革了生產方式,促進了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提升,是支撐工業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要素;另一方面,工業軟件將分散在技術人員頭腦中的知識和經驗予以固化和傳承,大大推動了工業技術知識的復用與重構,筑牢工業生產基礎。工業軟件具有不同于一般應用軟件的特征。
1.2.1 工業軟件技術門檻高,需要大量綜合知識與經驗
工業軟件具有高度的技術復雜性。幾何建模引擎、約束求解器等關鍵核心算法難度極大,模型的優化需要海量生產和運行數據作基礎,這些都建立在長期實踐和積累的基礎之上。渲染組件、人機交互等前端技術也對工業軟件的可用性有重要影響。此外,開發工業軟件不僅需要軟件技能,還需要數學、物理學、機械工程等眾多學科的專業知識,需要對制造工藝和工業機理有深刻的理解。這些都構成了工業軟件領域的技術壁壘。
1.2.2 工業軟件根植于工業領域的實際需求,需要與工業企業深度互動
工業軟件是應用驅動的產品,與工業企業聯系非常緊密。工業企業在深度應用工業軟件的過程中,對其中的功能和機理提出改進建議,協助工業軟件快速優化迭代,進而更好地支撐工業生產和運營。工業技術的發展與工業軟件的成長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工業軟件企業與工業企業良性互動機制是雙贏的基礎。
1.2.3 工業軟件研發周期長,投入大
工業軟件研發需要多領域知識,對可靠性要求高,體系也遠比一般應用軟件復雜,研發難度大,研發周期長,版本迭代速度慢。據估計,一般大型工業軟件的研發周期需要3-5年的時間,要被市場認可則需要10年左右。另外,工業軟件企業需要很大研發投入。2020財年,全球計算機輔助工程頂尖企業ANSYS研發投入3.55億美元,在營業收入中占比21.1%;電子設計自動化(EDA)龍頭廠商Synopsys研發投入12.79億美元,在營業收入中占比34.7%。
1.2.4 工業軟件通用性較低,規模效益較小
工業軟件客戶行業差異大,需求多種多樣,很難通過通用的標準化產品解決所有問題,常常需要針對不同工業場景進行定制或二次開發。專用的工業軟件往往適用于某個細分行業或特定場合,不具備普適性,市場空間有限,難以形成規模效益。還有部分工業巨頭會根據項目需求自行開發“in house(自用)”軟件,并不會商業化推廣。例如波音787整個研制過程用到8000多種軟件,其中只有不到1000種是常見的商業化軟件,其余7000多種軟件都是波音公司經過多年經驗積累自行開發的私有(自用)軟件。
2 工業軟件發展新趨勢
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興起帶來了工業軟件的不斷創新與重構,工業軟件已進入技術變革的新時代,在產品、開發、部署和商業模式等方面,都呈現出新的趨勢。
2.1 在產品模式上,工業軟件正在由單一、孤島式的產品向一體化和集成化轉變
工業軟件企業通過集成強關聯的軟件產品,加強軟件間協作,為客戶提供全流程的一體化解決方案,能夠有效增強客戶黏性,擴大品牌效應,提升制造業全價值鏈效率。CAD、CAE、CAM的集成有助于企業推進設計制造仿真一體化,優化生產流程;ERP、SCM、CRM的集成則能夠幫助企業提高管理水平,降低運營成本。此外,工業軟件正在朝著輕量化的方向演進,部分大型工業軟件在加速解構,工業APP等新型架構的工業軟件不斷涌現。
2.2 在開發模式上,工業軟件開發逐漸向組件化、模塊化的方式轉變
“松耦合”的微服務架構通過應用和功能拆分,幫助工業軟件企業進行敏捷開發和靈活維護。工業軟件開發環境更加開源和開放,為軟件功能拓展和二次開發奠定基礎,依托云平臺,產業鏈各主體都能夠參與到開發過程中,實現工業軟件協同開發。另外,低代碼開發技術的成熟有望降低工業軟件的開發門檻,通過可視化的方式,使大量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能夠加入到開發和應用工業軟件的過程中,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
2.3 在部署模式上,工業軟件向云端遷移的步伐明顯加快
工業軟件從最初部署于企業內部,逐漸轉向在私有云、公有云或混合云上部署、更新和維護。這種部署模式顯著減少了工業企業的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維成本,降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門檻。特別是對有多個生產地點的企業客戶而言,本地部署無法實現數據互聯互通,部署在云端的工業軟件能夠幫助企業匯集、處理和共享多地數據,滿足企業剛性需求。同時,云轉型也使工業軟件企業能夠更便捷地為客戶提供更新維護服務,優化客戶體驗,增強客戶黏性。
2.4 在商業模式上,工業軟件云端遷移推動了商業模式由一次性購買向訂閱模式轉變
訂閱模式打開了工業企業和工業軟件企業雙贏的新局面。一方面,工業企業將一次性的大額資本性支出轉為了長期的訂閱支出,緩解企業的現金流壓力。另一方面,工業軟件企業收入更加具有持續性,促進企業的穩健發展,如果客戶訂閱時間較長,訂閱收入將超過一次性購買的收入。在訂閱模式下,更多客戶,特別是中小企業客戶,能夠負擔得起工業軟件,這將幫助企業更好地應對廉價替代品的競爭。訂閱模式還增加了企業定價策略的靈活性,如按功能定價、按使用時間定價等,為業務拓展提供更多可能。
3 工業軟件市場競爭格局
3.1 全球市場競爭格局
目前,全球工業軟件產業已形成較為穩定的市場格局,產業規模穩定增長。2020年全球產業規模估計為4358億美元,2015-2020年五年復合增長率約為5.3%(如圖1所示)。

圖1 2012-2020年全球工業軟件產業規模及增長率
各細分領域的頭部企業已形成較為堅固的競爭壁壘。在產品研發設計軟件領域,歐美巨頭基本形成了壟斷態勢,CAD設計軟件由Autodesk、PTC、達索系統、西門子等企業主導,CAE仿真軟件幾乎被ANSYS、ALTAIR、NASTRAN壟斷,EDA芯片設計軟件由Synopsys、Cadence、Mentor Graphics(2016年被西門子收購)三巨頭引領市場。在生產控制軟件領域,傳統工業巨頭占據領先優勢,西門子、施耐德、羅克韋爾等處于行業龍頭地位。在業務管理軟件領域,產品比較成熟,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市場集中度明顯低于其他兩類工業軟件,這一市場由SAP、Oracle領跑,Workday、Infor、Sage等位于第二梯隊。
短期內工業軟件巨頭很難被追趕和超越。一方面,大型頭部企業加快收購步伐,不斷拓展產品線,構建產品生態,打造從研發設計到生產控制再到業務管理的全產業鏈、一體化產品體系,提高了客戶的依賴程度。另一方面,巨頭企業掌握著自主核心技術知識產權,且每年仍在持續投入巨額研發經費,這也提高了全行業的進入門檻。
3.2 中國市場競爭格局
近年來,我國工業軟件市場發展較快,國內供應商競爭力有所提升,自主可控的工業軟件產品不斷涌現。產業規模增速明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0年我國產業規模估計為1974億元,2015-2020年五年復合增長率約為12.8%(如圖2所示)。

圖2 2012-2020年我國工業軟件產業規模及增長率

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國工業軟件產業規模與工業規模高度不匹配。我國已形成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0年,我國工業增加值在全球占比約為25%,工業軟件產業規模在全球僅占7%左右。
在技術上,盡管我國工業軟件產品的少量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但大量關鍵核心技術仍舊缺失,特別是產品研發設計類軟件,內核高度依賴進口,主要面向中低端市場進行二次開發。在產業上,工業軟件企業與工業企業產用脫節,產業鏈不成熟,工業企業認為國內工業軟件無法滿足生產需求而不愿使用,國內工業軟件產品無法在實際使用場景中得到迭代優化,更加無法為工業企業提供支持。
當前,我國工業軟件市場整體呈現出“管理軟件強,工程軟件弱,低端軟件多,高端軟件少”的特點。
在產品研發設計軟件領域,除軍工、航天等個別垂直領域外,高端研發設計軟件是我國工業數字化轉型的一大痛點,軟件算法、機理和性能成為“卡脖子”難題。國產軟件產品工業機理模型簡單,對先進工藝支撐能力弱,無法滿足高端客戶的復雜場景需求。目前,我國絕大多數研發設計軟件依賴進口,CAD、CAE、EDA等國內細分市場中,九成以上的市場份額均被歐美龍頭企業占據。
在生產控制軟件領域,國內供應商將復雜的生產工藝和工業機理封裝成軟件產品的能力有限,主要滿足的是生產鏈條中某個環節的需求,無法提供全系統、全流程、體系化的一站式解決方案。國際巨頭在國內市場上的綜合競爭力仍舊有明顯優勢,但在鋼鐵冶金、石油化工等部分垂直行業中,寶信軟件、石化盈科等廠商常年深耕,正在逐漸向高端市場切入。
在業務管理軟件領域,我國已有較為成熟的軟件產品,ERP等傳統軟件的競爭格局較為穩定,用友、金蝶等國內供應商占據了主要市場,特別是中小企業用戶市場,但高端用戶仍以國外產品為主,且國內供應商的客戶絕大多數分布于中國大陸,在產品和技術海外輸出方面無法與國際巨頭競爭。
4 我國工業軟件產業的發展機遇
當前,我國工業軟件產業迎來了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首先,美國對我國高科技產業的技術封鎖持續加劇,多家中國公司和機構被列入“實體清單”,以EDA為代表的研發軟件和以MATLAB為代表的工程軟件先后被禁用,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外部壓力倒逼工業軟件國產化替代加速,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國產工業軟件產業體系勢在必行。
其次,國家層面高度重視,近年發布多項政策支持國產工業軟件發展。2020年8月,國務院發布《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要求聚焦集成電路設計工具、基礎軟件、工業軟件、應用軟件的關鍵核心技術研發。2021年7月,工信部、科技部等六部委聯合發布《關于加快培育發展制造業優質企業的指導意見》,要求推動產業數字化發展,大力推動自主可控工業軟件推廣應用,提高企業軟件化水平。
再有,我國正在由“制造大國”向“智造強國”轉變,產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轉型升級不斷加速,工業企業技術賦能需求迫切,新冠疫情這一突發事件助推工業生產方式的變革,作為促進實體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工業軟件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具有廣闊的市場空間。
最后,工業軟件上云已成必然趨勢,原先的單機產品需要重建整體架構,工業APP等輕量化產品的發展也建立在傳統大型工業軟件解耦的基礎上,工業軟件產品面臨的這些重大調整和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海外巨頭構筑的競爭優勢,為國內供應商的加速追趕甚至是彎道超車提供了寶貴機會。
5 結束語
在研判了工業軟件的技術趨勢和市場格局后,本文嘗試提出我國工業軟件產業未來幾年發展的主線——深入推進工業軟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造龍頭供應商,培育產業核心競爭力。
在政府層面,中央和國家機關應當建立切實可行的長期總體規劃,為工業軟件產業發展指明方向,各級政府應當根據地方發展實際,積極利用政策工具落實中央規劃,充分調動企業積極性,持續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保障。
在工業軟件企業層面,一方面要堅定自主創新,加大研發投入,深入研究工業機理模型,加強與需求方的溝通合作,建立快速迭代優化機制,提供高質量的工業軟件產品以建立競爭優勢;另一方面要延伸企業布局,嘗試通過并購優質標的實現技術補充或市場拓展,與自身產品和業務進行有效整合,增強自身實力。
在高校、聯盟等社會機構層面,應當重視工業軟件人才的體系化培養,為市場儲備優質勞動力資源;加快科研成果轉化,支持新興技術產業化落地;促進產研融合和供需對接,培育良好產業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