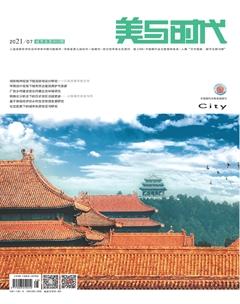共識社區在鄉村的可持續發展研究
吳介舒



摘 要:從在鄉村地區有意識地嘗試建立另類生活方式的角度出發,分析共識社區這一定義在國內外的認知發展以及其類別,綜述其逐漸向可持續方向發展的歷程,進而從共識社區的居住環境、組織形式、意識形態三個方面分析其在鄉村的可持續發展,進一步探索共識社區對于我國鄉村空間深入建設和文化傳承的更深層思考。
關鍵詞:共識社區;鄉村;可持續發展
共識社區(Another Communities)是人類群居生活的一種形式,它由一群出于多種原因自愿選擇共同生活的人共同創造一種生活方式。由于近年來,相關學者側重于研究如何合作、共享資源和可持續生活等方面,因此這些群體對社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于鄉村發展的資源浪費和人口流失問題,共識社區有助于改變鄉村地貌,恢復鄉村傳統,使鄉村參與更廣泛的社區發展,并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為那些希望以可持續的方式生活的人們提供另一種選擇。
一、共識社區的定義和分類
共識社區(Another Communities)一詞最早在1949年西方社區服務會議上提出,1960年后開始頻繁使用其他術語,如公社、另類生活方式、替代社區、替代社會等。而后,2004年,社會學家比爾·梅特卡夫(Bill Metcalf)提出了共識社區的當代定義:“來自一個以上家庭或親屬群體的五個或五個以上人自愿聚在一起,目的是避免出現人們認為的社會問題和不足。他們通過有意識的設計和經過深思熟慮的社會和文化選擇,尋求超越主流社會的生活。為了追求自己的目標,他們共同分享生活中的重要方面。”
2007年,露易絲·梅耶林等人總結提出了四類社區:宗教型、生態型、公社型和實踐型,并認為盡管大多數共識社區與主流保持距離,但仍在為主流作出貢獻,在不同程度上遠離主流規范和價值觀。
2009年,中國當代藝術家唐冠華將西方社會20世紀共識社區的定義的范圍擴大,認為共識社區特指有共識的某類群體自發組成的獨立生活社區,強調其自然組成的特性。共識社區是一個根據興趣愛好、宗教信仰、飲食習慣等理念類聚的無國籍限制人類社群[1]。
當今,共識社區定義和分類在變化和開放性方面更具彈性。本文關注的即是這種共識社區從主流城市撤回到農村地區,其內部共識關系以及外部環境關系的一種可持續發展。
二、共識社區與鄉村的關系
在西方,鄉村中存在三種鄉村主義:一為反應性鄉村主義,由傳統農村人口倡導,具有歷史性和自然性;二為理想的鄉村主義,由城市中的中產階級倡導,具有投資和保護的價值;三為進步的鄉村主義,是以簡單的生活方式和農村地區的自給自足為目標發展。共識社區在某種程度上與此相關聯。這些不同的群體本質上并不分開,可以形成聯盟,也會與其他社區發生沖突,以追求各自的生活方式。
中國目前對于鄉村生態建設側重于三類:一為實際生產模式,如生態類工程建設;二為田園綜合體、生態村培訓課程等;三為側重于原住民的生態鄉村建設。第二種雖只有少數與共識社區模式接近,但這些地區同樣因存在不一致的愿景有著不同的沖突。
也正是因此,鄉村空間被視為“一個有爭議的地方”,共識社區或許會成為未來鄉村發展中沖突較少之地。
三、共識社區的可持續發展歷程
(一)早期的意識
或許大多數人認為共識社區是嬉皮士運動中公社的代名詞,事實上,人類基于崇高理想努力創造新的生活方式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
梅特卡夫博士(Bill Metcalf)認為共識社區產生的雛形最早大概是畢達哥拉斯于公元前525年在現在的意大利南部開發的霍馬科內社區,人們共同生活和飲食,沒有私有財產。
1516年,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以“烏托邦”一詞來描述理想的社會,與東方儒家所提倡的“大同”理想社會有相似之處。實際上,這就是歷史上所有共識社區的共同點:每個人都基于對更美好世界的愿景,以及對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日常行為反映既定目標。
(二)實踐的發展
第一階段是烏托邦公社的興起。19世紀初,人們倡導烏托邦主義,想象如何創建共識社區,以解決資本主義快速工業化而產生的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他們否認工業的進步等同于道德的進步,倡導空想社會主義,提介建立公社,如“新和諧村”等,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自下而上的思路。
第二階段與經濟社會霸權主義危機有關。1957年,日本農村出現了一群提供醫療保障、教育和社會福利項目的團體,即“山岸合作社”,消除私有和私欲,該團體采用一體化生活、經營的生活方式,提倡人與自然和諧統一,以實現共同繁榮。
第三階段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和歐洲鄉村出現大量的嬉皮族社區作為一種實驗性社區。
1968年,丹麥提出了“合作居住”的社區模式。居民擁有私人住宅,并共享公共設施、活動區域以及必要的娛樂設施。而在美國,20世紀60年代建立了大批以無政府主義和享樂主義為原則的公社,并在1970年掀起了返土歸田運動,人們紛紛回到鄉村重建田園生活,如弗吉尼亞的Twin Oaks社區和田納西的Farm社區,后因沒有建立可行的經濟基礎逐漸走向衰敗。
第四階段是生態村的興起。隨著生態危機的出現,到20世紀90年代,共識社區出現了與農業有關的傳統知識和現代技術,這些社區被稱為“生態村”,即有意識地尋求環境可持續性,社會公正、平等與和平的社區,主要關注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探索有利于環境的價值觀念、行為和實踐。
歐洲的一部分生態村開始思考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的理想模型,有丹麥天鵝公社生態村(圖1)、瑞典泰格萊特生態村,提倡自足性經濟,鼓勵有機農田耕作,以保護地方資源及生態。美國在規劃設計方面同樣采用了來自丹麥的合作居住形制,如Ithaca生態村,同時也成為多所大學的研究實踐基地[2]。生態村積極地融入主流社會,為社區加入了現代文化中最好的方面:音樂和藝術的美好,以及技術的有效性。
1994年,“全球生態標簽網絡(GEN)”(圖2)在丹麥成立,將各個生態村聯系在一起。不少國家都在成立自己的生態村網絡,2000年,日本成立了“NPO生態村網絡”。
在第五階段,生態家園已成為全球社會運動的組成部分。21世紀初,對于非洲地區大量傳統村落面臨的經濟政治威脅,應用生態村理念將適宜性新技術(太陽能、風能和生物能等)與傳統實踐(泥胚房屋、有機耕種)完美結合,有助于實現節能和環保。另外,在共享的組織模式上加強社區內合作并提高集體認同感,通過傳播工具建立網絡和創造教育空間,以及建立線下和線上形式的模式逐漸受到認可。
在第六階段,共識社區已被視為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實例。它們已被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糧農組織)認可為可持續性實踐,已經將其確立為可持續的旅游空間,以及應用于生產的某些方面,如清潔能源的生產、有機農業發展、水的使用等。
四、共識社區在鄉村的可持續發展
(一)環境可持續
面對如今全球的環境問題,生態村已成為解決問題的典型先驅。目前,研究認為生態村有三種類別:大城市邊緣區生態村模式、典型農業區生態村模式、偏遠山區生態村模式。
相比于普通社區,共識社區有四個突出特點,即強大的社會網絡(主觀幸福感的關鍵參數)、社區認同的共識性、親近自然、生態足跡低,后者更是被認為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標準。
這些社區通常會采用有關生態的新技術,生態建筑、可持續替代能源、永續經營、中水處理與節能技術、蔬果有機耕種和自治的經濟體系,并且有生態教育空間、公共的共享空間,還有完善的共同參與決策的平臺和可持續教學系統。在一些生態技術較強的生態社區,同樣也有建造零化石能耗、排放零二氧化碳技術、在地化利用資源、建立瀕危動物保護區、有機自制農業等生態行動,以減少生態足跡,無害地將人類活動融入自然世界。
(二)組織可持續
在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幾年里,人們開始將共識社區看作另外一種謀生手段,參與者大多受過高等教育,這使得出于共識而聚集的人群能夠共存,且人口異質率較低。從某種意義上來看,他們正試圖改變財產和勞動關系領域的社會秩序,使之朝著共同協作的方向發展。
雖然共識社區的收入幾乎總是低于社會平均收入,但很少見生活的貧困,他們獲得的福利會略高,并享受比其他地方更好的生活方式。人們經常在一起吃飯,共享工作,具有土地共有權。
對于規劃層面來說,需要更好地給予共識社區居民自治。相比于早期快速建立和解體的共識社區,現今大多數共識社區已經存活了至少五年,更有一些共識社區成為數百萬美元的大型企業,如意大利達慢活社區(Damanhur,圖3)。
(三)意識可持續
共識社區的成員大多來自城市,他們與周邊村落里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居民不同,具有高度的個性化。
不同的共識社區會因為不同的原因而形成。共識社區的活動通常與促進藝術、手工藝、社會變革生態生活、和平工作、關懷和治療、實驗家庭有關。并且,其與下一代的成長教育和人生選擇有關,或許隨著個性化的發展,在今后也會針對單個家庭而成立。這種生態的、非物質的生活方式可以提高幸福感,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的。
站在社區內部的角度,人們一起生活的前提是滿足個人身份、自我認知的需求,且需要明白意識存在的形式、與他人的關系,以及明白這種形式在自己的感知中代表什么。同時也有研究發現共同體的生活方式有利于精神的進步。因而,共識社區正是以這種面對面的關系為特征的。
總的來說,共識社區總是處于一個變化的過程,從嬉皮運動中的公社最初遺留的非傳統和反文化的意識到試圖定居下來并期望變得穩定,意識由烏托邦更接近自然,從理想走向務實,促進更有意義、公共的和可持續的生活方式發展。
五、結語
隨著共識社區在鄉村的發展,近年來國外較多為以生態村為主流發展方向的可持續建設,而我國對于整體的發展機制和解決一系列共識問題還缺乏更多微觀的系統探討,更多停留在借鑒和思考的階段。
結合發展到現階段共識社區網絡的組織建設,以及其傳播廣度帶來更多來自各地的參與者,相信共識社區在不同傳統鄉村的背景下會有更可持續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唐冠華.共識社區的類型分析[J].就業與保障,2019(16):25-33.
[2]岳曉鵬,高珊,呂宏濤.后工業社會美國共識社區可持續轉型研究:以伊薩卡生態村為例[J].現代城市研究,2019(3):28-34.
作者單位:
中國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