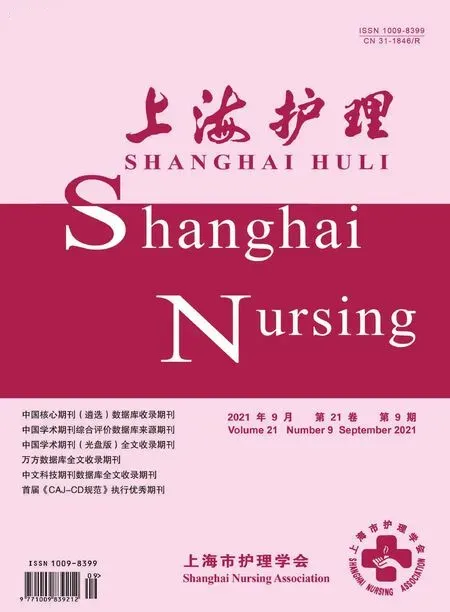上海市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焦慮抑郁現狀及影響因素
吳愛榮,呂 軍,解海霞,楊玉慧,高 瑩,王惠芳,沈 沉,林佩佩,陳 剛,萇鳳水
(1.上海市養志康復醫院/上海市陽光康復中心/同濟大學附屬養志康復醫院,上海 201619;2.復旦大學中國殘疾問題研究中心/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上海 200032)
脊髓損傷是由于外傷、疾病等引起的脊髓結構和功能受損,該患者可能存在多種功能障礙和并發癥,且治愈的可能性極低,因此患者往往離不開照顧者的照顧。脊髓損傷給患者及其照顧者都帶來巨大的心理和經濟等壓力[1]。國內外對脊髓損傷患者研究較多[2-3],對照顧者的研究相對較少。現有國內外對脊髓損傷照顧者的研究主要關注于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的心理狀況[4]、脊髓損傷患者生存質量與照顧者心理的相關性[5]、照顧負擔與抑郁的關系[6]、照顧者心理支持對患者心理的影響等[7],但基本上都是圍繞脊髓損傷住院患者的照顧者展開,尚未檢索到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心理健康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本研究旨在調查上海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的心理健康并分析其影響因素,為促進完善針對該特殊弱勢人群的社會支持體系提供參考。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采用便利抽樣法,于2017年3月至2019年11月,選取在上海市養志康復醫院(以下簡稱“陽光康復中心”)“希望之家”[8]參加康復訓練的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社區脊髓損傷患者是指來自上海市各社區的脊髓損傷患者,患者向各區殘疾人聯合會提交的康復訓練申請經審核批準后,可在陽光康復中心參加為期1個多月的康復訓練,該服務由上海市殘疾人聯合會按協議支付。納入標準:第1次來陽光康復中心參加康復訓練的社區脊髓損傷患者主要照顧者;照顧者認知正常,溝通能力良好;自愿參加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拿取勞務報酬的照顧者;年齡在80歲以上;沒有閱讀和書寫能力;照顧的患者在陽光康復中心已參加過康復訓練。研究經過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IRB#2017-09-0633)。
1.2 方法
1.2.1 調查工具
1.2.1.1 一般資料調查問卷調查問卷由研究者自行設計,內容包括性別、年齡、教育水平、工作情況、婚姻狀況與患者的關系等個人情況,累計照顧年數、是否與患者同住、每天照顧時間等照顧情況,以及自評健康狀況。其中,與患者的關系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等,由照顧者自行選擇;自評健康狀況是照顧者自我評價目前健康狀況與5年前比較的情況,分為比5年前好、和5年前一樣、比5年前略差和明顯比5年前要差4種情況。
1.2.1.2 焦慮自評量表采用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9]評價照顧者的焦慮情況,該量表包含20個條目,各條目均采用Likert 4級評分法,從“沒有或很少時間”到“絕大部分或全部時間”依次賦分1~4分。原始粗分乘以1.25計算得出標準分,標準分總分為25~100分,得分越高說明焦慮越嚴重。其中,標準分50~59分為輕度焦慮,60~69分為中度焦慮,70分及以上為重度焦慮[10]。
1.2.1.3 抑郁自評量表采用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11]評價照顧者的抑郁情況,該量表包含20個條目,各條目均采用Likert 4級評分法,從“沒有或很少時間”到“絕大部分或全部時間”依次賦分1~4分。原始粗分乘以1.25計算得出標準分,標準分總分為25~100分,得分越高說明抑郁越嚴重。其中,標準分53~62分為輕度抑郁,63~72分為中度抑郁,73分及以上為重度抑郁[12]。
1.2.2 調查方法問卷發放和回收均在社區脊髓損傷患者首次進行康復訓練1周內完成。研究者采用統一指導語向調查對象解釋本研究的目的及意義,征得其同意后發放調查問卷,由研究對象自行填寫。本研究共發放問卷147份,全部回收,其中有效問卷126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85.71%。
1.2.3 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13.0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構成比描述,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如數據不呈正態分布則用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焦慮和抑郁的影響因素,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一般資料126名社區脊髓損傷患者平均年齡(44.18±15.35)歲,受傷最長53.50年,最短4個月,平均(8.92±11.57)年。126名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中,84.92%的照顧者為女性;54.76%為患者的配偶、29.37%為父母;平均年齡(54.68±10.96)歲;只有1名照顧者不與患者同住;照顧患者時間為1個月至36.8年,照顧時間中位數為3.3(1.3~11.8)年;自評健康狀況方面:3.17%選擇比5年前好,19.84%選擇和5年前一樣,33.33%選擇比5年前略差,43.65%選擇明顯比5年前要差,認為自身健康變差的照顧者占76.98%。
2.2 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的焦慮、抑郁現狀126名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的SAS標準分為27~90分,平均(49.37±12.92)分;有58名(46.03%)存在焦慮表現,其中輕度焦慮30名(23.81%)、中度焦慮18名(14.29%)、重度焦慮10名(7.94%)。126名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的SDS標準分為25~90分,平均(55.06±13.35)分;有73名(57.94%)存在抑郁表現,其中輕度抑郁37名(29.37%)、中度抑郁28名(22.22%)、重度抑郁8名(6.35%)。126名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中,焦慮合并抑郁者51名(40.48%),同時報告中度及重度焦慮和抑郁者19名(15.08%)。
2.3 不同特征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焦慮和抑郁情況比較不同特征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出現焦慮例數的比較中,自評健康狀況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自評健康明顯變差的照顧者越容易焦慮。不同特征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出現抑郁例數的比較中,每天照顧時間、累計照顧時間和自評健康狀況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進一步分析發現,累計照顧時間為5年及以上的3個組間抑郁發生例數比較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P>0.05),自評健康狀況為比5年前好/和5年前一樣和比5年前略差組間的焦慮和抑郁發生例數比較,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每天照顧時間越長、照顧年數較短(5年以內)、健康明顯變得更差的照顧者,其發生抑郁的可能性更大。詳見表1。

表1 不同特征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出現焦慮和抑郁例數的比較 [n(%)]
2.4 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焦慮和抑郁的多因素分析為進一步分析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焦慮和抑郁的影響因素及其大小,將性別等8個因素設為自變量,自變量賦值見表2。以有無發生焦慮和抑郁分別為因變量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分析策略采用一次性全部納入法。結果顯示,工作情況和自評健康狀況是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焦慮的影響因素(P<0.05),無業的照顧者發生焦慮的可能性大于有工作人群(OR=4.728,95%CI為1.106~20.209),健康狀況明顯變差照顧者發生焦慮的可能性是沒有明顯變差者的4.69倍(OR=4.692,95%CI為2.518~8.743);另外,年齡大、退休、照顧者是配偶、每日照顧12 h以上、累計照顧時間≤5年可能是焦慮的危險因素(OR>1),而女性和高學歷則可能是保護因素(OR<1)。照顧年數和自評健康狀況是抑郁的影響因素(P<0.05),累計照顧時間5年及以內照顧者發生抑郁的可能性是累計照顧時間為5年 以 上 的3.91倍(OR=3.913,95%CI為1.538~9.953),健康明顯變差照顧者發生抑郁的可能性為沒有明顯變差者的6.24倍(OR=6.244,95%CI為2.491~15.651);同時,無業、退休、年齡大、高學歷和每天照顧時間超過12 h是抑郁的危險因素(OR>1),而女性和照顧者是配偶則可能是保護影響(OR<1)。詳見表3、表4。

表2 自變量賦值情況

表3 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焦慮的多因素分析 (N=126)

表4 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抑郁的多因素分析 (N=126)
3 討論
3.1 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的焦慮、抑郁情況較為嚴重本研究中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以女性、中老年、與患者同住、為患者的配偶和父母、退休或無業、學歷較低居多,平均照顧時間較長(中位數為3.3年,四分位數間距為1.3~11.8年)。本研究發現,46.03%的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存在焦慮,57.94%存在抑郁,其中40.48%的照顧者同時存在焦慮和抑郁。印度學者針對38名脊髓損傷照顧者(患者平均受傷7.2年,平均年齡33.2歲;照顧者女性占比71.1%,平均36.4歲,配偶占52.6%,父母占28.9%)的研究發現,55.3%的照顧者存在焦慮,65.8%的照顧者有抑郁現象[13];哥倫比亞學者在37名脊髓損傷照顧者(患者平均受傷11.8年,平均年齡34.6歲;照顧者至少照顧半年,女性占比86.5%,平均年齡44.9歲,父母占48.6%,配偶占29.7%)的研究中也發現,43.0%的照顧者有抑郁表現[14]。來自英國的研究指出,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124名配偶,90%是女性,平均年齡52歲)比患者(平均年齡49歲,平均受傷30.2年,最短受傷23年)的抑郁情況更嚴重[4]。本研究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的焦慮和抑郁得分均高于正常居民的得分[15]、略低于住院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的得分[16],而焦慮標準分與住院患者得分基本相同[17],抑郁標準分高于住院患者得分[17]。可見,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總體焦慮和抑郁水平較高,其心理問題不容樂觀。建議醫護人員關注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的心理健康問題,從而有助于提升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患者的照顧質量[18-19],促進患者康復。
3.2 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焦慮抑郁的影響因素
3.2.1 照顧時間社區脊髓損傷患者患病早期的心理問題較嚴重[20-21]。本研究發現,累計照顧年數是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抑郁情況的主要影響因素,照顧時間≤5年的照顧者更容易發生抑郁等心理問題(P<0.05)。因此,社區或康復中心醫護人員應加強對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的心理支持和干預,特別是照顧早期,如可開發更多切實可行的項目為照顧者提供社會支持以減輕其照顧負擔[22-23],從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上海市嘉定區脊髓損傷者“希望之家”開展的多種家屬喘息服務是可供借鑒的方法之一[24],另外還可采取建立照顧者微信互助群[25]、通過志愿者服務讓照顧者感受社會支持[26]、患者康復等候區播放心靈舒緩視頻或音樂等方法。
3.2.2 工作情況由表3可見,工作情況是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焦慮的主要影響因素,無業的照顧者比有工作的照顧者更容易出現焦慮情況(P<0.05)。這可能與脊髓損傷疾病病程長、經濟負擔重,造成的家庭經濟支出壓力大和自身無業加劇經濟壓力的雙重作用有關[27]。因此,社區或康復中心醫護人員應關注無業且其自身有就業能力和意愿的照顧者,積極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對其開展針對性地綜合幫扶,提供能力匹配、時間靈活的工作崗位相關信息,通過提高照顧者的收入可間接降低其焦慮水平。
3.2.3 自身健康狀況本研究發現,健康狀況與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的焦慮和抑郁密切相關,自認健康狀況變差的社區脊髓損傷照顧者其焦慮和抑郁的比例要比自評健康狀況沒有明顯變化者高出數倍(P<0.05)。當然,從WHO的健康定義可以看出,心理健康本身就是健康的組成部分,有焦慮或抑郁的照顧者其健康變差的可能性也應該會更高。Dreer等[28]研究也發現,健康狀況與照顧者的抑郁相關。因此,從改善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心理健康狀況入手,有助于提升照顧者的整體健康水平[29],而照顧者健康水平的改善,也能促進照顧者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社區或康復中心醫護人員應關注自評健康狀況較差的照顧者,通過提供各種促進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的相關信息,組織相關健康促進的活動等進一步提高社區脊髓損傷照顧者的健康水平。
3.3 研究局限性本研究對象主要來自于上海市的部分社區,研究對象的代表性有一定局限,未來需要在全國其他地區開展大樣本的相關研究;研究樣本量有限,可能會導致排除掉比如性別、年齡和教育背景等[16,30]在其他研究里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影響因素;照顧者心理的影響因素較多,未全部納入研究中,如研究發現干預患者對改善照顧者負擔和健康水平有幫助[31],提示未來研究中也應盡可能納入患者相關因素。
4 小結
社區脊髓損傷患者照顧者的焦慮、抑郁情況較為嚴重,照顧年數、工作情況和自身健康狀況是其主要影響因素,年齡、學歷、與患者的關系和每天照顧時間等也可能是其影響因素。今后研究將開展持續的、更大范圍的跟蹤研究,并將患者因素納入分析,為開展針對患者和照顧者心理健康的綜合干預提供參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