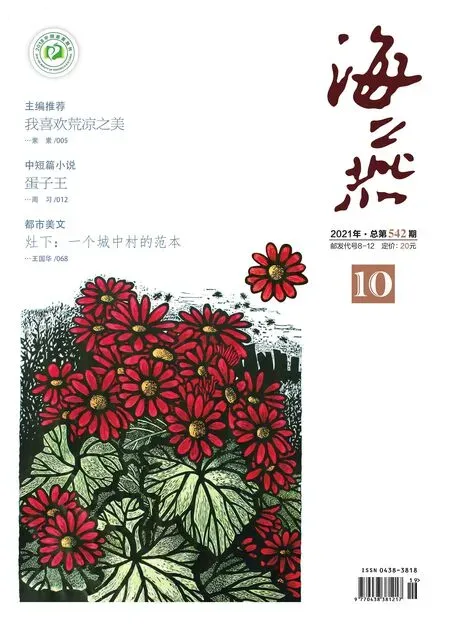小小說三題
文 龐 滟
去趟彩電塔
小青失蹤了。她沒有開車,騎著共享單車離開家的,手機也關了。
她魚一樣在無人的街道漂移,穿街過巷去尋找一座高高的燈塔。
婚后十年,隔離生活硬生生把兩個早出晚歸的人捆綁到一起。小青第一次和丈夫待在一起這么久,以分秒度日。
她一直在避免柴米油鹽中的磕碰和爭吵,盡量一個人做家務。丈夫每天刷手機、玩游戲或處理公司的事,她看書或寫一些憂傷的分行句子。兩人沒有了熱戀時的如膠似漆,像熟悉的陌生人,不知溝通什么好。她的心總是莫名地恐慌,擔心會發生什么想不到的矛盾,破壞了維持這么久的和諧婚姻。
風大了起來,她伏低身體減少阻力,用力蹬車。從小她就喜歡騎自行車,有飛翔的感覺,她向夢中的塔飛去。來沈陽登上彩電塔,俯瞰這座城是她一直未實現的一個愿望。很小的時候,她就聽說過三百多米高的彩電塔,上面有不滅的紅色信號燈,能發射廣播電視信號,還帶旋轉餐廳,站在上面有君臨天下的威風。去彩電塔的這條路,也是丈夫原來家的方向。他們在這條路上經歷了五年的戀愛時光,那是她這輩子最甜蜜的一段生活。丈夫說這是一條生長春天的路,充滿期待的極致誘惑和愉悅。
寬闊的路,看不到幾個人,只有紅綠燈在守規矩地變換顏色。買新房后,她和丈夫很少再經過這里。她逆風而行,逆光而行,身后是一團黑色影子,像從童年開始的夢里追趕者——看不清他們的臉,恐懼卻如影隨形,不放過她。那時的她很想逃往有燈塔的地方——高處才能避開洪水猛獸。
小青和丈夫沒有孩子,缺少可以調劑生活的東西。問題出在她的敏感上——疫情前,丈夫的手機從不設密碼;隔離在家后,手機上了“保護鎖”。她撒嬌地和丈夫要過密碼。隔一天,她發現曾經的密碼如同過期的舊船票,再也登不上去了。她努力控制情緒,故意把自己不設密碼的手機擺在丈夫面前——效果很不好。丈夫的躲躲閃閃,加重了她的懷疑——他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蓄積的情緒像一塊烏云,散發出腐濁的氣味,遮住了心的窗口。她終于爆發了,大聲說:夫妻要真誠相待,防賊一樣防對方,有必要生活在一起嗎?
丈夫先是吃驚地看她,繼而笑著淡淡地說:老夫老妻了,別亂猜。在家辦公,同事口無遮攔,怕你多心,才不想讓你看手機。再說,每個人都應該有一點兒隱私空間,彼此尊重比較好吧。
那好啊,帶上你的隱私權,一起滾吧!她脫口而出的粗魯話把自己嚇了一跳。
別鬧,都在防疫,我去哪兒住都得接受排查。
巨人一樣的高塔就在眼前,爭吵的聲音也消失了。小青大汗淋漓,一顆心怦怦地亂跳——第一次近距離觀看夢中的高塔。很多個白天或夜晚,她隔著好幾條街都能看到這高塔,被七彩變換的探照燈妝扮,在光影里玲瓏剔透。

插圖:齊 鑫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么美麗的塔也會老嗎?眼前的彩電塔像個衰老的巨人,沉默地守望遠方。她鼻子一酸,想哭,想去撫摸斑駁的塔身。她張開手臂,縱身飛過護欄,壁虎一樣貼在凸凹不平的灰白塔壁上,一步一步向上攀爬。夢中的燈塔從未如此粗糙,劃破了她的皮膚,滾燙的淚珠爬過她的臉,一顆顆砸向地面。
她想起和丈夫初見時的自己,小姑娘一樣羞澀,高高個子的他像一座塔,給她生命的安全感。他們牽手發誓:用一生來守護彼此。是什么時候起,她沒了安全感,日夜患得患失呢?她努力讓自己變得更好,可生活像一杯寡淡的白開水,甜蜜的感覺消失了。有種恐懼無法消除,被蒙面人追趕的噩夢頻繁地出現在她的黑夜里。夢里的她沒命地跑,向一個燈塔的方向奔跑。
夕陽給塔身披上一件金縷衣。她虛脫地坐在塔下,目光茫然又疲憊地在塔身爬行,又跌落到地上。她打開手機,此起彼伏的提示音是丈夫發來的消息和未接電話大提示音。
一串腳步聲挨近她,一個寬闊的懷抱收納了她所有的虛弱。丈夫輕撫她的頭,說我的小丫頭,乖!我們回家吧,手機歸你管。這么多年還欠你登上彩電塔的愿望,等開放時一定補上。親愛的,對不起啊!
小青仰起頭,淚流滿面地說:不想登塔了,我只想和自己愛的人,一起騎車來看彩電塔。我懷念,這條生長春天的路。
桃之夭夭
春桃是我大學閨密中最純真的一個,像極了一顆毛茸茸新生的桃子,長著一身人畜無害的絨毛,貌似要保護自己,帶來的卻是極致的誘惑和最痛的傷。
從大一到大四,一個酷似蒲松齡《聊齋》小說里的白面書生,對春桃窮追不舍。不管是什么節日他都送99朵玫瑰,連清明節、中元節和萬圣節都不例外。總之,四年來,我們寢室被幾千朵玫瑰占領過。
春桃的身心卻始終沒被書生成功占領,他們之間始終是若即若離的兄妹情感,這也和我與夏花兩個鐵桿閨密的干擾有關,總覺得白面書生靠不住,要長期考察。
看來,物極必反是條真理。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的是在大學畢業之際,春桃給我們領來一個像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一樣黑的男朋友,他是從大山里出來的,有一個肅殺的名字叫崔劍。還說畢業后,倆人一起回山里給孩子們教書。我和夏花氣得背過了氣,又拼命撮合她和白面書生,使勁破壞她和鄉下男朋友的關系。總不能眼睜睜看著水嫩嫩的春桃一失足落進大山的石頭堆里,那種風吹日曬下,再鮮的桃子也會加速枯萎掉。
就在春桃被誤診肝癌住院時,崔劍忙著驗血配型,非要把自己的肝臟移植給春桃,而白面書生勇氣不足,甘拜下風撤出了。把我們氣個半死。
后來,崔劍和春桃回到他的老家去支教。那座原始的山上有一個叫“桃花塢”的小村莊,春桃去后不想再出來了。她說要做桃花山的桃花仙,說那里是“桃花塢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的人間仙境。
春天桃花含苞待放時,我和夏花想到了春桃的“桃花塢”,被誘惑得坐不住了,激情浩蕩地趕往傳說中的仙境。坐了火車又坐客車,再坐牛車,顛簸了兩天兩夜,才趕到叫“桃花塢”的地方。落地轉了一圈,把我和夏花氣哭了——哪有滿眼的桃花啊,整個一大荒山,零星的桃樹分散在各家院落里。桃腮緋紅的春桃純真地指著一群孩子說:“看這些孩子們,就是這座山的桃花啊!我們已經在學校的周圍栽種了好多桃樹,再過兩三年,這里就會桃花飄飄了。”
純凈的藍天之下,山巔之上,我們仨齊聲朗誦:“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陪著春桃一起幻想成為衣袂飄飄、羞答答的桃花新娘。
世間美好的東西總是那樣易碎。一天夜里,春桃和崔劍抱著一個得闌尾炎的學生趕去山下醫院治療。路上遇到一只餓狼,春桃為了阻止狼的尾隨,失足滾下山送了命。從此,崔劍把山上空閑的地方都栽上了桃樹,發誓一生都守在桃花山的桃花塢,守著春桃的墳墓終老不分離。
我和夏花的婚姻也一直被春桃和崔劍的愛情影響著。我嫁了一個和崔劍一樣實誠的小學教師。夏花一直在換男朋友,發誓要找到像崔劍一樣癡情的男人。
一晃四年過去了。我和夏花很少主動聯系崔劍,都怕揭開歲月的疤,很疼。
一天,夏花打來電話,她發瘋一樣叫嚷著,讓我趕緊打開微信看她發來的新聞視頻。我目瞪口呆地傻掉了:屏幕上的崔劍正在接受電視臺采訪,他和一個女人手牽手,帶領著一群學生在桃花如云的桃花塢合影。夏花在電話那邊哭著叫:“你看到沒,看到沒?那個和他合影的女人,崔劍對記者說,‘那是他新婚的妻子’。這個男人太他媽的惡心了,怎么可以這樣背叛春桃啊?怎么可以……這樣背叛我們——背叛那么美好的愛情啊……”
“崔劍你混蛋,怎么可以這樣背叛春桃啊?你這個愛情騙子!”我給崔劍打去電話,流著淚喊道,我發瘋的狀態真想替春桃一劍封喉了他。
崔劍哽咽好久,才回答:“我沒有背叛和春桃的愛情,她一直是我一生最愛的女人!現在和我結婚這個女人打小就愛著我,一直都沒放下過。我不接受她,又害了一個女人,也害了一個未出生的孩子。世上再無春桃,我自知此生罪孽深重……”
話筒傳來忙音。我飄進空茫的世界,耳邊又響起三個女孩天籟一樣純凈的聲音: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何以桃之夭夭呢?
水哨男孩
余小水趕到醫院時,前夫已經死了,他手里緊攥著一張銀行卡和她簽過的離婚協議,背面歪歪扭扭寫著一行字:小水,我對不起你!卡密碼是孩子的生日。余小水撲到前夫身上,哭得昏天黑地。
回到家的余小水,看到兒子正坐在地上玩玩具,痛心地喚了一聲:柳笛,我的兒子!媽媽回來了。
男孩抬起頭笑呵呵地望著她,嘴唇蠕動了半天,發出兩個震撼人心的音節:媽……媽。
余小水愣住了——一直不會喊“媽媽”的兒子變正常了嗎?她捧住兒子的臉,連喚了幾聲:兒子,柳笛柳笛,再叫一聲媽媽,叫啊!
柳笛目光呆滯,呵呵傻笑著,不再說話,低頭擺弄玩具。余小水失聲痛哭:兒子啊,你爸死了,媽再走了,你連自己都不會照顧,怎么活啊?
晚飯后,柳笛扯著發呆的余小水說:走,走。他喜歡在晚上散步,去聽河里的青蛙叫。
余小水給兒子換上一套新衣服,破例帶上了兒子喜歡吹的陶瓷水哨。他們來到了云龍湖橋上,黑色的湖水把路燈的影子扯來扯去。兒子趴在欄桿上向水里望,掏出水哨要吹,她沒有阻攔,把瓶子里的水倒進去。頃刻間,婉轉的鳥鳴聲在黑夜中飛翔。
小水坐在地上,顫抖的雙手伸向兒子的腿,握緊他的腳踝,她心碎地啜泣低語:兒子,都怪媽媽不好,我們該怎么辦啊?
媽——媽,家。柳笛蹲下身,去拉地上的媽媽。
家,家?咱們回家!余小水擦干淚水,長嘆一聲說:這也許是天意,我應該做最后的努力。
第二天,余小水帶著柳笛上班了。她在這個野生動物園工作了十一年,第一次帶兒子來上班。同事們看了,都夸她兒子大高個兒,長得帥。她紅著臉謝過,帶著柳笛走進總經理辦公室。
小水,這是你兒子?不錯啊,一表人才!當初你要是嫁給我,早就有這么帥的兒子了。吳經理酸溜溜地開著玩笑。
吳經理,我今天來……有一件天大的事要求你幫忙!這是我的診斷書。余小水艱難地繼續說,我兒子柳笛有自閉癥,他十七歲了,智力只相當于五六歲。他爸爸出車禍死了。
啊?天哪,你這罪遭的,也太慘了!我先借些錢給你,再號召大家捐一些,趕緊先把病看了。
不,吳經理,醫生說我只剩半年了,我想帶著柳笛一起在大象館里工作。希望你能開恩,如果他學會了照顧大象,讓他在這里工作,給他一口飯吃就行。
什么?這恐怕不行,你兒子有那啥……不適合待在動物園,會有危險的。小水,這事真不好幫,其他忙我都可以幫。
志偉,看在同學的份上,你幫幫我吧!余小水“撲通”跪了下來,淚流滿面:我真是無路可走了,昨晚上我帶著兒子想去跳河,是他硬拉著我回家,才沒跳。我只好來這里求一條活路。你幫了我兒子,下輩子我給你做牛做馬來報恩!要是不能幫,我們還得去跳河。
唉,我的天啊!你這是干什么,趕緊起來,有話好好說。吳經理攙起余小水,愁眉苦臉地轉了幾個圈,說那就讓你兒子先試試吧。要是真能行,得等到孩子滿十八周歲才能應聘。即使不適合這里,我也會想辦法幫他,你放心!余小水連連答應,千恩萬謝著。
大象館里一共有三個大象家庭,第三個家庭只剩下一頭非洲母象叫西蒙,兩個月前它生的小象夭折了,一個月前,公象又染病身亡。西蒙的情緒很不穩定,總是煩躁地發脾氣,毀壞東西。余小水想盡各種辦法安慰它,效果都不好。她帶兒子來給西蒙送飼料,它正煩躁地在圍欄里暴走,亂撞。
柳笛扯過往水坑放水的管子,往大象身上噴水。西蒙“撲通撲通”向柳笛走來。余小水怕它傷到兒子,拿起棍子驅趕它。柳笛開心地笑著。大象目光變溫和了,繞過余小水用大鼻子把柳笛勾過來。柳笛一邊沖水,一邊用手在大象身上搓著,那種默契,好像一對老朋友。洗完澡,柳笛牽著大象的鼻子去吃東西,掏出陶瓷水哨給大象吹鳥叫聲。
余小水發現,兒子和大象相處時是最好的溝通時機,教他什么,能學會一些。她一遍遍告訴兒子,如果媽媽有一天不在你身邊了,那是媽媽變成了大象在陪著你。
一天,柳笛生病了沒來,大象西蒙的躁狂情緒又發作了。它毀壞柵欄,誤傷管理員后,狂奔進茂密的樹林里,怎么弄都不肯出來。吳經理急得火上房,要動用麻醉槍。余小水說,柳笛可能有辦法找回大象。
渾身發燙的柳笛被接了來,他吹著水哨,向樹林里走去。余小水狠下心,沒有陪兒子一同去。她相信兒子,一個人能把大象找回來,因為那是交心朋友之間的信任。
時間一分一秒流逝。半個小時后,大象西蒙馱著柳笛出來了。柳笛還在吹水哨曲子,鳥鳴聲響徹林間,仿佛一個盛大的春天在跟隨著柳笛。
吳經理帶頭給柳笛鼓掌。余小水淚流滿面,又抹去淚水,長出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