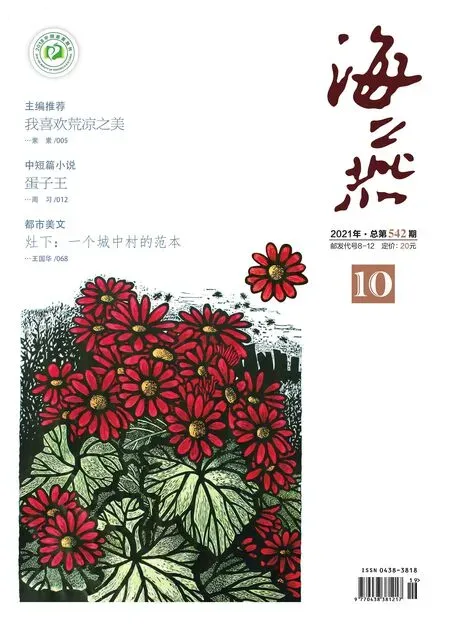時間的真相
文 朱 鏞
這是2014年的夏季。按照規律,一般來說,這個季節是莊稼瘋長的拔節期。可是,在我回家經過的莊稼地里,望見今年莊稼的長勢,它似乎沒有跟上季節的步伐,比時間的節令,慢了些節拍。我有些疑惑,為何同樣的村莊,同樣的季節,地里莊稼的長勢卻大不相同啊。本來對于莊稼,從我去年觀察到的一直在耕種土地的人們,莊稼的好與壞,似乎都激不起他們過多的興奮。但是,我回到村子里,聽到一些老人們說起的,還是莊稼,是去年的莊稼。有兩個老人,站在村口的田邊,一個在說,“去年的夏天,一陣風,就有一陣雨。自下種以后,就風調雨順的,到了四月間,一天雨水一天陽光,五月端午的雨,六月初六的陽光,有時,晚上下雨白日晴,莊稼的長勢多好啊!像有一只無形的手在往上提著一樣的瘋長呀。逢著這樣的年成,晚上下雨白日晴,一個人可以苦了養十個人。今年就不行了,不行了,風來了,雨卻沒有與它同路。”另一個也在嘆息,“又一個夏天了,又一個夏天了啊!這鬼打的時間,咋這樣快,也不等等莊稼的成長。”當然,對于一年的莊稼來說,只要有過鄉村經驗的人都知道,莊稼的好與壞,與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五谷豐登,不是哪一個季節的氣候決定的,它與一年四季聯系緊密。冬天的雪,夏天的雨露,秋天的光照和春天的溫暖,這些節令和過程對于秋天的收獲來說,都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我聽到他們的談話,更加觸動我的,是他們在嘆息的時間。他們對去年夏天每場風每場雨水的記憶,還都熟悉得要命,似乎去年的夏天才經過一個夜晚似的。從這個老人對時間的嘆息里,好像是吃了一定時間的安眠藥,仿佛一下醒來,就是又一個夏天的輪回。雖然與去年一樣是同樣的夏天,但是,時間又翻走了一年,它卻是在今年的日歷上。

插圖:王炫然
在這個夏天里,我要講述的是,村莊里一個老人過世的事情。我從老家離開還不到一個星期,就接到家里打來的電話,說村莊里的一個老人過世了,問我能不能找時間跟著回去送葬。過世的這位老人,就是前不久我回家時還聽母親說起,他病了躺在床上說只想吃昭通城西街上賣的包子的那個人。村子里的人都說,“他都挺了恁長時間了,現在終于死了。”當然,這不是在詛咒他。誰也不會巴望他死,任何死亡,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只是他白日黑夜那種病痛的苦楚,等同于在死的深淵,卻又不是在棺材里,在土里。而是人活著,在呼吸,在板命,最后才終于悲哀、痛苦和死亡。現在他走了,完全是一種解脫,沒有誰覺得惋惜,相反是為他松了口氣。人人都說,“他是被折磨了恁長時間,比死更受罪,像他這樣活著,就是不如早死早超生還好點!”
在村子里,面對這樣的事,我必須回去。這不僅是村莊里的風俗,重要的是,我頂上一輩的人,在村子里又少了一個,心里有種說不出的滋味。我雖然現在沒有長期居住在這個叫朱家營的小村莊,但作為故鄉的一個養子,這個叫朱家營的村莊永遠是我生命的開端,無論我離開還是在場,我時刻都在注視著,對它一往情深。在我的內心里,這個地方的自然萬物,它們是各種各樣神靈的化身,全都帶著神靈的啟示。并且,我以為,不光是我,就是從墓碑上的祖先到現在活著的每一個人,沒有一個人可以否定。因為在這塊土地上,永遠貯存著生命的意義,貯存著四季的種子。人的生老病死,生命的存在和離開,并沒有明確的分界線,因為墳墓和村莊,都是連在一起的。人與大地,與莊稼,與四季,與動物和自然的生活,關聯密切。
在我們老家,村莊里死了人,場景都會一一鋪開。每一個人由肉到靈后,規模不亞于剛過去的插秧的農忙場景。少則三五天,長則有十一天或者半個月。我回到老家,還未走進村子,就聽見凄怨的哀樂,長長的念經聲,孝子的哭聲,主事領頭安排人的喊叫聲,從一個高音喇叭里送出,幽幽地在高過村子的上空擴散。這些各種交織的聲音,仿佛在訴說沉重的生命,在為一個肉身喊魂。但我同時發現,一些東西確實不在了,四筒鼓舞不在了,拖聲曳氣的孝歌聲聽不見了,似乎隨著唱孝歌的那些人一起埋葬了,再不會從村莊飄出來。守靈湊熱鬧的人,也冷清得可憐,仿佛誰都把時間看緊了。但是,他們也不得不這樣,因為一幫年老的人又忙莊稼又得幫忙送葬,把一天的時間都分得支離破碎了,甚至像以前用錢一樣,把一分掰成了兩分來使用。
我唯一看見天空中還有一些飛鳥,在白天將要離去時,它們會扇著翅膀,相互嘰嘰喳喳,向著村莊集攏來。然后,在黑夜降下時,和村莊一起安靜,與人保持著最密切的交往。這種只有白天和黑夜的感覺,還讓我有些欣慰外,其余的場景,卻全帶著一種凄涼之感。我發現在整個葬禮的過程中,人到得最多,最熱鬧的是在送葬的這一天,留在村子里的人,幾乎都走出來了。這一天的人,不用誰喊,不用誰安排,自己都會主動走出來,是看熱鬧,也是為永遠離開村莊的人送最后一程路。這種氛圍是村子里一直留下來的,誰都會跟在10多個漢子抬著棺材的周圍緩緩移動。特別是抬棺材的人,步子是穩,是慢,走路的腳不是提起,是拖著,搓著地面。這種步伐,在我們老家稱為“抬喪步”。看熱鬧的人,也會像抬棺材的人一樣,走著緩慢的“抬喪步”,跟著緩慢移動。整個場景,唯一讓人感到輕松的是,跟在棺材后面不停地歡跳著,一幫又一幫敲鑼打鼓的婦人。她們濃妝艷抹,穿著花花綠綠的衣裳,不時地唱著一些民間歌曲,有的根據死者身份自編自唱,有的還會唱起流行歌。她們總是理直氣壯,一幫賽著一幫,比歌喉,比扭屁股,比圍觀的人多,使用各種技藝,把圍觀的人逗笑,把送葬的過程變成一場生活的鬧劇。
但是,其余的場景,會給人一種酸楚。其余看熱鬧的人,心里都帶著某種失落和悵茫。特別是一些老婦人,有的拄著拐杖,一邊走一邊不住地嘮叨,她們總是有說不完的家長里短,像是難得的聚會。有的走著走著,伸手抹一下眼淚,有的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嘆息,“唉!又走掉一個了!”又發出一聲嘆息,“唉!都走了!都走了!”是的,又走掉一個了。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人,現在村子里還活著的,太少了。現在又走掉了一個,對于同一個時代出生的人來說,等同于在他們日常的生活里,抽走了一絲能奢談童年的時光,更直接的是,找個打招呼的人,也意味著又少了一個。生活里增多的,不過是說起死去的人,又多了一個誰,多一份孤獨和失落。
我不想如實記錄一次葬禮,生命的離去,誰都無可奈何。在村子里,送走了一個人,過了就很少有人再提及。因為誰都清楚,把死去的人送入墳墓,活著的,一樣身在墳墓的邊緣,未來,誰都一樣。我更想記錄的是,活著的人們對時間的概念。我注意觀察一直沒有離開過土地的這一輩人,而在他們之上的一代人,已基本過世,他們已是村莊里目前最老的一茬了。在他們的下一代人中,勞動力非常虛空,因為大多都出去尋找自己的夢想,留給他們一片掛念。再在他們下一代的下一代,是出不起勞動力還要隨時讓他們照看著的小人兒。所以,面對那些生長莊稼的土地,他們不得不盡心盡力去把時間撕開。誰都仿佛被時間俘獲,焦慮和忙活,成了他們一種生活的主旋律。
其實,時間本是一個永恒的東西。它不緩不急,一個白天一個黑夜地走,它永遠不會走到兩個白天才有一個黑夜,或者兩個黑夜才出現一個白晝。但是,他們現在確實沒有辦法。有時,生活被切成了片段,一些日子,仿佛成為一種空白,被不停地忙剝奪掉。
我記得在以前,人們生活在這個村莊,對于時間的概念,誰都會覺得,只有白天和黑夜。白天過去是夜晚,夜晚過去回到白天,周而復始,一天就是一天,是整體,是籠統,不會支離破碎。沒有精確,只有大概,沒有小時,沒有分,沒有秒。如果在白天,人們想知道時間的大概,是上午,中午還是晌午,就抬頭看看天空中太陽的位置。如果在夜晚,無論是睡熟后醒來還是一直沒睡,要知道是三更還是五更,是子時還是卯時,就憑大地的感覺來判定。反正在一天之中,天亮了,就做事去了,即便在下地干活時,遇上住村東頭或者村西頭不是每天相見的人,也要站著拉拉家常。干活回來,炊煙和飛鳥一起繞在屋頂的上空,吃了晚飯,串門子擺擺龍門陣,或者到天黑了不久,睡覺去了。生活就這么簡單,日子就這么長久,村莊就這么有況味。生活于村莊里的人們,即便在一個季節或者一年的時光里,即便從春天播種守望到秋收的時候,也不會急急忙忙,焦焦慮慮,追追趕趕。農活多了,誰都在不需要報酬的相互幫助,管它是誰家在先還是誰家在后,誰也不會去計較,只要活路忙完就行。秋收的時候,管它是早一天還是晚一天,誰也不會爭搶,只要最后顆粒歸倉就行。這種傳統和樸實的一種親和,一種溫暖,成為了村莊一種無形的力量,成為了人們最真實的生活味道。并且,這種力量和生活味道,傳了一代又一代了。當然,以前這樣慢節奏的生活,倒不是說村莊的人們生活得有多么的逍遙和自在,或者是對生活的態度的消極和懶散,更不是說村莊的人心靈有多么高貴。但是,即便他們的思想和心靈,才有村前的山那么遠,才有村前的山那么高,才有村莊所在的范圍大,有一點卻可以完全肯定,就是他們容易懂得知足和滿意。
因為人們共同生活在這塊誰都熟悉的土地上,人與人之間的溫情,無時不在彌漫。有時,一句平常的話語,或者在訴說和傾聽的過程中,就傳遞了。有時,一個眼神或者一個無聲的行動,就可以在樸實的內心里相互感受到。有時,在一次相互幫忙勞作的過程里,就親近了,升溫了。可以說,這完全是一座村莊該有的一種生活秩序。雖然物質清貧,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無休無止地圍繞著每一天,但是,宮廷里有嘆息,茅屋中有歌聲,誰都自得其樂。精神是富有的,生活是不用如此地緊張、焦慮和匆忙的。它完全不像現在,人們在時間面前充滿了焦慮。當聰明的人類把時間割碎,分細之后,時間就像催命鬼一樣,不斷地催著人往前跑。對于時間的精確,這是西方最先干的鬼事情。西方人為了要充分利用時間,發明了鐘表等許多計量時間的裝置,當東方如法炮制地把它移過來時,它逐漸地成為了具體,不再是大概,是籠統。而是小時,是分,是秒,充斥在人們的內心里,成為了一種控制人們生活的節奏工具。時間的細碎之后,它割裂了生活的整體。
即便是在鄉村,當時間不再是一年,一個季節,一個月,一天,或者是太陽的位置,而是幾點幾分幾秒時,毫無疑問,時間就會把快捷、現代、時尚、潮流、趨勢和流行帶到了鄉村社會,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人們生活的主旋律。不知為啥,我總覺得雖然在同一個地球,但在不同的背景下,如果過度地把時間剝裂和撕開的縮小,和畝產上萬斤的夸大說法有異曲同工之感,有時,它不僅有弊端,還會有害。我不完全否定的是,一些事情是需要在時間中奮斗的,越快越好,越準確越好,但是,把所有的東西卡在時間中進行,秩序相反會混亂。因為當快節奏反過來推著人向前跑時,人的精神正在逐漸被瓦解。人失去的不只是信仰,還有內心的安靜和純凈,人們在千篇一律的生活節奏中,將喪失飛翔的夢想,喪失本源,喪失對自然的敬畏。幾千年傳承的一些優美的德性,將會被割碎和撕裂的時間耗掉。我想,這不只是對于生我養我的朱家營這個村莊,對于一個以農業占據大多數人口的國度來說,也同樣如此。一些東西,在上天那兒,保存和創造具有同等的意義,那些保存千年的傳統,難道不是一種創造,它創造了永恒。只是時間的細化,也正在一絲一絲地抽走一些東西。
當然,我所指的不是生命。時間讓生命誕生,也讓生命死亡,這是規律。正如這個剛過世的老人,他出生在這個村莊,又從這個村莊里離開,歸于了塵土,歸于了大地,這是必然。其實一茬又一茬的人都如此,我相信多年后,這個結果無疑會輪到我們這一茬人身上,誰也逃不過。我以為故鄉的土地,是永恒的,它之所以一直沒有改變,永遠給生活在上面的人,不但提供著一個巨大的糧倉,還供養著村莊和墳墓。人走出村莊,就會看見墳墓上越來越茂密的荒草,是與萬物同在的。其實,在這樣的倫理和情義的村莊里,是什么讓人們的生活在時間面前如此焦慮?它的無序的、模糊的、線性的、內在的、濃厚的生活味道,被什么東西取代了?難道未來,總意味著一切變化,在精確的時間中卻反而難以辨認?我不得而知。
我只知道,在我的故鄉,還有一點存在的是,對于生者和死者,誰也不會懼怕一座墳墓在村莊旁。誰都對已經離去很久或者剛離去的人,哪怕像背包袱一樣,都會背負著,因為誰都不愿意離開自己的親人。墓碑里的先輩們,永遠與村莊和土地緊緊聯接著,人們即便站在墳墓的面前,也同時在上帝的面前。在需要祭奠的節日里,墳墓一樣是神的符號,會虔誠祭奠。我發現,只有在這一點上,人們對于時間,誰也不慌,不急,不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