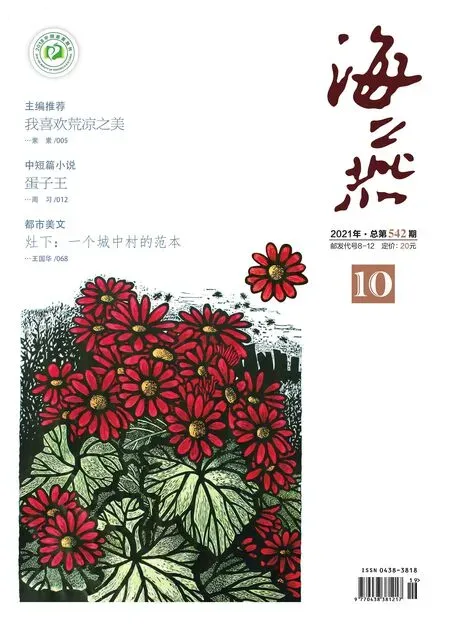與詩相濡以沫地舞蹈
文 劉恩波
1997年冬天謝冕先生為孫擔擔第一部詩集《舞者》寫序言,稱許作者以“輕盈的舞步,曳地無聲的長裙,帶給我們的是一種青春的召喚和感動。”(謝冕《初讀<舞者>》)那個時候的擔擔在隔年出版的《舞者》中,用自己“小荷才露尖尖角”一樣的生命涌動的初心和熱情,“把傳統的有著深厚內涵和獨特審美穿透力的意象引到了現代詩里來,這就大大擴展了她的詩的表現力,并具有了古典與現代融匯的特殊美感”(謝冕語)。
《舞者》讓我們看到了鶯啼小試的心靈歌者的第一縷吟唱和抒情,帶著新鮮的朝露一般的顏色、氣息和狀態,她寫著“時光是一雙美麗的手/把我的青春撕碎/且又拼接/成一襲灰色的幕”,實話實說,這的確有點席慕蓉作品常見的那種構造和修辭,擔擔可能一時間還跳不出《七里香》或者《無怨的青春》中席卷和包裹的席慕蓉腔調。初來乍到,引路人既是樣板,也是跳板。關鍵是你學習了,領會了,借鑒了,然后再走向自己的精神空間和領地。
應該承認,擔擔的詩從一開始就在意象組合、遣詞造句還有整體構思上,多向中國古典詩詞借鑒、承接和吸納。與此同時,也天然地與那個時代文壇盛行的現代詩歌潮流和運動銜接上屬于自己的會心領悟。
《紅山楂》《蝴蝶》《望雪》《心祭》等詩,無不縈繞著古典神韻,流露出一種寂寞而又滲透著個我優雅情調的含蓄幽怨之美。《清明》則以內斂節制的語句道出“未唱完的歌謠/順著春水漂移/卻無法彌合生死間/窄窄的縫隙”那樣的充滿彈性和原始文化鄉愁意味的精神錯覺。
早期的擔擔保持了語言的柔韌度與親和力,其疊加復沓的生命感知與交雜重合的節奏律動唯美地編織起一道詩歌迷人的風景線。讀她的《扇》,為里面“紅門丟了破舊的檐”“野鶴悠然/啄遍低低翠草”,抑或“扇已像蝶樣兒/死在冬的雨里”之類仿古、仿舊的句子而拍案叫絕。這里既有李商隱姜白石的遺緒流韻,也有余光中和席慕蓉的迷離詩思,擔擔的活學化用,融他為己,幾臻妙境。不過跟她聊天,知她悔其少作,其實大可不必——要知道初心亦好,不存在非要如何和怎樣,于是詩的味道更趨于天然和自然。
當然,《舞者》集子中的作品多有刻意而為的痕跡,即使后期的寫作也有這種痕跡。擔擔擺脫不掉追求完美的烙印,她的癡迷與孤絕,眷戀和背叛,孤芳自賞與離經叛道,幾乎將她的詩推向了個性的兩難之境:一方面,她走在詩的懸崖峭壁上努力深化自己已經找到的路標上的風物之魂;另一方面,她又很快唾棄了自我從前的步履,渴望著新的嘗試、探索與發現。
我們不難看到,擔擔在第二部詩集《刀的刃冰涼著》,以更大幅度的跳躍,穿插和縫補,見證了詩性的活泛、不拘一格與劍拔弩張。這部2004年出版的詩集隔年榮獲遼寧文學獎,獲得了業界的接納與肯定。
毋庸置疑,在現代社會各種思想和文化潮流交替聳動推演下的詩歌走勢,詩人也很難在其間獲得安靜的歸屬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意大利隱逸派詩人蒙塔萊曾說,“詩是不可救藥而有時間性的疾病。”
擔擔的《刀的刃冰涼著》,寫得冷、黑、暗、乖戾、夸飾、渲染,強化一種孤寂的痛與傷。“我打碎一只瓶/奶汁微笑”“夢魘變成我的鱗片”(《景致》),“記憶墮落成黃色的蟲/她瘋狂舞蹈”(《黃色》),“雪葬風/風又葬雪”(《半截影》),“我與一個蒼老的鬼/邂逅/從此成了她的兵”(《神經》)……這一連串打破日常常規感覺而往生命意識深處甚至是潛意識深處探尋覓取的姿態,有點西爾維婭·普拉斯等自白派詩人的味道。盡管那個時候,擔擔還沒有接觸到普拉斯,后來讀到了,也未能引起足夠的共鳴,可是她筆下呈現的詩意,卻不知不覺鬼使神差地擁有某種自白的陰影。其實,那種陰影也在翟永明等一系列中國當代女詩人的作品里獲得過潛在的回應和呼應,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將擔擔執迷于陰影和黑色的寫作,視為她的一次出走——她離開中國古典詩學的中正平和、哀而不怒、怨而不傷的中庸之道,有意識地出格和離譜。雖然還未至大逆不道的程度,但其詩歌經過了“正”而抵達“反”,經歷了延伸、拓展,從而獲得另一個維度上的成全。于是,這一時期的擔擔在其作品中,帶給我們的不是一個女孩,而是一個女巫(略微有點跡象吧)的生命體征與形象感。
其實,只要看看這一時期她的詩歌題目,便會一望而知,諸如《茶與傷與夜》《烏鴉》《鬼風》《白日夢》《僵局》《所以輕所以痛》……那的確是撲朔迷離的夢魘之歌的標識與佐證。至于詩的字里行間流露的匆促、乖戾、變幻、沉郁、蒼涼的格調,語義里雜陳的或空靈剔透或晦暗不明的悲哀之美,都顯示了擔擔作為詩意探索者的執著本色和個性鋒芒。
北大學者張輝教授當年在該書的序中,曾經以“偽裝成古典的現代”來指認擔擔詩歌的整體架構和精神內核,現在看來,這是驗明正身后的豁然覺知。女詩人游走在古典意蘊和現代形式之間,奔逐在變異的理性和近乎超拔的感覺中間地帶,進而形成了詩的私語風格。

插圖:齊 鑫
但是,客觀地說,擔擔在《刀的刃冰涼著》中的跋涉,盡管有著刻骨銘心的寫照和欲求,可還是多多少少有些虛張聲勢與用力過猛的嫌疑。如果說《舞者》代表了她的“正”,古典的優雅和中和之美,那么《刀的刃冰涼著》就是她的“反”,認知傳遞著現代精神的駁雜、囂張和挑戰。
然而,超越背離出走之后注定是另一層次的打通融匯與回歸,這樣擔擔理所當然會在自己的“正”“反”之后迎來“合”。其標志是2012年出版的《草藥說》。這次作者在自序中現身說法,她認同“詩歌和哲學是近鄰”,標舉“詩人的一次重生,詩人得以擁有無限本真。”并且源于人格的確認,她欣慰地告知“我已是酒神的親人,我的詩之美,是沉醉之美,御風之美,尤是我之美。”
《草藥說》第一卷里收錄的詩歌,有幾首是在《鴨綠江》2012年第9期以組詩的形式刊載的,那也是我走進孫擔擔作品的肇始。我的一組詩也發在同期,還有李皓的,這就有了得以認知辨識兩位詩人的機緣。
當我帶著懵懂迷惑甚至是疏離感品味著擔擔筆下的生命物象、語言肌理和思想蘊含,不免為她富于質感、穿透力和帶有挑剔意味的話語方式,深深地折服和打動。這也是到目前為止,我最為認同和喜歡的孫擔擔的寫作樣態。
《草藥說》一詩想來是她自己非常珍視的創作,不然全書何以以此命名?
《草藥說》的好,好在通透又奇崛,迷離又貼切。這是詩人自己對于古典精魂和現代形式的充分嫁接、融通與整合。在此,擔擔走出了前一階段的極端叛逆和分裂,重歸于溫婉、得體、擁有充實之美的大寫意境地。
詩人一個旋打回了明朝,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的邊沿,勾勒詩意的線條。“娑羅樹梢頭”“清苦的味道”“木魚聲聲”……這一連串緊致跳躍的詩之意象,疊加在一起,構成了靈性的傾訴與低吟。之后“屈子的悲歌”“流暢的母語”“被肢解的傳統”等等意念和命題,物象和悟性,交織成了亙古時光的觸摸、巡視與再造。這是對文化的鄉愁,詩之精神史的一次澆筑和洗禮。從此中,我們看到了擔擔置身詩之現場的詩人個性和內在情懷。她“無意說母語/無力唱悲歌”,卻留下了屬于詩之靈體的鮮活確證。
《星巴克的下午》,逼視了一個存在者的生命觀感,接續了一個內在自我的審視和洞察。在這里,擔擔放逐了從前作品中常常具有的女性本體意識或者身份感,而是創造了自我和異己的對話關系。將存在的維度向著形而上層面大大推進了一步。
《我在安靜的家里》也是難得的寫意之作,偏于現代詩體的感悟和律動——這個渴望“用畢加索的刀/去切塞尚的水果”的無畏想象者,在詩中一任詭異的思維發酵,狂放奔流,當她寫出“咖啡內部的雷霆/可能來自于/紐約中央地鐵站”,一會兒作為生命的求知者,面對自家高大的書架,又能體味到歷史的迷人和虛無。我覺得擔擔的詩性在此勃然噴涌,獲得了內在自我和外在物象的天然發酵、對位與融合。
到了《剩下的時間》,那帶著個體心意剖白性質的自語,已然跨越了西爾維婭·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頓等美國自白派詩人的精神枷鎖和界限,回歸至物我一體化的東方美學妙境,卻也帶著歐美現代主義的些許幽邃的神采和精魂。“剩下的時間里/我學唱一首清遠的歌/麥積山肩頭清雷一滾/舊宮墻邊一只蝴蝶失足/菩提樹葉飄動”,我讀其詩,見獵心喜,知道這才是擔擔真正應該擁有的詩意和精神糧食,是她遠游詩神的凝聚、落腳與停泊。
《草藥說》詩集里收錄了許許多多值得玩味的作品,它們或者高蹈激烈,或者低沉蘊藉,或者微象聚焦,或者抽離玄遠,或者機智沖淡,或者暢意鋪排……總之,我們會碰到無數個變體的擔擔,可是萬變不離其宗,總是會有一個合在一起的擔擔,保持了其詩的整體感和精神上的邊界屬性。
《草藥說》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擔擔自己的多重寫作元素的整合。在一些作品中,她將感覺和理性、沉思和抒情、敘述與形而上之道的言說,細部勾描與全篇架構等等,很美妙和諧地打磨成精神純正的音樂。
如果說《蘇三》將個體感悟與歷史傳奇和京劇文本,來了個變體的重構,道出了“我是蘇三/我是漢字的蘇三/我是琉璃的蘇三/三郎不見/我已是羞恥的蘇三”的生命悵惘和原始憂傷的話,那么《燒一只陶瓶》就是在“我”與陶的互相發現、塑造和再生過程中,寄寓靈性無限的可能性,精神創生無限的敞開性;如果說《日月潭》中盛放了作者帶著遠鄉口音,“持續一種錯認”,認知到日月潭雖“與我的身世無關/卻是一種故鄉”的悖論式存在,從而確證了“從少年經線走到中年緯線”的人生行旅的刻度與烙印;那么《犀牛與莎士比亞與我》就是在現代主義風格邊緣上去體味駐足放哨,傳神地審視了非理性盲區內的主體思想裂變和精神異化感中的內心靈魂的變焦;如果說《一年九班》是作者個人流年插曲的一個小花絮寫真,穿梭著本然的心事、細節的刻痕,融匯了美、信心、渴望還有追憶中雜糅的多重回眸的質感存在,讀起來令人深深嘆惋,在恍惚與迷戀中久久浸潤“窗前月光和兩只黃鸝的鳴叫/聲母和韻母像信物一樣深情”的表征,《春天里的言說》則是人與自然風情的零距離觸摸與擁抱,讓我們重溫落地生根、質樸深沉的“草本的味道”……
由此,我們不難感受到擔擔苦心孤詣的詩化追求和不斷求變的精神探索立場。從《舞者》到《刀的刃冰涼著》再到《草藥說》,她的嘗試、磨礪、突破、輾轉還有跳躍,總是將自己獻祭出來,進而達成詩性精神中必然面對的分裂、游弋、突圍、碰撞與和解。
而當我們把目光更縱深地投向女詩人的晚近之作,在即將出版的《老戲》里,那朝向更通透更智性更銳利也更圓融的詩意跋涉,就體現出作者不拘一格的在詩的本體重構上的嶄新安置、展放與回歸。蛻變舊我,構造新我,整合感覺與智性,試圖在抒情、敘事和沉思的變奏和疊加里,開拓出一種自我救贖、裂變及其新生的可能。
《老戲》中的許多詩,我是先睹為快,又一次見證了擔擔的變異和成長,砥礪與拓荒。
“人生最美麗的感受是性靈的展放”,作者屬于詩歌精神的悟道者,言說者和實踐者,她有意識地在為我們提供著“偏離”和“意外”,驚喜和覺知。在人生和藝術跋涉的遠途中,擔擔在精神困惑上的精神變更,顯得那么與眾不同,又水到渠成。當然,不是說她的寫作高峰已經到來,而是說她在持久真誠地努力著,她在默默蘊蓄著生命的能量,進而放射出屬于自己的鉆石般的詩性光亮。
擔擔晚近的詩,跨越了情感的拘束,抵達了經驗的復合,又有少數作品進而通過了超驗和幻象之美的誘惑。她學習里爾克在物象和經驗之間做智性的思辨與靈性的升華,同時也浸潤著保羅·策蘭命運深處中燒灼的那種無告無解的悲劇性的火。內傷,我想到這個詞,我覺得這是擔擔與策蘭的因緣。雖說她還走得不夠深遠,但她在用自己的創作與策蘭進行著真正意義上的精神對話,這在中國詩人中還不多見。
當然無論里爾克還是策蘭,都只是在助力加持,或者說成全著擔擔的詩意跋涉,而她骨子里的精神探索還是她自己的沉淀與追求的化合反應。
讀她晚近的作品,能發現她更加生活化歷史化個性化,也更趨于蒼莽混沌狀態,就是在銳利中保持了一定的鈍感,在理智中淬煉著生命幻美的感覺與悟性。
一方面,有些時候,她返歸日常習俗經驗,于近距離中去體味咂摸人情人性的深切而又蕪雜的況味。譬如寫倫理親情的《清掃者》就為我們帶來了樸實敦厚略帶傷感的詩意。女兒與父親的親緣卻是通過父親得病遇到搶救的極端情況來得以具象呈現的,尤其是這里擔擔充分動用了幻覺和想象力。一開頭就以“順著鐵軌撿拾時間”的意境來點染生病父親的艱難,而中間過程中有“兩只黃鸝在病房里飛舞”的句子,這是虛化還是實寫,已經不重要了,就像后邊作者說“那些翠柳/沿著他的胡須/發際/沿著一根細弱的呼吸的繩子/被他清掃”一樣,具體的生活細節已經進入了藝術的審美領地,化日常情景為精神寫真了。
同樣《鍘美案》寫的是小時候跟奶奶看戲的插曲與花絮,質感的瞬間,回憶的冷場和重溫的熱切來回轉化,字里行間充盈著兩個時空的交錯碰撞。那是共時,還是歷時,是現場,還是想象里發生的事件,在作者娓娓道來的詩化敘述中已經水乳交融難分彼此了。
另一方面,擔擔又從現實生活的腹地逃離——就像她從前的逃離一樣,她的詩更多的不是接地氣,而是呼吸自然、歷史和人文的空氣,在抽象或者象征乃至寫意性的精神撕裂整合的不斷磨礪之中,吸吮著道的氣息,透視著形而上的真諦。
閱讀《給策蘭》,我們不知不覺地走進了擔擔的心靈缺氧層,能覺察到一種氣喘吁吁的面對生命終極價值的眺望和補給。在“種子”“暮靄”“雨水”“黑牛奶”“灰燼”“亡靈”“天使”“媽媽”等詞語賦予的不斷遞進強化造成節奏和視像的巨大落差中,策蘭好像在擔擔的語詞間還魂附體,獲得了隔世生命的復歸、蘇醒和再生。那仿佛是策蘭精神和靈性的又一次輪回。
擔擔好像很在乎如何用一種有溫度的在場狀態看待和審視已逝的生命和歷史,她有意識地在縫合時間和傳統留下的用以印證個體生命價值的疤痕與記憶。對于她,沒有歷史感的人是失重的,就像沒有傳統的人是貧血的。而她的書寫既像與古典精神對視,交流,拼接,同時又像是在贖罪,在解構,在夢游。
《寒江獨釣圖》《秦俑》《變臉》《芍藥四言》等后期寫成的詩作,無一例外顯露了擔擔的良苦用心。在她銘心刻骨的體悟中,歷史不是冰冷的游戲,而是鮮活靈性的一次次復活與還魂。自然不是機械的運轉和宿命的更替交疊,而是有生命體征和性靈化呈現的有機體。
通讀擔擔的這些寄寓著自然和歷史魂魄與血脈的作品,我們會注意到其自覺的內省,思辨的意味,哲理的透視,其實就是要寫活人與物的無所不在、無遠弗屆的根本靈性。
無論怎樣,擔擔的心其實是通向中國古典精神的悠遠深處的。譬如那里有詩經楚辭的變體復現,也有唐詩宋詞的倒影流連,甚或曹雪芹的紅樓情結也常常蘊含其間——《芍藥四言》里就有史湘云的香魂出沒。還有西方現代詩的幽靈也常常給予她另一種豐盈的生命滋養,這樣形成兩種聲音兩種精神兩種傳統的對撞、并置與共鳴。
當然在擔擔漫長而又艱辛的充滿挑戰的跋涉中,她也為此付出了許許多多的寫作上的雷同、教條、重復與復制的代價。一些詩寫得要么過于隨意,沒有靈感的加持,或者意象飄忽、虛懸,要么少了應有的鋒芒和質感,抑或主題顯得相對單一,內在的韻味不夠豐富,等等。
盡管如此,就總體成就和水準而言,孫擔擔的詩意寫作,負載著靈性,表達著情懷,梳理著智性,傳遞著精神奧秘的福音,她是我們這個詩歌大花園里盛開的一朵奇花異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