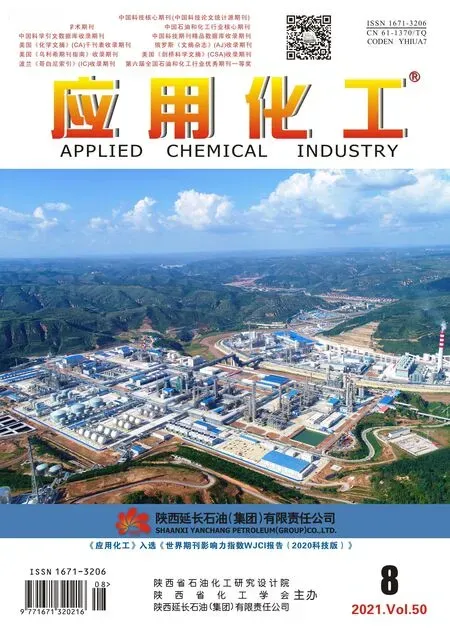國內外惡臭污染排放法規的進展
朱中楊,顏玉璽,金博強,朱仁成,李順義
(鄭州大學 生態與環境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隨著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對生活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1-2]。惡臭污染作為一種感覺性公害,在氣態污染物中占比很高[3-4]。2017年全國惡臭相關類投訴占所有環境問題的17.5%,2018年增加至22.0%,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這一比例高達30.0%,受到人們廣泛關注[5]。惡臭氣體是指在非常低的濃度下能夠刺激嗅覺器官并引起人們不愉快及損壞生活環境的揮發性物質[6]。惡臭氣體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通常不是由單一化學物質造成的,不同化學物質之間發生反應還會產生協同放大效應,顯著增加惡臭物質的污染性和難降解性[7-8]。目前人類嗅覺能感知到的惡臭有4 000多種,但按其來源大體可分為三類:自然源、生活源和工業源[9-11]。我國目前現行的《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GB 14553—93)已實行近30年,污染物限值相對寬松,不足以對當前復雜的惡臭污染進行有效控制[12]。本文通過部分發達國家相關法律體系及限排標準進行系統介紹和分析,為以后我國惡臭相關法規體系的修訂和完善,提高惡臭污染管理工作效率提供參考。
1 國外惡臭污染相關標準的發展
1.1 美國
美國空氣污染治理工作起步較早,1955年聯邦政府便頒布了《空氣污染控制法》;1963年又頒布了《清潔空氣法》,并于1990年出臺該法相關修正案,以此為主體逐步發展成為一套完整和規范的污染氣體控制法律體系。該體系主要包含三個方面:大氣環境質量標準制度、氣態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公民訴訟制度[13]。惡臭污染在美國被作為區域問題看待,因此各州政府可以根據經濟主要發展方向、氣象和地理條件等,分別制定不同的法律法規[14],主要有以下兩個形式:
(1)美國各州的工農業側重發展方向不盡相同,因此大氣環境中所含的惡臭物質也各有不同[15],分別設有不同的限值規定,例如康涅狄格州對硫化氫和甲硫醇排放標準作有專門的限值,而內布拉斯加州則對總還原硫作有限值規定等[16]。
(2)對于無組織源排放惡臭氣體的限制標準,美國普遍采用八級分級制的臭氣強度判定法[17]。根據現場臭氣濃度,結合韋伯-費希納公式將“濃度”這一物理量與居民的“心理感覺”聯系起來,科學地判斷出當地的惡臭強度(美國的臭氣排放感官限值單位為“D/T”)[18];而有組織源排放限制標準中主要針對特定惡臭物質的濃度進行限制,加州政府在2019年對當地企業排出的幾種惡臭物質做出限值規定,見表1[19-20]。

表1 加利福尼亞州惡臭物質有 組織源排放限值標準Table 1 California standards for organized source emission limits of malodorous substances
1.2 歐洲
為了控制惡臭污染,許多歐洲國家也相繼出臺了相關法律法規,其中英國、荷蘭在此領域開展較早[21-22],以下對其分別介紹。
1.2.1 英國 20世紀70年代英國政府制定了作為環境基本法的《污染控制法》,并于1990年對其進行一系列修訂,出臺了更加詳盡的《惡臭排放標準》[23]。2003年英國政府簽署了“環境綜合污染與控制條令(IPPC)”,據此頒布了《H4—惡臭管理導則》和《惡臭標準指導》[24-25],并以此作為處理相關惡臭污染的標準依據,其中惡臭氣體排放基準見表2[26]。

表2 混合惡臭氣體排放指示性基準Table 2 Indicative benchmarks for mixed odorous gas emissions
至今,英國關于惡臭物質限排的法律框架以《環境保護法》為統領文件,分管三類下屬法律,以此來達到對于惡臭氣體污染的有效控制,見圖1[27]:
1.2.2 荷蘭 荷蘭國內畜牧業發達,大量的豬牛羊及其排泄物等散發的惡臭氣味大大降低了牧場周圍居民的日常生活質量,因此荷蘭政府在1970年頒布了歐洲第一個國家層面上氣味影響管理法規,要求根據畜牧場的產量決定廠區與住宅區的最小距離[28-29]。上世紀末,為更好地分類管控惡臭污染,荷蘭重新出臺了《荷蘭排放指南》(NEG),惡臭氣體閾值采用了歐盟標準EN 13725∶2003;2016年荷蘭政府把NEG中標準限值部分和氣體信息部分又進一步拓展為兩部獨立的法規:《環境相關活動行政規范》和《工業排放信息法令》。荷蘭國內部分行業、設備的氣體排放限值見表3[30]:

表3 荷蘭國內部分行業、設備周邊環境限值Table 3 Environmental limits of some industries and equipment in the Netherlands
1.3 日本
為控制惡臭對居民生活造成的不利影響,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頒布了“宮城公害防治條例”,并于1972年正式頒布了第一部相關法律《惡臭防止法》[31-32]。這是世界上首部針對惡臭污染問題而制訂的法律法規,規定了8種惡臭氣體的排放標準[33-34]。該法規正式實施后,日本國內惡臭污染現象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工業臭氣污染投訴事件大幅度減少。
工業化迅速發展和各行業的興起,造成了惡臭污染的多樣化。因此,日本在1995年重新修訂了《惡臭防止法》,將原法規中的限排惡臭氣體類別增加至22種見表4。并規定了惡臭氣體的濃度和嗅強度指數兩種測定指標[35]。日本采用六級臭氣強度分級法(0~5級),政府可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方向及人口分布情況在2.5,3.0,3.5選擇某一臭氣強度水平,即為地方區域惡臭環境標準[36-37]。基于上述兩種基礎氣味控制機制,制定出了3種限制標準:廠區警戒線標準;煙囪排放口標準;廠區排水口標準,限制區域內的各類單位均受地方法律管制[38]。日本政府通過更新惡臭物質相關排放法律法規、修正臭氣濃度和強度測定方法修正,新增都、道、府地方性法規,建立了相對完整的惡臭控制體系[39]。

表4 1995年日本惡臭防止法 中受限的22種惡臭物質Table 4 22 Odor substances restricted in Japan’s Odor Prevention Act of 1995
2 國內惡臭污染控制相關法律發展
我國惡臭防治相關法規的制定起步較晚。1986年的天津市惡臭污染排放標準,是我國第1部惡臭污染相關控制標準。1993年頒布了國家標準《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GB 14553—93)(其中所規定的各類區域的廠界惡臭濃度標準及測定方法見表5),這意味著我國的惡臭治理工作開始有法可依[40-41]。

表5 惡臭污染物廠界標準值及臭氣濃度測定方法Table 5 Odor pollutant boundary standard value and odorous gas concentration measurement method
該標準促進了惡臭污染的管理,適用所有向大氣排放惡臭物質的單位廠區管理,屬于“一刀切”模式[42]。經過了近三十年的發展,惡臭污染的來源更加復雜,如化工廠、造藥行業等多種、各類源頭相互交錯,造成了污染物的多樣性和復雜性[43]。頻繁的投訴事件易導致社會不安定,僅依靠現行標準,已滿足不了如今復雜的惡臭污染局勢。經分析現行惡臭標準存在著以下幾點不足:
(1)現行的8種惡臭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太低,并且用統一的標準去應對各行各業所排放的不同污染物質并不合理[44]。
(2)排放限值分級分區設置已不適合當今的環境管理,且不同單位產生的惡臭污染千差萬別,通過人的嗅覺感知到的惡臭通常不會因為居住區域不同而產生明顯的變化[45-46]。
(3)標準中對于8種惡臭物質的監測方法始于20世紀90年代,對于當今復雜的污染成分顯得過于落后,同時管理比較簡單,無法實現對于不同企業識別其排放污染物的要求,缺乏針對排污企業自身責任的管理要求。
由此可見,我國惡臭污染形勢嚴峻,加強對惡臭污染排放的控制,對舊法規進行完善修訂迫在眉睫[47-48]。2017年原環保部印發的《國家環境保護標準“十三五”發展規劃》中提出“修訂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加強惡臭控制”;2018年,生態環境部發布了關于征求國家環境保護標準《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征求意見稿)》修改意見的函,決定重新修訂原GB 14553—93。
通過這次修訂,標準限值改進幅度為30%~90%;取消了分級分區,改為所有地域執行同一個標準;另外使排放標準中所明確的對象更加清晰,標準適用范圍從“所有向大氣環境排放惡臭氣體單位”拓寬為“所有建設項目中的環保設施設計及生產經營活動中產生惡臭氣體的企業單位”;將會采用更具現代化標準的監測方法,如苯乙烯的測定方法改為 “苯系物的測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氣相色譜法(HJ 584—2010)”,標志著我國對于惡臭污染方面的管理將步入一個更高的階段[49]。與此同時,我國地方政府也逐漸認識到惡臭污染的嚴重性和“區域治理”的重要性[50],部分省市頒布了不同的限制標準法規,如山東省2018年發布了《有機化工企業污水處理廠(站)揮發性有機物及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上海市2017年頒布了上海市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惡臭(異味)污染物排放標準》;2018年底天津市環保廳和省質監局于聯合發布了《有機化工企業污水處理廠(站)揮發性有機物及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
3 國內外相關法律對比分析
表6列舉了各地區的惡臭污染評價方法,通過對比可以發現,西方發達國家的惡臭控制相關法規著重于排污單位周邊環境內的惡臭物質含量,排放單位的臭氣濃度結合不同的大氣擴散模型,從而得出惡臭環境濃度是否超標(排放標準多是控制在某一時間段內不超過某個限值);而我國的排放標準主要通過對源污染物濃度判定其是否違法超排(這些相關標準適用于任何時間段,從而管控的尺度也更加嚴格)。

表6 各地區惡臭污染評價方法Table 6 Evaluation methods of malodorous pollution in various regions
發達國家的相關法規中,區域管理是一大特色,各個地區制定不同的標準;我國惡臭管理工作相較于發達國家開展較晚,現行的《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中規定了各省市中排污企業執行同樣的限排標準,便于統一管理。但我們從國家到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完善相應法規,部分省市根據自身情況已經制定了不同的限制標準。
惡臭相關測定方面,美國、歐洲國家和澳大利亞更多選擇使用動態嗅覺計測定法,該方法整體操作過程自動化高,所測得數據較穩定;我國和日本則使用三點比較式臭袋法,直接對源排放處的氣體進行測定評價,方法所得數據精確度高。由表6可知,英國的環境惡臭限值和我國的源排放限值均嚴于美國。
4 對于我國惡臭污染管理體系修改的建議
我國目前正在積極完善惡臭相關法律法規,2018年發布的《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征求意見稿)意見函,較之前修訂了部分內容。基于上述分析對我國惡臭排放標準修訂提出以下建議:
(1)建立更完善的惡臭物質限排標準體系
我國目前僅有的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不足以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來遏制臭氣排放,可根據我國目前的大氣環境污染特征,建立一系列具有我國特色的惡臭物質環境質量標準,污染物監測和處理方法標準等。同時加快相應檢測方法的更新,上世紀從日本引進的“三點比較式臭袋法”檢測惡臭氣體污染,根據嗅辯人員嗅覺閾值判定臭氣強度,結果會因人而異,有時會產生較大的偏差,因此需要開發出新型的檢測方法,利用標準儀器代替工作人員來減少結果誤差;利用大數據技術,調查惡臭氣體排放重點監控單位,以此制定相關的行業標準
(2)實現“因地制宜”管理
不同于英國,日本等小面積國家,我國盡管取消了惡臭排放分級管理,改用國家各地區統一標準,但各省地區的地理條件,經濟發展方向差別較大,建議在實行國家標準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根據當地重點污染物排放情況,對國家標準中未作規定的污染物項目,可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對于國家標準中已做出規定的污染項目,可以制定嚴于國標的地方污染物限排標準。
(3)加強基層管理
現如今大多數民眾也只是對惡臭污染有比較簡單的認識,這是國家推廣相應管控措施的一大阻礙。應加強基層群眾在惡臭污染防治方面的參與度,適度公開透明一部分惡臭相關的國家統計數據,以此增強公眾的環保意識;加強縣市級惡臭監測和管控的投入,社區積極宣傳等,構建群眾監督、舉報系統。與此同時,可將企業惡臭污染控制與所屬社區規劃聯系在一起,強化惡臭排放單位的主體責任,真正做到“責任到人”,將污染在源頭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