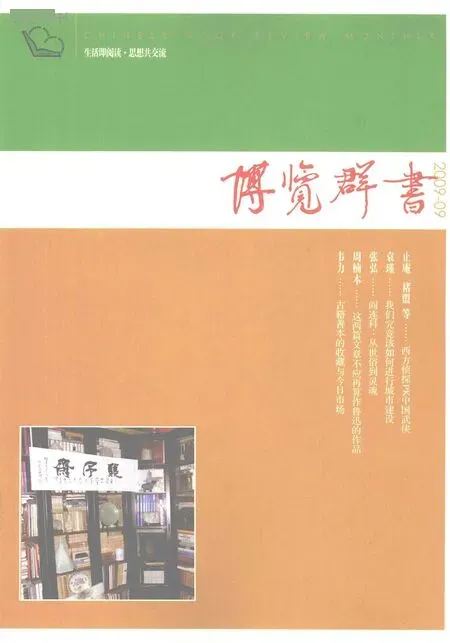尤其有影響力的人應(yīng)當(dāng)反思
王景新
在人類(lèi)社會(huì)發(fā)展史上,中華民族對(duì)庚子年有深刻記憶。尤其是近代以來(lái),每個(gè)庚子年,似乎都伴隨著重大災(zāi)難和歷史轉(zhuǎn)折。庚子年,全球似乎都不太平,一些震動(dòng)世界的大事件也容易發(fā)生在這一年。
1840年(庚子年),中國(guó)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zhēng),西方列強(qiáng)敲開(kāi)了古老封閉的清王朝大門(mén),是我國(guó)近代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ì)的開(kāi)端。
1900年(庚子年),義和團(tuán)運(yùn)動(dòng)在中國(guó)北方部分地區(qū)達(dá)到高潮,大清國(guó)和國(guó)際列強(qiáng)開(kāi)戰(zhàn),八國(guó)聯(lián)軍占領(lǐng)了北京紫禁城皇宮,導(dǎo)致中國(guó)陷入空前災(zāi)難,史稱(chēng)“庚子國(guó)難”。翌年(辛丑年)9月,中國(guó)和11個(gè)國(guó)家達(dá)成了屈辱的《解決1900年動(dòng)亂最后議定書(shū)》即《辛丑條約》,規(guī)定中國(guó)從海關(guān)銀等關(guān)稅中拿出4億5千萬(wàn)兩白銀賠償各國(guó),并以各國(guó)貨幣匯率結(jié)算,按4%的年息,分39年還清,史稱(chēng)“庚子賠款”。這一年,印度發(fā)生大饑荒,數(shù)百萬(wàn)人餓死;歐洲爆發(fā)罷工浪潮,南非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尸殍遍野。
1960年(庚子年),中國(guó)大面積受災(zāi),開(kāi)始了持續(xù)3年的自然災(zāi)害。這一年,美國(guó)正式派兵介入越南戰(zhàn)爭(zhēng),智利發(fā)生9.5級(jí)大地震,突破人類(lèi)記錄之最,14萬(wàn)人死亡;喀麥隆、多哥、馬達(dá)加斯加、剛果(利)(1997年改名為剛果民主共和國(guó))、索馬里、達(dá)荷美(現(xiàn)名貝寧)、尼日爾、上沃爾特(現(xiàn)名布基納法索)、象牙海岸(現(xiàn)名科特迪瓦)、乍得、烏班吉沙立(現(xiàn)名中非))、剛果(布)、加蓬、塞內(nèi)加爾、馬里、毛里塔尼亞、尼日利亞等17個(gè)非洲國(guó)家獲得獨(dú)立,因此被稱(chēng)為“非洲獨(dú)立年”。
2020年(庚子年),新冠肺炎席卷全球,給全人類(lèi)帶來(lái)巨大災(zāi)難。美國(guó)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xué)發(fā)布的實(shí)時(shí)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北京時(shí)間5月8日6時(shí)30分,全球累計(jì)確診新冠肺炎病例3833957例,累計(jì)死亡病例268877例。這并不是最后的結(jié)果,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庚子之后是反思。《人類(lèi)命運(yùn):變遷與規(guī)則》就是在這個(gè)特殊時(shí)間段完成的一部反思人類(lèi)發(fā)展歷史、思考人類(lèi)未來(lái)命運(yùn)的著作。
人類(lèi)學(xué)強(qiáng)調(diào)對(duì)脈絡(luò)的深度檢視、跨文化比較(尤其是社會(huì)文化人類(lèi)學(xué)),以及對(duì)研究區(qū)域的長(zhǎng)期、經(jīng)驗(yàn)上的深入了解,這往往稱(chēng)為參與觀察。作者遵循了社會(huì)文化人類(lèi)學(xué)的基本規(guī)則,把研究視野置于人類(lèi)自起源至今的全部進(jìn)化歷程,放在全球的不同地區(qū)(歐亞大陸、美洲、澳洲、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恒河流域、黃河流域等),不同人種(雅利安人、閃米特人、印第安人等),甚至放到螞蟻、蜜蜂等社會(huì)性極強(qiáng)的動(dòng)物群中去比較,試圖從人類(lèi)進(jìn)化的久遠(yuǎn)歷史和全球宏大場(chǎng)景的敘事中,解讀人類(lèi)命運(yùn)演化歷史脈絡(luò)及其人類(lèi)規(guī)則變遷的來(lái)龍去脈。這樣做的目的,作者明言:
我們只有站到了能夠看到人類(lèi)漫長(zhǎng)而艱難的遷徙歷程的足夠高度,回首過(guò)往,才能夠體會(huì)和認(rèn)清人類(lèi)明天應(yīng)該走向何方,明白我們當(dāng)下可以怎樣選擇、取舍。
看得出,作者是下了功夫的。盡管該書(shū)在敘事表達(dá)、推理論證、篇章小結(jié)等細(xì)節(jié)處理上,與當(dāng)今推崇的“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尚有一定差距,但著述的字里行間卻閃現(xiàn)出作者獨(dú)立思考的光芒,產(chǎn)生了許多超凡脫俗的新論。或許正是這種無(wú)拘無(wú)束的思維、表達(dá)方式,給予了作者自由馳騁的創(chuàng)新思維空間,而且這種在多學(xué)科之間從容自在游走,著實(shí)是需要足夠的學(xué)養(yǎng)功底和把控能力的。
作者認(rèn)為:人性是進(jìn)化的結(jié)果。滿(mǎn)足人性基本需要,與生俱來(lái)的屬性可稱(chēng)之為人性的原生屬性,如對(duì)于饑餓和安全的威脅,嬰兒與生俱來(lái)即存在明顯的反應(yīng)。這是人的天性,也是一切生命的通性。與生俱來(lái)的原真求生的本能恰恰是人性善美的內(nèi)容。史前原始人類(lèi)比我們今天的現(xiàn)代人更加具備利他、協(xié)作、依賴(lài)的本性,因?yàn)檫@一切都是自我生存的必備前提。人類(lèi)在進(jìn)化過(guò)程中與大自然較勁,與同類(lèi)族群交往中追求表現(xiàn),與自己的經(jīng)歷中苛求超越的特性,可稱(chēng)之為人類(lèi)的變遷屬性。比如人性中從眾的屬性,人們?cè)谫Y本至上的社會(huì)中的追求欲、占有欲、控制欲、超越欲……滿(mǎn)足這類(lèi)需求可以保證基本需求的更大滿(mǎn)足,但這些需求并不是通性,是部分個(gè)體苛求超越的特性。人性的原生屬性和變遷屬性是有沖突的:一方面,人類(lèi)的進(jìn)化和人性的變遷本來(lái)也具有雙面性,有進(jìn)化的一面,必定會(huì)有退化的一面,而且許多所謂的進(jìn)化本身可以說(shuō)就是退化,這正是人類(lèi)需要理性客觀認(rèn)知的;另一方面人類(lèi)作為大自然的一部分,地球村的一員,應(yīng)該歸于大自然自由公平法則的約束,從公義地認(rèn)知分析和判斷人類(lèi)原生屬性的人性美。他提醒:人性中從眾的變遷屬性何去何從?這是人類(lèi)特別需要思考的。
循著作者的思路去總結(jié),規(guī)則也是人類(lèi)遵循適者生存法則演化變遷的結(jié)果。所謂規(guī)則,是對(duì)應(yīng)于社會(huì)動(dòng)物而言,為協(xié)調(diào)個(gè)體、自然、社會(huì)之間,對(duì)內(nèi)或?qū)ν獾母黝?lèi)關(guān)系,以維護(hù)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基本約定。人類(lèi)在與大自然抗?fàn)幍耐瑫r(shí),更加是人類(lèi)自己與自己抗?fàn)帯_@種抗?fàn)幤鋵?shí)質(zhì)就是人類(lèi)通過(guò)一定的規(guī)則約束自己、約束大家、約束相互之間、約束人類(lèi)與自然萬(wàn)物的探索。人類(lèi)早期文明演進(jìn)中,如此豐富的各種崇拜和禁忌,歸納起來(lái)就是敬畏自然和敬畏生命。原始人類(lèi)為了自己和群體生命存在的需要,首先認(rèn)識(shí)和遵循的規(guī)則更多是以大自然的客觀規(guī)律為最基本最直接的準(zhǔn)繩,這些規(guī)則一部分是自然天成的自然規(guī)則,可稱(chēng)為天理法則,是人類(lèi)適應(yīng)自然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一部分是群體認(rèn)同的族群規(guī)則,其中既包含自然規(guī)則,也包含人情規(guī)則,是人類(lèi)在自然環(huán)境和人群環(huán)境雙重影響下形成的社會(huì)規(guī)則。這類(lèi)規(guī)則形成基本上是經(jīng)驗(yàn)歸納、習(xí)慣生成和約定俗成。比如,許多原始氏族和土著都有禁止砍伐水源周?chē)牟菽尽⒃诤恿魅浇笮”愫鸵昂现?lèi)的規(guī)定,是害怕因此遭受水神的報(bào)復(fù);禁止向火堆潑水、扔贓物、吐痰或用刀棍向火中亂插,是畏懼火神的懲罰。人們?nèi)绻蛔袷刈匀灰?guī)則和族群規(guī)則,必定很快受到自然環(huán)境和族群同類(lèi)的嚴(yán)酷責(zé)罰。人類(lèi)日積月累道法自然的規(guī)則傳承,不僅僅是合理的,往往是經(jīng)典的,應(yīng)該得到最基本的尊重和保護(hù)。
為了活著而規(guī)則,為了更好的活著而演繹規(guī)則。規(guī)則同樣按照自己節(jié)拍律動(dòng)和變遷。隨著社會(huì)生產(chǎn)力的提高,要維護(hù)社會(huì)秩序,解決不斷出現(xiàn)的新問(wèn)題和新矛盾,需要新的處理方式,新的行為規(guī)范。國(guó)家出現(xiàn)了,它首先需要制定剛性規(guī)則,這就是法的起源。法律是人類(lèi)規(guī)范的重要內(nèi)容,是自然規(guī)則、人情規(guī)則、經(jīng)濟(jì)規(guī)則、社會(huì)規(guī)則等一系列規(guī)則的凝練、升華和強(qiáng)制。依照法律治理國(guó)家和社會(huì)稱(chēng)之為“法治”。兩河流域(幼發(fā)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古巴比倫文明,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律體系,《烏爾納姆法典》是迄今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是古代西亞烏爾第三王朝的創(chuàng)始者烏爾納姆頒布的,距今已有4133年。從破損較嚴(yán)重的法典殘片看,法典包括序言和正文29條(傳下來(lái)的只有23條)兩大部分,法典的主要內(nèi)容是對(duì)奴隸制度、婚姻、家庭、繼承、刑罰等方面的規(guī)定。如:第一次離婚支付1米納白銀,而第二次離婚應(yīng)當(dāng)支付1/2米納白銀,通奸者將被處死;強(qiáng)暴自己的女奴者將被課以5西克爾罰金;作偽證將被處以罰款;斗毆中打折骨頭需支付1米納白銀,損傷腳需支付10西克爾;外國(guó)人的土地被淹沒(méi),每0.3公頃土地將給予3古爾(約900公升大麥)補(bǔ)償;將逃亡奴隸捉回的奴隸主要給捕捉者適當(dāng)?shù)膱?bào)酬;傷害他人的身世要處以酷刑并罰款;禁止行巫術(shù);破壞他人耕地者要支付食物賠償;女奴對(duì)女主人不敬則予體罰。婦女在家庭中地位低下,如犯通奸罪則處死等等。稍晚的《漢穆拉比法典》是中東地區(qū)的古巴比倫國(guó)王漢謨拉比大約在公元前1776年頒布的法律匯編,是世界上現(xiàn)存的第一部比較完備的成文法典。該《法典》由序言、條文和結(jié)語(yǔ)三部分組成,共3500行、282條,涉及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事、刑事、訴訟等領(lǐng)域,意在調(diào)解自由民之間的財(cái)產(chǎn)占有、繼承、轉(zhuǎn)讓、租賃、借貸、雇傭等多種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和社會(huì)關(guān)系。比如“6.任何竊取寺廟或者皇宮的財(cái)產(chǎn)的人將被處以死刑,而從他那里接收贓物的人也一并處以死刑。”“7.任何在沒(méi)有證人或者合同文書(shū)的情況下,于他人的兒子或者奴隸處購(gòu)買(mǎi)白銀、黃金、男女奴隸、斧頭或者是羊、驢以及其他任何東西的人,或者為此負(fù)責(zé)的人,都將被視為盜賊且判處死刑。”“14.拐帶他人幼子之人,將被判處死刑。”“55.如果任何人開(kāi)挖溝渠以澆灌田地,但是不小心淹沒(méi)了鄰居的田,則他將賠償鄰居小麥作為損失。”“282.若奴隸忤逆主人,一經(jīng)定罪,主人可以割下他的耳朵。”該書(shū)作者認(rèn)為:規(guī)則和法律約束力總是傷害個(gè)體的自由野性的,因此比較自由而言,任何規(guī)則、法律總是殘忍的;然而對(duì)于秩序而言,這種殘忍何嘗不是一種文明呢。
關(guān)于原始公有制內(nèi)涵和私有制形成,作者也有他的見(jiàn)解。他認(rèn)為:
在族群內(nèi)部大家是共同圍捕獵物,組織采集,分配食物,相依為命的共同體。但對(duì)于族群外的同類(lèi)來(lái)說(shuō),互相之間并不是共有共享的關(guān)系,有考古發(fā)現(xiàn)原始人類(lèi)捕獲同類(lèi)作為食物也是通常的情況。一直到部落形成之后殺戮異族的同類(lèi)還是非常平常的。因此我們說(shuō)原始人類(lèi)這種共有共享的共同體是相對(duì)獨(dú)立的族群內(nèi)部而言的,并不是整個(gè)原始人類(lèi)種群。可見(jiàn)原始公有制的存在是有一定范疇的,對(duì)于族群外的同類(lèi),各個(gè)族群一開(kāi)始就存在各自私有的利益。因此我們認(rèn)為對(duì)這段歷史的組織形態(tài)概括為“原始集體主義”或者“群落共產(chǎn)主義”,是不是比稱(chēng)之為“原始共產(chǎn)主義”更加準(zhǔn)確一些。
按照作者這個(gè)邏輯,原始公有制和原始私有制的起源是同步的。這樣一來(lái),私有制起源和形成就比現(xiàn)有文獻(xiàn)的說(shuō)法大大提前了。
我個(gè)人認(rèn)為:“原始集體主義”在原始人類(lèi)社會(huì)是存在的。它先后經(jīng)歷了血緣家族公社、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農(nóng)村公社或馬克爾公社等不同的組織形式;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村社公有、宗族公田祠產(chǎn)、血緣和親緣家庭以及熟人社會(huì)的伙有共耕、互助合作制度,大多數(shù)也是由原始公社中各種不同形態(tài)的公有制集體經(jīng)濟(jì)殘留或傳承下來(lái)的;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歷史存在,首先是人類(lèi)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自然產(chǎn)物,而非人們的行為偏好(主觀愿望),與“主義”無(wú)關(guān);集體經(jīng)濟(jì)伴隨著史前人類(lèi)和成文史以來(lái)人類(lèi)社會(huì)發(fā)展的各個(gè)歷史階段一路走來(lái),必將繼續(xù)伴隨人類(lèi)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未來(lái)進(jìn)程,集體經(jīng)濟(jì)可能是一個(gè)永恒話(huà)題。這一問(wèn)題,在我的《村域集體經(jīng)濟(jì):歷史變遷與現(xiàn)實(shí)發(fā)展》一書(shū)中曾辟專(zhuān)章研究“集體經(jīng)濟(jì)歷史演進(jìn):從血緣家族公社到農(nóng)村公社”,在此不贅述。恩格斯說(shuō)“群是由我們?cè)趧?dòng)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會(huì)集團(tuán)”;馬克思認(rèn)為人類(lèi)完全成形后,“血緣家族是第一個(gè)社會(huì)組織形式”。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diǎn),血緣家族存在的時(shí)間很長(zhǎng),相當(dāng)于舊石器時(shí)代早期和中期階段。在漫長(zhǎng)的以采集和狩獵為主要內(nèi)容的攫取經(jīng)濟(jì)時(shí)代,人類(lèi)“為了在發(fā)展過(guò)程中脫離動(dòng)物狀態(tài),實(shí)現(xiàn)自然界中最偉大的進(jìn)步,還需要一種因素:以群體的力量和集體行動(dòng)來(lái)彌補(bǔ)個(gè)體自衛(wèi)能力的不足”。當(dāng)代歷史學(xué)家也認(rèn)可“狩獵依靠集體進(jìn)行,因此狩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原始人實(shí)行集體主義”。
至于“私有制”的起源和形成過(guò)程,我認(rèn)為應(yīng)該進(jìn)一步深入研究。對(duì)于私有制的形成,歷來(lái)有不同見(jiàn)解。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私有制是跟隨人類(lèi)誕生就有的產(chǎn)物,是人類(lèi)社會(huì)天生的配套之物。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一些氏族和部落首領(lǐng)和少數(shù)家長(zhǎng)為了占有更多的產(chǎn)品供自己享用,……把一些集體財(cái)產(chǎn)竊為己有,私人占有財(cái)產(chǎn)的現(xiàn)象便出現(xiàn)了”。但有學(xué)者質(zhì)疑,“那些把集體財(cái)產(chǎn)竊據(jù)為己有的氏族部落和家長(zhǎng)的私有觀念是從哪里來(lái)的”。該書(shū)作者把原始公有制看成氏族、部落內(nèi)部公有制,而把氏族和氏族之間、部落和部落之間為領(lǐng)地、水源、獵物的爭(zhēng)搶看成是私有制觀念生成的環(huán)境。這樣一來(lái),上述質(zhì)疑可以得到解釋。
恩格斯認(rèn)為,私有制是生產(chǎn)力發(fā)展和婚姻制度演化的結(jié)果。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國(guó)家的起源》中,把人類(lèi)史前劃分為“三個(gè)主要時(shí)代——蒙昧?xí)r代、野蠻時(shí)代和文明時(shí)代”。就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而言,蒙昧?xí)r代是以采集現(xiàn)成的天然產(chǎn)物為主的時(shí)期,人類(lèi)制造品主要是用作這種采集的輔助工具;野蠻時(shí)代是學(xué)會(huì)經(jīng)營(yíng)畜牧業(yè)和農(nóng)業(yè)的時(shí)期,是學(xué)會(huì)靠人類(lèi)的活動(dòng)來(lái)增加天然產(chǎn)物生產(chǎn)的方法的時(shí)期;文明時(shí)期是學(xué)會(huì)對(duì)天然產(chǎn)物進(jìn)一步加工的時(shí)期,是真正的工業(yè)和藝術(shù)的時(shí)期。就婚姻制度和家庭演化而言,在整個(gè)蒙昧?xí)r代,人類(lèi)實(shí)行著群婚制,后來(lái)出現(xiàn)了按照輩分劃分的血緣家庭,在這種家庭中,輩分不同的人群禁止成為夫妻;到了蒙昧?xí)r代的中級(jí)階段,又出現(xiàn)了排除姊妹和兄弟之間性交關(guān)系的普那路亞家庭;蒙昧?xí)r代的高級(jí)階段,是氏族繼續(xù)發(fā)展時(shí)期,實(shí)行著共產(chǎn)制家庭經(jīng)濟(jì),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東西,都是共同財(cái)產(chǎn)。恩格斯說(shuō),“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誰(shuí)是某一個(gè)孩子的父親是不能確定的,但誰(shuí)是孩子的母親卻是知道的。……由此可知,只要存在著群婚,那末世系就只能從母親方面來(lái)確定,因此,也只承認(rèn)女系”這就是母系社會(huì)的根由。
進(jìn)入野蠻時(shí)代,“……群婚就被對(duì)偶婚排擠了。在這一階段上,一個(gè)男子和一個(gè)女子共同生活”。“對(duì)偶家庭產(chǎn)生于蒙昧?xí)r代和野蠻時(shí)代交替的時(shí)期,大部分是在蒙昧?xí)r代高級(jí)階段,只有個(gè)別地方是在野蠻時(shí)代低級(jí)階段”。“直到野蠻時(shí)代低級(jí)階段,固定的財(cái)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裝飾品以及獲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簡(jiǎn)單的家庭用具。天天都要重新獲得食物。”到了中級(jí)階段時(shí),隨著畜牧業(yè)的發(fā)展,“已經(jīng)有了馬、駱駝、驢、牛、綿羊、山羊和豬等畜群,這些財(cái)產(chǎn),只須加以看管和最簡(jiǎn)單的照顧,就可以愈來(lái)愈多地繁殖起來(lái),供給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但是,這些新的財(cái)富歸誰(shuí)所有呢?最初無(wú)疑是歸氏族所有。然而,對(duì)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是很早就已發(fā)展起來(lái)了”。究竟早到說(shuō)明時(shí)候呢?恩格斯提示:
很難說(shuō),亞伯拉罕族長(zhǎng)被所謂摩西一經(jīng)的作者看作畜群的占有者,究竟是由于他作為家庭公社首領(lǐng)所擁有的權(quán)利,還是由于他作為實(shí)際上世襲的氏族首長(zhǎng)而具有的地位。只有一點(diǎn)沒(méi)有疑問(wèn),那就是我們不應(yīng)該把他設(shè)想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財(cái)產(chǎn)所有者。其次,沒(méi)有疑問(wèn)的是,在成文歷史的最初期,我們就已經(jīng)到處都可以看到畜群乃是一家之長(zhǎng)的特殊財(cái)產(chǎn),完全同野蠻時(shí)代的工藝品一樣,同金屬器具、奢侈品以及人畜——奴隸一樣。
這說(shuō)明:野蠻時(shí)代的低級(jí)階段私有制就出現(xiàn)了;在畜群完全轉(zhuǎn)歸家庭所有以后,“這些財(cái)富,一旦轉(zhuǎn)歸各個(gè)家庭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來(lái),就給了以對(duì)偶婚和母權(quán)制氏族為基礎(chǔ)的社會(huì)一個(gè)有力的打擊”。
一夫一妻制家庭,“它是在野蠻時(shí)代的中級(jí)階段和高級(jí)階段交替的時(shí)期從對(duì)偶家庭中產(chǎn)生的;它的最后勝利乃是文明時(shí)代開(kāi)始的標(biāo)志之一。”在恩格斯看來(lái),一夫一妻制家庭產(chǎn)生的唯一目的是為了保護(hù)私有財(cái)產(chǎn)的社會(huì)延續(xù)。他寫(xiě)道:“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條件為基礎(chǔ),而以經(jīng)濟(jì)條件為基礎(chǔ),即以私有制對(duì)原始的自然長(zhǎng)成的公有制的勝利為基礎(chǔ)的第一個(gè)家庭形式。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統(tǒng)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應(yīng)繼承他的財(cái)產(chǎn)的子女,——這就是希臘人坦率宣布的個(gè)體婚制的唯一目的。”
作者對(duì)“資本文明”,尤其是對(duì)“資本的野性和殘酷”有深刻的反思和詰問(wèn),“探索理想秩序”與社會(huì)主義、共產(chǎn)主義一脈相承。作者謳歌了東方先哲諸如《禮記、禮運(yùn)、大道之行》描寫(xiě)的大同世界;詰問(wèn)“中國(guó)傳統(tǒng)統(tǒng)治者在五千年文明史中,為什么堅(jiān)定的極力固守‘重農(nóng)抑商政策,真的是在破壞社會(huì)規(guī)律中新生產(chǎn)力,自毀發(fā)展之路么?”他認(rèn)為“重農(nóng)抑商”是中國(guó)先人們對(duì)資本之惡“防微杜漸,未雨綢繆的深遠(yuǎn)治理謀略。華夏文明傳承者不是不懂,也不是不屑資本積累,而是早就洞察了資本的本性,明了資本積累后的社會(huì)、環(huán)境、自然、觀念等產(chǎn)生的變化,用商鞅的話(huà)說(shuō)就是‘國(guó)之危也……華夏文明是給資本這個(gè)潘多拉盒子有意上了封條”。“資本在帶來(lái)物質(zhì)繁榮的同時(shí)也在不斷掏空著一些人的靈魂”,“重農(nóng)抑商”是守住人性的最后底線(xiàn)。從資本本性和人性角度,而不從階級(jí)分化、階級(jí)斗爭(zhēng)角度去認(rèn)識(shí)資本、資本主義,我以為拓展了資本主義的研究視野。
人類(lèi)過(guò)往文明的每一段,都能夠糾結(jié)我們的內(nèi)心。要想“團(tuán)結(jié)起來(lái)到明天”,人類(lèi)必須團(tuán)結(jié)面對(duì)貧困危機(jī)、自然環(huán)境容量危機(jī)、人類(lèi)文明自毀危機(jī)、人類(lèi)綜合焦慮危機(jī)等四大共同敵人。人類(lèi)站在新十字路口,何去何從?人類(lèi)的命運(yùn),其實(shí)也就是一個(gè)個(gè)個(gè)體的命運(yùn)匯成的歷史河流。每個(gè)人,尤其有影響力的人應(yīng)該反思。這是該書(shū)作者的呼吁,也是我寫(xiě)此序言的初心。
(作者系浙江大學(xué)教授,國(guó)務(wù)院津貼獲得者。本文為《人類(lèi)命運(yùn)·變遷與規(guī)則》一書(shū)序言,標(biāo)題為編者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