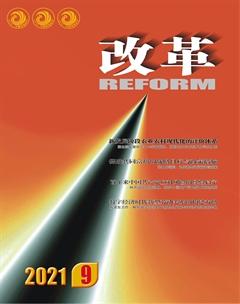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居民消費:進程回顧、思想變遷與民生實踐
毛中根 賈宇云 葉胥
摘? ?要:中國共產黨領導居民消費發展的歷史邏輯是伴隨經濟發展的自發式升級與自覺式消費調控相交融;理論邏輯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與時代發展命題相呼應;現實邏輯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與消費現實問題相結合。這為促進居民消費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堅持以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依據,推動居民消費持續穩定發展;遵循生產與消費的辯證關系,推動居民消費動態平衡發展;秉承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使命,推動居民共享消費發展成果。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中,邁向共同富裕的居民消費發展,其著力點在于:破除“共同”阻礙,推進居民消費均衡發展;增加“富裕”廣度,加速居民消費增量擴容;提升“富裕”深度,著力居民消費提質增效。
關鍵詞:建黨百年;居民消費;共同富裕
中圖分類號:F1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543(2021)09-0050-15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不同歷史階段,提出不同的消費發展思想,并用于指導民生實踐,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居民消費:演進歷程
一百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在不同階段,居民消費主要特征呈現階段性變化。總體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居民消費演進歷程可劃分為五個階段。
(一)1921—1949年:領導解放發展生產與居民消費基本保障
1921—1949年,中國共產黨逐步加強對國民經濟與居民消費的影響,以1927年開辟革命根據地為分界點,中國共產黨開啟了獨立領導居民消費的新篇章。
1.領導解放發展生產
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領導中華民族實現民族獨立。在領導實現民族解放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經濟建設進行了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一直處于財政困難、經費和物資供應緊張的戰爭狀態下。加強農業生產和重要供給設施建設成為重點工作,如修建軍械廠、被服廠、印刷廠和商店等。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絕大多數根據地都開始大力發展生產、保障民生和改善消費。邊區糧食產量逐年增長,1944年陜甘寧邊區糧食產量為1937年糧食產量的近兩倍[1];棉紡織業取得較大發展,1943年陜甘寧邊區擁有紡車120 255架,紡紗417 852公斤,織布63 334大匹[1]。解放戰爭時期,農業顯著發展。1946年,僅山東魯南、渤海、魯中、膠東四區就增產糧食34 000多萬公斤,基本實現糧食自給自足;晉冀魯豫解放區產棉12 500萬公斤,足有1945年全國棉產量一半之多[2]。同時,解放區非常注重輕工業和手工業發展,迅速恢復了解放區內的煤礦、電力、金礦、造紙、化學等工業生產。從建黨到新中國成立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逐漸擴大并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導經濟。
2.居民消費基本保障
土地革命時期,廣大蘇區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基本解決了糧食菜蔬需求,部分解決了棉花需求,居民消費得到基本保障。抗日戰爭時期,在減租減息和農業合作互助開展的推動下,農業得到迅速發展。例如,在太行一分區的7個村中,收入(折米)從1942年的38 832.82石增加至1944年的56 344.28石,平均每人收入從2.21石增加至3.37石[1]。1939年,陜甘寧邊區舉辦農業展覽會,陳列糧食、牲畜和藥材等多達2 000種展覽品[1],側面反映出邊區居民生活消費水平提升。進入解放戰爭時期,農業生產發展更為穩固,農民生活顯著改善。解放初期,山西省武鄉縣6個典型村中,有存糧者占43.3%,夠吃用者占47.2%,不夠吃者僅占6.5%[3]。由此可見,農民生活消費得到基本保障,這為解放戰爭勝利奠定了基礎。
(二)1949—1978年:經濟建設探索前進與居民消費初步擴大
新中國成立后,經濟建設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1949—1978年,我國逐步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系,隨著經濟的發展,居民消費也有了初步增長。
1.經濟建設探索前進
1949—1956年,我國生產力得到初步發展,完成三大改造,恢復并發展了工農業生產與國內外貿易。“一五”期間,工業產出每年以18.7%的速度遞增,帶動國民收入每年以8.9%的速度增長[4]。1957—1978年,受“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有限。“大躍進”造成經濟結構重大比例失衡以及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失調,工業與農業的產值比例由1957年的5.7∶4.3變為1960年的8∶2,積累率由“一五”時期的24.2%上漲到1960年的39.6%[4]。從1961年開始,國民經濟在供需關系和生產關系兩方面進行調整,到1965年積累率降為27.1%[5],大體回歸正常水平。總的來說,1949—1978年,經濟建設在探索中前進,經濟總量呈現波動式上升。
2.居民消費初步擴大
1949—1978年,我國居民消費初步擴大,居民消費水平從1952年的76元增加至1978年的175元[6]。其中,1949—1952年,居民消費迅速恢復,農民消費品購買力由1949年的65.3億元增長到1952年的117.5億元,增長79.9%[7]。1952—1956年,消費水平得到進一步提升。1956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為461億元,較1952年增長66.4%[8],同時期糧食、棉布、膠鞋零售量分別增長26%、39%和82%[7]。1957—1965年,居民消費水平表現為先下降后總體回升。1960年人均糧食、食油和豬肉消費水平較1959年分別下降12.3%、18%和48%[9]。1966—1978年,居民消費遭遇困境,消費水平波動加劇,市場供求關系緊張,我國對一些商品采取了憑票供應。1966—1978年,人均消費支出較上年增長的有11個年度,下降和持平的各有1年。
(三)1978—1992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居民消費潛能釋放
1978年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逐步實施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發展模式。商品經濟的確立,不僅加速了生產力發展,而且為居民消費潛力不斷釋放奠定了基礎。
1.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全方位加強和推進經濟建設。農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人民公社集體經營體制。城市的計劃管理體制改革逐步展開,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推行經濟責任制等改革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國民經濟運行格局發生巨大改變,市場調節的范圍和作用不斷擴大,國民經濟嚴重失衡問題逐步得到解決。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強勢復蘇,總需求迅速擴張。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圍繞經濟建設開展了一系列工作,極大地提振了國民經濟發展信心,前期被壓制的居民消費需求得到釋放,居民消費開始快速增長。
2.居民消費潛能釋放
隨著經濟發展與居民收入逐步增長,居民消費潛力得以釋放。按當年價格計算,1992年全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分別是1978年的5.4倍和5.7倍,年均分別增長12.8%和13.2%,扣除物價因素,1985—1992年實際年均分別增長6.4%和6.8%[10]。從消費主體來看,城鎮居民消費發展快于農村。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分別由1978年的405元、138元增長到1992年的2356元、718元,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比由1978年的2.9倍上升到1992年的3.3倍[4],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拉大。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速度明顯快于農村,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分別從1983年的59.2%、59.4%降低至1992年的53%、57.6%[11]。居民消費潛能的釋放,也意味著居民消費熱點不再局限于基本的生活需求,城鎮居民消費出現了首次集中式、排浪式的消費浪潮——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三轉一響”消費熱。
(四)1992—2012年:市場經濟體制確立與居民消費快速增長
1992年后,市場經濟體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在市場經濟作用下,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進入快速增長階段。
1.市場經濟體制確立
1992年“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階段,中國共產黨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以股份制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以分稅制為核心的財稅體制改革、以“放權讓利”為導向的國有企業改革等穩步推行,沿海地區建立起各類工業園區,在工業迅猛發展帶動下,國民經濟呈現高增長態勢。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對外貿易發展迅猛,凈出口總額大幅攀升,經濟總量一路高歌猛進。雖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但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我國經濟繼續維持高速增長。在這一階段,我國經濟邁上更高的臺階,加上逐步建立起覆蓋城鄉的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和醫療保障體系,居民消費得到快速增長。
2.居民消費快速增長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之后,居民消費發展的障礙得以破除,擴大內需政策被多次強調并得以落實。這一階段,居民消費快速增長,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分別從1993年的2 111元和769元提高至2012年的16 674元和5 908元,分別增長6.9倍和6.7倍[1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1992年的10 993.7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210 307億元①,增長19.1倍。城鄉居民消費差異在初期擴大之后逐漸縮小,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之比由1992年的2.5倍提升至2003年的3.4倍,之后逐漸降低,2012年降至2.8倍;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之差從1992年的4.6個百分點降至2012年的3.1個百分點,并趨于穩定。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優化升級,1993—2012年,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從50.3%降至36.2%,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從58.1%降至39.3%,城鄉居民生活水平邁入相對富裕水平[11]。
(五)2012年至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與居民消費高質量發展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有助于滿足居民消費新的需求。消費范圍不斷擴大、內容不斷充實、消費高質量發展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特征。
1.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其主要任務包括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等。這一階段,經濟發展的動力逐漸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一是技術創新取得較快發展,2019年科技進步貢獻率達59.5%[12],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我國位居世界第十四位;二是制度創新穩步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體系、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不斷建立與完善;三是企業規模和品牌度不斷提升,2019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進入世界500強企業最多的國家。2019年、2020年我國人均GDP連續兩年超過1萬美元,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總之,相比前一階段,我國經濟建設擁有更高水平,為居民消費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穩固基礎。
2.居民消費高質量發展
2014年以來,消費超過投資成為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2012—2019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貢獻率平均值為59.4%。消費水平不斷提高,人均消費支出由2013年的13 221元快速增長到2020年的21 210元,年均增長7.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2013年的237 810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391 981億元,年均增長8.1%[13]。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服務性消費增速快于實物性消費,享受型、發展型消費增速快于生存型消費。2019年城鎮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支出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之和為33.8%,較2013年提升4個百分點;2019年城鎮居民人均食品、衣著支出占人均消費支出比重之和為34.4%,較2013年下降4.5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傾向不斷提升,消費信貸迅速發展。根據《2019中國消費信貸市場研究報告》,2019年我國消費信貸余額占GDP比重為13.3%。綠色消費理念逐步形成,共享單車、共享汽車等符合綠色消費理念的共享經濟迅猛發展。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居民消費:思想變遷
針對各階段的經濟建設和居民消費特點,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緊緊抓住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居民消費思想。
(一)1921—1949年:關注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發展農業保障消費
1.關注人民基本生活需要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始終關注人民的基本生活。例如,黨的二大宣言中提到,“自從外國商品充斥中國市場以來,手工業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趨困苦,甚至破產失業”[14],黨的六大通過的《宣傳工作決議案》中提到“反對低廉工資與生活昂貴,改良食物,減少學徒時間”[15]等。進入根據地建設后,改善人民生活成為重要任務。毛澤東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講到:“我們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16]。1937年發布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強調,“須切實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17]。抗日戰爭時期,《關于冀南新政府成立后的工作指示》提到,要“救濟各地廣大饑餓的群眾”,“組織秋收運動”[18]。解放戰爭時期,黨對人民生活的關注范圍更加擴大。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到,“幫助退伍軍人解決生活和就業問題”,“救濟難民和救濟災荒”,“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19]。
2.發展農業保障消費
基于時局形勢,中國共產黨主要從三個方面促進農業發展:一是著眼于土地這一生產要素。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強調要立即實行而不僅限于宣傳農民的土地問題[15]。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土地政策亦作出相應調整。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中提到,要改良人民生活,以提高人民的購買力,繁榮市場,從而無限提高抗日力量,其中就需要取消苛捐雜稅,減少地租[20]。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政策調整為實現“耕者有其田”。二是扶助中農,從而抑制階級分化。針對陜甘寧邊區出現的農村中農化的情況,毛澤東指出,“邊區大多數的人民都是中農……我們要扶助中農,依靠中農,要使中農加緊生產,使邊區的農產品大大地增加起來,增加到有剩余。”[21]三是聯合富農,獎勵其生產。土地改革后,農民生產條件改變,出現了新的分化。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寫到,“不應過早地采取消滅富農的政策”[19]。1942年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明確提出,“在適當的改善工人生活條件之下……獎勵富農生產與聯合富農”[22]。
(二)1949—1978年:著眼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刺激生產創造消費
1.著眼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提到,“如果我們……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23]。能否“維持政權”取決于“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起草宣言中提到,要“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22]。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談到:“我國現在的社會主義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24]。
2.刺激生產創造消費
1958年,毛澤東深刻論述了生產和消費的關系:“生產轉化為消費,消費轉化為生產。生產就是為了消費,生產不僅為了其他勞動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費者。”不僅如此,毛澤東更是強調要刺激生產發展,“人們生活的需要,是不斷增長的。需要刺激生產的不斷發展,生產也不斷創造新的需要”[25]。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到了生產對于保障人民生活消費的作用,以及人民生活消費對生產促進的反作用,“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但是,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加重的結果怎么樣?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毛澤東指出:“基本建設多搞了,生產也發展了,結果利潤會更大。基本建設發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費性的、服務性的市場也擴大了”[26]。陳云談到,“先保證生產、后供應基建這種排隊的必要,主要是為了維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避免盲目擴大基本建設規模,擠掉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在財力物力的供應上,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必須先于基建,這是民生和建設的關系合理安排的問題。”[27]
(三)1978—1992年: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擴大生產適度消費
改革開放后,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成為當時的重要命題。但這并不意味著要盲目消費甚至過度消費,發展生產力仍是第一要務。
1.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1978年鄧小平指出,“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人民的物質生活”“文化生活、精神面貌”的最終實現,便是通過消費來完成的。鄧小平指出,“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是要大幅度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28]他在《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提出,“各項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29]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既強調人民的物質生活,又強調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與精神面貌,向著“好一些”的方向推動。
2.擴大生產適度消費
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階段,消費的作用得到重視,但主要任務仍然是發展生產力,而非盲目提升消費。鄧小平指出,生產與消費、生產與生活要并重,“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29]。他還強調要注意適度消費,“要注意消費不要搞高了,要適度”[29],“我們只能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生活。發展生產,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對的;同樣,不發展生產,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對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也反對現在要在中國實現所謂福利國家的觀點,因為這不可能”[28]。在面對實行高收入高消費的建議時,他直接指出,“我們國家情況有所不同,現在全國沒有條件實行高收入高消費的政策”[29]。對于我國經濟發展,他贊同未來“實行高收入高消費的政策”,在沒有條件實行時,就采用先富帶后富的方式,“如果將來沿海地區搞好了,經濟發展了,有了條件,收入就可以高一點;消費就可以增加一點,這是合乎發展規律的”[29]。
(四)1992—2012年:重視人民生活全面提升,擴大內需提振消費
1.重視人民生活全面提升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提出“三個有利于”標準,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標準。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十四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四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使全國人民過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的水平前進。”“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通過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科學發展觀要求“以人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們的多方面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同時,“我國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到市場約束,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如果消費需求上不去,投資也難以發揮效益。要把促進消費需求的增長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一項重大措施,使投資和消費雙向啟動”[30]。
2.擴大內需提振消費
為解決居民消費不足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擴大內需戰略。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的方針”,“逐步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2004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合理調整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消費作為擴大內需戰略的重要一環被加以強調。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2008年,全球遭遇金融危機,消費在擴大內需中的關鍵作用更加凸顯。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持續推進的這一時期,居民消費的作用被進一步認識,擴大內需、激發居民消費成為中國共產黨推動經濟發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舉措。
(五)2012年至今: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發揮消費基礎性作用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因此,消費發展更加追求高質量發展,強調要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
1.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滿足美好生活需要,關鍵是結構與質量。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努力釋放有效需求”,“有效”二字體現了結構性問題。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31]。因此,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就“必須推進供給側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尤其在“三期疊加”背景下,“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有效供給,實現“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31]。關于質量問題,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要“努力提高消費品質量和服務水平”。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產品質量”與“創新供給”,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提高供給體系質量”與“保護和提高……農產品質量、效益”,這些都表明,在新時代黨中央更為關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
2.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
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可以看出,黨中央關于消費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的認識在不斷深化。對消費的認識最先體現在“量”上,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消費穩定增長保證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二是通過消費升級實現消費高質量發展,助力經濟發展從高速增長轉變為高質量發展。消費是保持經濟平穩運行的“壓艙石”和“穩定器”,消費對經濟發展具有更“基礎性”的作用,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以及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消費升級則是消費從“量”轉變為“質”的“助推器”,圍繞消費升級,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更有效地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談到,“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孕育著大量消費升級需求”[32],“要緊緊圍繞……消費升級的方向……統籌部署創新鏈和產業鏈”[33],“推動供需結構有效匹配、消費升級和有效投資良性互動”[34]。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居民消費:民生實踐
在消費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為推動居民消費發展進行了一系列探索,直接反映在處理生產和消費的關系上,其出臺的一系列民生實踐呈現階段性特征,為居民消費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一)1921—1949年:分配土地要素,著力消費自給
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非常關注人民消費和生活,要實現此目的,必須尋求獨立與發展生產,尤其是以農業生產為中心,而土地要素是農業生產恢復和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實踐中,中國共產黨首先解決以土地為中心的生產要素問題,并動員軍民自己動手,以實現豐衣足食。
1.分配土地要素
1928年《井岡山土地法》頒布實施,規定將一切土地沒收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再以人口為標準將土地分配給農民進行耕種。1929年制定實施《興國土地法》,把“沒收一切土地”變為“沒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土地”。到1931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已形成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革命路線。抗日戰爭爆發后,為配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又對土地政策進行了重要調整。1937年,《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此后,又發布了《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等,主要內容包括要求地主減租減息并取消雜租、勞役和高利貸,農民交租交息。解放戰爭時期,全面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將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1946年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組織隊伍深入農村進行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運動。1947年通過《中國土地法大綱》,正式寫入“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2.著力消費自給
為滿足根據地人民需要,中國共產黨實行了一系列政策,致力于實現人民消費自給。一是積極調動人民生產積極性。中央蘇區大范圍發動農村婦女參加生產,1934年《關于春耕運動的決定》號召婦女參與蒔田、犁田與耕田。1939年,毛澤東號召邊區軍民“自己動手”,解決衣食住問題。1940年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關于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在根據地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在大生產運動中,中央領導人積極帶頭,主動參與到生產活動中。二是實施保障農民生產效率的措施。指導農民種植作物,其中人民糧食和工業原料各占一半;重視開墾荒地,發動、領導群眾進行開荒運動;新修水利,以減少水旱自然災害對農業收成的影響;建立互助合作社、勞動合作社,并通過組織社員、支付工資、精神鼓動等方式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建立耕牛社,本著群眾自愿原則,以匯集耕牛、出租耕牛的方式解決耕牛和農具缺少的問題。三是創辦信用合作社、國營商業和消費合作社,解決農民購買肥料、種子、農具時的資金困難問題。到1945年,陜甘寧邊區農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種三年莊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糧食[35]。
(二)1949—1978年:優先發展工業,先積累后消費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的消費思想主要是通過發展工業,達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這一時期的政策特點表現為優先發展工業與先積累后消費。
1.優先發展工業
優先發展工業的政策表現為兩方面:一是加強政府計劃管理,優先發展重工業;二是確立統購統銷制度,控制商品流通和銷售。1953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完整地闡述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即“一化三改”。社會主義改造是用計劃管理取代市場調節,將資源配置權放入政府手中,建立計劃經濟體制,保證政府在短時間內以高積累、緊運行優先發展重工業。1953年成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在全國范圍內對重要物資實行統一分配。1953—1957年,由國家計委直接分配的工業品占工業總產值的60%,種類高達300多種。政務院通過《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糧食統購統銷制度正式確立。此后,統購統銷的農產品種類不斷增加,包括糧、棉、油、烤煙、苧麻、茶葉、生豬、木材、水產品等。隨著國內外各方面條件成熟,“一五”計劃的制定出臺為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提供了指導,其主要內容包括:保證市場穩定;發展城鄉和內外物資交流,擴大商品流通;對供給少于需求的主要產品,在努力增產基礎上實施統購統銷。這一階段,以統購統銷為核心的物資管理制度保證了工業部門從農業部門獲取充足資源和剩余,控制重要商品的生產及流通,加速了工業化進程。
2.先積累后消費
為支持重工業的發展,消費政策表現為向積累傾斜。1953年,毛澤東在《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詳細解釋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由于工業化要以發展重工業為重點,而重工業需要的資金多,盈利較少、較遲,產品不能直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要,因而在工業化時期不得不進行艱苦奮斗。為了達成在短期內迅速建立起工業體系的任務,政策不斷向工業傾斜,將大量資源投向工業部門,由此造成的現象就是經濟建設成就主要來自工業,居民消費則跌入低谷。“一五”計劃時期,積累率只占24.2%,1958—1960年共積累1 438億元,積累率分別高達33.9%、43.9%、39.6%[4]。“大躍進”時期,只顧積累、忽視消費,只顧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只顧建設、忽視市場和人民生活,造成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嚴重失調,居民消費難以同步協調發展[36]。為改變畸形的消費積累比例,黨中央出臺了一系列調整政策。1961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確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隨后積累和消費的比例趨于協調。1965年全國每人平均糧食、食物、棉布消費量雖仍低于1957年水平,但開始逐步回升。
(三)1978—1992年:推動商品生產,擴容消費市場
改革開放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成為主要工作內容,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則是重要抓手。適應商品經濟發展,推動消費品生產和擴大消費市場,成為重要措施。
1.推動商品生產
1981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走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其核心是“千方百計地提高生產、建設、流通等各個領域的經濟效益”,圍繞此核心,提出十條方針,其中一條便是:把消費品工業的發展放到重要地位,進一步調整重工業的服務方向。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建設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通過發展商品經濟,搞活經濟,提升企業效率,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需要。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一新的經濟運行機制,極大地發展了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突破了“有限商品生產”的傳統觀念,有效推動了商品經濟發展與商品生產。
2.擴容消費市場
在體制改革政策指導下,消費市場發展逐步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集中統一管理,轉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下多種流通渠道、多種經濟成分和多種經營形式的市場發展格局。到1987年,國家指令性計劃和統一價范圍逐步縮小,農副產品市場和工業消費品市場基本形成,生產資料市場和短期資金市場有了一定發展。中央直接管理的工業產品從120多種減少到60多種,統配物資從180多種減少到22種。從各類商品的價格來看,農副產品、工業消費品和生產資料中已實行國家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的占比分別為65%、55%和40%,價值規律在銜接產需調節供求平衡方面的作用明顯加強[37]。通過以上舉措,居民消費方式從改革前國家統一計劃逐步轉變為由居民個人自理決策。
(四)1992—2012年:加強宏觀調控,實行多元消費政策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本在于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需要市場“無形之手”與政府“有形之手”相結合,進行宏觀調控,實施多元化的消費政策。
1.加強宏觀調控
這一階段,針對消費的宏觀調控多達3次,其中抑制消費需求的1次,拉動消費需求的2次[38]。1993年消費需求迅速擴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21.6%,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加大。199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通過16項措施來抑制過剩的投資與消費需求。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造成出口需求持續下滑、投資需求增長停滯,為堅持人民幣匯率不貶值,宏觀調控部門開啟刺激消費需求的政策,主要措施是降低利率與放寬貸款條件。2008年,外部需求急劇收縮,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央采取了強刺激政策。除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之外,還采用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培育和鞏固消費信貸增長點、拓展農村消費市場、實施家電和汽車摩托車下鄉補貼政策等措施。
2.多元消費政策
這一階段,消費的調控政策逐漸多樣化,產業政策、價格政策、收入政策、信貸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成為重要手段。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實行稅制改革,由此開始征收消費稅以抑制過度消費和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消費稅作為重要的調控手段,連續在國家“十五”計劃、“十一五”規劃中得到體現。其中,國家“十五”計劃提出健全稅收制度,完善消費稅;國家“十一五”規劃提出完善稅收制度,適當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合理調整部分應稅品目稅負水平和征繳辦法,適時開征燃油稅。之后多次調整消費稅,對消費進行調控。這一階段,在市場體制逐漸完善的基礎上,居民消費的相關政策由以前計劃的非市場化的行政調控逐漸轉變為以市場為主的間接的多樣化調控方式。
(五)2012年至今:完善體制機制,全面促進消費
面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中國共產黨提出要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在新的消費思想引領下,我國以破解制約消費擴大和升級的體制機制障礙為抓手,全面促進消費。
1.完善體制機制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建設”。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提出構建更成熟的消費細分市場,推動實物消費、服務消費和農村消費發展;建立完善質量標準和信用體系,健全評價制度與維權機制;強化政策配套以改善居民消費能力。建立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不僅要從市場環境著手,而且應改善消費主體收入狀況。2013年國務院批轉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消費質量提升離不開監管體系的支撐。2014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正式實施。2015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建立健全消費品質量安全監管、追溯、召回制度。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建設,能夠進一步保障居民消費的高質量發展,推動居民消費結構轉型升級。
2.全面促進消費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把“全面促進消費”作為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的關鍵措施。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發展“中高端消費”,以綠色消費、服務消費和信息消費為代表的新消費被重點關注。近年來,共制定與發布101項與推進居民綠色生活相關的政策,其中,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26項,主要為推進綠色消費的通知、意見和方案,占26%;各部委發布相關政策75項,主要為落實國家決策而開展的具體措施行動,占74%[39]。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提出,要以信息消費規模快速增長、信息基礎設施顯著改善、信息消費市場健康活躍為目標,加快促進信息消費,有效拉動需求,催生新的經濟增長點。服務消費涵蓋健康、醫療、養老、旅游、體育、文化等諸多方面,黨對服務消費的各重點領域提出政策規劃,積極推動各領域新業態新模式試點。
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居民消費:總結與啟示
一百年來,我國經濟建設穩步前進,居民消費穩步增長。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居民消費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現實邏輯,可以為促進居民消費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使命提供有益鏡鑒。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居民消費總結
1.伴隨經濟發展的自發式升級與自覺式消費調控相交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居民消費發展的歷史邏輯
一方面,隨著民族獨立與生產力發展,特別是國民經濟由規模初步擴大到高速度增長再到高質量發展,居民消費經歷了由低水平向高質量、由物質向精神、由實物向服務的轉變。另一方面,針對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不同特征,中國共產黨加強對國民經濟和居民消費的宏觀調控,不斷滿足人民需要,確保經濟穩中向好發展。回顧百年居民消費進程,消費與經濟的關系大體呈現從“脫離經濟發展”到“從屬經濟發展”,到“服務經濟發展”,再到“引領經濟發展”的演進歷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是領導民族解放而非發展經濟,對居民消費的認識并沒有從經濟發展維度著眼。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將發展重點聚焦到以重工業為主的生產方面,形成“重工業輕消費”與“先積累后消費”的消費思想,該階段居民消費從屬于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基本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同時擴大生產,居民消費服務于經濟發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充分認識到消費作為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的重要作用,政策制定開始以擴大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為重要落腳點,居民消費更深層次地服務于經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認為消費既是生產的最終目的和動力,又是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體現,為此提出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實現需求引領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互促進,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推動高質量發展,消費發展被置于引領經濟發展的地位。中國共產黨對消費的認識轉變,反映出居民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愈發重要,從根本上確保了經濟向著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方向發展。
2.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與時代發展命題相呼應,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居民消費的理論邏輯
馬克思主義消費理論的突出特點是并非就消費研究消費,而是把消費放在社會再生產大循環中,從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相互關系中來揭示消費的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消費思想變遷史,充溢著對生產與消費、積累與消費的辯證統一思考。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解釋消費問題,不僅能夠避免只從消費談消費的片面性,而且能將人民生產生活的各方面聯系起來;不僅具有深刻性和全面性,而且有很大的批判作用。改革開放后,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更加凸顯,結合實際,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消費思想,應用宏觀調控手段有效調節居民消費,并發揮出居民消費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進入新時代,又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支撐,全面引領消費高質量發展,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
3.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與消費現實問題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居民消費的現實邏輯
一方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積極領導農民運動,通過土地革命為農民解決生計問題;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發展生產,推動商品經濟發展滿足人民生活需要;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推動消費體制機制完善,全面促進消費,這些都是為了促進人民生活發展、推動人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另一方面,面對各階段的經濟特征與消費現實,中國共產黨因時制宜、因勢利導,抓住居民消費發展的主要矛盾,展現出勇于開拓的魄力。例如,在處理“積累與消費”關系上,呈現前后階段各有側重的特點。在社會主義初步探索期,為了加快提升生產力,建設獨立的工業體系,實施了重積累輕消費政策,消費讓步于重工業發展,居民消費增長疲軟。隨后,面對形勢變化,中國共產黨果斷調整政策,將發展居民消費、改善人民生活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初心秉持彰顯著中國共產黨百年的堅守與奮斗,勇敢開拓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前進之時所具有的領導力與決策力。
(二)新時代全面促進消費的啟示
1.堅持以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依據,推動居民消費持續穩定發展
縱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居民消費歷史,經濟發展始終圍繞解決社會主要矛盾而展開,社會主要矛盾反映了人民需求的變化與改善人民生活的癥結所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社會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只有解決了民族獨立問題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居民消費,因此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因此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搭建起工業體系是當時的主要任務,積累被放在首要位置,消費被暫時忽視。黨的八大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居民消費發展也圍繞此展開,積累與消費比例得到調整。改革開放后,社會主要矛盾逐步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發展生產力、發展商品經濟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工作重點。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進一步轉化,“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被提出,如何化解消費的不平衡不充分,實現高質量發展,成為工作重點。因此,任何時期都要注重國家穩定與居民生活、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之間的平衡,堅持以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依據,這是居民消費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
2.遵循生產與消費的辯證邏輯,推動居民消費動態平衡發展
回顧百年居民消費歷程,生產與消費始終緊密聯系,相互作用在不斷變化,始終是一對不可或缺的有機整體。新中國成立以前,生產力低下嚴重制約居民消費;新中國建立初期探索建立基本工業體系、優先發展重工業,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拉動了居民消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生產發展帶動居民消費快速增長;20世紀90年代,為應對宏觀經濟問題,消費對生產的作用開始顯現,促進消費擴大內需能夠更好推動生產力發展;進入新時代,生產與消費的關系進一步轉變,“美好生活”與“不平衡不充分”體現了消費需求的日益擴大與生產供給的結構調整。不僅如此,消費地位提高意味著不僅不能忽視生產的作用,而且要進一步強化生產與消費的有機聯系,新時代要更加注重生產與消費的協調發展,更需要全面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戰略相結合。一些涉及生產與消費的連接紐帶的領域,如現代流通體系的建設、互聯網、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則更是需要政策加碼的著力點。
3.秉承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使命,推動居民消費共享發展成果
以人民為中心,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堅持不懈的奮斗目標。回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居民消費發展,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耕者有其田”,到建立新中國后“改善人民生活”,到改革開放后“發展生產力,消除兩極分化”,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居民消費發展的主線。新時代居民消費高質量發展,更要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到2035年,要使“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居民消費已取得豐碩成果,人民生活從謀求生存到實現溫飽,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展望未來,除了繼續從“量”上向共同富裕穩步推進外,更重要的是實現“質”的飛躍,居民消費高質量發展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因此,在發展居民消費的同時,新發展階段更要堅持新發展理念,推動全體人民共享消費成果,兼顧效率與公平,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五、邁向共同富裕的居民消費
推動邁向共同富裕的居民消費發展,必須使居民消費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既要通過建立健全各項制度,完善社會政策消除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又要繼續推動經濟發展,做大蛋糕,實現“富裕”。具體來說,要從消除居民消費不平等、推進居民消費擴容、提高居民消費層次等方面著手。
(一)破除“共同”阻礙,推進居民消費均衡發展
實現共同富裕,要在現代化過程中逐步解決貧富差距,更加注重向農村、基層、欠發達地區傾斜,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中的“共同”意味著在下一步工作中要更加注重消除貧富差距,尤其是收入不平等與消費不平等。其中,消費不平等對于共同富裕來說更加重要,原因如下:首先,從微觀角度來講,消費是實現效用的直接途徑,居民消費與居民福利水平的聯系更為緊密。其次,消費包含了收入的信息,收入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消費不平等,因而消除不平等能夠更直接地刻畫“共同”二字的內涵。最后,收入構成比較復雜,收入不平等的統計和測算存在一定缺陷,而消費的含義則不存在偏差。推進消費均衡發展,需要從解決群體之間、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不平等著手,打出政策組合拳。具體而言,要從如下方面著手:一是通過完善社會分配等政策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二是通過建立國際、區域以及縣域消費中心等方式縮減區域消費差距;三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農村及中小城市消費發展,解決城鄉消費不均衡問題。
(二)增加“富裕”廣度,加速居民消費增量擴容
實現“共同富裕”,不僅要實現“共同”,消除不平等,而且要達到“富裕”,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需要進一步擴充居民消費的內涵。由于新的技術條件和經濟環境,居民消費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消費,其內容不斷豐富,范圍不斷擴延。回顧百年居民消費歷程,消費的命題在不斷轉變,內容在不斷豐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強調滿足基本生活;新中國成立初期,強調節省消費資源與實現生活溫飽;改革開放后,強調豐富消費品種類,解決消費品供給不足;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之后,更加強調擴大消費對生產和宏觀經濟的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隨著居民消費內涵的拓展,以及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要求,須全面強化促進消費的一系列舉措,具體包括:一是大力推動新型消費發展,加快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文旅消費、康養消費的發展,更全面滿足各類消費群體的需求;二是加強消費供應,增加產品和服務種類,推動消費品牌創建,豐富消費者的物質文化選擇;三是創新消費模式,豐富消費業態,以適應新興消費群體與消費文化。
(三)提升“富裕”深度,著力居民消費提質增效
在滿足人民多樣化需求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消費質量,使民生需求得到更高層次與更優質的滿足。從居民消費的演進歷程可以發現,以食品衣著為主的生存型消費占比逐漸減小,以旅游休閑和文化娛樂為主的享樂型消費逐漸增多,消費升級趨勢愈加明顯。這也表現在相似品類的商品上,民眾更追求質量而非數量。消費發展的提質增效,關乎民眾高層次需求的滿足,關乎民眾生活品質的提高。增強消費發展的質量與效益,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解決消費與生產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推動消費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具體措施包括:一是繼續破除市場壁壘,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推動市場競爭公平有序,促進技術、管理、組織創新,提高供給水平,為消費提質增效發展提供物質基礎。二是通過供給創新更好滿足和創造更高水平的消費需求,以新的消費熱點引領消費升級,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提高供給與需求匹配度,不斷滿足人民變化的產品需求。三是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提高更好、更優、更合意的產品和服務,充分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求。四是加速消費轉型,加強消費品質量監管,維護消費安全,倡導綠色理念,推動綠色消費發展。 [Reform]
參考文獻
[1]李占才.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2]魏宏運.中國現代史稿(下冊)[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3]中央農業部計劃司.兩年來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匯編[M].上海:中華書局,1952.
[4]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
[5]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統計司.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
[6]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
[7]董輔礽.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卷[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8]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卷[M].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0.
[9]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卷[M].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0.
[10]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
[1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3[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
[12]國家統計局.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20[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0.
[13]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20[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0.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15]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6]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5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
[19]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魏鵬娟.延安時期新民主主義經濟實踐與理論創新的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10.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9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6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
[24]尹世杰.略論毛澤東的消費思想[J].湖南社會科學,2009(6):99-103.
[25]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26]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7]陳云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9]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0]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1]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5-10(002).
[32]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8-11-02(002).
[33]習近平.把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 推動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方向發展[J].人民日報,2017-01-23(001).
[34]黃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習近平李克強作重要講話[N].人民日報,2016-12-17(001).
[3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
[36]孫豪,毛中根,桂河清.中國居民消費不平等:審視與應對[J].現代經濟探討,2019(4):8-14.
[37]高尚全.強國之路[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1:676-704.
[38]王一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演進與創新[J].管理世界,2018(3):1-10.
[39]國合會“綠色轉型與可持續社會治理專題政策研究”課題組.綠色消費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J].中國環境管理,2020(1):24-30.
The 100-year Development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Process Review, Thought Transformation and Livelihood Practices
MAO Zhong-gen? JIA Yu-yun? YE Xu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100-year residents' consump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found that,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is the fusion of spontaneous upgrad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s macroeconomic control. And the theoretical logic works in concert with both Marxist methodology and specific proposition of times. And the realistic logic is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centered value orientation and consumption reality. This provide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The first is constantly working on 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society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The second is to follow the dialectical rule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o promote the dynamic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The third is to uphol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to promote the sharing of development gains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in socialism and common prosperity, its main focus is: firstly, to break the "common" obstacles by promoting parity consumption. Secondly,? to increase the breadth of "prosperity" by accelerating the expansion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Finally,? to enhance the depth of "prosperity"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Key words: centennial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sidents' consumption; common prospe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