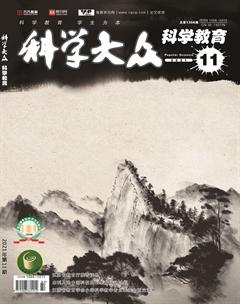美國災難影片中的生態危機書寫
張可菲 袁家麗
摘 要:隨著全球環境危機的加劇,人們對環境的關注和保護意識逐漸增強。電影首當其沖地成為呈現和討論全球生態危機的媒介,尤其是近幾年,國內外電影市場上災難影片不斷拍攝、上映,更突顯了全球的關注熱點和前沿問題。作為2017年中國電影市場唯一引進的美國生態災難片,《全球風暴》上映之初就引發眾議。本文通過分析該影片所展現的生態危機、探究其成因、挖掘影片中的人性光輝,并總結其中的生態啟示,為當代人們思考、應對生態危機提供借鑒。
關鍵詞:災難電影; 生態危機書寫; 英雄主義精神
中圖分類號:B83-06?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6-3315(2021)11-145-002
1.引言
電影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寄托了人們對現實的思考。近年來全球變暖等生態問題日益嚴重,因此生態災難成為許多影片聚焦的主題,人類運用多種視角審視目前的生態狀況。此類保護自然的電影主題反映了人類所面臨的生態危機及人類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和憂思。通過電影敘事手法,人們正在為如今的生態困境積極尋找出路。
《全球風暴》作為生態災難電影,較為全面地討論了“人——科技——自然”之間的關系,成為此類電影的典型之作。它不僅涉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還探討了人類使用科技對待自然的正確態度。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該片中機器與自然抗衡而引發全球性災難的事例也許即將成為現實,故事內核具有前瞻性和警示性。此外,該片中不乏對人性光輝的刻畫,在揭露生態危機的同時,對未來生態發展的希望和方向提出設想,傳達對生態的現實關懷。
2.生態危機的成因:二元思維的禁錮
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將二元論闡釋為:二元對立的兩者之間差異明顯,一方具有優勢,另一方成為“他者”。前者具有主動性,可以隨時為自己的權利發聲,而后者恰恰相反,處于被壓迫和被索取的地位。影片中災禍的始作俑者受到二元思維的影響,制造出可以控制天氣的“荷蘭男孩”(一個精密的人造衛星網絡),甚至企圖更改程序,將氣候變化視為政治博弈的籌碼。他們奉行工具理性態度,將人與自然割裂開來,認為人類高高在上,可以借助科技手段操縱天氣,馴服生態自然。由此產生機械主義自然觀,忽略自然是一個有機體,把自然當作運轉的機器,淪為實現人類欲望的工具。縱觀歷史長河,這樣的情節是當今世界發展的一個縮影,比如亞馬遜雨林的農民們為了農業種植,大量砍伐和焚燒樹木。在他們眼中,雨林的土地是收益的工具,而不屬于生活環境的一部分,因此可以隨意改變自然的運作方式,但最終是以森林面積減少、二氧化碳增加及全球變暖為代價。
人與自然形成對立面的二元思維還導致了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起源于古希臘,認為人類是世界的中心,是萬物存在的尺度。該影片中災難根源即為人類中心主義。幕后黑手為了掌握更多權利,不愿交出“荷蘭男孩”的控制權,于是實施“宙斯計劃”:他們利用病毒操縱衛星系統,借此指揮氣候衛星網,在特定的地方造成自然災害,成千上萬人因此喪生。人類干預自然“等同于飲鴆止渴”,原本是自然的“守護者”,卻最終成為“毀滅者”。而“宙斯計劃”表面上將隨意破壞自然的人類比作宇宙的中心,即“上帝”,但其中暗含“天神之怒”的隱喻,人類因罪過太多,觸怒宙斯(即自然),導致宙斯怒降洪水。“宙斯計劃”一詞,暗示了電影中人們不斷向生態進軍的做法是在自取滅亡。二元思維催生了機械主義自然觀和人類中心主義,在如何與自然相處的問題上,被禁錮了觀念的人們無法獲取終極自由。
3.危機中的人性光輝:英雄主義精神的塑造
《全球風暴》刻畫了許多持二元論觀點的反面人物,但也強調仍有少部分人在環境問題上能保持清醒意識。這些少數正面人物組成主角團,并在領導者的指揮下化解這場危機,體現領導者的個人英雄主義情懷。個人英雄主義反映對個人價值認知的探索,以及個體為群體利益犧牲自我的意識。主角杰克·羅森原本已經被政府解雇,卻還是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選擇一個人留在即將毀滅的太空站,堅守到最后一刻重啟系統。主角團中的兄弟二人原本就是政界和科技領域的精英,在全球生態崩潰的緊急關頭,他們也走在拯救世界的最前線,成為世界人民的“超級英雄”。這種個體呈現豐富了角色的形象,強調通過自我努力取得成功,單槍匹馬地完成任務,滿足了個體對實現英雄夢的憧憬。
但與大部分只凸顯個人英雄氣概的好萊塢大片不同,影片中的集體英雄主義精神以全人類的命運為基石,超越了只局限于個人、社會和國家的生態意識,上升到普世價值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荷蘭男孩”失控,香港被火海吞噬,奧蘭多遭遇閃電暴擊,迪拜爆發海嘯……生態災難不僅在局部地區爆發,而且在全球范圍肆虐,在宏大的災難面前,個人的力量渺小到不堪一擊,因此在主角團尋找解決辦法的同時,還有無數人齊心協力,為這場災難減少損失。在街頭巷尾,有幫助弱勢群體躲過地面塌陷的便利店員工們,也有不顧危險正面闖入火海的消防隊員,電影展示了人物群像的互相幫助和犧牲,每個小人物的力量匯集在一起,迸發出磅礴的集體英雄主義精神,使人震撼。面對全人類的生態危機,多國技術人員夜以繼日地在空間站工作,他們拋棄了以自己國家為中心的思維定勢。影片最后,當主角在浩瀚無際的宇宙中發出求救信號時,一名墨西哥技術人員立即駕駛太空梭前來搭救。此時,國與國的界限被打破,他們齊心協力共同作戰,注重團隊意識和大局意識,表現出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
4.生態危機啟示:大地共同體的倫理責任
《全球風暴》中的一些情節傳達了關于人類該如何應對生態問題的思考,比如空間站不再只張貼美國國旗,而是貼上了建造太空站的所有17個國家國旗。世界各國成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更開放、包容和積極參與的心態對待生態環境問題。接著該片從全球史觀的角度出發,描述了某國持實利主義的高層人員破壞生態環境,使全球遭到自然危機,因此要維護生態的良性運營,需要人類共同努力。同時,除了全人類是一個整體之外,人類和生態系統也是一個密不可分的“共同體”,即“大地共同體”。“大地共同體”由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首次提出,是生態整體主義的代表理論之一,“大地”是指自然生態系統,“大地”是有生命的整體性存在,“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者把它們概括起來:大地”,“共同體”則表明人類也屬于其系統之內[1]。其核心要義是:“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2]”該影片運用大量特寫鏡頭呈現生態災難的恐怖性和破壞性,凝視人類受到的嚴重威脅,而這些災難大部分是由于人類對自然認知的局限性所導致。人與生態系統組成生態整體利益,因此人類的道德關懷需要擴大到整個自然界,對他者產生強烈的同情心理。
“大地共同體”所闡釋的大地倫理在擴大整體范圍的同時,倡導人與自然有機統一的生態倫理觀。利奧波德的“大地共同體”賦予了大地新的隱喻意義:生態系統中的各個組成部分是地球的器官,每一個部分都有特定的功能,將功能相互整合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維持生態系統的順利運行。電影中破壞太空站程序的高層卻認為,人類和科技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然而現實中,人類無法全知全能,科技也不是毫無破綻。如果通過超出自然所能承受的技術手段維持生態秩序,終究會有機器失靈,走向失控的那一天。此外,太空站技術人員鄧肯被描繪成反面人物,受到重金誘惑而泄露信息,造成“荷蘭男孩”被病毒攻擊,系統崩潰。他認為災難來臨時,可以放棄地球,開辟新的家園,但他忽略了人與周圍環境的整體性。人類自我意識過剩是造成主客二元對立的原因之一。以電影中的鄧肯為代表,在他的價值衡量天平上,個人利益超過一切,因此才會被重金收買而不顧全人類的安危。如果人類的衡量尺度只局限在個人上,那么需要從全局考慮的生態問題永遠無法得到解決。要做到人與自然的有機統一,根據阿蘭·奈斯的深層生態學觀點,人類需要建立對自然的最大化認同。首先,要擴大自我認同的范圍,即對他人和對自然物的認同,由此會產生一種“利他主義”。其次,要承認生態系統的多樣性,以包容和共生為前提條件,“為其他生命受到最小的壓制創造條件[3]”。
在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的同時,還要避免陷入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極端。從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標準出發,自然系統中的任何部分都被看作完全平等的地位,人類不再是自然的主體和行為實施者,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人類履行保護生態系統的義務就會與其形成悖論。此外,當人與生態系統中的其他組成部分處于完全平等時,由于事物之間存在有意識與無意識之分,生態中明顯的差異性會被忽略。但目前為止,由于人類的意識和干預能力,生態系統遭到人類破壞,也需要人類進行維護。在大地共同體“完整、穩定和美麗”的三大原則中,可以規避非人類中心主義的邏輯悖論[1]。同時,奈斯的深層生態學也屬于整體觀念,在解決生態危機時,它宏觀地看待問題,將生態與人類社會聯系起來,從整體上深層次地徹底地解決問題[4]。當形成一個整體時,人類由統治角色轉變成生態系統中普通的一員,因為道德范圍的擴大,人類也是生態道德的承擔者,行為需要以生態整體利益為價值尺度。同時,人類也可以享受個體利益,在不破壞三大原則的情況下,合理利用地球資源,達到和諧共生的效果。所以,人類在認可生態利益重要性和尊重整體的其他部分的同時,也要發揮作用,承擔倫理責任,以避免惡性循環的惡果。
5.結語
《全球風暴》披露了二元論所導致的嚴重后果,用恐怖的災難畫面警示人類社會要摒棄機械唯物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生態災難面前,人類不僅要保有“以小我成全大我”和“團結一心”的英雄主義精神力量,也需要秉持“大地共同體”的三大原則,不走向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極端。正如電影結尾的小女孩所說:“同呼吸,共命運,我們有責任一起保護這個地球。”人類作為地球的一部分,要與生態自然有機統一,為“大地共同體”的發展創造可持續的生態環境,這是人類所共同面臨的重大問題。美國災難影片中的生態危機書寫為人類的共同問題敲響了警鐘。
基金項目:本文為南京林業大學大學生創新項目“中美影視文學作品中的英雄主義思想對比研究”(2020NFUSPITP0852)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利奧波德.沙鄉年鑒[M]侯文蕙, 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2]Callicott, J.B. “Introduction”[A]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Ecology [C] Eds. by Michael E. Zimmerman, et al. New Jersey:Prentice-Hall, 1993
[3]ArneNaess, “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M],in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Shambhala, 1995
[4]雷毅.阿倫·奈斯的深層生態學思想[J]世界哲學,2010(4):20-29
作者簡介:張可菲,1999年生,女,江蘇蘇州人,南京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學生。袁家麗,1979年生,女,江蘇南京人,南京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