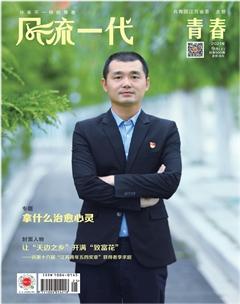為心靈找到一根“棲止木”
鄭晶心



“棲止木”是飛鳥暫時歇息的樹枝,為心靈找到一根棲止木,讓它累了、倦了時,有所停留,有所依靠。
自助:畫出那個躲在心里的小人
“別害怕,話說錯了,很快消散一空;別害怕,燈熄滅了,還有月色明朗。”
這是旅行繪本作家蟲蟲在她2021年5月出版的新作《我心里有個小小人》扉頁上的話。
蟲蟲曾出版過《跟我去香港》《跟我去澳門》等暢銷書,《我心里有個小小人》是一本風格獨特的書,樊登在他的直播室里將此書列為“人生必讀書”,推薦給了萬千讀者。很多心理咨詢師也將這本書推薦給來訪者。
對于蟲蟲來說,這本書是她“以繪畫釋放抑郁”的一趟艱難的心靈旅程。她第一次接受精神分析時,對咨詢師說的最多的是害怕,“害怕世界上的一切。害怕被不喜歡、被指責、被懷疑、被誤解;害怕突然暈倒在人群中;害怕病了、死了,一切沒有了……”
差不多有十年時間,蟲蟲都感覺身體有一種時隱時現的疼痛,多次去醫院檢查,都沒有結果。一位慈祥的內科專家告訴她,她身上沒有任何器質性病變,她的“痛”可能是“抑郁癥”,或者是“抑郁傾向”。蟲蟲卻不大相信:“我只是身體痛啊,我平日里活潑又開朗,哪里抑郁了?”但她的狀態卻越來越嚴重,2012年、2013年這兩年,她發現自己不會畫畫了。2014年5月的某一周內,她連續兩次在辦公室里無故暈倒。去醫院檢查,依舊無果。
2015年2月,她接受朋友的建議,下定決心接受長程精神分析,既有點死馬當活馬醫的味道,也抱著“系統治療”的期望。
第一次做完精神分析,蟲蟲的眼前就出現了一幅畫面,畫面中有一個黑黑的小人,面臨壓力重重,四周封閉,好像被包圍起來了。蟲蟲直覺這個小人就是她自己,她遲疑著,將它草草地勾勒了下來。有了第一次,又有第二次,從咨詢師那里結束咨詢,她的腦海里又蹦出一幅畫面……
有一段時間,蟲蟲和咨詢師討論一個極大的困擾,后來她發現,這個階段她畫的三張畫,竟然完整地展現了這個過程。第一張,小人封閉、無助,有巨大的憤怒;第二張,雖然處境艱難,但是有了一個突破口,蟲蟲畫了一頭大象作為命運之神,雖然生活中看不到它,但它護佑著小人;第三張,畫面歌舞升平,小人已經重見天日。
這里面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別人不知道,只有蟲蟲自己知道。一個創傷的發生、發展和處理,在畫中呈現得清清楚楚,沒有任何隱私被暴露,卻準確無比。
最初,蟲蟲習慣在每次精神分析結束之后,閉上眼睛,去獲得那幅畫面。后來,只要有一支小毛筆和一個小本子,她在等餐、候車時,在飛機或者高鐵上,隨時隨地都可以畫。
就這樣,四年多,50多個本子,400多張畫,每張畫都記錄了蟲蟲當時的狀態。虛弱連結著勇氣,茫然翻過去就是堅定,悲傷之后是長久的平靜……畫著畫著,蟲蟲一點點走向了健康和快樂。
蟲蟲本來沒想要出版這些畫作,后來決定出版,是想要告訴任何一個可能需要的人,也許可以像她一樣,提起筆來,哪怕亂涂亂畫,都可以獲得那一點點光亮。
蟲蟲在“以繪畫釋放抑郁”外,還自主閱讀了大量心理學書籍,聽線上和線下各種心理學課程。閱讀,正是心理自助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各類體育運動、公益活動等,都可以幫助調節身心狀態,緩解低落情緒。蟲蟲每天早晨堅持快走一小時,慢慢地,她的小腿長出了肌肉,她也忘了身體的疼痛。《跑步拯救了我的生活》一書講述的便是一位焦慮與抑郁患者通過跑步自愈的故事。
畫畫、閱讀、寫作、跑步……身處心理困境中的人們,都可以試著去尋找類似的可以傾訴和釋放的方式,從而拯救自己。
互助:組隊“打怪”,事半功倍
“如果我選了大城市的奮斗生活,可能會被摔打、被教育,過得辛苦又痛苦。但是,如果不經歷這些,我就說不出‘晚安,北京,也無法心甘情愿地說出‘平凡真好。只有去經歷了,我才有資格說出,其實我想要安穩的小日子……”網友“橫杠”畢業于一所“985”高校,臨近畢業,想進一線城市的私企奮斗,又覺得一線城市的房價以及生活成本難以承受。進入體制內單位,穩定,但又意味著很難挪動。
“橫杠”稱自己是個“糾結怪”,選擇哪一個,都不是容易的決定,在豆瓣上建“‘985廢物自救小組”的目的就在于“自救”。“在經歷磨礪之后,發現自己終究不過是個普通人。就算用盡力氣走進“985”“211”大學,卻最后成了名校廢物。但是,仍然還有一點微茫的不甘,還有當初的那點驕傲,絕不放棄自己,依然昂揚向上!”“橫杠”這樣寫給小組成員,“希望你從這個小組里可以收獲更多的力量,道阻且長,行則將至。我們都值得愛與被愛,都值得光明的前途或想要的人生。”
目前有1731人聚集于這個小組,組內參與度至今很高,陸續有人發帖傾訴。今年暑假有同學說自己從十八線小縣城考進了“985”高校,新生群里聊天都聽不懂,充滿了自卑,心理壓力很大,都不敢去上學了。帖子發出后,不斷有網友回復,講述自己來自十八線小縣城考上名校后初入學的心路歷程,“橫杠”也給發帖的同學打氣,并特別叮囑:“如果對大學生活適應有什么問題,可以在組里問,也可以私戳我們,能幫上忙的,我會盡力的。”
豆瓣上關于心理自助的小組有很多,大多數小組都給自己做了詳細的分類,“拋棄不良情緒小組”“害怕沖突型人格互助小組”“拖延癥患者互助會”等。這些小組的名字看上去有些喪,但創建宣言里都是滿滿的積極力量。
“我不要每次上豆瓣都看見自己在一個自卑自暴自棄焦慮壞脾氣的小組里。我要你們和我一樣看見的都是陽光健康的東西。現在這個組接受的都是想要好好生活、尋求如何好好生活的好孩子!愛笑的人運氣不會太壞,大家加油吧!” 這是“拋棄不良情緒互助小組”組長“下水道四號居民”說的。
“害怕沖突,害怕不愉快的場面,為了避免沖突,總是以友好的態度對待一切。但這并不能代表你的所有,這只是你最習慣的狀態。不夠獨立不是你的無能,而是你尚未知道如何獨立。也許你在了解自己這件事上遇到了困難,但不用怕。比起了解自己,生命的動力是創造。在這里,請大家分享自己的摸索經驗,共同探索路上的阻礙和成功的心得。”這是“害怕沖突型人格互助小組”組長“滿天星”寫下的。
網友“格子控”說起自己加入豆瓣心理互助小組的體會,就是不需要為自己有某種想法或存在某種問題而感到羞恥。“小組內的小伙伴懂我,不會嘲笑我,我們通過別人看到了自己,療愈了自己。”
個人的力量雖小,但群體的力量是巨大的。心理互助小組成立的初衷,是為了在非心理治療的環境中進行自發、自愿的互助,增加社會支持力量,因此大部分時候是沒有心理專家組織與領導的。
在2020年、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除了依靠12355這樣的心理熱線援助,民間自發形成了很多的心理互助小組。比如在人們各自同學、同事、親朋好友等的微信群里,無意中組成了一個個“情緒互助小組”,通過相互傾訴、樂觀調侃等方式,排解因疫情出現的信息焦慮、隔離恐慌等負面情緒。
國際心態療愈的核心理念便是以結成同伴互助支持小組的方式來踐行心態療愈。國際心態療愈專家Trish說:“要相信普通人之間擁有彼此支持的卓越能力。”
他助:認真捕捉每一個求助的信號
傳說古時候,心里藏著秘密又希望傾訴的人,跑到森林里找一個樹洞對其傾訴秘密。在當代,人們常在網絡社交媒體上傾訴自己的想法,社交媒體可以說是現代化的“樹洞”。但這樣的“樹洞”里,隱藏著大量的抑郁人群,是自殺的高危群體。
2018年3月的一天,一直研究人工智能的華人科學家黃智生在網上讀到了一篇關于網絡“樹洞”的報道。“樹洞”里盛滿了大量抑郁人群的心聲,很多人掙扎在深淵中。黃智生萌生了一個想法,那就是利用AI技術發現社會上需要精神幫助的人群,包括抑郁輕生群體等,黃智生將它命名為“樹洞救援行動”。4月12日,他在平時工作交流的“醫學人工智能群”里發了條相關的消息。黃智生的號召很快得到這些專業的醫學AI從業者的響應,他們成立“樹洞救援團”,開始研發“樹洞”監控智能機器人。
“樹洞”監控智能機器人上線后,可以自動監控分析輕生者自殺傾向等級,并對高危情形采取相應的措施實施干預。
黃智生給成員們發放了網絡救援行動指南,目前已經迭代到了第14個版本。現在每救一個人,就成立一個救援小組或者關愛小組,里面有兩位精神健康方面的專家或醫生,和三位普通的救援志愿人員。
2019年2月18日晚上,南京某高校的學生呂小康(化名)獨自一人在出租屋,因患重度抑郁癥,極度焦慮下抽了一根煙后,服下大量安眠藥,他在微信上給自己的家人留了言,并在微博上發了“再見”兩個字……
晚上7點8分,南京警方突然接到“神秘人”報警,稱一名微博網友,實名呂小康,在住處自殺了,他是南京某大學的學生,但不知道所在地址,希望民警趕快搜救。
警方通過警務平臺查詢到,呂小康最近在某房屋租賃APP上租了一間合租房,房屋位于邁皋橋某小區。出租屋大門緊閉,敲門無人應答。民警馬上請鎖匠現場技術開鎖,救下了生命垂危的呂小康。
那個及時的報警電話就是“樹洞救援團”的志愿者、南京中醫藥大學醫學信息工程教研室老師龔慶悅打的。此前人工智能“樹洞機器人004號”發出監控通報,目標對象就是呂小康。2月15日,“樹洞救援團”發現他不斷想自殺,于是成立了呂小康救援小組,其中有呂小康的親屬(小姨)、老師,兩位心理咨詢師和幾位志愿者。團隊老師以網友身份發私信和他聊天,一方面為了開導他,一方面為了獲取他的個人信息以備不時之需。
2月18日那天晚上,呂小康給團隊里一位他最信任的老師發了一條信息,說要“再見”了。看到信息后,團隊立刻組織了救援小組,并在團隊的工作群里發布信息,分頭聯系警方和家屬。
“樹洞救援團”目前的成員分布全國各地。機器人每天發布監控報告后,隊員們都傾向于對距離自己更近的人實施救援。根據機器人的統計數據,“樹洞”最活躍的時間是晚上10點到凌晨2點,而自殺者也一般都會選擇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實施自殺行為。因此,在救援行動中熬夜也是無可避免。有一次,一位姑娘第二天要實施跳河,時間太緊迫,不將她救下來的話,救援小組成員們實在沒法睡覺。萬幸在警方的配合下,在凌晨兩點多找到了她,挽救了生命。
從2018年7月底到2021年6月底,“樹洞救援團”已經對有高自殺風險的14617人次提供了幫助,阻止了4765次自殺。四年的積累,“樹洞救援團”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的出發點是利用 AI 技術阻止自殺,但現在很多人對我們的期待,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黃智生說,今年,“樹洞救援團”發起了一項海外留學生心理危機干預培訓,“疫情導致留學生心理壓力很大,大使館的人也很重視這件事,便找到了我們。”
對于每一個求助的信號,“樹洞救援團”都萬分珍視。對此,國際正念減壓師(MBSR)南林君深有同感,對于心理干預、心理治療的從業者來說,要萬分嚴肅、認真地對待每一個咨詢電話、每一條信息,這些都是求助者釋放的求救信號。及時捕捉這些信號,給予恰當處理,便是一次極好的療愈,有時候甚至足以拯救生命。
咨詢師說:珍惜你最珍貴的資源——行動力
“南老師,我現在坐在學校宿舍的窗臺上跟你說話,我什么辦法都沒有了……”
一接通大學生安妮的電話,聽說她坐在窗臺上,南林君知道必須要嚴肅對待,但同時心中也有幾分信心:她既已打來電話,就不大可能會產生最壞后果了。
南林君是國際正念減壓師(MBSR)、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有著數十年豐富的心理干預、心理治療經驗。她知道,心理干預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來訪者邁出第一步——承認現狀,尋求幫助。這一步,無論一個心理干預專家、心理學家多么牛,都無法替來訪者邁出。
隨著安妮斷斷續續地講述,南林君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安妮從小乖巧可愛,成績也好,備受父母器重,但安妮覺得越來越難以承受由父母的期望帶來的壓力。如今已上大學,父親一件事不滿意,還是大道理講個不停,安妮無數次想爆發,都用理智克制了下去。直到這一次過年親戚們團聚,父親又在餐桌上沒完沒了地說教,安妮一時激動,抬手就把一大杯可樂潑到了父親的臉上。這下不僅氣壞了父母,連親戚們都來批評安妮“太不孝了”。安妮度過艱難的一晚,第二天就從家跑回了學校,一個人住在空蕩蕩的宿舍里。
聽完安妮的講述,南林君問:“你說你現在坐在窗臺上?”
安妮說:“是的。”
南林君問:“能告訴我你現在身體有什么感覺嗎?”
安妮愣了一下,回答:“不知道。”
南林君說:“你感覺一下呢?”
過了一會兒,安妮說:“我感到手發麻,大腿的肌肉僵硬,心跳很快,感覺喘不過氣來。”
南林君說:“好的,能不能和我一起做一個呼吸?”
安妮又愣了一下:“呼吸?”
“是的,來,我們一起給身體一個呼吸。你能感覺到身體隨著呼吸在起伏嗎?呼吸是慢的,還是很快的?沒關系,我們再來幾次,用你自己的節奏就行。”
后來安妮才知道,南老師教給她的是正念減壓療法(MBSR)的一個重要方法——呼吸覺察。通過對呼吸的覺察練習,感受身體活動,平復情緒,減少焦慮,從而減輕壓力。正是通過這次小小的練習,安妮從窗臺上走了下來。
安妮此后跟著南林君正式學習正念減壓練習。
開始呼吸覺察練習時,安妮才發現,自己的頭腦里竟然有那么多念頭,跟跑馬燈似的,千變萬化、川流不息,但她總算堅持下來了,漸漸可以安坐著呼吸,從一分鐘到三分鐘、五分鐘了。
改變在不經意間發生了。當安妮再次面對父親連篇累牘的說教時,她不僅可以保持平靜,還從中看出了父親的恐懼,他有多希望她好,就有多害怕她不好。他承受不住這害怕,就用批評、指責女兒來轉移壓力。看到了,就有了一份體諒,安妮和父母的關系在慢慢改善中。
南林君是在一次大學校園開展講座時認識安妮的。在校園講座中,常有學生問南林君,到底什么情況下,才可以去找心理咨詢師?南林君總是這樣答:“任何情況都可以,只要你覺得有需要。學業困惑、人際交往壓力、對未來的恐懼,哪怕和同學吵了一架,覺得自己沒吵好,都可以找心理咨詢師聊一聊。”把痛苦說出來,就是療愈的開始。時代在改變,我們要認識到,向心理咨詢師求助,是一件跟我們牙疼了去看醫生同樣性質的事情,只是心理咨詢師“望聞問切”的是心靈。
“不要絕望,不要認為我們一無所有了,你還有最珍貴的資源——行動力。”南林君說。
“我要是中學時代就認識你,也許就不用煩惱這么久了。”安妮笑說。
“你會越來越好的,”南林君對安妮說,“因為你擁有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