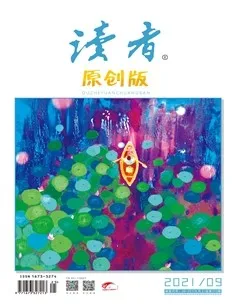唱支山歌給黨聽
楊晶宇 李延龍 周偉妮 岳青
有些歌詞,看到了就會下意識地唱出來,而且腦海中余音繚繞,久久不能散去。
6月初,我和4位同事從蘭州出發前往慶陽采訪。途中,同事龍總循環播放著《繡金匾》《軍民大生產》和《咱們的領袖毛澤東》3首出自甘肅慶陽的紅色歌曲,他為了采訪找靈感,認真跟著哼唱,我們其他人則各忙各的。晚上,我躺在酒店的床上,“萬丈高樓平地起,盤龍臥虎高山頂”的旋律在腦海里揮之不去,剛剛放空自己打算入睡,同屋的記者小周不自覺地哼唱:“一繡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氣……”我腦子里頓時響起“解放區呀么嗬咳,大生產呀么嗬咳……”果然是歷久彌新的紅歌,感染力依舊旺盛。
我一直以為傳唱度極高的紅歌《繡金匾》《咱們的領袖毛澤東》以及《軍民大生產》都是陜北民歌,畢竟演唱者阿寶穿著羊皮襖、頭上扎著羊肚子手巾的陜北放羊娃形象太深入人心。實際上,這3首歌曲都來自甘肅慶陽—甘肅唯一的革命老區。
從蘭州出發前往慶陽采訪,單位配備了性能最好的越野車和經驗最豐富的司機,預示著這趟行程路不好走。果然,駛過了漫長的高速公路之后進入省道、鄉道,車上就沒有人睡覺了,一個又一個的急轉彎讓從沒暈過車的我有點不適。從車窗向外看,車正在山頂行進,剛剛走過的盤山路蜿蜒崎嶇,像一條黑龍盤臥在山間。此時,我腦海中又一次響起了熟悉的旋律:“盤龍臥虎高山頂……”
當天的采訪對象就是這首《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的詞作者孫萬福的曾孫孫治慧。采訪車在翻過了兩個山頭之后,拐進了“萬福水廠”,如今的孫治慧在慶陽環縣經營著一家純凈水廠 。他選擇用自己太爺爺的名字給水廠命名,為了提升知名度—孫萬福的故事,在當地廣為流傳。
據慶陽市環縣黨史辦主任賈杰介紹,孫萬福的一生跨越新舊兩個社會。1883年出生的他從小給地主打工,幾乎沒吃過飽飯。1929年隴東大旱,再加上舊社會的苛捐雜稅,孫萬福典當了所有家產才得以過活。直到1936年,紅軍解放了環縣曲子鎮,孫萬福分到了土地,才過上半生從未感受過的溫飽日子。在后續的大生產運動中,孫萬福兩年耕地百余畝,1943年被評為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大會的勞動英雄代表,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接見。這首《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的歌詞,就是孫萬福被接見的時候有感而發,即興朗誦的詞。
如今看來,孫萬福的這次即興創作,是和孫萬福有著相同經歷的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心聲。
孫萬福的曾孫孫治慧沒見過自己的太爺爺,但是關于太爺爺的故事,他聽家里的老人說了無數回。如今,他也給自己的孩子講這些故事。現在的孩子對于舊社會的生活無法想象,但《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的旋律響起來,孩子們就會和孫治慧一起哼唱,熱情而堅定。
那個年代,生活在鄉村中的農民雖然目不識丁,但是表達起感情來真摯誠懇、直抒胸臆,《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是這樣,《繡金匾》也是這樣。
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中特區紀念館館長張志英介紹,和孫萬福的生活經歷類似,《繡金匾》的詞作者汪庭有也經歷過遭災、變賣家產,甚至還從陜西逃荒到了陜甘寧邊區慶陽正寧縣,在這里,汪庭有成了一名木匠。慢慢地,他從漂泊無依到用一技之長養活自己,不再受凍挨餓,不再遭受欺凌,翻天覆地的變化讓他萌生了編一首歌頌毛主席、八路軍的歌曲的想法。
正寧當地的民歌《繡荷包》旋律動聽,但是《繡荷包》體現的是兒女私情,在這首歌曲的基礎上,汪庭有將其改編成《十繡金匾》。目不識丁的汪庭有一邊改編一邊唱給村子里的孩子們聽,口口相傳,《繡金匾》的最初版本《十繡金匾》成型。歌詞里,除了歌頌毛主席、八路軍,也展現了當時陜甘寧邊區“老百姓,抗戰最熱情”“全家人都和氣,民主好商量”等邊區人民生活的真實風貌。
當地退休干部劉向陽是一位文藝愛好者,《繡金匾》這么高的曲調對他來說唱起來一點兒都不難。一曲唱完,他感慨自己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1952年出生的他,小時候聽老人講,過去的日子過得難,災荒年吃不飽飯,年景好了稍有點兒錢,就招來禍事被土匪盯上。如今,國泰民安,才是真正的好日子。說到激動的時候,他還握住我們的手,反復叮囑:“年輕人啊,不要不知足,要懂得感恩……”我想,當年汪庭有創作《繡金匾》時的心情也是如此吧。
傳唱紅歌也是傳承紅色精神。在慶陽華池縣軍民大生產紀念館見到甘肅省紅色歌謠傳承人李文軍老師的時候,他一身演出時的裝扮—上身羊皮坎肩,腰里系著紅色腰帶,頭上扎著羊肚子手巾,唱起《軍民大生產》,中氣十足,感情飽滿。這些年,李文軍老師參加采訪、演出成百上千次,無論是正式的大型舞臺,還是簡單的采訪,只要唱《軍民大生產》,他總要穿起這身行頭。他說:“這是作為第一批甘肅省紅色歌謠傳承人的素養,也是義務。紅色歌謠要進社區、進軍營,還要進校園。有學生問我為啥是這身打扮,我就告訴他們,過去人們穿的就是羊皮襖,戴的羊肚子手巾扎的頭巾,這樣他們才更有興趣了解過去的歷史。”
紅歌就是唱出來的歷史。1943年,抗大七分校及八路軍770團的戰士們進駐慶陽市華池縣大鳳川,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當地的勞動號子《推炒面》成為大生產運動時期人們干活加油鼓勁時哼唱的小調,歌詞里“西里里里嚓啦啦啦嗦啰啰啰太”一聽就是模擬磨面的聲音。1943年,人民藝術家張寒暉從延安來到慶陽華池縣采風時,將《推炒面》改編為《邊區十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時候正式改名為《軍民大生產》。
和被全國人民熟知的《南泥灣》一樣,當年荒草遍地的大鳳川,僅僅經過兩年的開墾,就成了“糧食倉滿、蔬菜有余、牛馬成群、豬羊滿圈、革命家務日趨鞏固”的“魚米之鄉”,有力地支援了邊區建設和抗日前線。如今的大鳳川,早已經成為郁郁蔥蔥的林場,為當地生態建設提供苗木供給。
近80年過去了,“大生產”的故事仍在繼續。
從慶陽回到蘭州后,只要聽到采訪時的錄音素材,仍舊會不自覺地哼唱起這些紅歌。以前,紅歌對于我來說,只是大合唱比賽時候的必備曲目,可是我從來沒想過,這些紅歌背后的創作過程和創作者的經歷都是時代洪流的見證,都是創作者彼時彼刻真情實感的流露。旋律響起,好像我和他們有了共鳴,心中總是充滿無限感激,感激如今日新月異的好日子,感激百年來為了這好日子而努力的人。這種感激就像基因一樣,是刻在每個中國人骨子里的激情與熱愛。
(特別感謝: 甘肅交通廣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