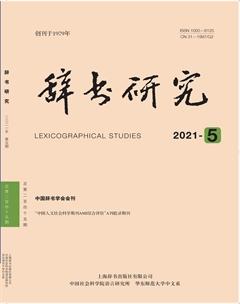基督教詞匯的本土化及背后的策略考慮
李璐溪



摘 要 文章以馬禮遜《英華字典》中的基督教詞匯為切入點,結合明清之際的西學新書和英漢辭書,從“外來詞漢化”和“外來詞泛化”兩個角度探索了這批詞匯的形式本土化,以便厘清詞匯的形式變動脈絡。分析不同階段下基督教詞匯呈現的形式特征,即漸由“合道親佛”轉向形式自主,其背后包含著人們在詞匯引入和應用時的文化心理變動和策略考慮。有助于認識近代西學新詞在漢語系統中的系統化演變及緣由。
關鍵詞 基督教詞匯 《英華字典》 本土化 造詞策略
一、 引? 言
19世紀至20世紀前半葉,近代中國掀起了一股英華字典的編纂之風,為我國的學科史和術語史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同時這批辭書也成為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打開西方窗口的重要渠道,它們囊括了西學譯著、報刊雜志中的眾多西洋詞匯,其中還不乏編纂者的獨創。在這些移植來的新詞里,基督教詞匯作為一類特殊的成員逐漸受到了學人們的關注。說其特殊,是因為基督教不像其他學科那樣可在中國找到自己的原型,也不易獲得漢族人民的文化心理認同。故而,相較于其他詞匯的創制要顯得更加艱難,其本土化的進程也頗顯曲折。
就當時對基督教詞匯收錄的情況看,馬禮遜字典的收取數量已遠超后期中外辭書,這似與他的傳教力度有關。作為19世紀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開啟了基督教在華傳播第四期的大門。為宣揚基督教義,他創辦報刊、漢譯《圣經》、編纂字典。其中《華英字典》是馬禮遜畢生的輝煌之作,全典共分為三部六卷,其所涵蓋的基督教詞匯集中存于它的第三部分《英華字典》中。依據來源,這些基督教詞匯可大致分成兩批:一批是對前期天主教傳教士所創新詞的批判性采納;另一批則是由馬禮遜個人新造,且為后來的傳教士們所繼承、發展。可以說,《英華字典》中的基督教詞匯正是處在該類詞匯承上啟下的關鍵時期。我們以此為軸點,觀察它們的承繼和發展狀態,可清晰地看到基督教詞匯是如何一步步完成本土化的。
“本土化”常言于外來詞研究當中,涉及“漢化”“泛化”兩個階段和形式、語義兩個方面(因囿于篇幅,本文僅討論形式一面)。形式即為在本土化過程中詞形逐步固定,譯名漸由多樣而單一;意義即為外來詞匯基本內涵的漢譯闡釋更為精當,其中部分詞匯的基礎意義又會在今后的語用中發生詞義偏離,衍生出非專門的修辭義項,(馮海霞,周薦2018)基督教詞匯即是如此。由馬禮遜及前期傳教士創造的基督教詞匯形式都頗為保守,而后才一步步走向現代之形,逐漸完成本土化,這背后實際存在著某種造詞策略的變動,需借助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來分析。
二、 《英華字典》基督教詞匯的確定及來源
早期的基督教詞匯有一個特征,就是盡量從詞形上隱去基督教宗教的色彩,甚至直接借用儒釋道詞匯來表達基督教概念,以實現文化調和。但由此可能會因其形式遮蔽內涵,從而引發對基督教詞匯的誤解誤釋。因此,詞匯的辨識工作就顯得格外重要。
對于那些同現代詞匯形式相同,或形式雖異,卻在釋語或例句中帶有明顯基督宗教標記的語詞來說,其判定難度不大。真正困難并需要進行文獻驗證的是那些漢譯形式與現代不一致,其后又無宗教標記的語詞。我們通過借助數本經典的明清西學新書,以此來確定馬禮遜的漢譯形式是否在宗教文獻中有基督教用法的存在。例如馬氏將prophet漢譯為“圣人”。而《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9版中的prophet共分五個英文義項,其中只有第一和第五個義項是表基督教義的學科義位,其余各項是與該基督教義近似的普通義位。所以“圣人”是否是對基督教義項的譯借,就需要通過明清西學文本來驗證。經查閱資料發現,在《齊旨》《七克》等耶穌會士文獻中都有將“先知”稱為“圣人”的譯法,由此我們可將“圣人”一詞歸列到基督教詞匯范疇之內。
基于以上判定方法,筆者共確定了《英華字典》中的146項基督教詞匯單位,并記錄如下:
神誡 十誡 信 信德 復活 再生 復生 罪 論神之理 外道 異端 邪教 圣經 圣錄 信經 信錄 福音 七十士譯出的圣經 洗身之事 領洗 付洗 祝福 言福 保佑 酬神 酬謝神 奉獻與神 祝圣 早晨的禱告 彌撒 拜神 禮拜 拜 禮崇 崇拜 祈禱 求神 祝告 禱告 耶穌圣體 圣灰日 安息之日 禮拜日 主日 修道院 修道堂 寺 天主堂 廟 天1(與“天堂”義同) 天堂 地獄 圣所 圣會 天主會 女修道長 師太 修道長老 主寺 使徒 信士 弟子 基利斯當 教友 背教的 反教的 歸信之人 門徒 徒弟 好媧 耶穌會士 摩西 牧者 監臨 和尚 僧 比丘 師姑 妮姑 女尼 先知者 達未來者 祭者 主祭 圣人 助祭 神使 天神 仙 天仙 神仙 天使 基利斯督 創造天地萬物者 造物主 惡神 邪神 惡鬼 魔鬼 神 上帝 天2(即“天主”) 天主 天后 圣母 圣神 圣風 神像 耶穌 主 救世者 魂魄 生魂 覺魂 靈魂 神明 三位一體 天主教 十字教 西洋教 新教 正教 圣教 神臺 十字架 圣物 神龕 無所不能 全能 背教 反教 贖罪 勸化 教化 創造 受造 被造之物 天地所生之物 天道 誘惑 煽惑 天帝化人 代天宣化 悔 悔過 懺悔
在這些基督教詞匯中有一批是對明末清初天主教傳教士所編譯著里用詞(語)的沿襲。我們目前尚未找到馬禮遜《英華字典》的藍本,但不可否認的是,他曾在翻譯《圣經》期間參考過天主教教士大量的宗教譯文。而他的譯經工作和字典編纂又幾乎是同時進行的,因此在《英華字典》出現的眾多基督教漢譯詞中,有相當一部分可在明末清初的西學文本中找到對應,但在使用分布上卻有廣狹之別,由此也可見各類譯名在當時的使用情況。據不完全統計,《英華字典》所沿襲的譯詞出處如表1所示:
除以上詞語外,“天主教、主日、教友、贖罪、禮拜日、信經、使徒、新教、圣會、悔、悔過”也可在明末文獻中覓得蹤跡。而“廟、和尚、仙、天仙、天道、神仙、魂魄”則出現在更早的文獻里。
陳力衛(2019)指出,19世紀前期,英漢字典中的漢譯詞多是對明末或清初耶穌會士西學新書中的詞匯汲取,但也不乏編纂者的新創。作為英漢辭書編纂的先驅,馬禮遜當年并沒有可供參考的底本,所能依靠的也只有利瑪竇以來的零星文獻和自己苦心得來的中國古書,面對新引入的概念,獨立創詞便成了自然之事。由馬禮遜創制的基督教詞匯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用新語詞來表達新概念,這些新概念在馬禮遜之前的西學譯著中都未曾有之;一類是用新詞(語)形[1]來表達舊概念,以實現與舊詞語的同義替換,并與相應的舊譯詞等價置于同一英文詞目之后。
三、 《英華字典》基督教詞匯的階段性本土化
本土化是一個漫長的歷時質變過程。此過程可分兩個階段:一為“外來詞漢化”;一為“外來詞泛化”。前者指的是外語詞初入漢語系統時發生的語碼轉換,后者指的是外來詞在漢語詞匯系統中的嬗變,又含“分化”和“固化”兩種。“分化”即在日后的發展中,詞項出現了形式或語義方面的變動,“固化”則反之。本文只觀察這批基督教詞匯在后世英漢辭書中的形式變動,原因是詞形可以最直觀地展現詞匯的本土化和其系統化的形成。基督教詞匯作為外來移植詞匯,筆者同樣分兩個階段來觀察它們在漢語詞匯系統中的流變。
(一) 第一階段:基督教詞匯的漢化[2]
《英華字典》收錄的基督教詞匯分別從形式和意義兩方面表現出了不同的漢化途徑,從而形成了三大詞匯構造類型。第一類是音譯詞匯,僅8例。字典中的音譯詞匯占比不多,所譯對象主要是基督教中的人物,如耶穌、摩西、好媧等。第二類是意譯詞匯,共55例。意譯的漢化程度要高于音譯,但為了表義的明晰性,譯者在計劃通過有義漢字來傳遞基督教概念時,就不免會用詞組來阻斷詞的出現。第三類是基督化漢語詞匯,共83例,是指因用漢語既有詞指稱基督教中的事物或現象,從而被基督教化的漢語詞匯。“基督化”的方式細分有三種:第一,用漢語既有詞形負載全新的概念,意義上與漢語既有詞完全斷聯;第二,漢語既有詞中的某一義項與該詞形后來負載的基督教義相近或相關;第三,原漢語既有詞的意義基本未變,只是為其中某一義項增添了基督教色彩義。我們依據基督化的方式,又可將基督化漢語詞匯繼續分成單純借形類和借形取義類。前者的形成來自第一種基督化方式。這類詞也同樣體現出了傳教士的造詞能力。它們利用漢語的古典詞去對譯西方的宗教概念,使詞義發生轉換。后由于新概念的借入,導致舊概念消亡,被新概念替換后的漢詞又作為近代新詞為后人繼承下來。
如“主日”本為漢語歷史詞,指太陽為諸神之主。《英華字典》所收的“主日”則指基督徒紀念耶穌基督復活的日子。借形取義類的漢化程度最高,它們從形式和意義兩方面磨損了詞匯的舶來品色彩。但“取義”存在程度的問題,其中多數是不完全取義,它們由第二種基督化方式得來。在這種方式下形成的基督化漢語詞匯,其意義一般與既有漢語詞在歷時發展中出現的某個義項相近。如“僧”本屬佛教用語,指男性佛教徒,基督教傳教士用其自稱,但指稱對象已發生了變化。當然也有少數詞匯處在完全取義行列。同形的兩類詞語在語義上幾乎無別,只是取義的一方會附上基督教這一宗教附屬義,屬于第三種基督化方式。若從義項的整個意義結構出發,這類漢語基督教詞義與對應同形的漢語既有詞義間也并非完全等值。
(二) 第二階段:基督教詞匯的泛化
《英華字典》中出現的基督教詞匯譯名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其他傳教士英漢字典中,呈現出了一條明顯的形式繼承和變動軌跡。自馬禮遜以來,很多辭書收錄的譯名基本都是從《英華字典》中繼承而來,抑或是以其為原形另加改造。例如麥都思、衛三畏的字典就是以馬禮遜字典為編纂基礎,實現了詞匯的傳承和發展。大概于羅存德時期以后,各英漢辭書中的基督教詞匯形式漸趨有了現代之影,一些儒釋道類的詞匯表述也在逐漸減少,直至赫美玲《官話》一典出版,基督教詞匯的“定形”工作基本全部完成。
經統計發現,《英華字典》中被沿用下來的基督教詞匯共有60例,如下:
十誡 信 信德 復活 罪 異端 圣經 信經 福音 領洗 付洗 祝福 祝圣 彌撒 禮拜 崇拜 祈禱 禱告 耶穌圣體 圣灰日 禮拜日 主日 天主堂 天堂 地獄 使徒 教友 耶穌會士 摩西 祭者 主祭 助祭 神臺 神像 天使 造物主 魔鬼 上帝 天主 耶穌 主 靈魂 三位一體 天主教 新教 正教 十字架 神龕 修道院 圣物 圣所 無所不能 全能 背教 反教 贖罪 創造 受造 誘惑 懺悔
《英華字典》中的每一英文詞條后往往對應著數個漢譯詞語,從而形成了多組同義聚合體。但在每組同義組內,也只有一個或兩個基督教詞匯單位會作為優勢形式被后世采納,其余成員則會因缺乏形式代表性而從基督教詞匯系統中汰出。具體情況如下所示(斜杠左側為繼承成員,右側為淘汰成員):
復活/再生 復生;圣經/圣錄;信經/信錄;祝福/言福 保佑;祝圣/奉獻與神;禮拜/拜神 拜 禮崇;祈禱/求神 祝告;修道院/修道堂 寺;天主堂/廟[3];天堂/天1; 使徒/徒弟;天使/神使 天神 仙 天仙 神仙;造物主/創造天地萬物者;上帝、天主/神 天2;靈魂/生魂 覺魂;誘惑/煽惑
另外,字典中還有30個詞匯成員于后世繼續發生著演化并逐漸與現代形式勾連,我們對這批詞匯在馬禮遜之后漢外辭書中的表現進行了面貌梳理,悉做流變考察,并借此觀察其演化規律。
可以說每一基督教詞匯在近代各漢外辭書間都呈現出了繼承和發展的關系。除此之外,在詞匯繼承的過程當中,其形式也被漸次規約,并呈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并存譯名數量由繁趨減。我們通過觀察《英華字典》到赫美玲《官話》期間出版的各類中外辭書,發現同一個基督教詞匯單位的譯名數量基本呈現出了一種先波動性增長而后又波動性減少的變動趨勢。馬禮遜及之前的譯名因尚處初創階段,譯者選取的構詞材料不相一致,常存譯名爭議,導致漢譯形式復雜不定。《英華萃林韻府》以后,部分詞語因使用范圍過狹而被淘汰。時至赫美玲時期,基督教詞匯的譯名形式已基本得以確立。
第二,非詞單位詞化。我們把從非詞到詞的過程看作是一種“詞化”。以非詞形式呈現的眾多基督教詞匯,由于形制較長,表達起來不經濟,于是人們就傾向于將其簡化為詞。而且詞化也是一個結構內部形式理據性逐漸弱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形式和意義間的關系會變得迂曲,意義也會趨向特異性。總體來說,整個詞在詞化階段的語義抽象等級會逐漸提高,符合人們從具體到抽象的認知規律。
第三,優勢譯名確立且使用頻率增高。筆者發現在清際的英漢辭書中,譯名重合并最終延續下來的形式多被當時的中國報刊采用,且時代越晚,基督教詞匯被采納的概率就越高,尤其是在《英華大辭典》和《官話》出版的年份,更是高頻次地出現在各大報刊當中。對此可反映出兩個事實:一是人們對基督教詞匯的態度已漸漸從排斥走向接受;二是譯名形式的逐步確立成為其廣泛應用的基礎。
四、 基督教詞匯形式變動后的造詞策略
外來詞匯本土化通常會涉及詞匯結構、用字和意義的轉變,而詞匯研究者也多愛從語言的角度去分析出現上述變化的原因,常忽視背后的文化機制和策略分析。外來詞的傳入涉及異文化的接觸和融合,且文化碰撞的結果往往以詞匯的形式直觀呈現。傳教士在造詞時通常要有語言和文化兩方面的兼容考慮,其過程始終內嵌著某種造詞策略,而策略的改變又推動著這些基督教詞匯本土化的進程。下文試從造詞策略的角度分析《英華字典》中基督教詞匯的形式特點及后來流變的原因。
(一) “文化求同”的造詞策略
在馬禮遜收錄的各項基督教詞匯單位中,有大部分詞語或直接借用佛道術語,或結合儒釋道文化另加創造。這其中不僅有來自耶穌會士文獻中的詞匯,同時也包括了馬禮遜自己的用詞。需要說明的是,這一造詞、用詞特點并非起自于馬禮遜,而是在基督教徂華之際就奠定了根基。基督教在中國的第一期傳播是景教入唐時期,那一時段的傳教士就已經有了教義傳播的本土化意識。他們認識到兩種不同宗教的激蕩,必然會產生文化斥力。一個新的教種要想在異文化中生存演進,就必須要尋找可使二者相諧的接口,其中最直接的一種表現方式就是通過文字符號來消除本土人的隔異心理。可以承認的是,為了使基督教的信仰要旨與中國文化契合,景教確實試探性地走了一段艱辛的路程。他們企圖利用或仿制儒釋道詞匯來闡述全新的基督教教義,以此方便統治者乃至民眾的理解。如“天尊”“寺”“無為”“受戒”“玄妙”等釋道用語在景教文獻中隨手可摘。景教入唐時的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頗高,可謂萬國朝拜。因此西方的傳教士們是以一種“文化仰視”的視角來傳播西學的。所以基督教詞匯本土化的第一階段是在中國文化的制約下順應完成的。其中使用的術語以漢語既有詞為最,而完全利用漢字新組合出的詞匯單位卻很少。
總的來說,基督教入華的前兩期并未給中國帶來真正的基督哲學思想,其影響力并不大,但是當時文獻中宗教用語的“合道親佛”色彩卻一直影響到了之后基督教詞匯的造詞風格。不得不說由景教傳教士開啟的這種譯詞譯語方式,對當時乃至19世紀中期以前的基督教傳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種作用就是通過語詞的貼近和融合,盡可能從文化上去求同,以達到方便教義傳授的目的。
16世紀以后,侵略者以槍炮轟擊中國大門,一些傳教士假布道之名,成為殖民擴張精神工具的操縱者。因此,這一時期的傳教更多帶有一種侵略性質,并有煽惑民心之嫌,自然會遭到統治者和百姓們的拒斥。于是以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傳教士便以僧人(后又轉換為“西儒”)的身份開始傳教活動。他們繼續在所編書刊中羅列佛道詞匯,以此說明基督教和中國的宗教有相通之處。雖然利瑪竇的這一做法被后來的很多傳教士們詬病,認為失去了基督教的本真,但在如今看來,這也是利瑪竇的無奈之舉。包括后來的馬禮遜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其實,在倫敦會派遣馬禮遜去中國傳播福音之前,他就深知此去一行的困難。漢族人民的心理排擠和清政府的嚴格管控,使其傳教的難度絕不亞于前期的景教和天主教。對此馬禮遜借鑒前人經驗,首先刻苦學習中文,博覽中國傳統經典,深入了解中國文化,這都為他后來編纂字典和漢譯《圣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有了這樣的語言和文化知識背景,馬禮遜自我的翻譯系統也就有了中國文化這一參照體系,導致他在翻譯和收錄譯詞時產生了一種傾向,即盡量貼合中國文化,實現文化求同,這在宗教傳播上尤為重要。因為佛、道兩教發展到明清時期已經深入人心,故而基督教的輸入必然會產生文化心理上的強烈沖突。為了減少宗教間的摩擦,馬禮遜只能采取求同策略,在教理傳授和詞語翻譯上適當地迎合儒釋道思想。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英華字典》中的“基督化漢語詞匯”數量會有如此之多。雖然其中有很多是對前人的繼承,但也說明了馬禮遜對這種“文化求同”式翻譯策略的認同。當外來概念植入異文化域時,選取什么語言形式作為其外殼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音譯雖最大程度上對外來概念進行了“保真”,但在布道初期對教義的理解是不便的,所以意譯以及對借入語言的術語借用就成為了傳教士重要的譯詞手段。(卓新平2013)意譯詞具有透義性,但有時為了更加清晰地闡述概念,或受制于傳教士自身的漢語水平,就會以詞組代替之,《英華字典》以及之后的傳教士辭書中,以詞組形式表達基督教概念的現象是很常見的。而字典中的基督化漢語詞匯更是構成了當時基督教詞匯的主要部分。這種對佛道術語進行形式借用的做法,既減輕了傳教士的造詞困難,又通過詞語互通的方式實現了宗教義理上的交流,不得不說是一種智慧。通過語言符號來達到文化求同,緩和了異族人民間的心理沖突,是包括馬禮遜在內的明末清初傳教士重要的造詞策略。
(二) “文化存異”的造詞策略
基督教在中國傳播路徑之困難,自不待言,早期基督教詞匯的保守譯法就可側面說明這一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群傳教士們的目的始終是要在這個東方大國布道宣教,施以“救贖”,并不可能完全向中國的文化和思想妥協,所以譯詞翻譯上的遷就只不過是給自己所做工作披上的一層“保護衣”。(朱志瑜2008)鴉片戰爭失敗后,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再度燃起,基督教各派紛紛強入中國,開始了被后來不少人認定的“文化侵略”。因此在宣揚基督教教義方面不再竭力與中國文化相契,漸有了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對當時中國的各社會階層帶去了不小的影響。例如受新教的啟發,太平天國運動領袖洪秀全創立了“拜上帝教”,開始接受基督教的洗禮。中國的士大夫們為實行社會改良,主動學習西學,也出現了同傳教士交互往來的情況。中西文化間的交流在摩擦中日益加深。繼馬禮遜以后,衛三畏、麥都思、傅蘭雅、盧公明等傳教士也在不斷通過創辦報刊、修建學堂、設立印刷所來獲得中國人的承認。19世紀后期,和合本《圣經》在中國問世,因文字內容貼近官話,“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白話文體十分契合”(唐逸1999),便受到了中國信徒的偏愛。在這一背景的作用下,傳教士們在譯詞的改造和翻譯上逐漸放開,其中的一個表現就是基督教詞匯的形式開始有了“存異”傾向。前文已統計,在馬禮遜字典中已有60個基督教詞與現代形式取得了一致,占了收詞總數的41%強。馬禮遜之后的英華辭書更是日漸趨向形式的自主化,褪去了儒釋道的保護外衣,盡顯專門術語的表達色彩。如上文所說,直至赫美玲的《官話》,漢語基督教詞匯已基本完成了現代化的進程。就詞匯類型構造看,原來占有大幅度比例的基督化漢語詞匯只有十幾個詞留存了下來,其余各詞或被淘汰,或為音譯詞和意譯詞替代。由此可以看出,基督教詞匯形式從依附漢語既有詞形轉向自主化造詞,是伴隨著文化態度的轉變的。
五、 余? 論
基督教詞匯是漢語外來詞中較為特殊的一類,其翻譯在歷史上也曾出現過較大的爭論。馬禮遜作為新教在華傳播的先驅,他的《英華字典》已經很全面地收錄了當時的基督教譯詞,并為后來的傳教們繼承和改造。通過19世紀各英華字典間的比較,可以清晰地看出基督教詞匯在漢語中的本土化進程。當然,當時基督教詞匯的翻譯工作主要是由傳教士們承擔,他們在譯詞的時候更多的是去考慮這個詞怎樣翻譯才能被中國人接受,才能更貼合基督教的要理而不失其本真,而不是先考慮這個詞的結構和形制。基督教詞匯本土化的進程固然體現了一般外來詞漢化的規律,其變化過程也伴隨著語言因素的影響。但基督教詞匯為何在不同的本土化階段下會產生不同的特點,其詞匯引入時的歷史文化背景是不能不考慮的。
附 注
[1]“新”詞形中的“新”指的是明末天主教未曾用來表達基督教概念的詞形,其中既包含馬禮遜新造的詞和語,也包含一些漢語的既有詞。
[2]若嚴密講,外來詞的漢化理應追溯到該詞首次借入的時期。但鑒于本文屬專書研究,故暫以本字典的詞匯面貌來說明漢化類型。
[3]目前在中國某些地方還有把教堂稱為“廟”的習慣,例如位于山東青島臺東的一所基督教教堂(原名“路德堂”),因其建筑外形與中國傳統的廟宇相似,故稱“臺東大廟”。
[4]本文參照了近代影響力較大、代表性較強的幾本中外辭書,分別是:《英華韻府歷階》(衛三畏1844);《英華字典》(麥都思1847—1848);《英華字典》(羅存德1866—1869);《英華萃林韻府》(盧公明1872);《英華大辭典》(顏惠慶1908);《官話》(赫美玲1916)。
參考文獻
1. 陳力衛.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2. 陳濤.近代在華傳教士的文化行為分析.澳門理工學報,2014(3).
3. 董秀芳.詞匯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1.
4. 郭繼民.基督教傳入中國的過程、機制及成因.中國石油大學學報,2016(3).
5. 馮海霞,周薦.新世紀漢語“詞義—修辭”研究現狀與前瞻.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18(2).
6. 黃河清.近現代辭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7. 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50種重要文獻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8. 霍恩比.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9版).李旭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9. 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匯的發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
10. 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11. 史有為.漢語外來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12. 譚樹林.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杭州:中國美術出版社,2004.
13. 唐大潮.佛教、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之比較.社會科學研究,2001(6).
14. 唐逸.中國基督信仰本土化之類型.世界宗教研究,1999(2).
15. 王銘宇.明末天主教文獻所見漢語基督教詞匯考述.漢語學報,2013(4).
16. 王銘宇.十九至二十世紀漢語基督教詞匯的傳承、流布與分化.澳門理工學報,2018(1).
17. 徐時儀.明清傳教士與辭書編纂.辭書研究,2016(1).
18. 張西平.馬禮遜《漢英英漢詞典》中的基督教詞匯研究.基督宗教研究,2000(1).
19. 張曉華.從佛教景教傳播中國的成與敗看外來宗教本土化的若干理論問題.史學理論研究,1999(4).
20. 周薦.術語創制與詞匯學學科發展.漢語學報,2017(2).
21. 周薦.明恩溥《漢語諺語熟語集》的語料價值和熟語理念.古漢語研究,2020(1).
22. 朱志瑜.《天主實義》利瑪竇天主教詞匯的翻譯策略.中國翻譯,2008(6).
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數據庫.http://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enter.php.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25. 卓新平.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處境.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26. 卓新平.基督教小辭典.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
(南開大學文學院 天津 300071)
(責任編輯 劉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