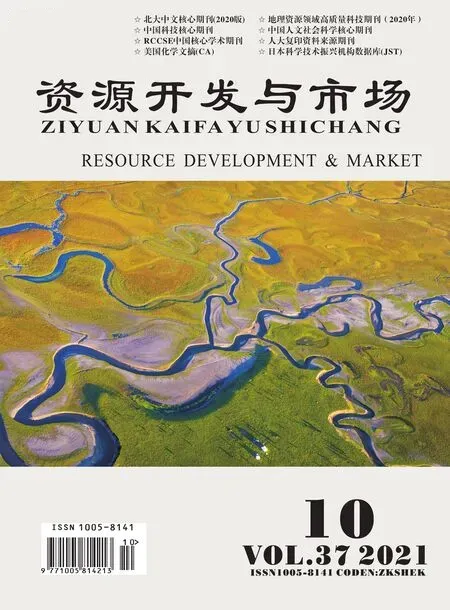我國不同類型景區旅游效率研究
董紅梅
(西安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4)
旅游效率作為旅游研究的新興領域[1],涉及旅游酒 店[2-4]、旅 行 社[5]、旅 游 上 市 企 業[6]、旅 游 目 的地[7]、旅 游 產 業[8-10]、旅 游 線 路 產 品[11]、旅 游 景區[12-19]和 旅 游 資 源[20,21]等 方 面。旅 游 景 區 效 率 研究對推動區域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有重要意義[12],但對其關注仍顯不足[13],尤其是在我國景區發展由數量增長轉入提質增效的關鍵時期。目前其研究對象有國 家 風 景 名 勝 區[14-17]、森 林 公 園[18]、A級 景區[13,19]等,側重于某類景區或資源的整體效率,缺乏不同類型景區旅游效率及其差異研究。本文以2017年、2018年我國六大地區14個亞類A級景區組成的84個景區類型為決策單元,采用數據包絡分析(DEA)進行旅游效率測量,研究并揭示我國不同類型景區旅游效率及其在不同地區的特征,剖析不同類型景區旅游效率的源泉,為有效地利用資源,挖掘技術利用潛力,提升景區發展質量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方法、指標選取和數據來源
1.1研究方法
DEA作為效率測量的有效工具[22],因其在分析多投入、多產出的效率時具有明顯優勢而被廣泛應用于諸多領域[23],近年成為旅游效率評價的重要方法之一。該方法的效率估計分為投入導向和產出導向兩種。其中,投入導向是指產出既定情況下,衡量投入要素減少的比例;產出導向則是在投入既定條件下,衡量產出增加的比例。旅游效率是指旅游投資活動所產生的收益和所消耗的資源之間的對比關系,是在給定的投入和技術條件下對資源利用水平進行衡量。旅游總效率是總體衡量指標,等于規模效率與技術效率之積。其中,規模效率是指資源要素投入滿足發展對資源需求的程度,是衡量決策單位是否在最佳資源要素投入規模下發展[3]。當資源要素投入低于或超出需求時,其發展均沒有效率,需增加或控制資源要素投入以獲得更大發展。技術效率反映決策單位發展過程中對現有技術水平發揮的程度,是指在既定的技術和環境條件下,用特定的投入生產最大可能產出的能力和意愿[10]。本文采用產出導向模式來刻畫不同類型景區的旅游總效率、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
1.2 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旅游效率測量涉及投入與產出指標,其指標選擇直接影響到測量結果的準確性與真實性[23]。既有景區效率研究多將游客量、旅游收入作為重要的產出指標,因為它們是景區發生旅游活動后最直接的產出表現[18];而投入指標的選取則受到數據可得性和相應研究問題的影響而差別較大,目前選取較多的投入指標是固定資產投資、土地面積[14-18]、從業人數[10,14-18],也有研究者用經營支出[14-17]或資金投入總量[10]來代替固定資產投資指標,用旅游資源稟賦[20,21]來代替土地面積指標。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旅游景區發展的客觀現實和數據的可獲得性,并依據可比性、整體性、系統性等原則[22],選取A級景區數量、景區建設投資、就業人數作為投入指標,旅游收入、游客量作為產出指標,以進行不同類型景區旅游效率測度,并默認當年景區建設投資當年獲得全部產出。
本文以我國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和西北六大地區的森林景觀、河湖濕地、地質遺跡、古村古鎮、文化遺跡、文博院館、紅色旅游、宗教文化、主題游樂、度假休閑、鄉村旅游、城市公園、商貿旅游和其他14亞類組成的84個景區類型作為決策單位,運用DEAP 2.1軟件進行旅游效率測量,以分析我國各類景區旅游效率及其在不同地區的表現。其中,森林景觀、河湖濕地、地質遺跡等亞類屬于自然景觀大類,古村古鎮、文化遺跡、文博院館、紅色旅游、宗教文化等亞類屬于歷史文化大類,主題游樂、度假休閑、鄉村旅游、城市公園、商貿旅游等亞類屬于休閑娛樂大類。數據來自于2017年、2018年《中國旅游景區發展報告》。
2 結果及分析
2.1 大類景區旅游總效率分析
2017年、2018年我國4大類景區旅游效率結果見表1。從表1可見,歷史文化大類的總效率最高,其次是休閑娛樂大類、自然景觀大類,最低的是其他類。從分解效率看,大類景區技術效率的變化特征與總效率一致,且明顯小于規模效率,表明景區旅游總效率低主要是由技術利用水平低導致的。

表1 2017、2018年我國4大類景區旅游效率
2.2 亞類景區旅游效率分析
在亞類景區中,旅游總效率在2017年、2018年分別介于0.24—0.86、0.18—0.84之間,變化較大(圖1)。

圖1 2017年、2018年不同類型景區的旅游總效率
總體上看,居前三位的是城市公園、紅色旅游、古村古鎮,其次是森林景觀、宗教文化、地質遺跡、文化遺跡、文博院館、河湖濕地、主題游樂和商貿旅游,排在后三位是度假休閑、鄉村旅游和其他。由此可知,城市公園、古村古鎮、紅色旅游等亞類景區的資源利用效率較優,產出水平較高;而鄉村旅游、度假休閑等亞類景區的資源利用效率較差,產出偏低。從變異系數看,在2017年、2018年分別介于0.09—0.57、0.14—0.59之間,其中地質遺跡、商貿旅游、宗教文化等亞類的變異系數較大,而城市公園、文博院館等亞類的變異系數較小,表明地質遺跡、商貿旅游、宗教文化等亞類的旅游效率在地區間不均衡性顯著,而城市公園、文博院館等亞類的旅游效率在地區間變化不大,這可能與城市公園、文博院館景區主要分布于經濟、交通與市場條件較優的城鎮有關。
亞類景區技術效率在2017年、2018年分別介于0.32—0.92、0.25—0.88之間,變化較大,且其變化特征與旅游總效率比較一致(圖2)。城市公園、古村古鎮、紅色旅游等類型景區的技術效率較高,表明其現有技術水平發揮程度較好;鄉村旅游、度假休閑、地質遺跡和其他等類型景區的技術效率較低,表明其技術水平發揮程度較差。從技術效率的變異系數看,其值在2017年、2018年分別介于0.15—0.59、0.13—0.59間。其中,商貿旅游、度假休閑、地質遺跡、宗教文化等類型景區的較大,表明技術利用程度在地區間的差異顯著;而城市公園、文博院館、紅色旅游、森林景觀類型的明顯較小,說明技術利用水平在地區間相對均衡。

圖2 2017年、2018年不同類型景區的技術效率
亞類景區的規模效率在2017年、2018年分別介于0.69—0.95、0.64—0.95之間(圖3),變化較小,且均在0.6以上,明顯高于技術效率。相比較而言,城市公園、地質遺跡、宗教文化、紅色旅游亞類較高,其次是古村古鎮、文化遺跡、森林景觀、河湖濕地、文博院類、主題游樂、商貿旅游和其他等亞類,較低的是度假休閑、鄉村旅游等亞類。由此可知,城市公園、地質遺跡、宗教文化、紅色旅游等亞類景區的資源要素投入能較好地滿足其發展需求;而度假休閑、鄉村旅游等亞類景區的資源要素投入與其發展需求不適應。從變異系數來看,其值在2017年、2018年分別介于0.10—0.24、0.04—0.30間,普遍小于技術效率的變異系數,表明不同類型景區規模效率在各地間比較均衡。

圖3 2017年、2018年不同類型景區的規模效率
在所有景區類型中,規模報酬遞減與不變的占絕大多數(表2),表明我國大多數景區類型的資源投入超過了其發展需求。其中,森林景觀、度假休閑、鄉村旅游和其他等亞類的規模報酬在六大地區均呈現遞減,表明這些景區類型在各地區的規模結構均不合理,存在資源投入過度現象,這需要開發者與管理者在今后制定決策時高度重視。但古村古鎮、紅色旅游、商貿旅游等類型景區在較多地區存在著規模報酬遞增,如西北、東北、華北地區的古村古鎮類,西南、東北地區的紅色旅游類,西南、西北地區的商貿旅游類,因此可適當增加資源投入,以提高其產出。

表2 2017年、2018年各地不同景區類型規模報酬
2.3 各地不同景區類型旅游效率特征
從各地不同類型景區旅游總效率的平均值來看,我國華東與西南地區較高,2017年、2018年分別為0.57與0.622、0.57與0.54;其次是中南與華北地區,2017年、2018年分別為0.475與0.511、0.434與0.427;西北、東北地區最低,2017年、2018年分別為0.45與0.364、0.422與0.366。從各地不同類型景區旅游總效率的離均差來看(圖4),我國華東地區的地質遺跡、紅色旅游、宗教文化、古村古鎮、河湖濕地、文化遺跡、城市公園、森林景觀等類型較優,鄉村旅游、商貿旅游、度假休閑和其他類型則明顯較差;西南地區的城市公園、古村古鎮、紅色旅游、森林景觀、商貿旅游、文化遺跡等類型的較優,鄉村旅游、宗教文化、度假旅游、其他等類型的則較差;華北地區的城市公園、商貿旅游、古村古鎮、河湖濕地、紅色旅游、文化遺跡等類型的較高,而度假休閑、宗教文化、鄉村旅游、地質遺跡、森林景觀、文博院館、主題游樂和其他等類型的偏低;中南地區的城市公園、宗教文化、主題游樂等類型的相對較高,而鄉村旅游、古村古鎮、度假休閑、地質遺跡、文博院館、森林景觀和其他等類型的較低;西北地區(除城市公園、紅色旅游等類型外)、東北地區(除城市公園、古村古鎮等類型外)的絕大多數類型景區的旅游總效率均偏低。這再次表明華東、西南地區不同類型景區旅游效率總體較優,其次是中南和華北地區,而西北與東北地區不同類型景區的表現則明顯較差。

圖4 2017年、2018年六大地區的不同類型景區的旅游總效率離均差
2017年、2018年六大地區不同類型景區的技術效率離均差結果如圖5所示。從圖5可知,在技術效率方面,華東地區整體最高,其次是中南、西南、華北地區,西北、東北地區則偏低。華東地區(除鄉村旅游、商貿旅游和其他類型之外)絕大多數類型景區的技術效率均較高;中南、西南、華北地區有半數以上的景區類型的技術效率較高,而偏低的有中南地區的古村古鎮、鄉村旅游、商貿旅游、地質遺跡和其他等類型景區,西南地區的宗教文化、鄉村旅游、文博院館、地質遺跡、度假旅游、其他等類型景區,華北地區的度假休閑、宗教文化、鄉村旅游、地質遺跡、森林景觀、文博院館、主題游樂和其他等類型景區。西北地區(除城市公園、文化遺跡、文博院館和紅色旅游等景區類型之外)和東北地區(除古村古鎮、城市公園等景區類型之外)的絕大多數類型景區的技術利用水平偏低。可以看出,不同景區對現有技術利用程度與其所在地方的經濟、科技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在經濟、科技發達的華東地區表現明顯較好,而在經濟、科技相對落后的西北、東北地區的表現則差強人意。

圖5 2017年、2018年六大地區的不同類型景區技術效率離均差
2017年、2018年六大地區不同類型景區規模效率離均差結果見圖6。從圖6可知,華北、東北、西南、西北在規模效率方面整體較高,在華東與中南地區則明顯較低,這表明目前我國西北、華北、東北、西南地區多數景區類型的資源要素投入能較好地滿足發展的需求,而華東、中南地區多數景區類型資源要素規模與其發展需求不相協調明顯,進而影響其產出效率。

圖6 2017年、2018年六大地區的不同類型景區規模效率離均差
3 討論
在我國4大類景區中,歷史文化的旅游總效率最高,技術效率、規模效率也較高,表明歷史文化大類景區的資源投入能較好地滿足其發展需求,且在發展中對技術利用程度較高。這可能與該類景區主要分布在人類活動相對頻繁地區,不但社會經濟發達、科技水平較高、人才相對集聚,而且靠近消費市場,開發利用相對容易有關。大類景區的技術效率的變化與旅游總效率的相似,且明顯大于規模效率,表明我國大類景區旅游總效率低主要受制于技術利用水平,因此提高我國景區產出的關鍵在于強力發揮技術利用程度。
在14個亞類景區中,城市公園、紅色旅游的旅游總效率高,其分解效率的技術效率、規模效率也高,表明這兩類景區在資源投入、技術利用上均較優;古村古鎮的旅游總效率高,但規模效率不能適應發展需要,未來需要調整投入規模,以提高產出;宗教文化、地質遺跡的規模效率高,但技術效率不高,影響產出水平,因此未來發展水平提高的核心在于擴大技術利用程度;鄉村旅游、度假休閑的總效率明顯低,其分解的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均較低,是制約這兩類景區產出的重要因素,因此今后的發展不但要引進高層次科技與管理人才,強化景區資源管理水平,提高現有景區資源的開發利用與技術創新,而且需要調整資源投入規模,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其他的景區類型的總效率不高,規模效率、技術效率也不高,需要在技術利用效率、資源投入規模方面同時改進,以提高產出效能。
各地不同類型景區的平均旅游總效率表現為華東與西南地區較優,中南與華北地區次之,西北與東北地區的相對最差。華東地區亞類景區旅游效率總體較好,但全面提升不僅要注意調整資源投入規模(除地質遺跡、紅色旅游等景區類型外),還需提高商貿旅游、鄉村旅游等類型景區的現有技術的利用水平。西南地區要提高景區旅游效率,一方面要加強提高宗教文化、鄉村旅游、度假休閑、地質遺跡、文博院館等類型景區的現有技術利用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調整商貿旅游、文化遺跡、鄉村旅游、度假休閑等類型景區的資源投入。中南地區不但要提高古鎮古村、鄉村旅游、商貿旅游、地質遺跡等類型景區的現有技術的利用水平,而且要重視調整紅色旅游、文化遺跡、主題游樂、鄉村旅游、地質遺跡、河湖濕地、森林景觀、度假休閑、文博院館等類型景區的資源要素投入,以提高區域內景區的產出水平。華北地區,既要調整文博院館、度假休閑、鄉村旅游等類型的資源投入規模,又需加強主題游樂、文博院館、森林景觀、地質遺跡、鄉村旅游、宗教文化、度假休閑等類型的技術利用,以優化其發展效率。西北地區各景區均需要加強高層次專業人才的培養與引進,增強現有技術利用與創新能力,提高其在主題游樂、商貿旅游、地質遺跡、度假休閑、古村古鎮、森林景觀、鄉村旅游、河湖濕地等類型景區的技術利用效率,并注意調整度假休閑、文博院館、文化遺跡等類型景區的資源投入規模,以提升區域內景區整體的旅游效率。東北地區需要加強各景區人才建設,提高商貿旅游、鄉村旅游、度假休閑、地質遺跡、文化遺跡、宗教文化、河湖濕地、主題游樂、森林景觀、文博院館等類型景區的技術利用水平,并適當調整鄉村旅游、古村古鎮、森林景觀等類型景區的資源投入規模,以提高其景區整體的旅游效率。
4 結論
本文運用DEA方法,以2017年、2018年我國六大地區14個景區亞類組成的84個景區類型為決策單元進行效率測量與分析,主要結論如下:①不同類型景區的旅游效率差異明顯。4大類景區中,歷史文化大類的旅游效率相對最優,其次是自然景觀大類、休閑娛樂大類,最差的是其他大類。在14個亞類景區中,旅游總效率最高的是城市公園,其次是古村古鎮、紅色旅游,森林景觀、宗教文化、地質遺跡、文博院館、河湖濕地、主題游樂和商貿旅游,排在后三位是度假休閑、鄉村旅游和其他類。大類景區、亞類景區技術效率的表現總體上與總效率相似,且均低于其規模效率,表明不同類型景區旅游效率低主要受技術效率的影響。規模效率較優的是城市公園、宗教文化、地質遺跡、紅色旅游等類型,明顯較差的是度假休閑、鄉村旅游類型。城市公園類型景區的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均較優,而鄉村旅游類型景區的規模效率、技術效率則偏低,導致前者旅游總效率最高,后者很低,這可能與二者所處的城鄉區位不同而產生的在經濟、社會、科教、人才等方面的顯著差別密切相關。②不同類型景區的旅游總效率在各地的差異顯著,其中華東、西南地區總體較優,其次是中南和華北地區,而西北與東北地區明顯較差。華東、西南地區絕大多數類型景區旅游總效率較優,前者較差的是鄉村旅游、商貿旅游、度假休閑及其他類型,后者較差的是鄉村旅游、宗教文化、度假休閑和其他類型。中南、華北地區不同類型景區的旅游效率一般,前者的鄉村旅游、古村古鎮、度假休閑、地質遺跡、文博院館、森林景觀和其他類型和后者的度假休閑、宗教文化、鄉村旅游、地質遺跡、森林景觀、文博院館、主題游樂和其他類型的表現較差。西北、東北地區的絕大多數類型景區旅游效率普遍較差,前者相對較優的僅有城市公園、紅色旅游類型,而后者唯有城市公園、古村古鎮等類型。各地區不同類型景區的技術效率低于其規模效率,其技術效率較優的是華東地區,其次是西南、中南、華北地區,較差的是西北、東北地區;其規模效率較優的是華北、東北、西南、西北地區,較差的是華東與中南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