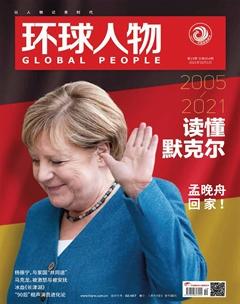冰血《長津湖》
楊學義 楊雯

“媽媽,我要去看一場戲!”1950年3月,18歲的上海青年劉石安匆匆跑出家門,他的媽媽當時怎么也不會想到,兒子一走就是兩年多。志愿軍老戰士劉石安對《環球人物》記者說,上海解放時,他看到解放軍睡在馬路上,見慣了囂張跋扈的侵略者和國民黨,人民軍隊的所作所為震撼了劉石安,使他下定決心入伍。但他是家中的獨子,擔心家人反對,就向母親編出“看戲”的謊言。
劉石安所在連隊后來被編入中國人民志愿軍第20軍,與26軍、27軍同屬于宋時輪任司令員的第9兵團。最初,兵團任務是解放臺灣,但隨著形勢發展,馬上成為抗美援朝的一支精銳。劉石安后來與戰友們坐著一列悶罐火車北上,當看到天津車站貼滿“抗美援朝”標語,才知道他們即將跨過鴨綠江。鴨綠江邊,美軍戰機在他們頭頂挑釁,瘋狂投彈,不僅讓朝鮮人民流離失所,還逼近我國境內。滿腔怒火的劉石安,即刻同第9兵團將士一道,奔赴一個寒冰與熱血交融、在世界戰爭史上留下不朽傳奇的戰場——長津湖。
“這是一場你應該參與的戰爭”
同劉石安對話,讓記者意識到:這些后來在朝鮮舍生忘死、保家衛國的民族英雄,在媽媽面前,也都是一個個愛撒嬌、有個性的孩子。
電影《長津湖》抓住了這個精髓。監制黃建新說:“這個戲最好的東西就是,每個角色都是生動的。”影片以伍千里、伍萬里兄弟為主線展開,從軍十余年的伍千里在新中國成立后回到家鄉,在江邊客船上看到多年未見的老媽媽,動情地跪下來,弟弟伍萬里就在一旁看著這一幕。
伍萬里是在江邊長大的野孩子,“從哥哥身上,我看到了軍人氣魄,就想跟著入伍,尋找自己的價值”,伍萬里的飾演者易烊千璽講述著他對角色的理解。但伍萬里只有19歲,剛參軍就遭排長雷睢生質疑:“一個不會打槍的悶蛋上戰場,那得牽連多少人啊!”
排長雷睢生被戰士們稱為“雷爹”;指導員梅生是上海兵,伍千里調侃他“到底是城市人,活得真精細”,然而他時常就會一聲怒吼,狠抓連隊紀律;火力排排長余從戎性格開朗,是連隊的開心果;戰士平河少言寡語,但到了戰場上卻火力最猛。
其實,那些戰死他鄉的忠烈英魂,也是這些有血有肉的中華兒女啊!雖然有些人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但他們都曾在祖國熱情、真實、眷戀地活過。當伍千里給老母親跪下的那一刻,他的身體不斷顫抖;當戰場上的梅生將女兒的照片捧在手心,眼中閃爍著淚光……戰士們也想活下來,盼著與親人重逢。可是,為了中國人不再受欺辱,他們唯有舍生忘死。
《長津湖》帶我們回到極寒之地,感受到志愿軍戰士的滿腔熱血。真實戰役雖比電影更慘烈,但電影也足夠震撼人心。通過拍攝,電影聯合導演之一徐克說:“讓自己進入那個世界,才明白我們當年為什么要打這場仗!”他領悟所謂英雄,“就是為了國家和民族去執行信念,這其實是一場你應該參與的戰爭!”
70年后,我們“參戰”的方式就是重溫和銘記。
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
電影聯合導演之一陳凱歌提到《孫子兵法》的一句話: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這強調軍紀的16個字,很好地概括了長津湖將士們。
剛成立一周年的新中國,與工業基礎雄厚的美國的軍備水平根本不是一個層次。特別是在長津湖與中國人民志愿軍正面交手的美陸戰第1師,被美國媒體這樣評價:“能打敗這支軍隊,那就已贏得朝鮮的戰爭甚至也許全世界的戰爭,因為這是我們軍隊中最精銳和最優秀的。這些海軍陸戰隊隊員承認,他們也許有一天會被打敗,是的,如果那一天太陽從西邊升起。”
美陸戰第1師組建于1775年,是美國海軍陸戰隊中歷史最為悠久的部隊,經歷過一戰和二戰的洗禮,特別是太平洋戰爭期間與日軍的肉搏戰,聲名赫赫。

長津湖地區圍獵美陸戰第1師經過要圖。(圖片來自《圍獵美軍“王牌師”——抗美援朝長津湖戰記》)
《圍獵美軍“王牌師”——抗美援朝長津湖戰記》一書作者、軍史專家邵志勇告訴記者,1950年10月24日毛澤東接見宋時輪,賦予第9兵團作戰目標——打掉美陸戰第1師,并說:“美國人是最怕死的,只要美陸戰第1師頂不住,抓住這個主要的精銳,就可以化解矛盾、爭得主動。”
毛澤東對宋時輪說:“解放戰爭中,你兵團練就了一身的硬骨頭,是善打阻擊、勇戰惡敵的部隊之一。現在用你的兵團,目的就在此。”
雖然斗志昂揚,但第9兵團面臨著許多現實問題。長津湖位于蓋馬高原,受西伯利亞寒流影響大。當時氣溫在零下30攝氏度左右,最低到零下43攝氏度。極寒天氣完全超出第9兵團的設想,據第20軍副軍長廖政國回憶,“當時什么資料也沒有,連1:5000的作戰用圖,軍司令部也只有一份。”
后勤保障也出現很大困難。志愿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任長榮曾回憶:“鴨綠江北岸的物資堆積如山……我們沒有制空權,又缺乏交通運輸工具,再加上朝鮮公路狹窄也很難走,又逢大雪封山……物資運不上去。”劉石安老人也回憶,部隊入朝時背的口糧幾天就吃完了,只能就地籌措食物,條件惡劣時甚至只能飲冰食雪。

1950年冬,長津湖戰役的志愿軍戰士們在補給匱乏的情況下,依然頑強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