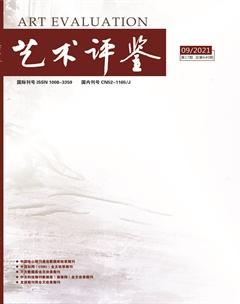試析戰爭與表現主義的興起
姜璐
摘要:本文試圖從19世紀下半葉的北歐危機與歐洲整體的戰前局勢開始探尋,對表現主義先驅蒙克的作品進行時代解析,論述表現主義的興起與戰爭之間的關系,并且通過一戰爆發前后期的德國表現主義思潮,探究戰爭對德國表現主義繪畫的影響。
關鍵詞:戰爭? 蒙克? 表現主義
中圖分類號:J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1)17-0029-05
蒙克作為19世紀末發展起來的挪威表現主義畫家,他的作品對德國表現主義的興起有著尤為關鍵的精神引領作用。蒙克作品中的表現主義因素,不僅僅是個人主觀情感和情緒的藝術表達,還反映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歐洲整整一代人的社會文化危機和精神混亂,并且,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全面爆發,在動蕩的戰爭年代和混亂的意識形態下,顯得尤為明顯。但是,目前的論文研究中,多以蒙克的繪畫語言進行解析,對蒙克表現主義的精神性和藝術性進行研究,或以美學思想和哲學思想對表現主義的興起進行探究。很少課題以客觀的戰爭歷史視角,將藝術的發展與戰爭的史實進行連接,對表現主義興起的根源和表現主義的個人范式進行深入研究。本文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就已出現的蒙克的表現主義藝術為立足點,以蒙克的藝術影響了德國表現主義的興起為由,到德國的表現主義呈現出藝術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為思考點。以蒙克的創作為例,對戰爭與表現主義的興起進行深入探究。
一、表現主義先驅-蒙克
愛德華·蒙克(1863-1944)是享譽世界的表現主義畫家,版畫家。蒙克生于挪威奧斯陸。5歲那年,他的母親死于肺結核,14歲時姐姐被肺病奪去生命,妹妹在年少時便患有精神隱疾。父親是位軍醫,篤信神學,時常因精神疾病而陷入癲狂。蒙克自幼體弱多病,從小被家人的疾病和死亡陰影所困擾,使他一生的精神和心靈受到創傷。1881年,愛好繪畫的蒙克考入挪威皇家繪畫藝術學校。幾年后,他和另外六名藝術學生在奧斯陸租了一間工作室,他們很幸運地得到了自然主義畫家克里斯蒂安·克羅格的支持和指導。1885年作品在安特衛普進行展覽期間,蒙克短暫的巴黎之行成為他認識藝術界的第一步。回國之后,依據年少的痛苦經歷創作《病中的女孩》,開啟了他藝術上的新紀元。1889年舉行奧斯陸個人展,贏得藝術贊助資金,前往巴黎繼續學習繪畫。他吸收了印象派、后印象派中運用線條和色彩的情感表現手法,同時,接受了先鋒的藝術思想,形成了自己奮斗一生的藝術理念。求學期間,他的父親去世了,極度的悲傷致使蒙克陷入情緒的深淵,久久不能平復。1892年于柏林展出55幅繪畫,當即引發巨大輿論。在科隆巡回展覽后,回到柏林時受到了德國小資產階級的認同和資助。此后的16年,蒙克大多在柏林和巴黎維持生計,這一時期也成為蒙克藝術發展的重要階段,著手創作《生命》系列組畫。他多以疾病、死亡、愛為主題,以象征主義的理論和自我內心情感的探索相結合,進行主觀性色彩和線條的藝術表現。1893年,蒙克的《吶喊》以強勁之勢,撼動了德國的藝術界。此后他依循主題性油畫的創作方式,開啟版畫的復制,追求細部刻畫,以黑白色彩帶入更具表現力的視覺呈現。這一轉變,開始備受人們的推崇。隨著戰爭局勢的嚴峻和社會矛盾的激增,德國爆發了一場由藝術家引導的精神革命,對德國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及其社會問題進行關注和反思。蒙克以其先鋒的藝術精神,推動了德國先鋒藝術團體“橋社”的確立。1912年參加科隆“獨立聯盟”,取得與梵高、塞尚、高更相等的藝術成就。45歲時,蒙克的精神狀況轉壞,回到挪威定居。二戰時,德國入侵挪威,他創作了大量自畫像,記錄精神和肉體走向死亡的進程。蒙克的藝術生涯長達60年,共計作品達60000余件。他一生將個人的傷痛經歷作為象征意象,以沉郁濃烈的色彩和主觀情感表現的手法描繪強烈的主觀情緒,成為戰爭年代下最具原始情感的生命抒寫。
二、蒙克作品的時代解析
(一)《病中的女孩》
19世紀初,北歐國家優越的海陸位置,迅速崛起的海洋市場,成為帝國戰爭中覬覦的對象。帝國主義為了占得自由經濟中的優勢地位,對弱小國家進行了殖民地的掠奪和擴張。不僅對丹麥發動戰爭,而且封鎖了挪威海岸、糧食和原材料的物資運入。挪威國力弱小,惡略的氣候和貧瘠的土地,致使挪威國內出現了嚴重的饑荒現象。1814年,拿破侖戰敗,簽訂《基爾條約》,丹麥無條件將挪威割讓給了瑞典,成立瑞典-挪威王國。“19世紀中期,饑荒再次在瑞典爆發。馬鈴薯的收成成為禍因,雖然它以前從營養方面對窮人而言是一種賜福—襲擊愛爾蘭的馬鈴薯疫病給瑞典帶來嚴重破壞,它造成了馬鈴薯在19世紀50年代嚴重欠收,而此時幾乎沒有什么替代性食物”。1863年起,由于沒有清潔的供水系統和垃圾的及時處理,造成的世界性霍亂疾病也開始流行,經記載,“1866年瑞典病死450萬人”,死亡人數之多令人戰栗。80年代,挪威內部政黨分立,政治分化嚴重。挪威的藝術界同樣紛爭不斷,“新型的藝術表現與激進的政治參與之間存在著明確的聯系”,左翼政府支持激進的藝術展覽,年輕藝術家們則一致擁護左翼政黨并支持民主。同時,蒙克的“導師”克羅格是該激進藝術群體的領頭人,支持和鼓舞了蒙克的藝術創作。蒙克自小經受疾病和死亡的陰霾,促使他在藝術上關心受苦的勞苦大眾,同他們站在同一戰線上。面對戰爭局勢的動蕩和國家的積貧積弱,蒙克深感革命的風暴為何如此猛烈。1885-1886年,蒙克創作《生病的女孩》,將死亡作為主題,記敘十五歲姐姐病逝前的情景。畫面中,女孩微弱的看著母親,母親則因無法面對孩子的病情,埋頭哭泣。蒙克沒有采用現實主義的描繪,以主觀化和平面化的處理方式,凸顯出主體人物之間的關系,將背景和透視關系模糊化。畫作的筆觸干澀蒼白,刮痕明顯,像草稿一樣狂放和隨意。畫面中,女孩蒼白的面容最為明顯,在紅色的頭發和綠色的裙子互相碰撞下,整個屋子被黑暗所包圍,充斥著灰暗沉郁的色調。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里曾提到:早在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早期所形成的那些與結核病浪漫化息息相關的隱喻。他們對結核病的風格化的描繪中,將柔弱病態的實際感受壓抑下去,轉化成為柔美浪漫的情感抒發。蒙克的“導師”克羅格也曾畫過患有結核病的妹妹,她的手里拿著一株正在萎謝的粉玫瑰,畫面仍舊賦予浪漫的情感色彩。蒙克試圖還原最初的悸動和陣痛,遵從自己的內心感受,畫著有呼吸有痛感活生生的人。這使他與傳統相背離,在后印象主義色彩的基礎上,吸收象征主義的氣氛,將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所有外在的現實轉化成第一幅關于“感覺”的表現主義油畫。這幅作品,雖然遭到保守派猛烈的抨擊,但卻是蒙克最重要的一幅畫,畫面中流露出的真情實感,激起了過著如此病態生活的人的共鳴。
(二)《吶喊》
19世紀末期,俄國瘟疫嚴重,英國市場經濟收縮,歐洲大陸的經濟蕭條使北歐市場收縮,波及挪威,支撐挪威經濟的木材出口和航運業陷于停頓,饑荒和經濟危機再次出現。而瑞典-挪威聯盟因相互爭奪更多的國家權益,早已出現嚴重危機,瑞典以武力相威脅,挪威內部政黨分立,資產階級和人民群眾之間出現嚴重的經濟斷層,社會陷入混亂。斯特林堡曾為窮苦人民發聲,“人不過是一堆垃圾、雞蛋皮、胡蘿卜梗、菜葉和破布條”。蒙克26歲時,父親暴病離世,妹妹的精神狀況出現危機,這無情的打擊深深啃食和吞噬著蒙克的心,使他作品中的情感表達比以往更加強烈。1892年,杜塞爾多夫派畫家阿德斯坦·努曼發現了蒙克藝術的偉大,推薦他參加了柏林藝術展覽,并認為必須將蒙克的畫展示給柏林藝術界中最先鋒的成員。“而德國藝術家協會的領袖安東·馮·沃納爾執掌了一套處理歷史和風俗題材的繪畫標準,表現當時盛行的愛國主義情緒,深得皇室的認可,而其他城市的各種機構皆與這種歷史風俗題材的官方沆瀣一氣”。蒙克的作品被官方指認為是無政府主義的挑釁而引發巨大輿論,作品被要求立即撤下。為此,以利伯曼為首的少數派退出委員身份,以此對抗德國藝術家協會。在此期間,蒙克經受著精神和心靈的隱疾,內心陷入無限的緊張和焦慮。他寫下“響徹寰宇,經久不息”這樣尖叫的一種情緒和畫面。1893年,整個歐洲的局勢開始分崩離析。比利時的工人階層出現大罷工,引起社會騷亂。德國正處于威廉二世統治時期,他向人民鼓吹“民族主義”,打著“國家”競爭力的旗號,開始增設軍事需要的鐵路、鐵甲軍艦等工業。對內實行擴軍備戰的計劃,對外進行殖民地的侵略擴張。此時,無政府主義者的人肉炸彈,在巴黎下議院爆炸。蒙克眼看著世界愈發瘋狂,道德秩序愈發混亂,幾近崩潰的情感,使他在藝術上尋找出口。終于蒙克創作了《吶喊》,又名《絕望》,他沖破了學院派的教條,直抒胸臆,將人生的困苦和社會的陰暗化為強烈的自我感受和主觀意象,以對比強烈的視覺色彩象征精神的隱疾,揭露內在現實的本質。他以極夸張的方式刻畫了一個扭曲且變形的主體人物,人臉被異化成骷髏,那張大了的嘴似乎發出了極為驚恐的聲響,猶如身處森林里的鬼一般在嚎叫。傾斜的橋和人物位置的遠近加強了畫面的空間感和層次感。遠處的峽灣和夕陽,以簡潔的色塊和夸張的色彩進行表現,韻律感的線條似乎帶有某種不可遏制的情緒。蒙克用鉛筆在血紅太陽上寫道“只有瘋子才能畫出”。蒙克帶著挪威人民的自我覺醒和身份焦慮,吶喊著世紀末身處戰爭年代的焦灼。“藝術成為了一個可以實現反抗的領域,為一種藐視傳統的沖動所驅使著,并希望在這樣一個權威社會中建立自己的獨立性”。1893年12月3號,蒙克的作品首次出現在柏林展覽中,瞬間震動德國的藝術界,成為了風暴的核心。同時,蒙克也為德國表現主義的興起發出了最強勁的一聲吶喊。
蒙克的藝術以其強烈的自我意識和藝術理念沖擊著德國威廉政權下的官方藝術和學院派藝術,對德國表現主義的興起有著極為關鍵的精神引領作用。他以北歐特有的陰郁色調和主觀表達情感的方式,描繪戰爭年代下震人心魄的心靈體驗和個人感受,影響了德國的先鋒藝術家們以一種全新的道德姿態和繪畫方式,對一戰前德國資本主義的社會都市文明提出批判和反思。
三、一戰爆發前后的德國表現主義思潮
自90年代開始,隨著西方的分裂危機日益嚴重,德國在高速發達的機械化進程中,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變得高度物質化和技術化。瘋狂的資本積累打碎了德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從市民階級到資產階級都開始全盤腐化,個體流入城市陷入身份和心靈的雙向缺失。在明顯富裕的國家,社會用強大的力量去創造財富時,工人階層的財富配比同之前卻更加分配不均。“據悉德國工人1894年增至590萬,他們的生活情況比英法還要壞得多,工資低,勞動強度大;對童工的濫用也是工業化時期一種臭名昭著的罪惡行為”。茨威格曾在《昨日的世界》里寫道:“《啟示錄》里那幾匹蒼白的大馬全都闖入我的生活,這就是:戰爭和饑饉、通貨膨脹和暴政,疾病和政治流亡”。這些無疑加深了德國民眾在現代性處境中的危機。同時,在皇帝威廉二世的統治下,藝術領域不得違背軍國主義宏大的歷史敘事和保守的封建浪漫主義色彩,并宣稱:“單純表現痛苦的藝術是對德國人民的犯罪”。
哲學家尼采曾斷言,為了使精神生活獲得重生,必須要對物質主義發起戰爭。這場精神革命,注定要發生在科學、宗教和道德式微的時代,這是一場由外轉向內的精神革命,并在文學、繪畫和音樂等最敏感的領域率先出現。此前,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藝術家紛紛宣布退出藝術家協會,成立先鋒藝術組織“分離派”。由少數的資產階級資助的“分離派運動”在歐洲各大城市開始如火如荼地進行著。1896年,弗洛伊德成立精神分析學說。1898年,柏林分離派正式誕生。在德國,隨著出版社,畫廊和展覽這種新型傳播方式的推廣,梵高、高更、蒙克等藝術先驅的作品開始廣為流傳。受先驅藝術家和美學思想的影響,在1905年和1911年成立了兩個年輕的德國先鋒派藝術團體:“橋社”和“藍騎士”,共同以繪畫的形式對抗威廉二世時期資產階級的審美趣味和被壓抑的價值觀念,賦予精神上和主觀上的個人意義。在世界戰爭的陰霾下,“橋社”的繪畫關注社會現實,以對比強烈和不協調的色彩描繪城市生活,對德國的意識形態進行批判。“青騎士”拒絕走入現實的混亂,只關注純主觀的精神世界,走向了抽象。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鐘聲敲響,他們的作品開始帶有攻擊性,流露出末世的氛圍。
隨著一戰的爆發,德國統治階層從根本上美化戰爭,宣揚“戰爭是上帝規定的法則”,是為民族和正義而戰。威廉二世在1914年8月1日宣稱:“當國家投入戰爭時,一切政黨應該停止爭吵,我們大家都是兄弟”。一戰前夕,威廉二世就有意拉攏表現主義畫家進入自己的陣營。“政府曾于1913年懇請分離派藝術家參加一個紀念國王統治25周年的展覽會,雖然他們最終拒絕參加,但政府還是認可了其作品的藝術價值。同樣重要的是,表現主義者開始擺脫其在德國藝術界的邊緣地位”。戰爭開始后,許多表現主義畫家也自愿服兵役,加入了戰爭的隊伍,并與德國的主流藝術出現了融合。德國現代藝術界的奠基人馬克斯·貝克曼曾說:戰爭可以滋養“藝術”。“青騎士”的代表藝術家弗蘭茨·馬爾克也曾把戰爭視為有助于藝術家自身發展的積累經驗。他們繪制了大量的草圖,汲取戰爭給予他們的素材和養料。例如志愿入伍的奧托·迪克斯,1915年創作的《作為戰神的自畫像》虛構了戰爭中混亂的景象,并將自己自詡為戰神,充滿了戰爭賦予作者的激情和榮譽感。但是,這場戰爭就是歐洲人的自殺,戰爭使用高精尖的科學武器,以更快的速度進行殺戮行為。表現主義藝術家開始對戰爭充滿了懷疑,1915年應征入伍的基希納創作《作為士兵的自畫像》,將自己描繪成雙手被截肢的戰士,失去了工作能力,諷刺了戰爭的殘酷和個人的禁錮。自愿擔任軍醫的貝克曼,于1917年創作《戴紅領巾的自畫像》,描繪了畫家開始滿臉狐疑的看著周圍,誠惶誠恐的心理被鳶然紙上。隨著戰爭的升級,戰爭場面增多,畫面開始出現肢解、混亂,不符合尋常意義上的美感。奧托·迪克斯于1923年創作《戰壕》,描繪了一場真實的毒氣戰,在充滿毒氣的溝壕里,或垂死掙扎的戰士,或被肢解的的殘忍和恐怖畫面。他的作品直面戰爭的殘酷,賦予人類道德的審視和評判。1924年完成《戰爭》版畫系列,繪制了共50幅戰時的真實場景,以一個親歷者的視角講述戰爭的冰冷和無情,使人們開始重新看待戰爭,轉入精神的思考。表現主義畫家們頑強地豎起了精神性的旗幟,將戰爭的神圣和榮耀揭穿,以繪畫的形式反叛和對抗著戰爭的真實面貌。
德國表現主義是時代下的必然產物,像歐洲必然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它是在戰爭的環境下孕育,在極端的社會生存環境下引起的藝術變革。
四、結語
本文對戰爭與表現主義的興起進行探究時,分為了三個方面進行論述:第一,論述蒙克的表現主義藝術與挪威國的社會問題,對表現主義先驅—蒙克早期的代表作品《病中的孩子》和《吶喊》進行時代解析。分析出蒙克的表現主義藝術來源:是在挪威國被英法大國蠶食所引發的國家分裂和社會危機,以及歐洲整體的戰前局勢的社會大背景下,引發了蒙克家庭的悲劇和個人傷痛經歷,從而發展起來的個人主觀情感的藝術創作和形式語言的藝術革新。同時,將蒙克《病中的孩子》與19世紀的浪漫派、挪威自然主義藝術在結核病主題上作對比,客觀論證了表現主義的平民階級立場、反抗歐洲資產階級政體對人民壓迫的藝術主張和個人主觀情感的藝術表現。第二,論述蒙克與德國表現主義之間的聯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的社會矛盾激增和德國表現主義藝術思潮的蔓延下,蒙克的作品被引薦到德國參加展覽,使他的藝術與德國的先鋒藝術建立了緊密聯系。在末世的戰爭陰影下,他以北歐特有的陰郁色調和極具自我意識的藝術精神,直接推動了德國表現主義的興起。第三,論述德國與德國表現主義之間的關系。德國表現主義的興起,有它自身發展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一戰前,它是在德國自身社會危機的基礎上,由德國快速發展的科技和工業引發,在整個歐洲的戰前局勢和表現主義思潮的背景下進行的。它的作品形式不同于蒙克對疾病、死亡和愛的主題表達,多以描繪市民階層的城市生活為主,進行社會和道德的藝術批判;或是脫離社會現實走向抽象性的藝術表達。一戰時期,德國的表現主義與德國強權的政治因素有關系。在威廉二世的政治號召下,德國表現主義的創作被“軍國主義”所利用,遮蔽了藝術表達的初衷,險些淪為德國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政治宣傳工具。但是,戰爭的真實和慘烈喚起了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家的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德國的表現主義藝術家們由此帶來了新一流的藝術革命。因此,探究戰爭與表現主義的興起,不可一概而論。他們雖同在戰爭的背景下,將戰爭的災難語境變為表現主義的催化劑,但他們依然有著不同的創作背景和藝術表現方式。同樣,在認識表現主義時,應該了解表現主義的興起與戰爭史實的根源性聯系,對它們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任何藝術作品的完成,任何一種藝術流派、藝術思潮的產生,一定與客觀的社會和歷史相關聯。因此,了解藝術史和懂得歷史學,才能全面的認識藝術和學習藝術。
參考文獻:
[1][瑞典]尼爾·肯特.世界歷史文庫—瑞典史[M].吳英,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191.
[2][中]戈丹,千舒.危及世界的100場災害(上)[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5:65.
[3][挪威]阿特勒·奈斯.蒙克傳[M].方芳,譯.南寧: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78.
[4][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M].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28.
[5][挪威]迦馬·喬·伯以森.挪威史:從遠古時代起[M].文凈,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0:255.
[6][瑞典]斯特林堡.斯特林堡小說戲劇選[M].李之義,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167.
[7][中]曹衛東.審美政治化:德國表現主義問題(德國學術第三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3.
[8][挪威]阿特勒·奈斯.蒙克傳[M].方芳,譯.南寧: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173.
[9][奧]斯特凡·茨威格.昨日的世界[M].徐友敬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6.
[10][英]J.M.羅伯茨.新知史·歐洲一萬年[M].李騰,史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9:459.
[11][美]約翰·拉塞爾.現代藝術的意義[M].常寧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04.
[12][中]曹衛東.審美政治化:德國表現主義問題(德國學術第三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8.
[13][中]曹衛東.德國青年運動(德國學術第一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6.
[14][中]丁建弘.世界歷史文化叢書—德國通史[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273.
[15][中]曹衛東.審美政治化:德國表現主義問題(德國學術第三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92.
[16][中]曹衛東.審美政治化:德國表現主義問題(德國學術第三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