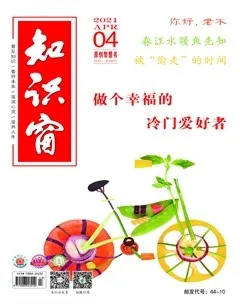你好,老木
黃愛梅
從醫院回來,心緒久久不能平靜。我必須寫一寫我的父親,他是這個多彩世界的一抹“亮色”。
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搬運生活的父親》,發表在當時很暢銷的《女友》雜志上。那本定位時尚都市的刊物,居然刊發了我這篇鄉土味濃郁的散文,料想是文章里我父親那種俗世中罕見的樂觀和堅強打動了人。
父親名叫黃紀杰,小名木林,已經72歲了。同事們喜歡叫他老黃或老木。“老木”這個名字頗有深意,不僅代表名字,還有“傻”“迂”的意思。何以得此“美名”,與他做過的那些獨特事情有關。
然而,每當想起這些事情,我眼前最先浮現的,是父親那張血肉模糊的臉。在一個白露未晞的秋日早晨,父親騎著電動車,懷揣著對生活滿滿的熱愛,勻速行駛在上班的路上。突然,一輛同向行駛的小貨車像喝醉了酒似的,往父親行駛的車道開過來,在即將碰上父親的時候,車子又突然往左側拐去,車尾狠狠地撞倒了父親。
天空瞬間傾斜,父親眼前一片漆黑,繼而一片血色。安全帽飛出去幾十米遠,骨骼斷裂的聲音從他身體的不同部位傳來。
“眼內出血、淚管斷裂,臉部多處撕裂,縫針五處,手背皮肉深度撕裂,縫針七八厘米長,手腕骨折,手肘腫大,有無骨折等拍片結果……”弟弟把父親傷勢告訴我的時候,我雙腿發軟,眼底刺痛。
在醫院病房里,父親和從戰場上掛彩的傷兵并無兩樣,蚯蚓一樣的傷疤布滿臉頰,手上打著繃帶。
“爸爸!”我們叫他。
片刻,父親緩緩睜開了眼睛,做過手術的眼睛,剛摘了紗布,一片血紅。
“你們怎么來了?”父親困難地吐出一句話。沒牙的癟嘴明顯漏風,嘴唇四周冒出的一茬灰白胡須使整張臉更加滄桑憔悴。父親的假牙不中用了,一個月以前他取掉了假牙,重新做了一副,還在等待牙齦恢復好了再裝上去。上次在照片中,我看到取掉假牙的父親,大為驚駭,父親怎么突然老了十歲?而現在躺在病床上的父親,更加羸弱,他終于像個老人了。
父親翕動著嘴唇,不滿地說:“我都和交警說了,輕微處理,不要打電話通知子女。”
“都傷成這樣了,還輕微?”我們幾人你一言我一語,開始接力數落父親的任性。
父親卻嘴角一咧,笑了。被貨車撞倒、緊急搶救、一系列檢查、接連幾個手術……歷經一天一夜的折磨后,他忍不住笑了,說:“我還活著,真是命大!”
聽弟弟說,父親最初是被送進八里湖的新醫院,但新醫院不敢做他的眼科手術,所以轉到了老醫院。做手術之前,醫生反復強調風險,要求家屬簽了一摞風險責任書。父親對醫生說:“你們不用擔心,如果這只眼睛治不好,我還有另一只眼睛呢,不影響我看世界。”這些話把醫生都說愣了,大概他們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的病人。
出車禍之前,父親在表弟的電子加工廠做事,好心的表弟為了滿足父親的勞動需求,給他安排了一份園林綠化工作,父親格外珍惜他的勞動機會,每次都是帶著巨大的幸福感和滿足感來完成他的工作。廠區是早上八點上班,他七點多就開始干活了,他總是笑著說:“能勞動就是福啊!”因為在工廠特別受尊重和照顧,父親無以為報,就只能偷偷地多做事,就像沒退休以前,他在單位也總是重活、累活都往自己身上攬,因此很多人都認為他傻到了家。
更讓人驚訝的是,肇事司機把父親送到醫院后,父親對他竟然沒有一絲怨意。他受到這么大的傷害,血人似的躺在病床上,還誠懇地對肇事司機說:“耽誤你的生意了,真是不好意思!”
“爸,你以后可要消停了,就不要再出來做事了,你也要替我們想一想。”我們這樣勸父親。
“哎!”父親嘆息一聲,“你們不知道歇下來有多難受,動動筋骨才是最健康的。”
我們幾人圍著父親,開始討論他這次退休后的晚年生活。談話間,醫生進來查房, 護士進來換藥,他們都驚嘆父親身體的機能,竟然比年輕人恢復得還快。
父親自豪地說:“為什么我的身體這么好啊?因為我天天勞動,而且我吃的是天地間最天然的食物。”談起家鄉的山莓、野生藍莓、桑葚、山楂、楊梅、獼猴桃、刺梨……父親受傷的眼睛里透出一抹光亮。那些我們兒時吃過又叫不出學名的野果子,是父親生命的底色,在山村田野間,他像一個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的孩子。
我們幾人圍在父親的床前,談話的內容漸漸從車禍、手術、康復等關鍵詞轉到了童年時代。我們的童年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是現在城里的孩子想象不出來的。所以,談起這些,我們的心情也漸漸開朗了起來,父親傷痕累累的臉上也布滿了笑容。此刻,他好像不是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而是回到了我們的童年時光。那時候,只有在過年,父親才會有時間和我們兒女一起說笑談天。
我們享受著一場精神的盛宴,好像父親遭遇這么大的罪和痛,只是為了把平日里忙得連電話都沒空聯系的我們聚到一起,聽父親講述我們童年的各種趣事。
兩個星期后,父親出院了。他對醫生說:“躺在醫院里真是無趣極了,我想去山里采藥、摘野果子。”
弟弟說:“你也不能再一個人去爬山了,如果出了意外,怎么辦?”
父親說:“哪有那么多意外?傻人有傻福啊!”
屬牛的父親,內心里卻像兔子一樣好動。哎,遇上這樣獨特的父親,我們也只能祈求“傻”人有“傻”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