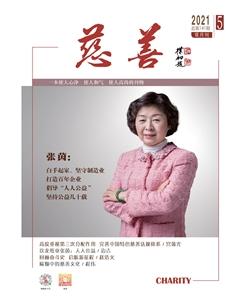我的大嫂
劉巨真
俗話說,“長嫂若母”,這話一點不假。我今年八十多了,幾十年風風雨雨,可以說,隨著年歲的增長,體會也愈來愈深。“大嫂”這兩個字,經常地出現在腦海里,隔些日子不通個電話,就好像缺了點什么。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嫂子,嫂子……”那首情深意篤的老歌。
我的大嫂,其實是我的大表姐。我的姥姥家門戶大,人口多,在當地也算得上名門望族。我的姥爺兄弟十人,他行二。大嫂是我六姥爺家的孩子。她嫁給我大哥,應該說親上加親。那是1956年的夏天,我在長春航校當兵任職的大哥第一次探家,父母便忙忙活活地要給他定親成家。對象是哪一個呢?我好奇地問母親,母親說,到時候你就知道了。我當時讀初三,正是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半大小子的年齡,就等著,欲一睹未來嫂子的風采。記得是“八一”那天下午,一輛馬車停在我家大門口,母親領著老舅家的大表姐下車走進院子里。我跟在后面不住地左顧右盼,好像不認識她似的。大表姐伸手拽了一下我的耳朵,說:“看什么?你不認識我,我可認得你。你小的時候,我姑姑抱著你的照片,我還保存著呢。”
母親笑著說:“還不過來叫大表姐。”我喊了一聲大表姐,就仔細地看她。只見她紅紅的臉蛋兒,眉清目秀,俊俏而靈動。她的穿著顯得干凈利索,藍條紋的“的確良”上衣,淺灰色的制服褲子,腳上是一雙黑絨拉帶布鞋,一副樸實的工人形象。那時“的確良”剛剛面世,是高貴的布料,只有城里的人才穿得起。第一次會面我喊她大表姐,過了兩年,我們第二次會面,我就喊她大嫂了。
大嫂是大連石油七廠的化驗員,大哥轉業到吉林市一所中學擔任校長,她就隨之轉到吉林油脂廠工作,在美麗的江城安家落戶了。我那時在新金一中讀高中,雖然相隔千里,但她的品質和吃苦耐勞的精神,大哥在信中屢屢提起。他們的住處是學校的兩間庫房,冬冷夏潮,老鼠猖獗,大嫂從無怨言。三年困難時期,她挺著個大肚子,每天推著個四個輪子的鐵轱轆車,帶著大女兒每天步行七八里路上下班,她從未喊過一聲累。“文革”期間,大哥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她承受了多大的壓力!由此,我對大嫂的敬重已然無以言表。
更令我感動的是,大嫂有一顆慈母心。她對自己的兩個女兒是這樣,對大哥下邊的弟妹們也是關愛有加。我的父母是農民,家境不富裕。1959年,我讀高中時,腰痛休學,大哥大嫂把我接到長春,經吉林醫大附屬醫院診斷為腰椎骨結核,治療花掉了大哥的全部軍轉費。他們還為我拉下了不少饑荒。母親對我說:“你是攤上了一個好嫂子,她在我面前,從來就沒有提過一個錢字。”1964年,我考入遼寧財經學院,每月的伙食費15元。大嫂怕我交不起,四年里,每次都是準時寄來,從來沒有誤過。1968年,我走出校門,在黑龍江省克山縣沈陽炮兵學院某部鍛煉。當地的氣候,冬天常常零下40攝氏度左右,凌晨的“鬼齜牙”尤甚。大嫂聽說了,擔心我挨凍,買了毛線,織成毛衣,連同大哥轉業時帶回的軍用皮帶寄到連隊,令我的同學十分羨慕。這是我此生的第一件毛衣。那時,人們的生活水平不高,產品不夠豐富,毛衣被視為奢侈品。
轉眼間,我們哥幾個都退休了,回到家鄉安家落戶。幾個家庭雖同在大連地區,但湊在一起并不容易。母親健在時,她一個電話,全家老少都立馬聚集在她身邊,老人離世后,大哥大嫂就擔負起母親的職責。弟妹們有什么事,都愿意向大哥大嫂討教;大哥大嫂對弟妹們也是有求必應。在大哥大嫂的率領下,妯娌們互敬互愛,孩子們也團結一心。從2016年開始,我們四兄弟及其孩子們,30多口人的一大家子,每年都歡聚一次。每當此時,我都會想起“長嫂若母”這四個字。她在我的心目中,是永遠的大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