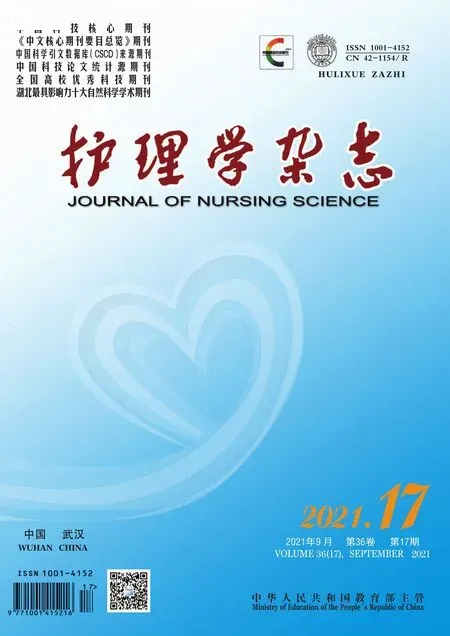癌癥患者診斷知情心理體驗(yàn)質(zhì)性研究的Meta整合
盛源,高偉,姜玫,劉德山,尹慢慢,鄭雪露,吳廷蘭,范春梅
癌癥是全球第二大死因,告知疾病診斷無(wú)疑會(huì)引起患者不同程度的心理應(yīng)激反應(yīng)[1]。但無(wú)論是后續(xù)治療還是長(zhǎng)期管理都必須建立在患者知情的基礎(chǔ)上,而不同人群對(duì)此也持有不同的態(tài)度。告知患者癌癥診斷是西方國(guó)家的普遍做法,但在東方或發(fā)展中國(guó)家,醫(yī)生往往遵從患者家屬的意見選擇隱瞞疾病診斷[2]。隨著醫(yī)學(xué)研究的深入,知情同意的實(shí)施日臻完善,人們對(duì)于癌癥告知的觀念也悄然發(fā)生變化。據(jù)文獻(xiàn)報(bào)道,60%~80%的患者希望被告知真實(shí)的疾病診斷,并提供不同程度的疾病信息[3],臨終前約60%的患者家屬希望告知患者真實(shí)的病情,其中80%的家屬希望由醫(yī)務(wù)人員完成疾病診斷告知工作[4]。因此,由醫(yī)務(wù)人員主導(dǎo)的有計(jì)劃、有策略的疾病診斷告知方式已經(jīng)成為患者主要知情手段。近年來(lái),癌癥患者診斷知情過(guò)程心理體驗(yàn)的質(zhì)性研究不斷增多,但單一的質(zhì)性研究結(jié)果受地域、文化背景和疾病類型等差異影響,其結(jié)果指導(dǎo)臨床實(shí)踐有限。本研究對(duì)癌癥患者診斷知情經(jīng)歷和體驗(yàn)的質(zhì)性研究結(jié)果進(jìn)行Meta整合,旨在為制訂更全面和更有針對(duì)性的癌癥患者診斷知情方式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文獻(xiàn)納入與排除標(biāo)準(zhǔn) 納入標(biāo)準(zhǔn):①P(Population)研究對(duì)象,由臨床醫(yī)生明確診斷為癌癥(含血液腫瘤)的患者;②I(Phenomenon of Interest)感興趣現(xiàn)象,患者的體驗(yàn)、感受;③Co(Context)情境,患者診斷知情過(guò)程;④研究方法,質(zhì)性研究。排除標(biāo)準(zhǔn):①非中英文文獻(xiàn);②信息不完整或無(wú)法獲取全文;③使用混合研究設(shè)計(jì),其中量性研究數(shù)據(jù)無(wú)法分離。
1.2文獻(xiàn)檢索策略 計(jì)算機(jī)檢索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Medline、中國(guó)知網(wǎng)、萬(wàn)方數(shù)據(jù)等數(shù)據(jù)庫(kù)從建庫(kù)至2020年12月收錄的關(guān)于癌癥患者診斷知情心理體驗(yàn)質(zhì)性研究文獻(xiàn)。中文檢索詞為“癌癥/腫瘤”“患者、病人”“知情、告知”“心理、體驗(yàn)、感受”“質(zhì)性研究”。英文檢索詞為“neoplasms,cancer,tumor, carcino*,malignan*”“notification,inform*,disclos*,truth-telling,break”“psycholog*,experiences,perceptions,emotion*,feeling*”“qualitative,narrative,phenomenolog*,grounded theory”。
1.3文獻(xiàn)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dú)立檢索并閱讀文題,排除明顯不相符文獻(xiàn)后,進(jìn)一步閱讀摘要和全文,以確定是否納入本研究,對(duì)于遇到分歧的文獻(xiàn),第3名研究者參與討論并進(jìn)行判斷。資料提取內(nèi)容包括作者、地區(qū)、研究對(duì)象、研究方法、感興趣的現(xiàn)象、研究場(chǎng)所和主要結(jié)果。
1.4文獻(xiàn)方法學(xué)質(zhì)量評(píng)價(jià) 采用JBI質(zhì)性研究質(zhì)量評(píng)價(jià)工具[5]對(duì)納入文獻(xiàn)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沖突時(shí),第3名研究者參與討論并進(jìn)行判斷。評(píng)價(jià)內(nèi)容共10項(xiàng),每項(xiàng)以“是”“否”“不清楚”或“不適用”評(píng)價(jià)。文獻(xiàn)質(zhì)量A級(jí)為全部滿足質(zhì)量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偏倚可能性較小;B級(jí)為部分符合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偏倚可能性中等;C級(jí)為完全不符合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偏倚可能性較大。最終納入質(zhì)量等級(jí)為A級(jí)和B級(jí)的文獻(xiàn)。
1.5資料分析方法 采用NVivo12版軟件進(jìn)行數(shù)據(jù)提取,采用匯集性整合方法[6]對(duì)研究結(jié)果進(jìn)行整合,即研究人員反復(fù)閱讀原始研究、充分理解研究者含義后提取研究結(jié)果,形成新類別并整合成主題。
2 結(jié)果
2.1文獻(xiàn)檢索結(jié)果及文獻(xiàn)基本特征 初步檢索出相關(guān)文獻(xiàn)1 333篇,經(jīng)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18篇文獻(xiàn),其中英文文獻(xiàn)16篇[7-22],中文文獻(xiàn)2篇[23-24]。納入文獻(xiàn)的基本特征及方法學(xué)質(zhì)量評(píng)價(jià),見表1。
2.2Meta整合結(jié)果
通過(guò)反復(fù)閱讀和理解,將文獻(xiàn)提煉出的62個(gè)主題歸納成12個(gè)新的類別,綜合成3個(gè)整合結(jié)果。

表1 納入文獻(xiàn)的基本特征及方法學(xué)質(zhì)量評(píng)價(jià)
2.2.1整合結(jié)果1:多重因素影響癌癥患者對(duì)診斷的接受度
2.2.1.1類別1:患者承受能力 ①生活經(jīng)歷。有家族史的患者較容易接受診斷信息(“我老爸也是這個(gè)樣子,我自己心里有數(shù)”[24])。②心理狀態(tài)。多數(shù)患者對(duì)癌癥存在焦慮和恐懼心理,但老年人更愿意以平常心對(duì)待診斷(“我認(rèn)為癌癥就像感冒一樣,死亡在等著我們所有人”[17])。③心理準(zhǔn)備。通過(guò)常規(guī)體檢途徑獲知疾病診斷的患者,往往缺乏心理準(zhǔn)備(“我一直吃得很好,也經(jīng)常鍛煉身體,現(xiàn)在卻在醫(yī)院里。這本該是一次常規(guī)體檢”[19])。④性格特點(diǎn)。對(duì)樂(lè)觀、積極的患者告知疾病診斷,有利于對(duì)后續(xù)治療的配合(“比起一種同情的方式,我更喜歡直來(lái)直去地被告知,找到問(wèn)題總比到處亂投醫(yī)好”[9])。⑤經(jīng)濟(jì)水平。獲悉疾病診斷后患者往往考慮的是能否支付起巨額的醫(yī)療費(fèi)用(“需要付一大筆錢,我負(fù)擔(dān)不起”[15])。
2.2.1.2類別2:家屬角色定位 西方國(guó)家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權(quán)利不可侵犯,在疾病知情中家屬承擔(dān)的角色往往是陪同者(“我的妻子在我身邊,因?yàn)槲医⊥运龝?huì)替我想到一些問(wèn)題”[7])。在東方或發(fā)展中國(guó)家,由家屬?zèng)Q定是否告知患者實(shí)情(“我是最后一個(gè)知道診斷的人,在任何人之后,包括我的家人、朋友甚至我丈夫的親戚”[14])。
2.2.1.3類別3:醫(yī)護(hù)人員告知準(zhǔn)備與水平 患者對(duì)疾病的認(rèn)識(shí)往往是循序漸進(jìn)的,醫(yī)生需要預(yù)留充足的時(shí)間回答患者的疑問(wèn)(“醫(yī)生太忙了,只有一會(huì)兒的時(shí)間”[13])。部分醫(yī)生面對(duì)患者時(shí)表現(xiàn)得過(guò)于緊張(“醫(yī)生很緊張,給出診斷后他沒有給我任何安慰”[7])。
2.2.1.4類別4:疾病特點(diǎn) 患者對(duì)不同疾病診斷的接受度是不同的(“我真的不知道會(huì)發(fā)生什么,因?yàn)樗?病情)變化得太快了”[10])。由于疾病確診困難,過(guò)多的檢查會(huì)使患者情緒波動(dòng)較大(“天天抽血,抽血的結(jié)果沒有告訴我,抽血的目的是什么?”[24])。
2.2.2整合結(jié)果2:診斷告知方式方法
2.2.2.1類別1:合適的告知環(huán)境 ①安靜。應(yīng)盡量選擇安靜、獨(dú)立和不被人打擾的房間(“當(dāng)時(shí)周圍有很多人,我覺得很難受”[23])。②家屬陪同。家人是疾病告知過(guò)程中最好的陪伴者(“我兒子陪我一起去看的醫(yī)生,有他陪伴在身邊真好”[13])。③建立信任。良好的醫(yī)患關(guān)系是后續(xù)治療的前提(“我完全信任我的醫(yī)生,比任何人都更相信他的話”[20])。
2.2.2.2類別2:告知內(nèi)容因人而異 患者對(duì)診斷知情的方式和內(nèi)容因人而異,現(xiàn)階段主要存在3種疾病告知模式。①全部告知模式。心理素質(zhì)較好的患者,疾病知情有利于患者配合治療(“知道了有利于治療,任何病都是這個(gè)樣子的”[24])。②選擇性告知模式。過(guò)多的信息有時(shí)會(huì)加劇患者的焦慮(“太多的醫(yī)療細(xì)節(jié)只會(huì)增加我的苦惱,而不是緩解焦慮”[17])。③隱瞞病情模式。晚期患者知情反而會(huì)使其喪失希望,放棄治療(“醫(yī)生告知我他們無(wú)能為力的話一直出現(xiàn)在我的腦海里”[9])。
2.2.2.3類別3:注意用詞 ①委婉。患者往往無(wú)法承受直接告知疾病診斷帶來(lái)的壓力和打擊(“這樣的事情真的不應(yīng)該一下子說(shuō)出來(lái),應(yīng)該慢慢地被告知”[21])。②誠(chéng)實(shí)。患者希望獲得的疾病信息是真實(shí)的(“剛開始跟我講的(病情)是還可以,但后來(lái)又跟我家屬談話,當(dāng)我手術(shù)結(jié)束恢復(fù)得比較好了,我姐姐才告訴我(實(shí)際病情)”[23])。③謹(jǐn)慎。獲悉信息前后不一致會(huì)加劇患者的負(fù)性情緒(“嚇懵了,一開始說(shuō)這是可以治愈的,后來(lái)又告訴我不能手術(shù)”[7])。④清晰。告知的信息應(yīng)盡量通俗易懂,減少專業(yè)術(shù)語(yǔ)(“我們不知道這些專業(yè)術(shù)語(yǔ),也不知道是良性的還是惡性的”[7])。
2.2.2.4類別4:提供信息應(yīng)全面 ①疾病相關(guān)信息。患者希望獲得關(guān)于疾病的相關(guān)信息,包括疾病誘因、臨床表現(xiàn)和治療方案等(“我想知道這個(gè)病,治療的預(yù)后會(huì)怎么樣,還需要注意哪些方面”[24])。部分誤導(dǎo)性信息會(huì)降低患者的治療積極性(“看了他們給我的那本書,書上說(shuō)化療沒有多大意義”[11])。患者知曉的預(yù)后信息應(yīng)盡量是積極和樂(lè)觀的(“當(dāng)醫(yī)生告訴我是可以治療的,我很激動(dòng)”[7])。②日常生活的影響。了解疾病對(duì)生活的影響,有利于患者調(diào)整和適應(yīng)新的生活方式(“我出現(xiàn)了類似女性更年期的癥狀,如潮熱、出汗”[11])。③治療效果理想的病友信息。積極的病友信息會(huì)增強(qiáng)患者戰(zhàn)勝疾病的信心(“我看到其他和我一樣的人都在快樂(lè)的生活,這使我放松很多”[7])。
2.2.2.5類別5:社會(huì)支持 社會(huì)支持是癌癥患者緩解經(jīng)濟(jì)壓力的重要手段(“我得到了社會(huì)救助小組的幫助,很棒的機(jī)構(gòu)”[11])。醫(yī)護(hù)人員應(yīng)盡可能表現(xiàn)出真誠(chéng)溫暖的態(tài)度(“我好像擁有了整個(gè)世界,感到很有力量,覺得他(醫(yī)護(hù)人員)完全理解了我”[20])。
2.2.3整合結(jié)果3:獲悉患病信息后的改變
2.2.3.1類別1:獲知病情信息后的反應(yīng) ①否認(rèn)。年輕患者很難從家庭的照顧者角色轉(zhuǎn)變?yōu)楸徽疹櫿呓巧?“我從不認(rèn)為我生病了,但你們都告訴我生病了”[19])。②懷疑。患者在得知疾病診斷后往往處于懷疑與震驚狀態(tài)(“我也有其他的一些健康問(wèn)題,但這個(gè)真震驚到了我的內(nèi)心”[10])。③接受。部分樂(lè)觀、理智的患者會(huì)接受疾病帶來(lái)的威脅并積極配合治療(“它會(huì)持續(xù)幾個(gè)月,然后生活就會(huì)繼續(xù)”[19])。
2.2.3.2類別2:治療方式的抉擇 ①配合治療。隨著醫(yī)療水平的進(jìn)步,越來(lái)越多的患者接受治療(“當(dāng)我知曉診斷時(shí),我不得不制訂一個(gè)時(shí)間表,把治療融入我的生活”[19])。②中立狀態(tài)。多重因素使患者及其家屬對(duì)治療方式處于觀望態(tài)度(“真的別無(wú)選擇,要么接受治療,要么去死”[10])。③姑息治療。部分患者認(rèn)為生命的質(zhì)量要比生命的長(zhǎng)度更重要(“我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治愈和痊愈的區(qū)別。我知道在這里不可能恢復(fù)健康,但是治療是一個(gè)直到最后一刻都在進(jìn)行的過(guò)程……我可以接受”[22])。④放棄治療。經(jīng)濟(jì)條件和疾病惡化往往是影響患者放棄治療的首要因素(“我覺得在浪費(fèi)時(shí)間,治了也沒什么效果”[23])。
2.2.3.3類別3:向他人隱瞞患病信息 ①害怕與擔(dān)心。部分獲知疾病診斷的患者會(huì)選擇對(duì)家人隱藏患病信息(“我的家人無(wú)法承受這種悲痛,我愛他們”[14])。②輕視與尊嚴(yán)喪失。患者擔(dān)心告知他人后會(huì)引起嘲笑與疏遠(yuǎn)(“他們只會(huì)撕開我的傷口,就好像我就要死了一樣”[16])。
3 討論
3.1注重人文關(guān)懷,提升癌癥患者對(duì)診斷的接受度 隨著醫(yī)療技術(shù)的進(jìn)步,癌癥診療方式、治療手段有了大幅提高,但患者的焦慮和抑郁水平卻遠(yuǎn)遠(yuǎn)高于健康人群,影響著患者的身心健康。陳行堯等[25]的研究顯示,有效的人文關(guān)懷可以提升癌癥患者對(duì)診斷的接受度,降低焦慮和抑郁水平,繼而提升治療效果。本研究顯示,合適的告知環(huán)境、家屬的陪同和建立平等信任的醫(yī)患關(guān)系等人文關(guān)懷措施有利于疾病告知工作的順利開展,但家庭的支持、社會(huì)的理解才是癌癥患者獲知疾病診斷后能否真正接受疾病、融入社會(huì)的關(guān)鍵因素。因此需對(duì)患者加強(qiáng)人文關(guān)懷:第一,建議腫瘤病房結(jié)合實(shí)際需要建立一個(gè)安靜、允許家屬陪同的談話環(huán)境,醫(yī)護(hù)人員在與患者逐步建立信任并詢問(wèn)信息需求后,再告知患者患病信息。告知時(shí)用詞應(yīng)委婉與謹(jǐn)慎、內(nèi)容真實(shí)與清晰,盡量先告知積極的診療信息。告知過(guò)程中注意患者的情緒變化,做好患者及家屬的情緒安撫工作,必要時(shí)調(diào)整告知策略。第二,合理安排班次,給臨床醫(yī)護(hù)人員預(yù)留充足的談話時(shí)間,根據(jù)患者情緒和行為變化選擇合適的告知方式。第三,融入社會(huì)、適應(yīng)生活是癌癥患者接受疾病診斷的重要表現(xiàn),建議醫(yī)院多開展疾病公益講座,逐步糾正“絕癥”等大眾誤區(qū),從而使社會(huì)接納癌癥患者,進(jìn)而改變患者的自卑心理。
3.2選擇合適的診斷告知模式以減少二次傷害 越來(lái)越多的癌癥患者希望被告知真實(shí)且全面的疾病信息。告知疾病真實(shí)診斷已成為一種趨勢(shì),但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適合被告知疾病的所有信息。受年齡、生活背景和醫(yī)療水平等多因素影響,不同患者得知癌癥診斷后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不同的。本研究結(jié)果顯示,獲知疾病診斷后,患者會(huì)處于否認(rèn)狀態(tài),存在焦慮、恐懼和逃避心理,可能與癌癥患者發(fā)生心理應(yīng)激障礙有關(guān)[1]。因此,醫(yī)護(hù)人員在開展疾病告知前需評(píng)估患者文化背景、經(jīng)濟(jì)水平、心理狀態(tài)等,根據(jù)評(píng)估結(jié)果選擇適宜的疾病診斷告知模式,針對(duì)心態(tài)樂(lè)觀或具有醫(yī)學(xué)背景的疾病初期和中期患者,可選擇全部告知模式;選擇性告知模式適用于絕大多數(shù)患者,在保證告知真實(shí)性的情況下,應(yīng)盡量告知積極的治療信息;對(duì)于病情嚴(yán)重的老年患者或兒童,可選擇隱瞞病情模式,善意的謊言可以減少告知疾病信息帶來(lái)的二次傷害,延長(zhǎng)患者的生命。
3.3提高醫(yī)護(hù)人員溝通能力 癌癥診斷告知是醫(yī)患溝通的重要內(nèi)容,在告知過(guò)程中需遵循循序漸進(jìn)、慎重、個(gè)體化和真實(shí)準(zhǔn)確等原則,對(duì)醫(yī)護(hù)人員的溝通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26]。本研究顯示,未接受過(guò)系統(tǒng)培訓(xùn)的臨床醫(yī)護(hù)人員在開展疾病告知工作時(shí)表現(xiàn)為過(guò)度緊張和不自信,而疾病相關(guān)知識(shí)、心理素質(zhì)和責(zé)任心也會(huì)間接影響疾病診斷的告知效果。建議醫(yī)院或科室緊密結(jié)合臨床需要,定期開展溝通模擬教學(xué),以提高醫(yī)護(hù)人員溝通能力。
3.4完善經(jīng)濟(jì)補(bǔ)助政策以降低患者經(jīng)濟(jì)壓力 本研究顯示,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是影響癌癥患者診斷接受度的因素之一。近年來(lái),癌癥患者生存率不斷增高,越來(lái)越多的患者對(duì)腫瘤疾病的認(rèn)知和應(yīng)對(duì)態(tài)度有了較大改觀,然而新的問(wèn)題卻接踵而至。隨著治療周期的增加,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成為癌癥患者獲知疾病診斷后拒絕或猶豫治療的首要因素。建議相關(guān)部門針對(duì)偏遠(yuǎn)地區(qū)、貧困家庭提供一些補(bǔ)助政策,減輕患者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從而提升癌癥患者對(duì)診斷的接受度。
4 小結(jié)
本研究以Meta整合方法探索癌癥患者診斷知情的經(jīng)歷和體驗(yàn),診斷知情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不同患者獲知疾病診斷后的反應(yīng)也不同,如何與癌癥患者及家屬溝通,選擇最合適的疾病告知方式是每個(gè)醫(yī)務(wù)工作者面臨的問(wèn)題。本研究納入的文獻(xiàn)僅以患者視角了解疾病診斷知情時(shí)的經(jīng)歷和體驗(yàn),后續(xù)研究可以納入醫(yī)方和家屬視角探究癌癥患者診斷知情時(shí)的經(jīng)歷和體驗(yàn),以增加其實(shí)踐的指導(dǎo)性。
- 護(hù)理學(xué)雜志的其它文章
- 代理決策者預(yù)立醫(yī)療照護(hù)計(jì)劃參與問(wèn)卷的漢化及信效度檢驗(yàn)
- 河北省老年人生產(chǎn)性養(yǎng)老現(xiàn)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 基于信息化管理平臺(tái)的延續(xù)護(hù)理對(duì)產(chǎn)婦盆底功能康復(fù)的影響
- 前列腺增生手術(shù)患者膀胱功能康復(fù)訓(xùn)練方案的構(gòu)建
- 基于IMB模型的初產(chǎn)婦及配偶雙主體母乳喂養(yǎng)健康教育
- 泌尿外科實(shí)習(xí)護(hù)生人文關(guān)懷臨床教學(xué)的設(shè)計(jì)與實(sh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