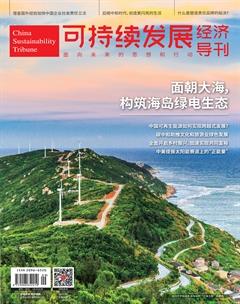中美提振太陽能賽道上的“正能量”
吳昌華
9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主動要求”與中國領導人通話。媒體報道披露的細節不多,“坦誠”和“公開”地對待彼此,是雙方認可的“姿態”。白宮發表的聲明,用“廣泛和戰略性討論”來描述兩國首腦的通話“氣氛”,在涉及的內容上,涵蓋了“雙方利益一致的領域和雙方在利益、價值和觀點上有歧義的議題”。中國官方媒體對此次通話也用了“坦誠”和“深度”來描述,尤其提到,世界的未來,很大程度上依賴兩國能夠處理好雙邊關系,而且將此定位在雙方必須回答的“世紀問題”。
我非常認同這個定位。在氣候變暖、疫情繼續肆虐、經濟恢復緩慢等諸多全球危機和挑戰面前,世界上兩個最大經濟體的“求同存異”和“齊心合力”,已經成為人類“穹頂突圍”的必然選擇,而且,這一定是“共贏”遠遠超出“所失”的不二出路。其中,應對氣候變化是雙方認同的“利益一致”的聚焦點,加速推進清潔能源轉型已經具備相當的“合力”基礎。正在全球太陽能賽道上“馳騁”的中國和美國,要借力兩國首腦開始加深溝通帶來的“東風”,用實際行動交出一份這個“世紀問題”的靚麗答案。
“勵志”和“合力”
9月8日,拜登政府宣布美國歷史上“最激進”的太陽能計劃,2050年,45%的電力來自太陽能。2020年,全美電力不到4%來自太陽能,這是一個從4%到45%的跨越。美國政府承諾到2050年實現凈零碳排放,這無疑將起到重大的作用,也是促進清潔能源轉型的重要舉措。《紐約客》一篇文章稱,這也許會成為美國歷史上被記住的一個“重要時刻”,一個能源“登月”計劃。也有人說,這個太陽能計劃更加“雄心勃勃”,因為阿波羅項目聚集了當年美國全國的科技能力來將一個人“送上”月球,而太陽能計劃更像是要讓所有人“登陸”到一個“非常新奇”的地方。
我將拜登此舉放到中國已經在引領的全球太陽能賽道上去看,頓覺振奮,也看到了中美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合作”的潛力,希望在這個賽道上,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可以“相互切磋”,在競爭中謀求共贏和攜手促進,形成合力和正能量。過去10年中,美國太陽能行業年均增速49%,中國太陽能行業年均增長76%。過去10年的實踐和探索,兩國在太陽能行業都提升了自己的能力,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寶貴的“學習曲線”,也奠定了太陽能發電成本快速下降的牢固基礎,促成了“安裝翻一倍,成本下降30%”的現實存在。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太陽能組件生產國,2020年提供了全球90%的需求;太陽能發電,中國從2010年的不到0.86GW的起點,“沖到”2020年的253GW。一方面,在快速降低成本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不斷加快步伐,推進國內清潔能源轉型。2020年年底,習近平主席向全球宣布了中國加速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新目標,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裝機達到1200GW,如果大約風能和太陽能分半,那就意味著,今后10年,中國的太陽能裝機要再翻一番。目前看來,這個難度不會太大,中國很可能、也應該會“超額”完成計劃。
“理想”與“藍圖”
目前,美國宣布的計劃還只能被稱為一個“藍圖”,真正落地需要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需要國會立法。最近能源部的一份《太陽能未來研究》報告發現,不斷降低的成本、實施新的政策、加速安裝太陽能板三個“點”共同發力,美國到2035年就可以實現40%電力來自太陽能。為了實現目標,美國今后十年至少要“翻兩番”。所以,到2050年,完成45%的目標,也似乎沒有太大“懸念”。
現任能源部長在一份新聞稿中說,“實現這個光明的未來,要求在確保平等基礎上大規模安裝可再生能源,也需要強有力的去碳政策。” 這些政策已經在目前國會兩黨支持的《基礎設施法案》和《就業法案》有明確闡述,也包含在拜登的“建回更好未來”的議程當中。于是,我們明白了那個還“徘徊”在國會的3.5萬億“預算調和”的至關重要,因為那就是剛剛宣布的太陽能目標和計劃的第一筆“預付款”。
能源部發布的報告中包括了一些政策目標,但是將更多的細節留給了國會去決定。報告對資金投入和產出描繪了一幅“藍圖”:一是到2050年目標實現,大約需要5620億美元的投入來建設太陽能項目;二是這個投資成本有效,最終可以節省1.7萬億美元,通過避免的氣候破壞和改善的空氣質量來兌現;三是繼續不斷的科技進步支撐裝機容量的大幅上升,也會極大地控制電價,增加太陽能的儲能量,建設韌性;四是太陽能成為最廉價和最高速增長的清潔能源,到2035年,足以為美國所有家庭提供充足的清潔電力。
“陷阱”與“懸念”
正如能源部報告所言,落實太陽能目標,美國需要在科技、能源產業、就業和人們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的廣泛變革,需要房產主、商業和政府幾萬億美元的投資;建立在煤電、燃氣發電和核電基礎上的電網,幾乎需要全面改造,增加電池、輸電線和其它各種技術,以確保吸納太陽能發電,確保將太陽能發的電傳輸到各個角落。
但是,我們看到了至少兩個“捉襟見肘”的現實障礙。一是美國制造業和能源行業制約,激增的生產材料需求無法短時間得到滿足,尤其是鋁、硅、鋼、玻璃等,還有相應的儲能和電池所需的稀土和貴金屬材料。
二是快速的太陽能行業發展帶來勞動力市場需求隨之上升,具備技能的勞動力極度短缺成為美國今天“普遍”的現實挑戰。兌現目標,需要短時間內找到和培訓幾十萬的技工。據咨詢公司Wood Mackenzie估計,到2035年,實現100%清潔電力,太陽能行業將在目前規模上增長5-10倍。可是,美國太陽能行業的勞動力這幾年已經開始“縮水”,技能差距隨處可見。疫情進一步加劇各個行業的人工短缺。美國太陽能行業缺人,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觸發因素,那就是2018年2月開始啟動的“201條款”,對從中國進口的太陽能組件增收關稅。一來極大減少了美國市場的組件安裝,二來造成美國巨大就業崗位消失,加劇今天太陽能行業勞動力跟不上太陽能發電目標提升的局面。
“糾結”與“訴求”
在中國“掌控”全球可再生能源供應鏈“半邊江山”面前,現屆美國政府的心態非常“糾結”,體現在圍繞氣候變化領域如何在“對手”和“合作”之間找到“定點”。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是“左右搖擺不定”。一面是氣候特使克里為代表,倡導應對氣候危機上的“合作”承諾;另一面是能源部長表現出的“斗士”精神,主張美國必須在可再生能源供應鏈上,從中國手中“搶回”更多的“控制權”。
作為國務卿的布林肯,明確將中國“鎖定”在美國需要“克服”的“對手”,聲稱“如果美國不能引領可再生能源革命,難以想象出美國會贏得與中國的長期戰略競爭”。結果顯得“口是心非”和言行“自相矛盾”,給市場造成不必要的“混淆”和“不知所從”。但國務卿坦白,“目前,我們的確落后于中國”。也就是說,中國目前主導著全球的清潔能源市場,已經成為太陽能板、電池和電動汽車領域的最主要生產國和消費國,同時,中國“控制”著清潔技術所需的關鍵原材料的生產。
許多智庫建議的明智之舉是,美國應該聚焦在兩件事上,一是創新和研發,尤其是下一代技術,如綠氫或先進地熱等,還有在能源轉型中的市場開發和硬件安裝領域的綠色就業機會;二是不要試圖在供應鏈中的低端環節上競爭,例如污染嚴重的原材料采掘等,而應該激勵國內對綠色技術的需求,發揮美國在經銷和零售上的競爭優勢,從中國采購來廉價的太陽能板,需要有人去銷售和安裝,這也是實際可以“抓住”更多收入的地方。
拜登一直堅持將氣候行動定位在創造美國就業上,但是,清潔能源行業對全球供應鏈高度依賴,繼續貿易保護主義,注定是一個“頗具風險的戰略”。最終,美國很可能發現,要實現2035年100%清潔電力目標,如果可以繼續依賴中國不斷降低生產原材料的成本,可能成為一條相對“簡單易行”的選擇。美國更多的精力和資源應該投入大學研究和就業培訓,既能夠夯實自己的競爭優勢,也能夠為建造工廠“贏得”時間。
走出“脫鉤”,走向“合作”
最近,有兩件事值得關注。一是9月1日《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商界對拜登入住白宮7個月之后依然沒有在對華經濟關系戰略上做出清晰政策方向表示不滿,尤其是圍繞特朗普期間定下的對高達36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問題,其中關于超過2000個產品的關稅免征政策已經過期。同時,對華出口限制和諸多禁令依舊存在,讓美國的科技巨頭公司在對中國市場的方法和策略上“無所適從”,對扭轉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脫鉤”局勢的希望充滿不確定性。
二是9月7日《華爾街日報》報道,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之一的美國貝萊德作為在中國第一個全外資公司,管理募集大約10億美元(相當于66.8億人民幣)的共同基金,允許直接向中國個人出售,為美國和全球資產管理公司“長久渴望”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市場上擁有“一席之地”,創造一個“關鍵性的里程碑”。
各界對美國的下一個“目標”的“猜測”,讓中美關系的未來命運,不僅成為雙邊的關注“焦點”,也給全球未來安全前景籠罩了一層“陰影”。從具體的可再生能源切入,美國需要謹慎選擇經濟之戰,否則,將加劇拖慢能源轉型的速度之風險。
從中國對雙邊關系定位于“世紀之答案”的高度看,中美都需要選擇嶄新的外交政策“雙軸”,重新思考如何建立“人類命運與共”和加強全球安全基礎上的新型關系,一個緯度是彼此關系,或“脫鉤”對“合力”之軸,另一個是人類命運與共,或“加速滅絕”對“生態文明”之軸。于是,我們看清楚了這個“世紀答案”,中美必須合力協作,在“1+1大于2”的時代里,合作才能實現“互利共贏”,既惠及本國的百姓,也惠及人類和自然界的可持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