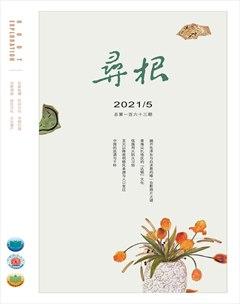傅斯年閑章尋義
閔惠泉


2015年,我在臺北訪學時尋見了不少民國時期文化名宿的故居、紀念館(室)、藏書和墓碑等。如蔡元培、梅貽琦、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王云五和張大千等,對所能見到的印章也禁不住隔著玻璃展示柜左看右看。先說說傅斯年先生吧,他是北大的學生,做過北大的教授,還當過不到一年的北大代理校長。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在他的紀念室里擺有鈐印朱文、白文多方,其中的“廉立散儒”“絕琴瀟湘”以及“烏萬斯年”三方閑章,尤其令我感興趣。此外,還有他的學弟、金石學家柯昌泗為其夫婦篆刻的一枚。在臺北南港傅斯年紀念室的這些閑章,觀者、留意者不多,內地更鮮有見聞者。
“廉立散儒”是枚述志章。具有“狷介之性”的傅斯年先生,當年蔣介石想請他做官,傅堅辭,稱自己“負性疏簡”,“是一愚憨書生,事務非其所能”。羅家倫曾這樣評價傅斯年:“孟真貧于財,而富于書,富于學,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為正氣而奮斗的斗勁。”“廉立散儒”可謂名副其實。
“絕琴瀟湘”這枚印章令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人或事,會讓傅斯年先生發出類似“伯牙絕琴”般的感嘆?后來看過傅斯年與胡適的有關文論,我猜測可能與丁文江有關。傅斯年與他相識緣于胡適,胡適回憶“民國十五年,孟真同我在巴黎相聚了幾天。有一天,他大罵丁在君,他說:‘我若見了丁文江,一定要殺了他!后來我在北京介紹他認識在君,我笑著對他說:‘這就是你當年要殺的丁文江!不久他們成了互相愛敬的好朋友。”
耿直的山東漢子傅斯年是個性情中人,“傅大炮”罵人的火氣是出了名的。胡適說“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傅斯年罵丁文江,并揚言要殺丁文江,是氣憤這樣的人才早先竟然參加過軍閥孫傳芳的政治集團。后來,用傅斯年自己的話說,“相見之后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后成好朋友,最近幾年竟成為極好的朋友”。
極好的朋友因考古時煤氣中毒意外身亡,傅斯年曾連夜一氣寫成幾千字的回憶文章《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他在文中甚至寫道:“在其病重時,心中自思,如果我死,國家之損失少得多。”
他在文中還順勢將了具有“歷史癖”“傳記癖”的胡適一軍,直言:“我希望胡適之先生將來為他作一部傳記。他若不作,我就要有點自告奮勇的意思。”
傅先生寫得“感情動蕩”,覺得許多話還沒有說完,隔夜又寫了《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彩》。他甚至打算再寫幾篇追憶丁文江的文章,可惜未能如愿。
胡適在《〈傅孟真先生遺著〉序》中說:“我回想那年在君在長沙病危,孟真從北平趕去看護他的情狀。我想念這兩位最可愛、最有光彩的亡友,真忍不住熱淚落在這紙上。”
當年能成為傅斯年極好朋友的除了丁文江,當數他在北大時的師友胡適、羅家倫和留德時的摯友并牽線將妹妹嫁給傅斯年的俞大維。然而,生死離別趕去看護的往事,未見傅斯年憶文中提及。不過傅斯年在1935年12月28日致胡適的信中卻詳細地講述了丁文江的病情,表露了對在君病狀“兇多吉少”的哀切之情。
時以“丁大哥”稱之的丁文江,1936年1月5日逝于湖南長沙。“所故地之地方”也成了丁文江的葬地,這是不是讓傅斯年生出痛失知音“絕琴瀟湘”的悲痛?在君先死之憾的感懷刻骨銘心,會不會融入這枚印章之中?
2020年9月,我向臺灣史語所數位資料中心友人請教,得到了熱心回復。致婷女士將圖書管理員的答復告知了我,“‘絕琴瀟湘是1938年刻,私意:1938年春,史語所由湖南長沙再遷云南昆明,或此隱喻”。
史語所1928年建立于廣州,1929年遷至北平,1933年遷至上海,后于1934年在南京建立新址。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史語所從南京遷往湖南長沙,1938年春又輾轉云南昆明。
如果這枚印章確實刻于1938年春,這種解釋也很合乎情理,在這種民族危亡的時刻,整個史語所被迫從湖南長沙遷往云南的悲壯,和當年秋傅斯年“移家昆明”,亦能讓傅先生發出“絕琴瀟湘”之嘆。不過,史語所的答復者十分謹慎,用了“私意”“或此隱喻”這樣的字眼。筆者倒是覺得傅斯年“絕琴瀟湘”或許涉及一人一事,兩種“隱喻”兼而有之。
在史語所典藏的“印記”中,印主傅斯年名下還有一枚“烏萬斯年”的印章。“烏萬”為何意?查詢的文獻中“烏萬”有幾種解釋:其一指一種少見的復姓;其二是指一種宗教信仰,意為人死后他的生命和命運就以流星的形式歸入太陽;其三烏是指孝鳥烏鴉,“萬”則為大也。筆者認為對于孝子傅斯年來說“烏萬斯年”,就有斯年“以孝為大”之意,當然這也是一種猜測;其四是臺灣學者告知:“‘烏萬斯年的意思,在傅圖印行的筆記書末載,文物館引用之。”認為烏同於字,“《詩經》‘於萬斯年,受天之祐,意為千秋萬載都能承受上天的福祐。”
前兩種解釋可能與這枚印章的關聯度不高,后兩種解釋究竟哪個更接近傅斯年印章的本義?鑒于從文字學的角度“於,烏的本字”,史語所文物館作這種解釋說服力確實最強。當然,如果我們知曉治印人、治印時間,以及是傅先生自己有意刻的還是別人祝福他為其治印,所有猜測和疑問都會化解。
傅斯年1949年去臺灣,任臺大校長,1950年去世,死后就安葬在臺大校門外,墓碑上用小篆體寫著“傅校長斯年之墓”。這也成為臺大校門前的一景。那年我去臺大時,正值陰雨,踩著腳下泛著青苔的石階和飄落的樹葉,在那里徘徊良久……
斯人遠去,印章尤存,先生其人、其格、其品,還有多少人記惦著?
“廉立散儒,絕琴瀟湘,烏萬斯年。”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