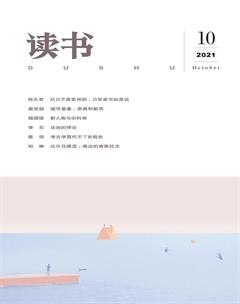城市意象:原典和新用
唐克揚
在城市設計這個領域中,《城市意象》怕是迄今最有名的理論著作之一了。它的作者凱文·林奇(一九一八至一九八四)早年是耶魯建筑生。面臨一個全面變革的時代,林奇對巴黎美院式樣的建筑教育感到不滿,因此他出走成了當時人望甚高的建筑師弗蘭克·L. 萊特的學生。但是,在塔里埃森的萊特工作室,這位同樣出自中西部的青年沒有得到他需要的東西,正好,不久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了他去遠東的機會。最終,林奇又回到了東海岸的波士頓,他在多處,包括《城市意象》一書中表達了對這座城市的喜愛。他于一九四九年成為麻省理工學院(MIT)的一名城市規劃教員,一生的教學時光都基本在這所學校度過。最終,因為心臟病突發,在他最喜愛的度假地,也是美國東北部的瑪莎葡萄園島去世。
就算是非專業人士也時常征引,《城市意象》并非什么大部頭理論著作。它本來就緊湊的篇幅中,有一小半是說明研究方法的附錄。這本書起源于一九五二年林奇的一個小研討課,然后他找了一群師生繼續這項研究。緊接著得到一筆資助,林奇得以在佛羅倫薩待了一段時間,我們有理由相信,在舊大陸城市的這段經歷對于林奇的思想形成一定有著巨大的影響,一九五四年他回到美國之后重拾這個題目,書中描述的研究計劃終付諸實施。該書可以稱作是這項研究計劃的一個“結題報告”。
林奇這項研究計劃的大語境,是“城市設計”這個學科在戰后的興起。一九五六年,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啟動了他們的第一次“城市設計會議”,列席這次會議的不僅包括學院內的城市研究者,還有簡·雅各布斯和劉易斯·芒福德這樣在城市思想史上有著非凡地位的學者和活動家。直到現在,“城市設計”這個詞也易產生歧義,讓人覺得不過是將建筑實踐的對象由較小的對象轉移到了大尺度的城市——事實上,城市“設計”正是對將建筑方法直接套用在城市“規劃”上的做法的一種撥正,但同時它也不希望完全放棄建筑師研究形式的特長。在林奇接受教育的時代,現代主義建筑學尚沒有取代波雜(Beaux-Arts)在大學里成為風尚,規劃師和建筑師的養成教育相差無幾,相對于耶魯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這樣的老牌建筑學院,波士頓的風氣有所不同,尤其在戰后,它吸收了歐洲來的現代主義人物,成了新城市思想的策源地。當年貝聿銘在考慮報考建筑專業時,就是感到自己并不長于繪畫而選擇了麻省理工學院,隔壁的哈佛大學建筑研究生院(GSD)也撇清了它和傳統美術學院的關系,后者是最早在大學中設置城市獨立設計課程的建筑學院之一。
林奇當時進行的是一項沒有前例的工作,在他的團隊中沒人有過提煉“城市意象”的訓練——今天聽到這話的建筑學院師生或許略感困惑,因為繪制意象地圖已經成為城市設計中一項常規方法,這項工作的門檻看上去也不高。但是,讓我們歷史地考慮一下當時既有的建筑與規劃專業教育,源自美術學院的訓練雖然看重“形式”對空間生成的意義,但是對于空間形式,尤其是城市尺度的空間形式,只學過平面構圖,也沒有今天模型軟件助力的學生往往無從下手,畢竟,它們不真的是一幅“畫”。剛剛從意大利歸來的林奇一定了解,在城市史上,不乏藝術大師同時塑造城市空間的范例。比如米開朗琪羅在羅馬設計的卡比托利歐廣場(Piazza del Campidoglio),它的要點并不在于平面的圖案和靜態的對稱布局,對于那些氣喘吁吁從西北面臺階往上爬的游人而言,斜方形的上升面構成了“仰角透視”,廣場像是伸出了下傾的手臂攫取了來訪者的身心。這種立體城市空間的樣式,容易讓近代的明信片式風景畫和攝影圖像簡單化,“地方”真的成為“畫”之后,虛實之間的關系就更讓人迷惑了。
簡單來說,凱文·林奇開展此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更清晰地理解城市環境和人的心像(mental image)之間的關系。首先,當時大多數的心理學家都在實驗室中從事他們的研究,而對心理學頗感興趣的林奇希望能找到在城市環境中運用行為心理學的方法,從而把城市設計向科學拉近。其次,作為一個城市居民而言,城市景觀的美學問題是不容回避的,大多數城市規劃者認為城市規劃是一種技術問題,而一旦涉及主觀的話題都成了無法討論的個人趣味,城市設計不排除定量分析,但也和“效果”有關。無論如何,城市不可能不考慮具體的人對城市的感受,哪怕它是一種錯解也罷。再次,本身作為一個設計師、一個城市的實踐者,林奇希望將對個人的感受研究和表達發展為一種城市尺度的工具,不同于傳統建筑學,他“……希望思考一座城市究竟該是什么樣……尋求直接在(城市)那個尺度上設計的可能性”。最后,在政策制定層面,林奇希望影響城市實際的規劃者,希望他們更加注意生活在某個地方的人的感受,然后做出適當的決策,也就是說,一座城市的實際感受理應影響到一個城市發展的政策。
林奇并不打算像十九世紀的美學家那樣制造出一種籠罩一切的心理結構,他受到了轉型心理學(transitional psychology),尤其是約翰·杜威的巨大影響,后者尤其強調個體經驗(experience)的重要性。他所談論的城市意象主要是一個“翻譯”的問題:一個人如何將感知翻譯為地方(place)?前者難以實體化,而后者才是城市經驗的基本載體。傳統的心理學雖然給他重大的啟發(“故事、記憶,和人類學表述……”),但是并沒有提供給他具體的工具,受過建筑師訓練的林奇因此發明了一種全新的,能夠落實為形式分析的方法,對具體的空間主體有效,也對日常生活有效。
林奇的團隊通過采訪三十個人檢驗了這種方法。他精心挑選了三個他認為具有代表性的美國城市:在紐約哈德遜河對岸的澤西城,一座毫無特色的城市;洛杉磯,人們覺得它是依靠機動車的“未來城市”;不用說,還有林奇一輩子最喜歡的波士頓,挑選它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就在那兒,我們了解而且喜歡(這座城市)”。研究從兩方面來進行,一方面,通過“畫圖找路”的辦法,采訪者設法讓受訪者描繪出一個人腦海中的城市意象是什么樣子的,他們還會根據這些意象地圖實際在城市中行走,看看它們到底有沒有用。另外一些成員則專注于城市“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根據他們了解的城市,人們畫出另外一種簡圖。最后把這些圖放到一起和采訪過程互相比照。
林奇團隊最大的發現是,通常認為城市意象會受制于一個地方的文化和風俗,但是通過這些采訪他們發現,對地方的感受中確實存在著細節性的共同特征,因此,假如一個城市的觀察者對本地文化不全然陌生,也理解這種表達“城市意象”之道,就可以通過仔細研究城市,得出有共通性的結論。城市意象于是像考古器物一樣,可以區分出清晰而穩定的類型,一個城市研究者也可以像考古學家一樣對這些圖像進行分類,并推演出可能存在的其他類型。林奇認為,對于形成一個地方優良的本地特征來說,這些意象的“質量”至關重要。
書中列舉的五個分析城市意象的要素,也就是路徑(paths),邊際(edges),區域(districts),節點(nodes)和地標(landmarks),現在已經廣泛用于城市設計中的形式分析了,在城市項目的匯報中你也常聽到這些術語。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這種方法的實質,甚至產生誤會,比如,這五種要素并不是并列的關系,它們與其說是“成套”工具,不如說是對同一城市對象的不同的解析方法,與古典城市形式的要素不一樣,林奇的“要素”既可以構成整體系統,也可以獨立存在,而且“要素”本身是中性的,并不一定就是需要追隨的“范式”,比如“邊界”有好的邊界也有壞的邊界,“哈肯泰克河岸的垃圾焚燒場”就是一類“令人不快的邊界”。
書中的插圖亦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們并不是寫實的城市地圖,也并非完全沒有層次的符號,它們更適合被稱為一種介于詳圖和概念之間的視覺圖解(diagram),林奇認為它們是“城市意象”的基本邏輯,或者至少說明了這種邏輯。比如類似本書第五十三頁的一張插圖:不大的圖解僅僅有一個圓圈,圍繞著圓圈的彌散的黑點,加上幾個向心的箭頭。事實上,它也概括了此頁下方大幅照片所表述的空間信息:
圍繞一個強烈核心,主題單元向外漸弱、遞減的區域……有時一個強烈的節點在更大的相似地帶范圍內,僅僅通過“輻射”,即接近節點的方式,也可能形成一種區域……
確實,圖解所描述的“城市意象”,用視覺簡圖的方式表述了很難用其他方法講得更清楚的空間感受。它必然是對城市現實的一種有意識的簡化,不是全息地復制人造環境的做法,所以“城市意象”的背景必是具體的和有語境的。按林奇自己的解釋,這個研究首先是因為“識途”(wayfinding)的需要,一個人在導航(navigation)的時候,依據的是一個更大的心理結構,從而喚出了“城市意象”,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這個研究計劃本身也是通過有限的訪談形成的,它依賴于受訪者下意識的、即時的圖解。最終,這種思路必然會延伸到另外一個維度,就是“城市意象”也會隨著時間和對象不斷發展,它是一個可以被持續講述的空間的故事。
在這本書出版二十年之后,林奇回顧了圍繞著《城市意象》的一些核心疑難,這篇文章也可說是對當初質疑他的理論的人的一種回應。如此短小篇幅,而且基于有限經驗的書,如何確信能夠涵蓋更為廣大的現實?——這個問題實際上也涉及上述的一般和特殊、要素與系統、瞬時和長久之間的關系。比如,人們會問,林奇挑選的如此少的采訪對象,都是年輕的中產階級人士,大多是專業人員,他們真的能代表普遍性的城市意象生成的狀況嗎?
林奇回答說,這些不多的樣本卻是具有“代表性”的,至少在基本成分、提煉的技術和分析方法上而言,總體穩定的城市意象,并不因為受訪人員的變化有顯著的變化,即使短時間內發生波動也沒關系,這才會有一個城市和地方的基本特色可言。他承認,另一種對他們研究方法的質疑,倒是更切中要害一些,那就是繪制地圖需要較高的心智和技巧,并非每個人所擅長,那么那些不掌握這種技巧的人,是否就不會有活潑的“心像”呢?這顯然和人的一般生活經驗是有出入的,因為不能畫圖并不代表就不認識城市(不“識圖”也不見得就不“識途”),有的人即使不熟悉特定的城市意象,對城市生活還是有較好的體驗。就像貢布里希在《圖像和眼睛》中所說的,辨和回完全是兩回事。林奇承認這種質疑有道理,但他認為隨著時間發展出的集合圖像(composite picture)彌補了單一圖像可能的偏頗,兩者并不矛盾。“冰山之一角,”林奇說,“畢竟是冰山。”
而且,即使城市地圖和城市圖像兩者偶不相合,學會積極地識圖(“識途”)也有社會感情的價值。林奇認為,尤其對于當時開始出現的電視一代而言(推而廣之,對于今天的智能手機一代),自己的意象地圖繪制方法具有高度的教育意義。
既然“城市意象”的生成中有著如此眾多的“規律”,此書一出,設計師不免害怕他們的角色會被這種方法掩藏的“人工智能”所代替,林奇的方法終將演繹為“設計科學”。那時林奇安慰他們,僅僅是分析和歸納現狀并不意味著猜測未來的能力,這部分的潛力依然掌握在藝術家的手中,這就好像天氣預報并不會改變我們和氣候的關系(我們看到,僅僅就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而言,真正的人工智能時代已經帶來了林奇不能預想的挑戰)。
至關重要的批評還不是上述這些,而是對于城市意象的研究是否高估了(清晰)意象的作用。一座迷宮般的城市不也讓人們覺得富有魅力嗎?不容否認的是,在林奇的書籍出版前后的那個時代,科學主義的傾向流行于各個學科中,魯道夫·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學,藝術史研究中流行的視覺心理學分析,等等,城市研究也不例外。這種風氣的直接后果,就是清晰擊敗了一切“蒙昧”。林奇自信地認為,沒有特征的環境必然使我們喪失了非常重要的情感滿足。地方,尤其是波士頓那樣有著出色城市意象的地方,對于一個人的心智成長乃至身份認同有著不容置疑的意義:“應該設想,一個威力巨大的場所意象是集體身份的礎石,感受鮮明的生動的景觀而致的喜悅常有體驗,并記錄在案,一個成熟自信的人可以對付枯燥混亂的環境,但是對那些內心迷惑,或者在成長瓶頸期間的人而言,這些環節就造成了巨大的麻煩。”
但是林奇自己承認這種假設本身有待證明。因為通俗文化中有很多軼事和個人體驗證明,鮮明、積極、開放的城市意象并不是所有城市的唯一選擇。在心理學研究、藝術作品和小團體社會中出現的很多例證,證明了多樣化的城市意象之間存在著聲息相通的關系,突出其中一種并不意味著就取消其他種。
林奇為豐富他的理論找到了更積極的觀點:首先,更民主的對待這項研究的態度,是尊重不同體驗個體的多樣性,無論他/ 她的年齡、性別、對城市的熟悉程度,不同的角色扮演,城市意象的生成本身將演變成一種“參與式”的設計過程,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范。其次,加入時間維度的“城市意象”是在變化中求得理解。某些規劃者誤以為意象就如同城市的標準照一樣不容更動,其實“我們是尋求范式的人,但是我們并不崇拜范式”。最后,林奇清醒地意識到“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長青”,“城市意象”不會發展成系統的空間語義學,因為地方特征并不是一種語言,在它的意義激發過程中,人們無法清楚地將那些能指和它的所指分離開來。
相對于美麗的郊野風景,林奇顯然是一個偏好“城市”的人,雖然佛羅倫薩是林奇研究的最直接前因,但是他的城市顯然是有廣闊的取向的,它是文化的也是日常的,有激動人心的場景,也有庸常的現實和由此產生的矛盾,不只是那些旅游明信片中的城市,而可能是佛羅倫薩、波士頓、澤西城和洛杉磯的總和。想必,這也是當年他離開自我、孤立、索居的萊特的原因。
一九八四年林奇去世的時候年紀并不大,但他所憂心的事情,尤其是在美國之外的一些國家已經演變成現實。本意是為了用于分析現狀影響城市政策,制定出一種沒有太多門檻的工具,但他略有些好笑地看到,在美國,政策制定者對于“城市意象”倒是不大熱衷,因為在美式政治中,大都會的生民們眾口難調,政策制定者總是試圖保持一種表象上的中立,不想把城市歸于特定的審美訴求。與此同時,在一些國家——比如日本和以色列,城市推廣的需要帶來了這個話題的意外熱度,在全球旅游工業的迅速整合之中,原本虛無縹緲的城市“意象”,卻變成了一種強有力的文化資本宣傳口徑。
更有甚者,林奇心目中的未來現在已經成為過去時,有些城市意象的前提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比如在書中波士頓的高架鐵路是所謂“空中邊界”的積極實例,但是波士頓的大開挖(Big Dig)取消了這種邊界,原因和很多美國城市一樣,大國崛起期間,大家樂意看到的繁忙公路穿過城市中心的情景已經不受歡迎。
就像林奇著作在亞洲國家的意外影響一樣,和工業社會一起滋生的“城市漫游者”現在已經賦予“城市意象”新的生命;或者,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舊文化的重生,和每個時代特定的技術使命并無直接關系。不久前,英國的建筑師聯盟學院(AA School)舉辦了一個名叫“城市意象浸入”的會議,討論電影、空間和建筑的關系。其中引用了瓦爾特·本雅明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段話。本雅明提到,全景畫同時還是一種面對生活的新態度,它帶來了一種藝術和技術間關系的騷動——那就是居伊·德波稍晚些時候說到的。那些相對于外省有著政治上優越性的城市居民,通過這些全景畫,“將鄉村帶進了城市。在全景畫中城市展開了,(城市)變成了景觀……”
這證明了林奇著作持久的生命力,也說明了“城市意象”在實際功用層面之外更廣泛的意義。
(《城市意象》,凱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曉軍譯,華夏出版社二00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