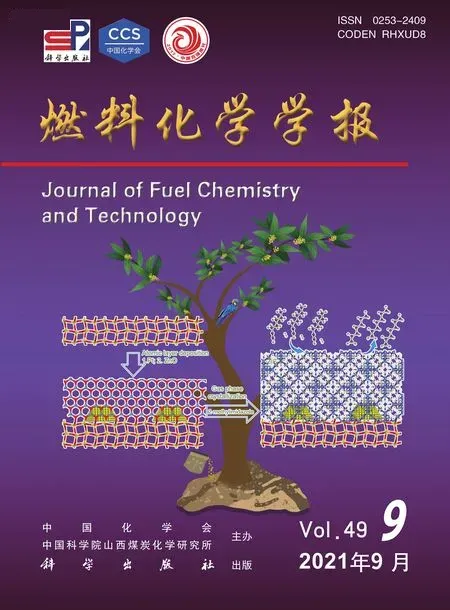金屬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的NH3-SCR機理研究進展
張文博 ,陳佳玲,* ,郭 立 ,鄭 偉 ,王光華 ,鄭申棵 ,吳曉琴,*
(1.武漢科技大學 化學與化工學院 煤轉化與新型炭材料湖北省重點實驗室,湖北 武漢 430081;2.黃岡師范學院 化學化工學院 催化材料制備與應用湖北省重點實驗室,湖北 黃岡 438000)
氮氧化物(NOx)是常見的五種氮的氧化物(N2O、NO、N2O3、NO2和N2O5)的統稱,其中,NO和NO2在大氣環境中的比例最高,是現今大氣的主要污染物。NOx會導致嚴重的環境問題,如酸雨、光化學煙霧、臭氧消耗和煙霧等,并危害人類健康[1]。大氣中約90%的NOx排放來自化石燃料的燃燒,如燃煤發電廠(固定源)和機動車輛(移動源)中的煤和燃料油的燃燒[2]。由于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的負面影響,世界范圍內各國對大氣中NOx的排放控制標準越來越嚴格。根據美國清潔空氣法案,工業鍋爐的排放煙氣中NOx不能超過553.5 mg/m3。而中國的NOx排放標準更為嚴格,根據中國GB 13223—2011國標要求,新建發電廠和天然氣鍋爐中的煙氣排放中NOx不能超過100 mg/m3,天然氣透平裝置中不能超過 50 mg/m3。此外,針對機動車的尾氣排放,根據國標GB 18352.6—2016,中國將于2023實施更為嚴格的機動車尾氣排放標準(從 2020 年的 60 mg/km 調整到 35 mg/km)[3]。因此,針對工業污染源尾氣中NOx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NOx的脫除主要有三種技術研究方向:催化分解技術、儲存還原技術和選擇性催化還原技術(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簡稱 SCR 技術)[1]。NOx催化分解技術是指利用催化反應將NOx直接分解為N2和O2。NOx儲存還原技術是指在稀燃條件下儲存NOx,在富燃條件下將NOx還原的技術。由于這兩種技術的催化劑容易中毒、活性和穩定性有待提高,目前,還無法進行大規模的應用。而SCR技術,是指在催化劑的作用下,利用還原劑選擇性地將煙氣中的NOx還原,得到N2和H2O。根據還原劑的不同,SCR技術可以分為碳氫化合物選擇性催化還原技術(HC-SCR)和氨選擇性催化還原技術(NH3-SCR)。HC-SCR技術的設計理念是以車載燃油作為還原劑(如丙烷、烴類)的來源,通過催化劑作用使碳氫組分與NOx發生選擇性氧化還原反應,主要采用Ag/Al2O3等作為催化劑,但存在NOx凈化效率偏低、活性溫度窗口窄和催化劑容易積炭等缺點,尚未達到大規模實際應用的要求[4, 5]。氨選擇性催化還原(NH3-SCR,主要反應為:4 NO + 4 NH3+ O2→ 4 N2+ 6 H2O)是目前廣泛應用的脫硝技術,可以使用液氨或者尿素作為NH3源;由于其高效率、低成本的特征已成為主要的固定源和移動源脫硝技術[6, 7]。
釩鈦基催化劑是應用最廣泛的固定源脫硝NH3-SCR催化劑之一。目前,中國科研工作者已制備出具有寬活性溫度窗口的鈰改性釩鈦基催化劑 CeO2-V2O5/TiO2-ZrO2,其在 150?475 ℃ 表現出80%以上的脫硝活性[8],但此類催化劑容易被煙氣中的SO2毒化;此外,釩類催化劑具有生物毒性,因此該類催化劑無法適應越來越嚴格的環保要求[9],歐美等一些發達國家已陸續禁止在移動源脫硝體系中使用釩鈦基催化劑[10]。為此,研究者們開發了新型釩酸鹽催化劑[11],以及其他過渡金屬催化劑如 Cu 基、Fe 基、Mn 基氧化物催化劑[12, 13],然而上述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
自1986年Iwamoto等[14]發現Cu/ZSM-5在NH3-SCR反應中具有良好的催化活性以來,由于具有較寬的活性溫度窗口(200?600 ℃)、較高的催化活性和水熱穩定性,金屬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受到廣泛關注[15]。此類催化劑上,分子篩載體規則、穩定的骨架結構和較高的比表面積,賦予了其較高的熱和水熱穩定性,并確保了活性金屬的高度分散,以及反應物和產物的高效擴散,促進反應的迅速進行。此外,分子篩上往往具有豐富的表面酸性位點,在NH3-SCR反應中,不僅能起到吸附和活化NH3的作用,還能通過靜電平衡作用鉚定活性金屬正離子,從而提高活性金屬離子的穩定性。同時,由于靜電穩定作用,分子篩上活性金屬的負載量和分布,還可以通過高效匹配分子篩載體的硅鋁比(硅鋁分子篩中)或Si含量(硅鋁磷分子篩中),以及金屬物種的負載量來進行調控[16 ? 18],從而進一步改善催化劑的活性和水熱穩定性。因此,金屬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成為NH3-SCR脫硝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
大量研究表明[19 ? 21],由于能高效活化 NO、催化氧化還原循環,并具有較寬的氧化還原活性溫度窗口,Cu和Fe負載的分子篩催化劑是NH3-SCR領域的研究熱點。由于氧化還原性能的差異,Cu基分子篩催化劑的最佳NH3-SCR溫度窗口為150?300 ℃,超過 300 ℃,容易導致氨氧化副反應的發生,使得NH3-SCR催化活性下降;與Cu基分子篩相比,Fe基分子篩具有更高的還原溫度,此外Fe物種能促進N2O副產物的分解,因此,后者具有明顯的中高溫NH3-SCR催化優勢,其最佳溫度窗口為 250?500 ℃。
目前,研究者們已發現多種高效的Cu或Fe改性NH3-SCR分子篩催化劑,如Cu/SSZ-13、Fe/SSZ-13、Fe/Beta、Cu/SAPO-34、Cu/LTA 等。通過詳細調變催化劑上金屬物種的含量[22]、分布[23],分子篩載體的種類[24]等,研究者們相繼開發出了具有工業潛力的Cu/ZSM-5、Fe/Beta、Cu/SSZ-13催化劑。目前,小孔型Cu/SSZ-13由于具有寬溫度窗口、高NH3-SCR活性和水熱穩定性,已在歐美成功應用于柴油車尾氣脫除中,但其仍存在高溫活性差、水熱穩定性差和耐硫性能不佳等問題[25]。因此,開發具有寬溫度窗口、高水熱穩定性的金屬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是NH3-SCR催化劑研發函待解決的首要問題。
NH3-SCR體系中的化學反應是相當復雜的,根據反應氣中不同的NO/NOx比值,NH3-SCR反應一般分為標準NH3-SCR、快速NH3-SCR和NO2-SCR(慢速NH3-SCR)。當反應溫度低于400 ℃時,式(1)是主要反應,NO與注入的還原劑NH3發生反應且化學計量比為1∶1[26]。Antonio等[27]通過研究不同反應溫度下原料氣組成的影響,探究了Fe/Beta分子篩上的NH3-SCR反應途徑,他們發現,在140?160 ℃,當 NO 與NO2的摩爾進料比為 1∶1 時,主要發生快速NH3-SCR。

這三種途徑中,NO2-SCR報道的最少,Antonio等[27, 28]利用瞬態反應實驗,研究了NO2-SCR在Fe/ZSM-5分子篩上的反應歷程,通過在恒溫狀態(190 ℃)下,向含1% H2O 的He原料氣中階躍性的加入0.1%的NH3或NO2,實時檢測出口氣體種類及濃度的變化情況,提出了NO2歧化生成亞硝酸鹽和硝酸鹽的NO2-SCR反應機理(式(4)?(8))。此外,他們還發現同一分子篩催化劑上,NO2-SCR反應的反應速率明顯低于標準NH3-SCR和快速NH3-SCR。

當反應溫度高于300 ℃,NH3-SCR反應過程中會發生明顯的副反應:NO和NH3的氧化反應。其中,NO 主要被氧化為 NO2(> 300 ℃)(式 (9)),NH3則被氧化為 N2、NO、NO2、N2O(> 400 ℃)(式(10)?(13)),在金屬負載 NH3-SCR 反應中,氨氧化副反應的主要產物是 N2(> 90%),其余產物很少[29]。此外,NH3-SCR體系中,高溫下的氧化副反應,會隨反應溫度的升高而增強,最終導致標準NH3-SCR反應無法正常發生,NOx轉化率迅速下降。

在NH3-SCR反應體系中,當溫度低于250 ℃時,還會有硝酸銨的生成和分解發生。當反應體系中 NO2含量較高(NO2/NOx> 50%)時,NH3在低于200 ℃溫度下,會生成硝酸銨(式(14)),部分硝酸銨會分解生成N2O(式(15))。此外,低溫下生成的部分NH4NO3物種還會覆蓋在催化劑表面,且不易分解,最終導致催化劑活性位點被覆蓋,失去脫硝活性。

綜上,一般認為NOx的轉化速率按快速NH3-SCR > 標準 NH3-SCR > NO2-SCR 的順序依次降低,且只有快速NH3-SCR完成后,標準NH3-SCR和NO2-SCR才能進行[4];每種NH3-SCR反應均伴隨著吸附態硝酸銨、亞硝酸銨物種的形成和分解;在眾多副反應中,不僅有NO、NO2、N2O、N2等副產物的生成,NH3也被大量消耗從而限制了NOx轉化率的提高。因此,在研究催化劑反應機理的基礎上,通過對催化劑進行定向設計,可以減少副反應的發生,從而提高催化劑的NH3-SCR反應活性。
研究金屬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在NH3-SCR反應中的反應機理,如活性金屬物種的種類與分布[30]、活性金屬物種在分子篩骨架中的最佳催化位點[31],能為催化劑上活性位點的定向設計提供指導。此外,對特定催化劑體系上具體催化路徑,和動力學反應機制的探究[32, 33],有助于針對性的開發具有特定反應路徑的催化劑,并從調控反應條件的角度,優化反應動力學,加快NH3-SCR反應速率,從而提高催化劑的反應性能。
目前,研究者對金屬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的NH3-SCR反應機制的研究并沒有達成統一共識[34],其原因在于:(1)由于金屬活性物種物理化學性質的差異,不同催化劑體系(如Cu基和Fe基分子篩催化劑)催化NH3-SCR反應時的具體活性物種、氧化還原途徑等存在較大的差異,這導致其氧化還原反應機理的復雜性。(2)NH3-SCR反應機理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對金屬活性物種有準確的認識基礎上,因此依賴于多種表征手段,甚至原位表征。而金屬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上,金屬物種的存在狀態往往較多,且隨分子篩載體的拓撲結構、硅鋁比、負載量而變化,這使得對活性物種的定性、定量表征存在一定的難度。此外,當采用離線表征手段時,獲得的金屬物種存在狀態往往不能準確反映其在真實NH3-SCR氣氛中的化學環境,這也增加了金屬活性物種狀態分析的復雜性。(3)反應機理的本征動力學研究的復雜性:由于標準 NH3-SCR 反應溫度范圍較寬(150?600 ℃),且反應氣氛中存在多種氣體(NH3、NO、O2、H2O、N2O、N2等),反應條件的復雜性導致反應速率加快、副反應增多,從而影響動力學參數的測定。因此,對標準NH3-SCR的本征動力學研究,需要建立在排除內外擴散和副反應的基礎上,通常在較低的反應溫度下進行,但這會導致反應速率的下降,影響測定結果的準確性。此外,即使在同一金屬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體系中,由于制備方法的差異,各催化劑上活性金屬的種類和分布也會存在差異,從而影響其在NH3-SCR反應中的主要反應途徑[35, 36]。除此之外,分子篩載體也是影響催化劑上反應動力學的重要因素,不同分子篩載體具有不同的孔道結構和物理化學性質,會影響催化劑的擴散性能[24]、活性金屬落位和反應途徑[37]。這些因素,都會導致研究者們獲得的NH3-SCR反應中表觀動力學參數的差異,從而使得對本征動力學的研究存在分歧。
為了正確認識以上問題,本文詳細調研了文獻,對鐵和銅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在NH3-SCR領域的研究進展、活性位點和反應路徑進行了總結,重點闡述了反應過程中活性物種及反應物分子的行為,反應中間產物的種類、結構及作用。此外,還介紹了采用密度泛函理論研究NH3-SCR反應機理的相關進展,以及NH3-SCR反應動力學的研究方法,并對比了不同催化劑體系下的動力學參數,為金屬改性分子篩催化劑的NH3-SCR反應機理研究提供方法與思路。
1 Fe 基分子篩催化劑
1.1 催化劑研究
20世紀90年代,Fe/ZSM-5分子篩被首次開發為NH3-SCR催化劑[38],該催化劑在較寬的溫度窗口(350?550 ℃)表現出 100% 的 NOx轉化率[22],明顯優于常規 V2O5-WO3/TiO2催化劑(320?450 ℃);但由于鐵物種的氧化還原起活溫度高,催化劑在250 ℃以下活性較低[39],此外,催化劑在高溫水熱條件下容易水熱失活[40],這兩個關鍵因素限制了其大規模的應用。此后,Qi等[41]發現,在催化劑的制備過程中,提高活性鐵物種的分散性能,可以明顯提高Fe/ZSM-5的低溫活性,并使NOx轉化率提升到 70% 左右(< 300 ℃)。
之后,研究者把注意集中在具有大孔結構的Fe/Beta分子篩上,發現使用不同制備方法制備的Fe/Beta在NH3-SCR催化活性和熱穩定性上均優于 Fe/ZSM-5[42 ? 44]。然而,Fe-Beta 分子篩的水熱穩定性仍不能滿足實際NH3-SCR的工業應用要求,如經歷較長時間的水熱處理后催化劑明顯失活,無法滿足所規定的催化劑高溫催化耐久性要求[45];此外,由于具有較大的孔徑和較高的比表面積原因,分子篩內易吸附大量碳氫化合物,因此BEA拓撲結構很容易被燃料的不完全燃燒所產生的高熱量碳氫化合物所毒化、抑制[45],形成碳質沉積物而阻斷反應活性位點與分子篩內氧化還原位點相互作用,造成催化劑失活。
2009年,Bull等[46]在專利中首次報道了具有高NH3-SCR活性的Cu/SSZ-13分子篩[46]。隨后,Kwak等[47]對比了Cu/ZSM-5、Cu/Beta和Cu/SSZ-13分子篩的NH3-SCR活性,發現小孔型的Cu/SSZ-13表現出更高的反應活性。此外,研究者發現,由于SSZ-13具有八元環的CHA小孔結構,能抑制骨架脫鋁(骨架脫鋁形成的鋁氧化物無法從孔口脫出)從而穩定活性銅物種,同時減少分子篩對碳氫化合物和水的吸附,避免其對活性中心的毒化,在NH3-SCR反應中具有高水熱穩定性和抗碳氫化合物毒化性能[48, 49]。Gao 等[50]也對含鐵的Fe/SSZ-13進行了大量研究,發現新鮮樣品中鐵物種多以骨架外陽離子存在(其中單體和二聚態分別為[Fe(OH)2]+和 [HO-Fe-O-Fe-OH]2+),經過苛刻條件下的水熱老化后分子篩結構仍保持完整且在400 ℃以上保持了較高脫硝活性,但300 ℃下NH3-SCR活性下降明顯;最后他們提出,將Fe/SSZ-13與Cu/SSZ-13混合使用應用于NH3-SCR反應中,以進一步拓寬Fe/SSZ-13的活性溫度窗口。
此外,與Fe/SSZ-13具有相同CHA結構、但不同元素組成的Fe/SAPO-34分子篩,也是一種優良的NH3-SCR催化劑。Andonova等[51]發現,Fe/SAPO-34在300?600 ℃的條件下,具有超過80%的NOx轉化率,且由于水熱老化過程中出現鐵物種的遷移、形成更穩定的NH3-SCR活性鐵位點的原因,水熱老化后其NH3-SCR催化活性進一步提高。其特殊的小孔徑結構也保證了體積較大的烴類物質無法毒害催化劑,從而提高催化劑的穩定性[52]。由于Fe/SAPO-34在高溫下的優異活性和水熱穩定性,研究者提出,將Fe/SAPO-34與商用Cu/CHA混合作為催化劑使用,從而同時拓寬活性溫度窗口和提高NH3-SCR反應活性[53]。但有研究指出Fe/SAPO-34在70 ℃下會因大量金屬位點轉化為非活躍狀態而失去脫硝活性[54],因此該類催化劑仍需進一步改良,如引入第二種陽離子(Cu或Mn)以提高其抗H2O和碳氫化合物的性能[55]。
除上述分子篩外,研究者還開發了其他小孔型NH3-SCR分子篩。由于AEI型Fe-SSZ-39分子篩與CHA類分子篩[56]具有相似的雙六環(D6R)結構,其在NH3-SCR反應中同樣表現出優異的低溫活性和高水熱穩定性。此外,一鍋法能顯著改善鐵物種在分子篩內的分布情況,該方法合成的Fe-SSZ-39催化劑在300?550 ℃具有90%以上的轉化率;且小孔徑的拓撲結構也導致了其在600 ℃中水熱老化后仍具有較高的脫硝活性[57]。Ryu等[58]發現,鐵離子和鐵氧化物團簇在高硅鋁比的Fe/LTA內的熱力學穩定性明顯高于Fe/SSZ-13,因此Fe/LTA分子篩在各個溫度都表現出優于Fe/SSZ-13的性能,甚至在水熱老化溫度達到900 ℃時仍保持較高活性。高硅鋁比的LTA分子篩作為穩定的NH3-SCR載體,有希望代替CHA類分子篩。
然而,用于NH3-SCR的高效催化劑并沒有完全依賴于小孔徑的分子篩,采用特殊方法制備的中孔分子篩也被證明具有較高的NH3-SCR催化潛力。近期,本課題組報道了一鍋法制備的具有十元環孔道結構MWW結構的Fe-MCM-22分子篩,由于一鍋法能確保活性鐵物種的更好分散,其在190?490 ℃具有約80%的NOx轉化率和100%的N2選擇性,使鐵基分子篩低溫活性差的問題得到一定的解決[23]。此外,Ryu等[56]采用液態離子交換法,制備了具有三維十二元環孔道結構的Fe/UZM-35催化劑,發現由于能更好地鉚定獨立Fe3+物種,Fe/UZM-35上活性Fe3+物種高度富集,其低溫下(<300 ℃)脫硝活性明顯高于Fe/SSZ-13和Fe/Beta催化劑。以上研究表明,催化劑的制備方式和分子篩載體的物理化學性質,能顯著影響催化劑在NH3-SCR反應中的催化性能。
表1中總結了具有不同孔道拓撲結構的鐵基分子篩催化劑及其NH3-SCR性能指標。一般來說,與機械混合法相比,使用一鍋法制備鐵基分子篩催化劑的脫硝活性往往較高,這是由于一鍋法能確保活性鐵物種更好的分散。此外,與大孔徑分子篩(如ZSM-5、Beta)相比,由于小孔徑分子篩(如CHA)能抑制碳氫化合物進入孔道,并阻礙水熱老化過程中分子篩脫鋁,具有更高的水熱穩定性及抗碳氫化合物性能。

表1 代表性的鐵基NH3-SCR分子篩催化劑Table 1 Summary of representative Fe-based NH3-SCR zeolites catalysts
結合以上分析,鐵基分子篩催化劑研發方向為:(1)選擇具有合適拓撲結構的分子篩載體,從而優化活性金屬物種的分布,并增加其穩定性,進而拓寬催化劑的NH3-SCR溫度窗口和水熱穩定性;(2)改進催化劑的制備方法,如采用一鍋法等方法優化活性鐵物種的分布;(3)改良現有催化劑,如引入第二種陽離子(Cu或Mn),以提高其低溫活性和水熱穩定性等。
1.2 活性位點
鐵基分子篩催化劑上的NH3-SCR反應主要發生在活性鐵位點上,因此,研究活性物種的種類、含量及分布,對于理解NH3-SCR反應機制至關重要。Javier等[63]在探究Fe/ZSM-5催化劑上,各類鐵物種的含量與NH3-SCR催化性能間的構效關系時,結合EPR、UV-vis表征結果發現,鐵基分子篩上的Fe物種種類有:獨立鐵離子、低聚的FexOy物種、高度聚集的鐵氧化物種如Fe2O3等[63, 64]。進一步,Yuan等[65]采用一鍋法制備了具有不同鐵含量的Fe-ZSM-5分子篩,并通過EPR、UV-vis、H2-TPR等手段對樣品中的鐵物種及含量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他們發現,Fe/ZSM-5的NH3-SCR催化活性,與EPR譜圖中歸屬于具有高對稱性的八配位態Fe3+的特征信號峰強度呈正相關,認為這種鐵物種是Fe/ZSM-5上的主要NH3-SCR活性中心。Gao等[22]制備了一系列具有不同鐵含量的Fe/SSZ-13分子篩,對其進行低溫(8 K)下穆斯堡爾譜研究,可探測到催化劑上的三類鐵物種:水合狀態的獨立 Fe2+物種(Fe(Ⅱ)-P);雙核 Fe3+物種,即 [HO-Fe-O-Fe-OH]2+物種(Fe(Ⅲ)-P);Fe(Ⅲ)-M 鐵物種,包括獨立Fe3+和多核FexOy鐵物種(三核及更高度聚集的FexOy物種或納米顆粒)。基于此,結合動力學催化實驗,他們發現:標準NH3-SCR反應中,獨立Fe3+為低溫下(< 300 ℃)的主要活性中心,[HO-Fe-O-Fe-OH]2+物種為高溫下(≥ 300 ℃)的主要活性中心;NO氧化反應中,雙核Fe3+物種為主要活性中心,NH3氧化反應中的主要活性中心為高聚態FexOy物種。
長期以來,鐵基分子篩低溫下(< 250 ℃)的低NH3-SCR活性,是制約其商業化進程的關鍵因素之一[39],研究者認為有兩個原因:(1)低溫下,NH3會與活性鐵位點強烈結合,從而阻止NOx與鐵物種進行配位并活化NOx;(2)由于NH3的強還原性,鐵物種“被滯留”在二價,使得低溫下無法進行NO氧化從而完成氧化還原循環[40]。大量研究表明[28, 66],向增加原料氣中添加 NO2,能顯著提高含鐵分子篩催化劑在250 ℃以下的NH3-SCR活性,因此原因(2)更有可能[67]。
除活性鐵物種的種類外,鐵物種在分子篩孔道內的空間分布,也顯著影響其催化性能。Velez等[31]探討了活性鐵離子在ZSM-5沸石孔道中的位置,他們發現:位于α位點(十元環中的單體鐵位點)的Fe3+是標準NH3-SCR的主要活性位點,而位于β位點(六元環中)和γ位點(五元環中)的Fe3+物種主要催化快速NH3-SCR反應。這與之前研究中[50, 64, 68, 69],Fe3+是 NH3-SCR 反應中唯一的活性位點是一致的,但由于孔道不同位置的空間約束不同,導致不同位點的鐵物種的氧化還原活性存在差異,因此改善鐵活性位點的空間分布也能增強其催化性能。
分子篩中活性鐵位點的配位環境也是研究重點。科研人員普遍認為,NH3-SCR反應中鐵基分子篩上活性鐵物種的配位數為4[68];在反應過程中,NO吸附到鐵位點后配位數增加到4到5之間[70]。配位數的增加說明鐵位點除了與沸石結合外,還直接與一種反應物成鍵。如圖1所示,Boubnov等[70]通過原位紅外研究了不同反應條件下,Fe/ZSM-5分子篩在NH3-SCR反應中的配位變化情況;他們發現,NO與活性鐵位點的配位是通過羥基氧原子形成配合物 [Fe2+?Oδ+H?N=O]實現的。Jiang 等[71]認為,相對于不是很穩定的鐵胺配合物,穩定的[Fe(CN)5NO]?更有可能是生成的活性鐵硝基配合物。綜上,目前對活性鐵物種與反應物NO的活化方式,研究者還沒有達成共識。

圖1 鐵基分子篩中 FeII 與 NO 的配位研究[70]Figure 1 Coordination of FeII with NO in Fe-based zeolite[70](with permissions from ACS publications)
總體來說,鐵基分子篩催化劑在NH3-SCR反應中主要活性位點為獨立的Fe3+物種,但由于反應條件的差異,不同溫度下具體的活性鐵物種存在形式不一樣:當進行低溫NH3-SCR反應時以[Fe(OH)]+為主,但在高溫條件下以獨立Fe3+為主。此外,分子篩載體的孔道結構的差異,也導致活性鐵物種的空間結構的細微差別:由于位于不同分子篩孔道內對活性鐵物種的空間約束作用不同,不同位點的Fe3+物種的氧化還原活性存在差異,這導致其在NH3-SCR反應中的活性也不一樣。
1.3 反應路徑
關于鐵基分子篩的NH3-SCR反應活性位點的研究已逐漸形成共識[3, 27, 28, 72, 73],但對于不同催化劑上的具體反應路徑,仍有很多不同報道[22, 72]。一般來說[72],低溫下的NH3-SCR反應主要遵循Langmuir-Hinshelwood機理(L-H機理),即NO和NH3同時吸附在催化劑上,并相互作用生成過渡態中間體后分解為N2和H2O。如圖2所示,L-H機理中,NH3吸附在酸位點上形成,NO被高價金屬氧化位點氧化形成活性雙齒硝酸鹽、橋連硝酸鹽或單齒亞硝酸鹽,它們與反應形成NH4NO2或NH4NO3后,分解為N2和H2O[3],同時高價的氧化還原位點被還原為低價后,可被O2再氧化,從而完成氧化還原循環。

圖2 金屬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上 NH3-SCR 的反應路徑[3]Figure 2 NH3-SCR reaction pathway over metal-based zeolite catalysts[3](with permissions from ACS publications)
與L-H機理不同,研究者認為,高溫下的NH3-SCR更多地遵循Eley-Rideal機理(E-R機理)[3]。ER機理中,僅NH3分子吸附在催化劑上,氣相NO分子與吸附、活化后的NH3反應,生成過渡態中間體后分解為N2和H2O。在此途徑中,NH3首先被吸附在酸性位點上形成NH3和/或,然后被NO和O2氧化形成活性中間體NH2NO和/或NH3NO,最后分解形成N2和H2O。
從圖2中可知,L-H與E-R路徑形成的反應活性中間體存在差異,因此,通過中間體的捕捉可以判斷具體反應路徑。Antonio等[27, 28]在研究Fe/ZSM-5催化劑上快速NH3-SCR反應機理時,使用質譜及紫外分析技術,對反應出口氣體組成進行在線檢測,發現NH4NO3和NH4NO2是反應中的關鍵中間體;他們發現,在沒有通入NO2存在的情況下,表面硝酸鹽能明顯增加低溫(< 250 ℃)下的脫硝反應速率,表明NO與硝酸鹽之間的氧化還原反應是速控步驟。但Jiang等[71]提出了Fe基分子篩上的NH3-SCR反應的E-R機制:在標準NH3-SCR反應中,NO首先與活性[FeIIIO]+鐵位點發生氧化還原反應,生成由兩個亞硝酸基聯接的二聚體鐵配合物 [FeⅡO(NO+)-(NO+)OFeⅡ]2+(如圖3(a)所示),然后與NH3親核加成形成[FeⅡO(N(OH))-NH2]+配合物(如圖3(b)所示),該配物內很容易形成分子內氫鍵[74, 75],從而生成 [FeII(OH)]+和 NH2NO,后者迅速分解為N2和H2O。Kovarik等[76]通過原位紅外光譜研究了Fe/SSZ-13上NH3-SCR反應過程中的活性物種及反應機制,發現不同活性鐵物種的反應途徑不一樣:[Fe(OH)2]+可以活化NO生成HONO,[HO-Fe-O-Fe-OH]2+二聚體和較大的含鐵團簇可以活化NO生成NO2,活化后的NO物種與NH3通過反應(16)和(17)生成 N2和 H2O。

圖3 鐵基分子篩在 NH3-SCR 反應中可能形成的中間態過渡配合物Figure 3 Possible intermediate complexes formed on Fe-based zeolites in NH3-SCR

以上研究表明,對Fe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上的NH3-SCR反應,具體反應機制較為復雜,與反應體系、活性鐵物種種類、反應條件等因素有關。
此外,由于二價鐵物種的氧化能壘較高,鐵基分子篩上的活性鐵位點的氧化半循環是NH3-SCR中的關鍵步驟[19]。Kovarik等[76]通過M?ssbauer譜,結合ICP-AES的手段,對Fe/SSZ-13上各種鐵物進行了定量測定,研究發現,NH3-SCR反應中,獨立Fe2+無法被O2直接氧化為獨立Fe3+,從而不能完成氧化半循環;而[HO-Fe-O-Fe-OH]2+二聚體和較大的含鐵團簇,容易被O2氧化為三價鐵物種,從而完成氧化半循環。Jiang等[71]發現,在標準NH3-SCR 反應中,[FeⅡ(OH)]+物種可直接被O2氧化,再生為[FeIIIO]+物種,該四電子的氧化還原過程在高溫下很容易發生,但在低溫下(< 250 ℃)難以發生[71]。在低溫下,活性三價鐵物種的再生主要通過O2氧化二聚體鐵配合物實現:O2可將二聚體鐵物種 [FeⅡO(NO+)-(NO+)OFeⅡ]2+(如圖3(a)所示)氧化為活潑的過氧亞硝酸鹽二聚體([FeⅡON(O)OON(O) FeⅡ]2+) (如圖3(c)所示),后者的過氧鍵不穩定,斷裂后生成NO2,并將二價鐵氧化形成[FeIIIO]+,從而恢復催化活性[77, 78],但這一過程速率很慢,導致反應活性較低。然而,當反應氣氛中存在NO2時,能提供新的途徑促進活性位點的氧化還原循環,從而加速 NH3-SCR 過程發生:低溫下 (< 250 ℃),NO 和 NO2可與 [FeⅡ(OH)]+作用生成 [FeⅡO(NO+)-(NO+)OFeⅡ]2+(如圖3(a)所示),之后其繼續與 NH3親核加成,通過形成[FeⅡO(N(OH))-NH2]+配合物(如圖3(b)所示),最終生成N2和H2O,即通過快速NH3-SCR反應途徑來避開FeII的氧化半循環;高 溫 下 (≥ 250 ℃),NH3和 NO2可 與 [FeII(OH)]+形成絡合物(如圖3(d)所示),該絡合物不穩定,氫轉移后分解為[FeIIIO]+、H2O和NH2NO,后者最終生成N2和H2O,從而實現二價鐵物種的氧化再生。因此,二價鐵物種的氧化半循環的難易,與鐵物種的種類,以及反應氣氛有關。與獨立Fe2+物種相比,由于二聚的Fe2+物種更容易被O2氧化,選擇性的提高催化劑中二聚鐵物種的濃度,有利于NH3-SCR的氧化半循環發生,從而提高催化劑的反應活性。此外,向反應氣氛中添加適量的NO2,也有利于二價鐵物種的氧化,并提供新的反應途徑,從而加速NH3-SCR反應的發生。
綜上,鐵基分子篩上NH3-SCR反應過程中,二聚體Fe3+物種含量較高或形成此類物種難度較低的鐵基分子篩可能擁有更高的反應速率,這與前文中提到的較大孔徑的 Fe-UZM-35[56]、Fe-Beta[42, 44]分子篩擁有更好低溫活性相符,較大的孔徑可以有效降低反應阻力,形成更多的二聚體Fe3+位點,增加NH3-SCR反應速率。溫度不同會導致反應路徑的差異,低于250 ℃下NO2能提供新的途徑來加快反應速率,但低溫下不同鐵物種氧化活性不同,其氧化半循環是活性鐵物種再生的關鍵部分[19]。在反應過程中,中間產物大多為硝酸鹽或亞硝酸鹽類物質(NH3-SCR反應的速控步驟),此類物質能有效脫出N2和H2O使反應高效進行,不同中間產物可能代表反應路徑的不同,反應機理也存在差異。對反應中間體的研究利于優化反應速控步驟,改善鐵基分子篩的脫硝性能。
2 Cu 基分子篩催化劑
2.1 催化劑研究
銅基和鐵基分子篩在NH3-SCR反應中都有很高的選擇性與活性,但化學性質與催化性能卻有很大不同[71, 79, 80]:(1)Fe 與 NO 形成強配合物且與氨形成弱配合物,而Cu與NO、NH3的的配位強弱順序相反;(2)Fe具有親氧性,與含鐵分子篩中的骨架氧原子配位且可以牢固的結合在骨架上,而Cu則被分子篩上吸附的NH3“溶劑化”[71],在分子篩孔道內容易流動和遷移。這些化學性質的差異導致了兩者在催化活性方面的差異[27, 40, 67]:(1)低溫下(< 250 ℃),銅基分子篩具有較高的 NH3-SCR 活性,而鐵基分子篩存在較強的NH3抑制現象,導致其較低的NOx轉化率;(2)銅基分子篩對反應氣氛中NO2/NOx比例不敏感,即標準NH3-SCR與快速NH3-SCR之間的NOx轉化率差異非常小,而由于鐵物種更親氧,鐵基分子篩對NO2更敏感,NO2/NOx= 0.5 為低溫下最佳進料比;(3)鐵基分子篩水熱老化過程中會形成的高度聚集鐵氧化物種不易遷移和流動,對催化劑的破壞性較小;而由于銅物種容易被水溶劑化,且具有很高的遷移速率和流動性,因此銅基相比鐵基分子篩的水熱穩定性一般較差。
由于銅基分子篩較寬的NH3-SCR活性溫度窗口與較高的低溫活性,其相關研究比同類的鐵基分子篩提前3?5年。由于寬活性溫度窗口(200?550 ℃)、高催化活性、高水熱穩定性,具有八元環的小孔CHA結構的Cu/SSZ-13和Cu/SAPO-34分子篩是目前最有應用前景的NH3-SCR催化劑。盡管由于形成的金屬氧化物種的遷移性和流動性的差異,銅基分子篩的水熱穩定性無法與鐵基分子篩相匹敵,但采用Fe/SSZ-13分子篩充當助催化劑的Cu/SSZ-13催化劑已經成功進行商業化使用[81];這是由于Fe基分子篩催化劑具有更高的高溫脫硝活性,并能催化N2O的分解,因此,與Cu/SSZ-13催化劑相比,復合催化劑能大幅拓寬催化劑的活性溫度窗口,提高產物中氮氣的選擇性[40]。
目前,商用銅基分子篩催化劑的重要缺點是高溫下的低活性及低水熱穩定性,為此科研人員相繼開發出了多種銅基分子篩催化劑。Martinez-Franco等[82]發現,與CHA類分子篩擁有相似雙六元環結構的AEI類分子篩Cu/SAPO-18、Cu/SSZ-39在NH3-SCR反應中也表現出優異的低溫活性及水熱穩定性,如Cu/SAPO-18分子篩在240?460 ℃具有90%以上的轉化率,經750 ℃下水蒸氣氣氛老化13 h后,該分子篩晶體形貌保持良好且NH3-SCR活性變化不大。Xin等[83]發現,Cu/SAPO-44分子篩用于此反應時,在180?550 ℃都具有90%以上的脫硝活性和100%的N2選擇性。Picone等[84]使用共模板法合成了具有SAV拓撲結構的Cu/SAPO STA-7分子篩,它具有與Cu/SAPO-34相似的骨架結構,因此,在NH3-SCR中也表現出優異的催化性能。
2017 年,Ryu 等[85]采用具有高硅鋁比(Si/Al =16?23)的LTA分子篩為載體,通過離子交換法制備了一系列具有不同銅含量(0?0.65%)的Cu/LTA催化劑,研究發現,銅含量適中的(0.32%和0.48%)樣品上,Cu/LTA具有與相似銅含量和硅鋁比的Cu/SSZ-13相匹敵的NH3-SCR催化活性,但具有明顯更優異的水熱穩定性。即使在900 ℃、10%水蒸氣的水熱氣氛下老化12 h后,Cu/LTA仍然具有良好的NH3-SCR活性,而Cu/SSZ-13迅速失活。表征發現,Cu/LTA催化劑中Cu2+離子僅位于分子篩單個六元環中心的離子交換位置,是NH3-SCR反應的活性中心;此外,六元環的小孔結構還能有效抑制水熱老化中的脫鋁現象,提高催化劑的水熱穩定性。同時,LTA中較高的硅鋁比,也能有效減少分子篩骨架脫鋁現象,因此,高硅Cu/LTA具有比常規Cu/SSZ-13更高的抗水熱老化能力,是一種極具潛力的高水熱穩定性催化劑。后續研究表明[58, 86, 87], 高 硅 鋁 比 LTA 分 子 篩 是 一 種 高 穩 定的NH3-SCR催化劑載體,這使其具備了替代商用CHA類NH3-SCR催化劑的潛力。
表2總結了具有不同孔道拓撲結構的銅基分子篩及其NH3-SCR性能指標。由于小孔分子篩具有更大的骨架原子密度,且小孔口能抑制分子篩脫鋁和活性Cu物種的遷移,目前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小孔分子篩催化劑的制備上。但Lee等[88]對比了具有大孔結構的Cu/UZM-35、Cu/ZSM-5、Cu/Beta和小孔型Cu/SSZ-13分子篩在NH3-SCR反應中的催化活性,發現具有十元環和十二元環大孔結構的Cu/UZM-35上獨立Cu2+物種含量較高,其脫硝性能與Cu/SSZ-13接近。進一步研究發現,由于Cu/UZM-35分子篩上銅物種與分子篩骨架作用更強,其在750 ℃水熱老化后仍保留了較高的脫硝活性和較寬的溫度窗口,是一種具有應用潛力的大孔型分子篩催化劑。此研究表明,擁有十二元環的大孔分子篩Cu/UZM-35具有與小孔型Cu/SSZ-13相匹敵的脫硝活性與水熱穩定性,因此開發高效脫硝催化劑并不嚴格局限于小孔徑分子篩催化劑。

表2 代表性的銅基NH3-SCR分子篩催化劑總結 (續表2)

表2 代表性的銅基NH3-SCR分子篩催化劑總結Table 2 Summary of representative Cu-based NH3-SCR zeolites catalysts
2.2 活性位點
在銅基分子篩催化劑上,NH3-SCR的機理仍存在較大爭議。出現分歧的關鍵問題如下:(1)活性催化位點是獨立銅還是二聚態銅物種,或其他銅離子團簇;(2)由于NO2能催化快速NH3-SCR反應的發生,提高NOx的轉化率,一些研究人員認為NO2的生成是NH3-SCR過程的決速步驟[95];但后續研究發現,實驗測得NO2的生成速率遠大于NH3-SCR的速率[31],因此,NO2的具體作用還存在爭議;(3)銅物種在反應中的具體氧化還原反應路徑還不清楚;(4)分子篩上Br?nsted酸位點是否與Cu2+離子起金屬-酸中心的協同催化作用。
目前,具有CHA結構的Cu/SSZ-13被用于NH3-SCR反應中活性位點的研究較多,其重要原因是結構中僅存在一個晶體學等效位點,結構較為簡單。Gao等[96]通過離子交換法改變銅物種的引入含量,采用EPR結合ICP的方法探究了Cu/SSZ-13催化劑中銅分布隨銅含量的變化規律,發現在低銅含量的分子篩上,獨立Cu2+通過與兩個骨架Al原子相連的氧原子配位而存在于六元環的離子交換位點;隨著銅離子交換水平的提高,分子篩內形成了穩定的雙氧橋聯二聚銅物種,其位于CHA籠內八元環附近的離子交換位點。此外,Verma等[97]
發現,在Si/Al=4.5的Cu/SSZ-13催化劑上,六元環處的獨立Cu2+存在密度極限值,銅引入濃度一旦超過此值,部分銅物種就會聚集形成二聚態的銅物種。以上研究表明,分子篩中金屬活性物種的分布與金屬引入量有關,調控金屬活性物種分布的關鍵在于匹配分子篩載體的硅鋁比與金屬引入量。
目前,研究者普遍認為,獨立Cu2+物種是銅基分子篩在 NH3-SCR 反應中的活性位點[79, 98, 99],這是由Korhonen等[80]率先提出的,后來Deka等[79]基于同步輻射原位X射線衍射(XRD)和吸收技術(XAFS)的表征結果進行DFT計算,證實了位于六元環平面上或稍微偏離中心位置的離子交換位點的Cu2+離子是Cu/SSZ-13上催化NH3-SCR反應的活性位點。Song等[100]采用H2-TPR結合EPR的表征方法對Cu/SSZ-13上銅物種進行研究,發現催化劑上存在兩種獨立Cu2+物種:Cu2+-2Z和[Cu(OH)]+-Z(Z代表分子篩)。由于Cu2+-2Z在熱力學上更穩定,其H2-TPR還原溫度約為400 ℃,而[Cu(OH)]+-Z更容易被還原,其還原溫度約250 ℃。基于此,Yu等[72]采用原位電子順磁共振(EPR)技術證實了Cu2+的作用:他們發現,當催化劑在270 ℃下暴露在NH3氛圍下時Cu2+被還原為Cu+,再向體系中通入NOx后吸附態的NH3被消耗,而被還原的Cu2+得到再生。Xue等[101]采用EPR、H2-TPR、CO吸附紅外等表征手段,對不同銅負載量的Cu/SAPO-34上銅物種進行了定性和定量表征,發現Cu/SAPO-34分子篩中存在四種銅物種:外表面CuO團簇、獨立Cu2+、納米尺寸的CuO和Cu+;此外,獨立Cu2+物種的濃度與NH3-SCR反應中的NOx轉化率具有正相關關系;進一步,通過動力學研究發現,在100?200 ℃不同銅負載量的Cu/SAPO-34催化劑上的獨立Cu2+的轉換頻率(TOF)幾乎保持不變,這證實了獨立Cu2+是NH3-SCR反應中的主要活性位點。
此外,也有文獻表明,低溫下二聚態的Cu2+物種為主要活性物種,而高溫下獨立Cu2+物種為活性物種。Gao等[96]通過EPR結合ICP的方法,對具有不同銅含量(0.065%–5.15%)的Cu/SSZ-13分子篩上銅物種的分布進行了測定,發現不同溫度下NH3-SCR反應活性中心存在差異:低于250 ℃時,脫硝反應速率與銅負載量的平方成正比,證實二聚態Cu2+物種是低溫下標準NH3-SCR反應的活性中心;但由于Cu2+二聚體不穩定,隨著溫度升高該物種分解為獨立Cu2+物種,并且遷移到分子篩六元環表面成為主要的NH3-SCR反應的活性中心。
最近,許多研究指出活性位點不單是Cu2+物種,Cu+物種在NH3-SCR反應中(尤其在低溫下)同樣起重要的催化作用。因此,活性銅物種是包含Cu+物種和Cu2+物種的混合物,這是由于Cu+/Cu2+之間的氧化還原循環對于NH3-SCR反應非常重要[102]。Mcewen等[103]利用原位擴展X射線吸收精細結構譜(XANES),探究了Cu/SSZ-13分子篩中銅物種在真實NH3-SCR反應過程中的變化,發現在快速 NH3-SCR(氣氛為 NO2/NOx= 0.5)和 NO2-SCR(NO2/NOx= 1)反應中,Cu/SSZ-13 上的活性中心主要是四配位的Cu2+物種;而在標準NH3-SCR(NO2/NOx= 0)反應中,Cu+和 Cu2+物種同時存在,說明Cu2+物種部分被還原為Cu+,兩者共同起催化作用。Chen等[104]發現,由于骨架密度更大,相比于較大孔徑的ZSM-5和Beta分子篩,小孔徑的SSZ-13分子篩上銅物種與分子篩之間的靜電效應更強,更易于形成高穩定性的Cu+,因此能促進銅物種在低溫(< 200 ℃)下的氧化還原循環,降低反應活化能,增強反應活性。Zhao等[105]發現,在Cu-Mn/SAPO-34 上進行低溫(< 200 ℃)NH3-SCR 反應時,Cu+物種與八面體Cu2+物種之間的氧化還原循環,是NH3-SCR反應發生的主要途徑,而與四面體Cu2+物種的之間的氧化還原循環較難發生,導致活性較低。
綜上,銅基分子篩催化劑上金屬活性物種的分布與金屬的引入量有關,實現活性物種分布的高效調控在于匹配分子篩載體的硅鋁比與金屬引入量。NH3-SCR反應中,位于分子篩離子交換位點的獨立Cu2+(如在Cu/SSZ-13上,其占據結構中六元環平面上或稍微偏離中心位置)是該反應的主要活性位點,并且八面體配位的Cu2+與Cu+物種間的氧化還原循環在該反應中起主要催化作用,因此Cu+物種同樣承擔著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低溫下Cu+濃度較高的分子篩具有更加優異的低溫反應活性。因此,改善銅基分子篩上銅物種的分布、增加NH3-SCR反應活性中心物種濃度,對拓寬催化劑的活性溫度窗口、增強水熱穩定性具有重要意義。
2.3 反應路徑
銅基分子篩上的NH3-SCR反應與鐵基分子篩類似,有 Eley-Rideal(E-R)與 Langmuir-Hinshelwood(L-H)兩種反應途徑。多數研究者[72, 106]認為,Cu/SAPO-34上的NH3-SCR反應以L-H機理為主:NH3吸附在Cu2+活性位點與酸位點上(Br?nsted酸與Lewis酸),與Cu2+氧化NO生成的硝酸鹽或亞硝酸鹽結合產生中間體,硝酸鹽類中間體分解產生N2O,而亞硝酸鹽類中間體分解產生N2和H2O。但是,Xin等[107]通過原位紅外表征技術研究了Cu/SAPO-44上的NH3-SCR反應機理,發現向反應體系通入 NO + O2后,Lewis酸位上的 NH3吸收峰立即消失,說明吸附態的NH3能與氣態NOx反應,因此該反應也遵從E-R機理。因此,對銅基分子篩上的NH3-SCR反應途徑的主要爭議在于:ER機理是否與L-H機理同時存在[83]。
此外,銅基分子篩上,Br?nsted酸與Lewis酸位點在NH3-SCR反應中的作用還存在爭議。大部分研究者認為[108],反應中間體主要形成于Lewis酸位點上,而Br?nsted酸位點僅起存儲NH3的作用,不會直接參與反應。Yu等[72]通過原位EPR技術、原位NH3及NO吸附實驗探究了Cu/SAPO-34上NH3-SCR反應中這兩類酸位點的作用,他們發現,在反應開始的 3 min Lewis酸位點(主要為Cu2+位點)上吸附的NH3最先被消耗,之后5 min Br?nsted酸位點(主要為骨架羥基位點)上的NH3才被消耗,生成硝酸鹽或亞硝酸鹽類物種,證實了Lewis酸位點在NH3-SCR反應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也有研究者認為,Br?nsted酸與Lewis酸均在NH3-SCR中發揮重要的作用。Schwidder等[102]通過調節ZSM-5分子篩的Si/Al比研究了Br?nsted酸(主要位骨架羥基數目)對此反應的影響,發現由于Br?nsted酸能促進催化反應的中間步驟(如亞硝酸鹽類物種的分解反應),從而利于NH3-SCR反應的進行,因此,Br?nsted酸濃度高的樣品反應活性高。此外, Brandenberger等[109]還發現,由于靜電穩定作用,分子篩上鋁氧四面體形成的帶負電Br?nsted酸中心,還能促進帶正電荷的金屬離子在分子篩上的分散,從而有利于獨立Cu2+物種的生成。因此,Br?nsted酸與Lewis酸位點在NH3-SCR反應中都具有重要作用,Lewis酸位點上進行主要的反應中間體形成,而不直接參與反應的Br?nsted酸在儲存及運輸NH3和促進中間反應等方面同樣起到重要作用。
研究表明,NH3-SCR反應過程中,反應中間體主要有兩大類:硝酸鹽和亞硝酸鹽類[3]。大部分研究認為,起主要活性的中間體是亞硝酸鹽類中間體,而硝酸鹽會導致N2O副產物的生成。Ruggeri等[110]通過程序升溫脫附實驗和離線紅外表征等手段研究了Fe/ZSM-5分子篩上進行NH3-SCR反應時的中間體的形成過程,證實了亞硝酸鹽/HONO中間體的生成,且其為標準NH3-SCR反應中生成氮氣和水的重要中間體。Tyrsted等[111]通過NO吸附原位紅外研究了Cu/CHA上的NH3-SCR反應中間體,發現NO和O2生成NO2后,可歧化得到雙齒硝酸鹽,后者又可以被NO還原為雙齒亞硝酸鹽(速度慢),從而生成氮氣和水。Wang等[108]采用原位紅外光譜,對Cu/SAPO-34催化劑上,NH3-SCR反應的活性中間體的進行詳細表征,他們觀測到了硝酸鹽類中間體的生成,卻并沒有檢測到亞硝酸鹽類物質,但他們認為,這可能是由于NH4NO2的反應活性太高,無法觀測到,并不能排除NH3-SCR過程中此類物種的生成。Su等[37]采用原位紅外光譜與程序升溫表面反應技術,研究了Cu/SSZ-13催化劑上NH3-SCR的反應動力學,提出了Cu/SSZ-13上硝酸鹽與亞硝酸鹽類中間體的形成與分解的反應機理(圖4)。他們認為,Lewis酸位點上與NH3反應的物質主要是,而的生成難度較大,這是由于NH4NO2的高反應活性,其容易生成N2和H2O而很難被O2氧化為;此外,硝酸鹽生成后,容易分解形成N2O副產物。因此,硝酸鹽的主要作用是與NO反應生成亞硝酸鹽活性物質(被普遍認為是NH3-SCR反應中的重要中間體),其本身并不是活性物質,但亞硝酸鹽活性物質不穩定,因此不易捕捉;此外,硝酸鹽還容易導致N2O的生成,形成副產物,對反應不利[72]。

圖4 Cu/SSZ-13 上硝酸鹽與亞硝酸鹽類中間體的形成與分解[37]Figure 4 Forma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nitrate and nitrite intermediates on Cu/SSZ-13[37](with permissions from ACS publications)
除了催化劑上酸性中心的影響外,Cu負載分子篩催化劑上的NH3-SCR反應路徑和中間體還受反應溫度的影響。Ma等[112]使用原位紅外技術對Cu/SSZ-13和Cu/SAPO-34分子篩上,NH3-SCR反應過程中產生的活性中間體進行在線測量,發現高溫下(≥ 390 ℃)的反應路徑與低溫(< 390 ℃)下完全不同:低溫下,表面氨與硝酸鹽反應生成的NH4NO3是關鍵中間體,被氣相NO進一步還原生成N2和H2O;而在高溫下,氣相NO2是NH3-SCR反應中的重要中間體,預吸附氨與氣相NO2反應生成中間體NH4NO2,形成最終產物N2和H2O。
反應過程中分子篩內銅物種的氧化還原過程,也是NH3-SCR反應路徑研究的重要課題。氧氣對銅的再氧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是NH3-SCR反應的決速步驟[113],再生得到的Cu2+與H2O水合形成較為穩定的[Cu-OH]+。Gao等[21]采用低溫動力學實驗結合DFT理論計算,發現Cu/SSZ-13上進行NH3-SCR反應時,低溫下的氧化半循環由兩個獨立Cu+物種參與,通過形成[CuI(NH3)2]+-O2-[CuI(NH3)2]+中間體來進行,是低溫下氧化還原循環的決速步;而高溫下,NH3脫附后暴露的Cu+與分子篩骨架存在靜電平衡作用,Cu+被氧化為Cu2+的氧化半循環可以在獨立Cu+上完成。Gao等[114]對Cu/SSZ-13催化劑進行了標準NH3-SCR動力學研究,發現只有在反應過程中,XANES光譜上才會出現Cu+特征峰,他們通過原位紅外吸收光譜提出了 Cu2+與 Cu+的氧化還原循環機制(式 (18)?(20)):NO2(ads)生成后發生歧化反應(式 (21))生成 NO+,其與NH3繼續反應,最終生成N2和H2O。Paolucci等[115]通過原位XAFS結合DFT計算的手段,提出了Cu/SSZ-13上獨立Cu2+活性位點的完整NH3-SCR反應機理:吸附在Lewis酸位點上的NH3與被活化后的NO反應生成中間體[CuⅠ-NO-NH2]+,分解生成N2和H2O;O2和NO再生活性位點后與吸附的NH3反應生成亞硝酸鹽中間體,該中間體同樣分解生成N2和H2O,完成NH3-SCR氧化還原循環。

總體來說,銅基分子篩上NH3-SCR反應路徑的研究結論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Br?nsted酸與Lewis酸位點在NH3-SCR反應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反應過程中,中間體形成主要在Lewis酸位點上進行,而不直接參與反應的Br?nsted酸在儲存及運輸NH3和促進中間反應等方面同樣起到重要作用。(2)在NH3-SCR反應中,起主要活性的中間體是亞硝酸鹽類中間體,但由于該類物質反應性較強,相對難以捕捉。而硝酸鹽會導致N2O副產物的生成,且該物質是能提供反應關鍵物種的前驅體。(3)溫度區間的差異導致催化劑上NH3-SCR的反應路徑、反應中間體及反應活性位點等均存在差異。低溫下,二聚態的Cu2+物種為主要活性物種,而NO能還原催化劑表面硝酸鹽類物質生成亞硝酸鹽,進而分解為N2和H2O;高溫下氣態NO2為反應中較為重要的反應中間體,主要活性物種為獨立Cu2+物種。
3 密度泛函理論研究 NH3-SCR 反應機理
目前,在NH3-SCR反應中,由于原子水平的動態和瞬時實驗檢測存在局限性,部分反應機理仍未得到合理的解釋,如NO在反應中如何被活化,氧氣在什么階段參與反應,反應中間體的種類及具體生成路徑等。此外,在NH3-SCR體系中,存在多個的基元反應,這使得具體反應路徑非常復雜,采用實驗手段往往難以區分和研究。而基于量子化學的理論計算能較精確的計算體系的結合能,通過計算分子勢能的變化獲得最優的過渡態分子結構,從而獲得最可能的反應路徑。其中,密度泛函理論(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DFT)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該理論充分考慮了電子的相關勢能,計算精確度較高且速度較快,因此,常用于金屬基分子篩催化劑在NH3-SCR反應中活性位點、反應物吸附形式、反應中間體物種及反應路徑的研究中。
NH3-SCR反應主要發生在活性金屬位點上,因此,對反應路徑的密度泛函理論計算從活性物種在分子篩上的最優位置開始。Mao等[116]基于HSE06能帶理論,計算了Cu2+引入SAPO-34上不同離子交換位后體系的結合能,發現SAPO-34上存在五種銅離子交換位點,而位于六元環平面上或稍微偏離中心位置的Cu2+的結合能最低,是最穩定的分布位置;該位點的Cu2+與分子篩六元環上的四個氧原子配位,平均距離為2.08 ?,為Cu/CHA類分子篩上NH3-SCR反應的主要活性位點。Deka等[79]通過基于密度泛函理論的第一性原理計算,獲得了Cu/SSZ-13上不同離子交換位點上Cu2+的配位鍵長和鍵角參數,發現位于CHA結構中六元環平面上的Cu2+(圖5(a))最穩定,這與原位EXAFS實驗數據結果一致。此外,他們發現在125 ℃ 的標準 NH3-SCR 氣氛下,NH3會與 Cu2+結合,導致活性位點的局域結構從平面正方型變為扭曲的四面體(圖5(b));這種幾何變化在較高(> 250 ℃)的溫度下是可逆的(圖5(c)),且 Cu2+周圍的化學鍵長度和角度都有輕微的變化,表明此位點在反應條件下處于活性狀態,為NH3-SCR反應的主要活性位點。

圖5 Cu/SSZ-13 的六元環平面上的 Cu2+化學環境變化[79]Figure 5 Changes of the local copper environment in d6r subunit of Cu/SSZ-13[79](with permissions from ACS publications)
在某一金屬活性位點上,通過計算反應分子在活性位點上的吸附能、生成活性中間體的吉布斯自由能變化情況,以及反應路徑的活化能壘大小,可獲得反應分子參與反應的具體形式,判斷NH3-SCR反應的路徑和具體機制。Christopher等[117]基于DFT理論,計算了Cu/SSZ-13上NH3、NO、O2及H2O的吸附能,發現在200 ℃、標準NH3-SCR環境下,NH3與H2O會競爭吸附在位于六元環中的Cu2+活性位點上,而由于吸附能太大,NO不會吸附至活性位點上;基于此,計算了NH3的解離過程,發現隨著產物[CuⅡ-NH2/H+]的形成,Cu的氧化態減小到+1.55,但該過程活化能壘太大,不太可能在200 ℃下發生。最終,他們提出了NO輔助NH3解離吸附的機理:NH3吸附至Cu2+位點后與NO生成NH2NO中間體及一個Br?nsted酸位點,而Cu2+被還原為 Cu+,該過程很容易發生(ΔG≈ ?9 kJ/mol);隨后,NH2NO中間體分解為N2和H2O,該過程可自發進行(ΔG≈ ?288 kJ/mol)。因此,[CuⅠ-H2NNO/H+]為Cu/SSZ-13上NH3-SCR反應還原半循環的反應中間體,反應生成 CuⅠ/H+、N2和 H2O。
在NH3-SCR反應中,CuⅠ的氧化半循環涉及到反應中間體的形成與分解,是反應路徑中的決速步。Christopher等[117, 118]通過 DFT理論,計算了200 ℃下Cu/SSZ-13中位于六元環中CuⅠ位點上NH3、NO、O2及H2O的吸附能,結果發現,僅NH3與CuⅠ/H+具有強的結合能力(ΔG≈ ?47 kJ/mol),NO 與 O2僅存在弱吸附(ΔG≈ ?5 kJ/mol),但單個反應物的吸附無法解釋CuⅠ的再氧化過程。因此,進一步計算了其他反應物在該位點上的吸附情況,發現NO2具有更高的吸附強度(ΔG≈ ?90 kJ/mol),且吸附后銅的氧化態由+1變為+2,形成吸附態亞硝酸鹽物種。因此,他們提出,CuⅠ的氧化半循環通過NO2氧化途徑進行,該路徑的反應中間體為[CuⅡ-NO2/NH4+],CuⅡ活性位點被再生且產生N2和H2O。
Mao等[116]基于HSE06泛函理論,計算了NH3-SCR反應中,Cu/SAPO-34上的NO及CuⅠ氧化過程,并充分考慮分子篩中各原子間的范德華相互作用力,得到三條可能存在的路徑(圖6)。他們發現,由于CuⅡ被還原為CuⅠ/H+后吸附氧氣的能力顯著提升(ΔG由+0.52變為~0 eV),三條反應路徑中Z-NH4的反應活化能壘(+0.86 eV)明顯低于ZH(+1.06 eV)和 Z(+3.65 eV)。基于此,他們提出了Cu/SAPO-34上NH3-SCR反應中CuⅠ氧化半循環的反應路徑(式 (22)?(23))。

圖6 Cu/SAPO-34 上不同反應路徑的自由能變化[116]Figure 6 Free energy diagrams of different reaction paths on Cu/SAPO-34[116](with permissions from ACS publications)

綜上,由于NH3-SCR反應的復雜性和原子層面的原位實驗手段的局限性,密度泛函理論是研究金屬基分子篩催化劑上NH3-SCR具體反應機理重要方法。根據分子篩模型中金屬占據不同離子交換位點后體系的結合能的大小,可判斷活性位點的穩定性,從而獲得活性反應位點的最優空間位置;根據不同狀態下的活性位點在反應中化合鍵參數(鍵長、鍵角及鍵能等)的變化情況,可獲得反應中金屬離子的局域環境信息;根據各反應物分子在分子篩模型中吸附能的大小及分子活化勢能的變化情況,可判斷反應物參與NH3-SCR反應的具體途徑;通過設計和計算不同反應路徑,計算反應中間體的生成能壘,可判斷最優的過渡態分子結構及活化能壘最小的反應路徑,從而推測最可能的NH3-SCR反應機理。
4 本征動力學研究
對催化反應的動力學研究,有助于深刻認識催化反應機理及催化劑的作用特征,同時還為工業催化過程確定最佳生產條件、反應器的設計提供理論依據。本征動力學是指消除傳熱、傳質、流體流動等影響因素(排除內外擴散等限制),只研究表面反應部分,因此,更能反映催化反應本身的特性,如催化反應的速率常數可用來比較催化劑活性的高低,表觀活化能可用來判斷催化活性中心的變化情況,指前因子可來判斷反應過程的活性中心數量的變化情況,這些參數都是改進現有催化劑及設計新型催化劑的依據。
通常,為了獲得金屬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在NH3-SCR反應中的動力學參數,首先需要測定各反應物的反應級數以及不同溫度下的反應速率常數,從而構建催化反應動力學模型,最終計算得到反應活化能及指前因子。對于穩態標準NH3-SCR反應,通常使用冪函數模型方程式(式(24))計算反應速率[119]:

式中,r為 NH3-SCR的總反應速率,mol/(g·min);ka為表觀反應速率常數,L/(g·min);t為空時(即反應氣體穿過固定床反應器床層的時間,用W/V表示),單位為(g·min)/L,與表觀反應速率常數單位相反;V為進料氣總流量,L/min;W為催化劑的質量,g;α、β、γ分別是NO、NH3、O2的反應級數。
大 量 文 獻 研 究 表 明[73, 76, 96, 101], 標 準 NH3-SCR 反應中,NO、NH3、O2的反應級數約為 1、0、0.5;此外,O2在原料氣中一般是過量的,因此,其濃度對反應過程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基于此,式(24)可簡化為式(25),對其兩端同時積分并簡化后可得式(26),最后將t和x(x為 NOx的轉化率, %,x=1?[NO]1/[NO]0)帶入式(26)中可得式(27):

因此,可通過測定同一空時t、不同反應溫度T下的轉化率x,根據式(27)獲得不同反應溫度T下的反應速率常數ka,再帶入阿倫尼烏斯公式(28)中,在 lnka和 1/T的線性區間內,通過式(28)擬合得到表觀活化能Ea和指前因子A。

式中,Ea為表觀活化能,J/mol;A為指前因子,L/(g·min);R為理想氣體常數,取 8.314 J/(mol·K);T為反應溫度,K。
Kovarik等[76]采用本征動力學實驗,研究了NH3-SCR反應中,Fe/SSZ-13分子篩水熱老化前后的表觀活化能與指前因子的變化情況,發現800 ℃水熱老化后,樣品的指前因子從 1500 s?1下降到 140 s?1,而表觀活化能從 52.9 kJ/mol下降到 43.8 kJ/mol),指前因子的下降是由于老化過程中活性鐵物種含量下降,導致活性碰撞概率降低引起的;而活化能的下降則說明老化過程使得催化劑上鐵物種的分布發生了改變,活性鐵物種種類有了明顯的變化。進一步,結合活性位點的定量表征,他們發現,老化過程中部分活性鐵物種發生了遷移和聚集,最終與分子篩上的非骨架鋁形成了幾乎無NH3-SCR活性的鐵鋁氧化物種,從而導致活化能和指前因子的下降,以及催化活性的降低。
參考文獻[101],不同研究者獲得的Cu/SSZ-13分子篩在NH3-SCR反應中的表觀活化能差距很小(40?43 kJ/mol),這說明同一催化劑體系下反應活性位點存在相似性。但研究者通過對NH3-SCR反應過程的詳細動力學研究發現,NH3-SCR反應對溫度敏感,不同的反應溫度范圍內,反應機理、活性位點和活化能都存在較大的差異。Brandenberger等[64]采用詳細的表征手段結合動力學實驗,研究了不同反應溫度下,各種鐵物種對Fe/ZSM-5分子篩上的NH3-SCR反應活性的影響,他們發現低溫下(< 300 ℃)獨立 Fe3+為主要活性位點,對應Ea=36.3 kJ/mol; 而 高 溫 下 (> 500 ℃ ) 二 聚 Fe3+物 種([HO-Fe-O-Fe-OH]2+)為主要活性位點,此時Ea為77 kJ/mol,這說明表觀活化能能反映催化劑上活性物種的變化情況,并從側面反映反應路徑的變化。
表3統計了文獻中報道的具有代表性的鐵基和銅基分子篩催化劑上,NH3-SCR反應的表觀動力學參數結果。由表3可知,銅基分子篩的表觀活化能為 29?58.9 kJ/mol,而鐵基分子篩上的表觀活化能為46?58 kJ/mol,這說明不同的分子篩載體中,由于分子篩孔道結構與活性金屬位點的作用力不同,使得活性金屬物種的局域環境和氧化還原活性發生改變,從而使得其催化性能存在差異。此外,表3中,盡管各Cu基分子篩催化劑的表觀活化能測定的溫度范圍均為低溫范圍(100?250 ℃),但也存在差異,這也是導致其表觀活化能不一致的原因之一。而Fe基分子篩是測試溫度范圍比 Cu 基分子篩更高(200?400 ℃),這是由于Fe物種的氧化還原溫度更高引起的[4],這也解釋了鐵基分子篩良好的中高溫活性。

表3 各鐵基和銅基分子篩催化劑上標準NH3-SCR反應的表觀反應活化能Table 3 Apparent activation energy values of standard NH3-SCR reactions over Fe- and Cu-based zeolite catalysts
總體來說,指前因子代表催化過程中活化分子碰撞概率,指前因子的大小間接反映了催化劑上活性中心數目的多少,可用來判斷催化劑中活性位點數目的變化。而表觀活化能則反映催化劑上活性位點的性質,表觀活化能的大小變化,可用來間接判斷催化劑上活性位點種類和分布行為的變化[76]。
5 總結與展望
在NH3-SCR反應中,由于與NO、NH3和O2等反應分子和產物H2O分子之間的配位作用、親和性能等的差異,銅基分子篩具有明顯的低溫(< 300 ℃)催化優勢,但其水熱穩定性往往較差;而鐵基分子篩催化劑具有高溫催化優勢(300?550 ℃),以及相對更高的水熱穩定性。此外,在鐵基和銅基分子篩催化劑的NH3-SCR研究中,與中孔和大孔分子篩相比,小孔分子篩催化劑的催化活性、水熱穩定性等性能均較為優越;但后續研究發現,催化劑的制備方式和分子篩載體的物理化學性質,也顯著影響催化劑的NH3-SCR活性,因此,高活性催化劑的制備并不一定依賴于小孔分子篩催化劑。
鐵基分子篩催化的NH3-SCR反應中,低溫下的主要活性中心為[Fe(OH)]+,在高溫下主要活性中心為獨立Fe3+物種。而銅基分子篩中,NH3-SCR活性中心以位于分子篩離子交換位點的獨立Cu2+為主,但有研究者認為Cu+物種同樣起重要催化作用。此外,活性物種的空間分布和配位環境也是影響其催化反應活性的重要因素,實現活性物種分布的高效調控在于匹配分子篩載體的硅鋁比與金屬含量,對拓寬催化劑的活性溫度范圍、增強水熱穩定性具有重要意義。
提高金屬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的NH3-SCR性能可從以下三點著手:(1)選擇具有合適拓撲結構的分子篩載體,從而優化活性金屬物種的分布,并增加其穩定性,進而拓寬催化劑的NH3-SCR溫度窗口和水熱穩定性;(2)改進催化劑的制備方法,如采用一鍋法等方法優化活性鐵物種的分布;(3)改良現有催化劑,如引入第二種陽離子(Cu或Mn),或采用Cu基和Fe基分子篩的混合,從而拓寬溫度窗口,提高催化活性和水熱穩定性等。
目前,研究者對于金屬基分子篩催化劑在NH3-SCR反應中的具體催化機制,還存在爭議,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1)反應路徑是L-H還是ER機制,還是兩種機制都存在?反應的中間體的捕捉?一般認為,低溫下更傾向于L-H機制,高溫下E-R機制更容易發生,但由于反應催化劑體系和反應條件的差異,以及中間體捕捉的困難性,研究者往往會得到不同的結論。(2)Br?nsted和Lewis酸中心在反應中的具體催化作用?目前,大部分研究者認為,反應中間體主要在Lewis酸位點上形成,而Br?nsted酸中心不直接參與反應,主要起儲存及運輸NH3和間接促進中間反應,如亞硝酸銨分解等作用。(3)金屬活性位點的氧化半循環如何發生?金屬活性位點的氧化反應,受其結構特點、空間環境和反應條件如溫度、氧化劑的影響。綜合文獻,Fe基分子篩中,與獨立Fe2+物種相比,二聚的Fe2+物種更容易被O2氧化,因此,選擇性的提高催化劑中二聚鐵物種的濃度,有利于NH3-SCR的氧化半循環發生,從而提高催化劑的反應活性。此外,向反應氣氛中添加適量的NO2,也有利于二價鐵物種的氧化,并提供新的反應途徑,從而加速NH3-SCR反應的發生。Cu基分子篩中,低溫下的氧化半循環必須在兩個Cu+物種的參與下進行,而高溫下,氧化半循環可以在獨立Cu+上完成,因此,提高獨立銅物種的濃度,有利于低溫下氧化半循環的發生,從而提高低溫催化活性。
以上NH3-SCR反應機理問題的研究,可以通過以下方法進行:(1)首先,構建合適的金屬負載型分子篩催化劑體系,并通過詳細的表征手段(UV-vis、H2-TPR 、XPS、CO-IR 、NO-IR 、EPR、M?ssbauer、XAFS等)分析催化劑上活性金屬物種的含量和分布,并獲得催化劑的酸性質和物理化學性質特征。需要注意的是,為避免反應機理的復雜化,以及活性金屬物種的定性和定量困難,催化劑體系需盡可能簡單,如金屬含量不宜過高(< 2%),金屬種類相對簡單等。(2)通過原位實驗研究,捕捉活性中間體,推測具體反應路徑。如通過原位NH3吸附、NO+O2吸附紅外實驗,探究Br?nsted酸與Lewis酸位點在NH3-SCR反應中的變化情況,并捕捉反應中間體,從而判斷反應路徑和催化機制;通過原位EXAFS實驗,研究活性金屬物種在真實NH3-SCR反應過程中的配位狀態、結構等化學環境的變化情況,從而推斷具體氧化還原反應途徑等。(3)通過反應動力學研究,進一步研究表面反應本征催化機制。通過對反應動力學參數的測定,并結合對活性金屬位點的定性和定量表征,獲得活性金屬位點的主要特征,從而判斷其反應機理。需要注意的是,對反應動力學的研究,需要在本征動力學反應區域內進行,因此,需首先優化反應條件,排除內外擴散的影響,盡量在低溫、副反應較少的情況下進行,這樣能更準確的研究表面反應的本征反應機制。
NH3-SCR反應機理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對金屬活性物種有準確的認識基礎上,需要依賴于多種表征手段。此外,離線表征手段,往往無法準確的反映金屬活性物種在真實NH3-SCR反應氣氛中存在狀態,以及其與反應物和產物的作用形式。因此,對NH3-SCR反應機理的進一步研究,需要借助于多種原位表征手段,如原位紅外、原位EXAFS、原位EPR等,并結合理論計算和詳細的反應動力學研究,從而準確地獲得催化劑上活性物種的活化、反應途徑,進而推斷其具體反應機制,為更深入理解NH3-SCR反應過程提供理論支持,并指導進一步開發新一代的高效NH3-SCR催化劑。
此外,工業實際NH3-SCR反應氣氛中,還存在SO2和H2O等組分[128]。低溫下,SO2會與氨、O2反應,在催化劑表面沉積形成硫酸銨鹽類,覆蓋表面活性位點;此外SO2還會與催化劑上活性銅或鐵物種反應,形成穩定的硫酸鹽類化合物,導致催化劑發生硫中毒從而失活[45]。而高溫水蒸氣反應氣氛下,金屬基分子篩催化劑容易發生結構破壞(分子篩骨架坍塌),以及活性銅或鐵物種的遷移和聚集(形成低催化活性的CuOx或FexOy,以及CuAlOx或FeAlOx等氧化物團簇),最終導致催化劑水熱失活[129]。而在催化劑體系中加入其他過渡金屬(如Ce和Mn[55])作為助劑,可提高催化劑的抗水、抗硫中毒能力,但其具體促進機制仍需進一步研究。因此,探究水、硫中毒過程中催化劑結構和活性物種的變化行為,深入了解催化劑的失活機制,有助于開發出高效、高抗水抗硫性能的NH3-SCR催化劑,以滿足實際工業應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