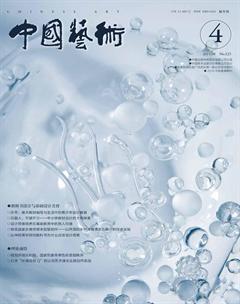日本“環境造型Q”的公共藝術理念及其創作實踐
趙云川 關立新
摘要:在日本公共藝術設置事業中,出現了許多公共藝術家和設計團體,他們以超前的視野和別具一格的方式積極展開城市公共藝術的探索與實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介紹的環境造型Q是由三位頗有名氣的現代藝術家組成的設計團隊,他們以“集團思考開發法”為創作思維方式,將“無個性”的“敞開式紀念碑”作為公共藝術的表現圖式,其鮮明而清晰的創作思想和造型觀念,體現出了對公共藝術本質和原則的深諳,對我國現代藝術家參與公共藝術事業建設具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環境造型Q 公共藝術 共同創作 理念
一、環境造型Q與“共同創作”
“環境造型Q”是一個雕塑家團體,由住在日本關西的山口牧生[1]、增田正和[2]、小林陸一郎[3]三人組成。1968年夏天,小豆島采石場召開了“日本青年雕塑家論壇”[4],三人便以此為契機成立了該團體。在經過了長達20年的創作活動之后,團體于1988年秋解散。關于環境造型Q的名稱,“環境造型”表示環境與造型之間的關系,至于“Q”,則沒有任何意義,只是一個符號而已。
環境造型Q所嘗試的,是三位雕塑家能否站在平等的立場上共同進行創作,并且通過這種合作,對設置在城市公共空間的紀念像或雕塑景觀進行設計實踐和探索。一般而言,人們對雕塑或藝術創作中的平等合作方式常抱以懷疑的目光,因為要達到共同創作似乎只有通過妥協才能實現。事實上,雕塑家在凝神構思時,會在腦海中對造型和樣式進行反復的構建或解體。即便是幾個雕塑家聚集在一起同時構想一個計劃時也不例外,每個人的腦海中都會浮現出各種各樣的形象,且這些形象大多具有明顯的個性化特征。而具有個性的東西常常是非常頑固的,例如,A提出自己所構想的形態,執迷于其他形態的B和C就會很難接受。[5]個性與個性之間是相互排斥的,很難完全對某種個性化的形態達成共識,因此,必須通過妥協才能完成。而這種妥協的方式可能會抹殺藝術家的個性,從而導致藝術品質下降。還有一種情況是其中一個人強烈主張某種個性化的形象,雖然得到了其他人的接納并最終完成了作品,但完成的作品,很難說是建立在平等基礎上共同創作的結果。
可見,共同創作是一個很難發揮出個性的體系。但是,對于環境造型Q而言,他們三人之所以能夠進行共同創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共同創作的作品大多是無須獨特語言和強烈個性的紀念碑式的造型。正如環境造型Q成員之一增田正和所說:“幸運的是,環境造型Q共同制作的是沒有個性的紀念碑。對于作為藝術的雕塑,其價值在于個性的展示,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設置在戶外公共空間的紀念碑,如果以藝術個性之名毫無掩飾地展現出創作者的獨特品位和自我表現欲望的話,就麻煩了。”[6]他繼續解釋說:“戶外公共空間是集散不同人群的場所。在這樣的共享空間中,如果強加上不顧及環境的、個性化的、突出的藝術雕塑,很可能會成為雕塑公害。設置者、制作者、管理者必須十分留意這一點。環境造型Q力求通過探求‘敞開式紀念碑來嘗試解決這一問題。”[7]
上述文字表達出團隊的一些意向。一方面,這里所指的雕塑是設置在戶外公共空間的紀念碑,空間是指各種各樣的人們集散的場所。另一方面,設置在這種特定場所中的雕塑,如果不考慮其環境因素,勢必會造成雕塑的視覺公害。因此,環境造型Q旨在通過共同制作來創造適合于公共空間的、能被公眾認可的紀念碑。應該說,這里所謂的沒有個性,并非是不要個性、不要創作的特色,而是與那些追求造型的純粹性、強調表現欲望,且不用考慮第三者的認知和感受的個性張揚的作品相比,他們的作品更符合環境藝術或公共藝術的創作原則,即在充分考慮環境性、公共性、公眾性的基礎上,追求作品的特色和價值。
在多年探求“敞開式紀念碑”的創作活動中,環境造型Q創作了很多作品。這些作品無不體現著作者對環境造型和公共藝術的理解。下文通過對該團體一些重要作品的介紹,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其藝術思想、創作理念、運作方法和表現形式。
二、環境造型Q的作品分析
1.《致安德羅米達》
在位于日本兵庫縣神戶市填海建造而成的人工島上,共建有北、中、南三座公園。《致安德羅米達》(圖1)是由神戶市港灣局訂購并于1977年設置于中公園的作品。由于當時兵庫人工島還處于建設之中,公園又是從北向南依次建造的,北公園已經設置了由環境造型Q創作的《海豚噴泉》(圖2),所以把該作品放置在中公園。
與開放式的北公園不同,中公園是一個由建筑和樹木環繞的公園。在設計《致安德羅米達》的方案時,設計團隊請來港灣局相關專家以及與神戶有著密切關系的有識之士,聽取他們的意見、了解他們的需求和想法。這種訂購者、制作者以及第三者之間相互交換意見的方法,消解了訂購者與制作者之間的對立和隔閡。在具體設計構思方面,設計者考慮到這是一個為人們提供安心休閑和娛樂的廣場,應避免在這里出現打棒球和排球之類的現象,故采取了兩個具體的對策:一是讓整個廣場起伏不平,二是使用很多石頭加以點綴。對于前者只要考慮好排水問題即可實現。而對于后者,應該放入什么樣的石塊、放入多少及怎樣放置,則需要設計者精心布局和維護者悉心經營。
另外,中公園的周圍環繞著樹木和建筑物,在這樣一個被圍合的空間中沒有可供眺望和欣賞遠景的地形。但躺在草地上,可以看見藍天白云、明月星辰。當把這個廣場作為天與地對話的場所進行考慮時,仙女星的旋渦狀星云便作為重要的主題和共同形象縈繞在環境造型Q團隊三人的腦海中。于是,三人以天體照片為參考,用52個石塊表現出中心稠密、呈旋渦狀并向四周擴展的星云圖樣。布局忠實地以天體照片為依據,52塊石頭布滿了整個廣場。在石頭上爬上滑下的孩子以及守護著他們的父母眼里,《致安德羅米達》可謂是滿足他們的愿望和需要的雕塑作品。
2.《水的廣場》
1984年,環境造型Q在名古屋市名城公園完成了造園要素很強的作品《水的廣場》。名古屋市農政局公園綠地部計劃將古屋市名城公園改造為兒童雕塑公園。在整體規劃中,環境造型Q負責其中一個廣場的改造,這便是《水的廣場》(圖3、圖4)。
改造前的《水的廣場》所在地樹木叢生,還殘留著建筑物地基的平地,是一個給人陰冷感覺的地方。為了把其改造成讓孩子們盡情玩耍的廣場,就需要把這里變成一個明亮的空間。為此,環境造型Q做出了如下構想:首先,只保留周邊的主要樹木,除去中心部的樹木,并在廣場中心部向下挖掘,使其成為平緩傾斜的研缽狀地形。其次,在中央建造小水池,在水池中設置間歇性噴泉,并沿著池塘的外圍布置環狀石帶。然后把從遠處幾個雕塑流出的水營造成流向池塘的潺潺溪流,并在樹蔭下設置石桌和石凳。最后,樹木、溪流、石頭與雕塑的構成還要避免日本式庭院的形象,以帶有圓形劇場的明亮開闊的空間為目標進行建造。具體做法包括在樹根的周圍蓋上表土,然后用小石子覆蓋剩余空間,避免在樹木的周圍配置尺寸高大的造型物。作為溪流水源的雕塑,也被塑造成深受孩子們喜愛的“小馬”“羊羹”“軟糖”等具象造型,同時出于安全考慮,造型物的高度也受到嚴格控制。
《水的廣場》完成后成為公園的中心,并成為兒童喜歡且樂在其中的集景觀與游玩娛樂為一體的場所。該設計在1985年獲得了第一屆“名古屋市都市景觀大獎”,同年又獲得了第二屆“本鄉新獎”。[8]
3.《北斗曼陀羅》
《北斗曼陀羅》(圖5)是1986年設置在札幌藝術森林野外美術館的作品。該作品由樹木和石頭構成,是一個在邊長約為36米的正方形土地上,由459塊北海道產的安山巖基石、9塊經過研磨的能勢產的黑花崗巖以及84棵庫葉云杉苗木所組成的作品。隨著所種樹木的成長,其形態也發生著變化。
人們對此作品有這樣的評價:“像一個沿著地形起伏而擴展開來的巨大的手帕”,“仔細觀察,可以從中看見環境造型Q的原創性”。[9]事實上,把無名性作為理念之一的環境造型Q,很少在作品上署名。這種對無名性的執著,引發了他們把樹木這種自然事物引入作品當中的構思。其典型的做法是先在土地上按照圍棋盤的形狀鋪設安山巖基石,然后在內側按照正方形植樹,進而在內側營建出一個小廣場,再在其中設置造型物。
怎樣才能有效地脫離藝術作品個性化的創作意識,創造“開放式紀念碑”吸引游客呢?為此,環境造型Q考慮用高大的樹木制作一個立方體,該立方體在很遠的地方就可以被人看到,吸引著人們的目光和好奇心。環境造型Q利用已有的樹木進行創作的方式,在名城公園的《水的廣場》中就已嘗試過,但采取植樹的手法這卻是頭一次。栽種的苗木必須是能夠適應北海道寒冷氣候的樹種。在北海道大學農學部的建議和幫助下,環境造型Q選擇了北海道最具代表性的樹木,種植苗木的高度被嚴格控制在四米以下。建造在庫葉云杉林中的草坪廣場是一個面向陽光的暖和的小場所,其中設置了作為該作品核心的造型物。北海道的象征是北斗七星。該作品以北斗七星的形象設置在廣場中。如果把該設計以平面圖呈現,北極星位于正方形最外側的輪廓線上,正好是曼陀羅圖形,由此作品得名《北斗曼陀羅》。
環境造型Q制作的作品管理手冊中有如下內容:樹木下枝開始交叉,為不妨礙成長,1.5米以下的枝按順序剪掉。即使長出苔蘚或出現裂縫,也不要管它。[10]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樹木可能枯萎,石頭可能崩裂。但是在環境造型Q設計者們看來,推移變換的全部面貌盡收眼底或許才是他們期待中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環境造型Q尊崇自然、質樸的造型意象以及追求人造物與自然物在特定環境中融合統一的理念和主張。
4.《美利堅劇場》
《美利堅劇場》(圖6、圖7、圖8)是配合神戶港建造120周年的慶祝活動創作,并設置于美利堅公園的一座紀念碑(1987年4月完成)。1896年,在神戶的神港俱樂部上映了日本最早的電影。在迎來電影放映90周年之際,電影迷組成了電影發祥地神戶紀念碑建設委員會。起初,紀念碑的設置場所定在電影最初上映的地方,后來改在神戶市新建設的美利堅公園中。美利堅公園是為了紀念美利堅碼頭而建造的公園,該碼頭是明治時期以后神戶港的中心,也是許多外國人登陸日本的第一站。當然,電影也是從這里登陸日本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環境造型Q認為,將象征電影的熒幕作為紀念碑主體造型是最合適的。他們設想通過打穿巨石來表現虛擬的映像。人們透過鑿穿巨石的熒幕仿佛可以看到大海和行船,從而牽引出歷史的情節和想象中的映像。在具體營建中,紀念碑以熒幕巨石為中心,對面是舞臺巨石,舞臺石的前面是觀客石,以此來表現與電影相關的制作者、演出者、觀眾的一體感。游客在這里可以成為明星,可以成為導演,也可以坐在觀客石上為明星獻上掌聲。無論誰在這里眺望,都可以自由變換身份。在記憶石的正面,刻著“神戶開港120年紀念·外國電影登陸第一步1896”的字樣,背面鑲嵌著刻有歷史上電影明星名字的青銅板,記錄著20名外國明星、20名日本明星的名字,這些明星是由與神戶非常有緣的電影評論家定川長治選定的。每位明星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都分別被刻入一塊觀客石中,共有42塊。多出的兩塊,是在影迷們的強烈要求下,增加了兩位沒有在定川長治名單中的明星。毫無疑問,設計者在《美利堅劇場》中極力想追求的是,通過以熒幕巨石為中心的景觀設置,加上在電影史上創造業績的觀眾喜愛的明星們的名字的鐫刻,使這里成為電影愛好者的休閑娛樂廣場。
5.其他作品
環境造型Q創作的作品還有很多,如1974年設置在神戶市中央區加納町東游園地的《日本近代洋服發祥地紀念碑》(圖9)、1981年設置在神戶市中央區加納町的《泉聲》(圖10)、1982年設置于兵庫縣姫路市川西臺的《夢想是無限的指標》、1985年設置于伊丹市市政廳前的《白鳥噴泉》(圖11)、1987年設置于須磨離宮公園的《細胞分裂——平行移動》和設置于青野壩址公園的《圣克萊門特巨石墓》(圖12)、1988年設置于碧南市市民醫院前的《螺旋形》(圖13)等。這些作品都不是單一的造型,而是由群體造型組成的,并多與噴泉結合,形成系統化的場所景觀。人們不僅可以在外部觀賞,還可進入其間,形成良好的互動。
三、環境造型Q的理念與方法
環境造型Q團隊共同制作的作品是通過“集團思考開發法”[11]實現的。“集團思考開發法”是一種由多人自由地發表創造性的意向,并逐步引發和展開聯想的方法。在這一過程中,設計者首先要圍繞所給的條件進行自由發言,但是不能當面對他人的發言進行批判或進行關于“形”的帶有個人印象的陳述。他們總是非常耐心地等待設計方向的確定。方向確定了,剩下的就只是細節問題了。在共同擁有了不是哪一個人的方向而是集體智慧所決定的方向之后,便可以推進作品制作工作的展開。
為了不在雕塑配置中加入個人的造型感覺,按原型進行星座配置的方法除了在之前提到的《致安德羅米達》和《北斗曼陀羅》中使用過之外,1985年設置在伊丹市市政廳前的噴泉雕塑《白鳥噴泉》也使用了這種方法。該作品雖然設置在辦公樓前面,但是卻能夠讓市民感到親近,并成為孩子們樂于游玩的地方。應該說,這種不在配置中加入個人造型感覺的設計方式,從1973年在小豆島坂手港共同制作的《八十八所》(圖14)就有所體現。在此作品中,88根石柱(或石墩)的高度分別由88個扎所[12]決定。在以后的作品中,環境造型Q持續使用了這種方法。
創造是環境造型Q所追求的理想,而在野外公共空間設置的紀念碑,必須要得到人們的參與和互動,才能有價值和生命。在這里,“敞開式紀念碑”構想為人與自然共鳴狀態下形成的物象。與因追求個性而呈現出具有獨特性、奇異性的作品相比,他們更在乎作品與公眾、與環境的關系。“就像光的三原色混合在一起成為白光一樣,希望能夠產生沒有三個人個性的無色透明的造型。”[13]盡管環境造型Q還不能完全自信地說可以進行嚴格意義上的共同制作,但是他們的做法可以證明接近理想的共同制作是可能的。
從環境造型Q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或者說是兩種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其一是受東方園林“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的影響。多借助天然的石材作為造型構成的元素,并利用水這種與人極為密切和親近的自然物穿插于其中。在石陣的經營布局中,吸收了中國園林和日本“枯山水”[14]的設計手法及意境,從而使這種“敞開式紀念碑”有了深層的文化內涵。
其二是受到現代抽象藝術(特別是抽象雕塑)和后現代藝術思潮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和受日本“枯山水”設計手法的影響,現代景觀設計開始大量出現硬質景觀。石景設計也伴隨著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日本現代景觀設計大師走上世界舞臺,如野口勇、佐佐木等人的作品中就有大量石景。與此同時,一些杰出的西方景觀設計大師也開始使用經過抽象后的規則石景,如伊拉·凱勒水景廣場的瀑布,就是勞倫斯·哈普林(Lawrence Halprin)對美國西部懸崖與臺地的大膽運用的作品。另外,人造石頭——混凝土的大量使用,也產生了一批杰出的景觀設計作品,如哈普林的經典之作——《愛悅廣場》中極具韻律感的折線型大臺階,就是對自然的高度抽象與簡化。而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產生的后現代主義,極大地擴展了藝術的范疇,其中對景觀設計較具影響的是歷史主義和文脈主義等敘事性藝術思潮。它們或直接引用符號化的“只言片語”的傳統語匯,或采用隱喻與象征的手法,將意義隱含于設計文本之中,使景觀作品帶上地方文化的印跡,具有表述性且易于理解。與20世紀前半葉現代主義設計只注重滿足功能與形式語言相比,后現代主義設計更加注重對意義或場所精神的追求,如野口勇的《加州情景園》等景觀作品就是典型案例。
或許正是兩種思維的交織和碰撞,使環境造型Q能用豐富的設計手法構成自由的平面與空間布局,產生簡潔明快的風格,從而在雕塑創作中開辟出一方不同于傳統雕塑的新天地。事實上,環境造型Q在設計創作中力求每一件作品都能體現出不同的風格和特點,避免樣式的固定。當人們在縱觀環境造型Q的全部作品時,也會看到屬于環境造型Q個性的東西蘊含在這些作品之中。
四、結語
環境造型Q團隊中的三人是日本著名的現代雕塑藝術家,具有超前的意識和現代創作思想。但當他們面對設置于城市環境和公共空間的藝術創造時,便不能張揚個性、自我宣泄,而是要充分考慮公共環境的特性和公眾的需求,展現出一種為社會公眾服務的責任。這一點對藝術家介入公共藝術創作具有啟示作用。另外,環境造型Q在創作中將“無個性”作為一種原則,運用“集團思考開發法”展開工作,一方面是通過深度的溝通融合,為共同合作減少或消解矛盾沖突。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關鍵的一個方面,即“無個性”實際上是對公共環境、場域性、在地性的充分考量,是對社會大眾心理的悉心揣摩,是對公眾性的尊重,體現出設計者對公共藝術性質及設計原則的遵守。他們深知“如果以藝術個性之名毫無掩飾地展現出創作者的獨特品位和自我表現欲望”,會造成與環境空間的不協調,與公眾心理的不對應。而如果以強加方式將這種作品布置于公共場所,不僅難以獲得公眾的認可,最終還可能變成一種公害。因此,環境造型Q力圖肩負起公共藝術家的責任,通過“無個性”的“敞開式紀念碑”的探索來解決問題。他們認為公共藝術作品的設計必須考慮公眾的權利,要深入了解人的生活心理,使人們在與公共藝術作品接觸時,有參與感和互動感。從環境造型Q的公共藝術實踐看,其作品幾乎都能得到公眾的喜愛和認可,正好印證了他們所倡導的“與人的對話才是作品的內容”的創作理念。除了追求與人的對話外,他們十分注重作品與環境性質、空間形式等關系的協調、融合,并追求與周圍風景相呼應,力圖達到作品與人、與自然物的相映生輝。[15]縱觀環境造型Q的作品,表面上看是一種對獨特個性和語言關系的妥協,但實際上是一種公共藝術理想的體現。“無個性”并非真的沒有個性,而是以開放、包容的方式呈現其獨特性。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中日近現代美術比較研究”(項目編號:20BFO82)階段性成果。北京市宣傳文化高層次人才培養資助項目“北京當代公共藝術設置觀念和方法研究”(項目編號:2017XCB02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山口牧生(1927-2001),出生于福岡縣戶畑市。1950年于京都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美學美術史專業畢業,1952年至1958年在大阪市立美術研究所學習雕刻。
[2]增田正和(1931-1991),出生于廣島縣廣島市,1950年于京都大學文學部美術科畢業。
[3]小林陸一郎(1938- ),出生于滋賀縣,1961年畢業于京都市立美術大學雕刻專業。
[4]雕塑論壇是指在特定的自然環境和公園場所,通過明確的目標企劃,設定一定的主題,邀約雕塑名家或經過招募競賽、審查通過的入選者,集中在一起進行一定周期的創作,在主辦方策劃、藝術家創作、公眾參與方面形成互動的公共雕塑設置方式。詳見:趙云川.公共雕塑設置方式略評[J].雕塑,2020(03):50-53.
[5]趙云川.日本公共雕塑的觀念與方法[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226.
[6]增田正和與環境造型Q的共同制作與作品,參見:酒井忠康,米倉守.現代日本野外雕塑[M].株式會社第一出版中心,1991:158.
[7]同[6]。
[8]本鄉新(1907-1980),出生于北海道札幌,日本著名雕塑家。從20世紀60年代起,他為北海道等地制作了大量的公共雕塑,眾多作品被札幌雕塑美術館收藏。“本鄉新獎”是以其命名的日本雕塑領域重要的獎項。
[9]同[6],第160頁。
[10]同[6],第161頁。
[11]集團思考開發法:由許多人自由地發表創造性的想法,逐步引發和展開聯想的方法,也指會議形式。[12]扎所:日本的佛教圣地。
[13]同[6],第162頁。
[14]“枯山水”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庭園藝術。這是一種沒有使用水來表現,卻能體現水態的山水庭園。它不強調“使用”,更多是借用庭園的形式來營造一個能讓觀者遐想的空間,是一種精神的棲息所。
[15]同[5],第265-2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