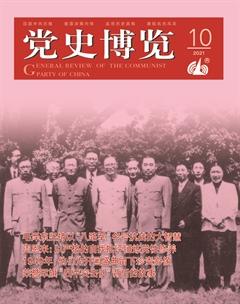如何理解毛澤東1930年提出的“反對本本主義”口號
2021-10-12 02:25:19
黨史博覽 2021年10期
當時,中國革命正在探索正確道路,遇到百怪千難的事情。毛澤東在“山溝里”急于讀到一些能夠用作實踐指導和參鑒的馬列著作,卻非常困難;一些在“洋樓里”能夠遍讀馬列著作的教條主義者,因照搬書本上的詞句而一再壞事。
于是,毛澤東花相當大的精力如饑似渴地去讀另一本“無字大書”——中國農村社會,并寫了大量調查報告。從1927年上井岡山到離開中央蘇區,毛澤東作了10多次社會調查。1930年寫的《尋烏調查》,有8萬字左右。該文寫得非常詳細,尋烏縣城有多少雜貨店,是什么樣的人在經營,經營的本錢和貨物,都詳細列出。縣和有代表性的家族,出過多少秀才舉人和進士,他們在對待革命的態度上的區別,也都寫上了。正是通過大量的農村調查,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獨特性有了越來越實際的感受,由此反對本本主義。隨后,他讀到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類理論書,把書上說的內容和現實感受一結合,便產生“恍然大悟”或“點石成金”之效。這種閱讀效用,和那些號稱“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的人形成鮮明對比,使毛澤東越發覺得有反對本本主義的必要。
反對本本主義的實際含義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離開調查研究,就會產生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領導方法。顯然,這些都是針對教條主義的,反映了毛澤東在讀書問題上的一個鮮明而科學的主張:要把“有字之書”和“無字之書”結合起來讀。要善于運用所學,就必須既入“書齋”,又出“書齋”。這就是他后來反復強調的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毛澤東并不反對“本本”而是反對“唯本本是從”的學風。
(逢周摘自《炎黃春秋》2018年第9期,陳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