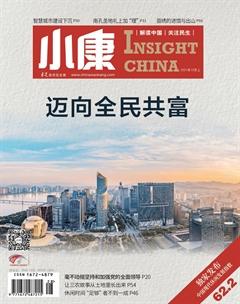入寨出山 留住苗繡
趙狄娜

大山深處的苗寨,人杰地靈,山清水秀。這里既純粹又神秘,盡是別致的風(fēng)情。在苗繡收藏家、中國首座苗繡主題博物館創(chuàng)始人曾麗看來,這樣的風(fēng)情早已被完整無缺、一針一線地繡在了一件件盛裝之上,“苗繡的美是極致的,而極致的美理應(yīng)得到最具誠意的守護”。
盡管身為漢族,曾麗卻早早與苗繡結(jié)下不解之緣。幾十年的收藏和研習(xí)激蕩著她的靈魂,浸染之下,苗繡已成為她生命中不可剝離的存在。
“金領(lǐng)”辭職,只為苗繡
曾麗與苗繡收藏的結(jié)緣,最早可以追溯到她七八歲的時候。她的父親曾憲陽當(dāng)時在貴州畫報社工作,是一名攝影記者,也是后來第一批使用彩色膠卷的人。“在我的印象里,父親常常要去各地出差、探訪,一走就是大半個月,回來時不僅帶著數(shù)量龐大的膠卷,還有各式各樣的苗族服飾和苗繡繡片。”那個時候,曾家的工作臺上到處都攤開著畫冊和書籍,年幼的曾麗就站在工作臺的旁邊,幫父親打理他帶回來的服飾和繡片,一件件地整理熨燙,“很枯燥,感覺好像永遠都做不完似的,也沒什么時間出去玩。”她還記得,小時候因為不懂苗繡的錫繡技法(用金屬錫來刺繡),她還用熨斗把繡片燙化過(錫的熔點很低)。回憶起這些她笑著說:“想一想,那時候我對苗繡甚至是有一點抵觸的,更不用說收藏它們了。”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成年后的她在耳濡目染之下漸漸地體會到了苗繡的魅力。“這里為什么要這樣繡?為什么會選擇這種色彩?這兩處繡工的差別在哪里?從收藏的角度來看它到底好在哪兒?”曾麗常常就這些細(xì)節(jié)和父親一起探討,看繡片或繡服,往往一看就是一整天。這些扎實的知識基礎(chǔ)早已成為她做收藏的“養(yǎng)分”,在苗繡市場涌現(xiàn)之初,她就去參觀和購買過,發(fā)現(xiàn)自己的眼光很獨到,“我能看出哪些和我打小看到的差別很大,哪些才是‘精品。”她意識到,做這行,她有這個能力。
彼時,曾麗其實有一份“金領(lǐng)”工作:做進出口貿(mào)易。她畢業(yè)于西安交通大學(xué),專業(yè)是金屬材料,從事的職業(yè)又光鮮亮麗。但就在事業(yè)風(fēng)生水起時,她卻選擇了辭職,只為了自己那份暗涌于內(nèi)心的情結(jié)——苗繡收藏。
辭職后,曾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赴苗寨。“去苗寨”,早已成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常是趕上一個周末,她開著車就走了,一走很多天。“村民們往往都會翻箱倒柜地找出自己的苗繡嫁衣,穿上讓我拍照,教我運針,分享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故事。”苗鄉(xiāng)苗寨,人杰地靈,卻也古老而神秘,早年間通訊極不發(fā)達。她遭遇過不少驚險時刻,其中一次是在去丹寨石橋的路上,當(dāng)時正逢汛期,快到村子的時候,她剛剛把車從橋上開過,就聽見“咕咚”一聲,整座橋已經(jīng)被大水淹沒。她特別后怕,“再晚一點兒,我肯定連人帶車被吞進去了”。
即便如此,幾十年來曾麗始終堅持扎根在苗寨最深處,“去的次數(shù)根本數(shù)不清”,直到近兩年因為疫情的緣故,進寨的頻率才降低了一些,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7月份。她進寨之后,往往都是和村民們長時間地待在一起,關(guān)心他們的生活現(xiàn)狀,也關(guān)心苗繡在當(dāng)?shù)氐陌l(fā)展。她至今都記得她曾認(rèn)識一位剛剛從福建打工回來的繡娘楊秀芝,“她的技藝非常精湛,繡品精美絕倫,我特別震驚。”但曾麗興奮之余又非常難過,因為這樣的一個“苗繡大師”,迫于生計放棄了手藝,去福建包裝筷子。“她完全不知道她的繡工有怎樣的價值。她甚至?xí)f,還好我沒有女兒,我要是有女兒,絕不讓她繡花。”
類似的情況在苗寨比比皆是。特別是在2000年之后,因為生活的困頓,村民們不得不走出大山,有手藝的繡娘越來越稀缺;而留下來的村民為了迎合銷售,會隨意篡改繡圖,嚴(yán)重破壞了苗繡原本的精神表達,加之苗族各個支系中的老人紛紛離世,代表族群“史書”的紋樣也開始逐漸失傳。這一切都讓曾麗痛心,“收藏之外,我一定還能為苗繡再做些什么。”
是守護者,更是帶動者
曾麗知道,父親曾憲陽始終有一個熱烈的愿望:成立一個苗繡博物館。但由于種種原因,博物館尚未成型,父親卻突發(fā)腦溢血病倒了。“那個時候我想,再難也要把這個博物館做起來。”于是她帶著身上不足兩萬元的現(xiàn)金,找場地,琢磨客源,甚至跑到了當(dāng)時旅游局局長的辦公室。曾麗至今都很感激她遇到了一位特別好的領(lǐng)導(dǎo),“他被我的講述打動了,給了我很多的幫助和支持。”
中國人的小康生活“錄”曾麗:苗繡收藏家、中國首座苗繡主題博物館創(chuàng)始人“正常上班,正常生活,身邊有家人,有朋友,有苗繡,每一天都過得有滋有味。”
如今,博物館已經(jīng)成立10多年,是中國首座苗繡主題博物館,曾麗為此傾注了很多心血。“這些年無論是人們對苗繡的認(rèn)知,還是對博物館的認(rèn)知都在發(fā)生變化。我們也做了很多改進。”除了在博物館中展出自己多年的藏品之外,她還與當(dāng)代藝術(shù)家進行了不少跨界合作展覽,“只把傳統(tǒng)的文化美學(xué)陳列在那里,其實也是一種遺憾。我希望把更多新的技術(shù)引進館內(nèi),讓藏品和觀眾‘互動起來,走入現(xiàn)代人的生活之中,這才是更大的價值所在。”
曾麗對苗繡的付出,遠遠不止這些。此前,她出版了有關(guān)苗繡圖源梳理的書籍《無字天書》,對陰陽魚紋、萬字紋、水波紋、饕餮紋等紋樣做了詳細(xì)注解,希望人們能夠系統(tǒng)了解苗繡;她創(chuàng)立了文創(chuàng)品牌,通過絲巾、服裝、首飾、鞋子及瓷器等形式,傳遞苗繡的魅力,讓繡娘們可以因刺繡而致富。此外,她還開設(shè)了苗繡課堂,從技藝留存和文化傳承兩個方面,把自己的經(jīng)驗分享給人們,“開課的時候我會把繡娘請來,和我一起站在講臺上,我要給她們最大的尊重。”
這么多年,曾麗始終把村寨里的苗人掛在心上,不遺余力地扶持他們。繡娘楊秀芝被她請到過北京講課,后來回到苗寨繼續(xù)刺繡、蠟染,還帶著她的兒子和兒媳婦一同走上通過苗繡致富的道路。苗寨的人們大多對曾麗很熟悉,“我常年都在村子里來來去去,和他們的關(guān)系都像家人一樣。”她經(jīng)常帶大家做苗繡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訂單,帶他們?nèi)コ鞘欣镩_課、教人學(xué)習(xí)苗繡……很多人因為有了這些訂單,可以重返家園賺錢,過上了小康生活,“尤其是現(xiàn)在國家提出了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我特別高興自己可以出一分力。”她非常欣喜地看到,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身苗繡事業(yè),比如丹寨苗族的王石丹,讀完大學(xué)后又返回苗寨,搜集苗繡,撰寫文章,為自己的族群做文化傳播工作,搭建了一道苗族與外界溝通的橋梁。另一位苗族青年顧偉偉,自己開始系統(tǒng)地學(xué)習(xí)苗繡,立志恢復(fù)傳統(tǒng)苗繡和蠟染手工藝。
至于自己心目中的小康生活,曾麗給出的答案意外地簡單:“正常上班,正常生活,身邊有家人,有朋友,有苗繡,每一天都過得有滋有味。”
或許是因為把苗繡作為終身的事業(yè),曾麗始終干勁十足,腦海里關(guān)于未來的規(guī)劃也有很多。“我還想做一個苗繡的全球巡回展,讓世人感受它的魅力和價值,希望消費苗繡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人更多一些,給大山深處的繡娘們創(chuàng)造實實在在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