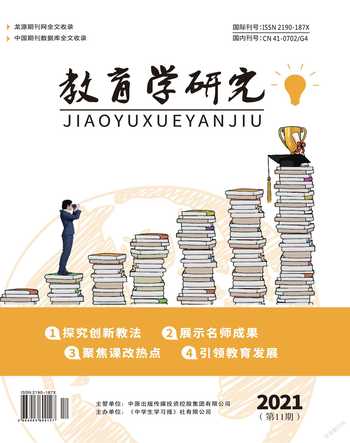從古典審美中的“靜”到近代審美中的“動”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比較18世紀和20世紀初在中國繪畫交流史上融合中西具有代表性的兩位畫家郎世寧和徐悲鴻的畫馬藝術審美中“靜”與“動”,對郎世寧和徐悲鴻的中西融合理論的比較分析,探討中西融合給藝術發展帶來的影響。
關鍵詞:郎世寧;徐悲鴻;中西融合
二、從古典審美中的“靜”到近代審美中的“動”
郎世寧作為第一個將東西方藝術成功結合的外國畫家,他將西方古典油畫技法與中國傳統繪畫相融匯,開創了一種新型的優美的畫風,用靈“靜”的筆法詮釋出全新的靈魂,在宮廷畫中把透視和立體感體現的淋漓盡致,用可視的藝術作品溝通中西方文化內涵;而徐悲鴻身處近代,作為留洋西學的中國畫家,將西畫系統地引入到中國繪畫中,與郎世寧相反的是,他的畫中無不體現出“動”的美感,處處展現著瀟灑、崇高的韻味,使其在中國繪畫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他們二人完美地實現了中西融合,而“畫馬”做為他們繪畫中的代表,在表現上也是各有特點,對中國繪畫有著極大的影響。
郎世寧和徐悲鴻同樣是中西融合繪畫的先驅,都能將中國和西方的繪畫技巧巧妙的結合起來,并且二人都擅長畫馬,但是兩位畫家所呈現的馬是有著不同的視覺感受和心靈震撼的。是什么讓他們二者形成不同的繪畫風格呢,當時離不開他們所處時代的影響以及對繪畫的認識。“各個美術有它特殊的宇宙觀和人生情緒為最深的基礎。”從郎世寧古典審美的“靜”到徐悲鴻近代審美的“動”,向我們展示著不同的中西融合之法以及不同的審美趣味。
(一)從《百駿圖》到《八駿圖》
郎世寧所畫的《百駿圖》被稱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此圖描繪了姿態各異的駿馬百匹放牧游息戲的場面。《百駿圖》是郎世寧的代表作一,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原作分別收藏于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
郎世寧與徐悲鴻所畫的這兩幅作品,都屬于中國藝術史之瑰寶。二人雖都使用中西合璧式的技法,但其馬的形象和畫的特色卻是各不相同,爭奇斗艷。
(二)“靜”與“動”
郎世寧筆下的馬真實、寫實,畫中馬的皮毛、肌肉、骨骼、動作、神態逼真到呼之欲出。在對馬的塑造方面,他沿用西方素描的畫法來描繪馬匹的外形,用非常細的短線來進行塑造。同時又用顏色的深淺變化來突出馬皮毛的獨特質感,用寫實的手法將馬生動形象的表現出來。缺點是缺乏馬的神態表現,畫中的馬大多目光呆板;另一方面馬的毛過于整齊,缺少變化。
徐悲鴻在畫馬時,雖借用西畫素描法十分寫實,但在筆墨上卻仍注重中國傳統畫中的寫意。徐悲鴻畫筆下的馬,一反當時宮廷里所畫的肥碩的馬,則表現的是一群不被束縛的桀驁不馴、自由奔放的野馬,給人脫韁野馬一般的崇高“動”態,八匹駿馬在徐悲鴻的畫筆下被人格化了,充滿生機,頑強且有動力。但是因為徐悲鴻所處的時代背景,他所畫的寫實的馬并不能完整直接地表現他所表達的想法,所以徐悲鴻將馬的造型加以改變和夸張,形成了永恒于世的高長形的悲鴻馬。
郎世寧注重對馬這一客觀事物的表現,強調寫實,而徐悲鴻更多表現的是自己的情感,將馬作為自己情感的主體流露出來,二者在情感的表達方面也都各有不同。
三、“被動”與“主動”的中西融合
從二人的立場來看,二人所處的情境和立場是十分不同的。
(一)郎世寧——被動
郎世寧研習中國繪畫是在皇帝的直接干預下進行的,探索中西合璧的繪畫方式也是迫于壓力亦或是為了迎合皇帝的審美趣味而進行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贏得皇帝的欣賞和信任。
(二)徐悲鴻——主動
與郎世寧的被動相比,徐悲鴻則是積極主動地投身到中西融合的探索中。因辛亥革命后科學和民主思想獲得廣泛傳播,許多文人畫家批評近代中國畫注重模仿而不重寫生,認為西洋藝術尤其是寫實藝術是藝術的精神食糧,學習西方繪畫方式成為了中國美術革命的良方,于是出現了大批有志于藝術的愛國青年外出留學,徐悲鴻便是一員。
四、“西體中用”與“中體西用”
郎世寧和徐悲鴻在中西融合的探索中都選擇用西方寫實繪畫與中國繪畫相結合,但是融合兩方文化的主次是不同的。
首先,郎世寧選擇的是將西方的古典寫實主義油畫的技巧和畫法與中國工筆繪畫的技巧相結合,以西方的繪畫技法為主,中國傳統繪畫的技法為輔。徐悲鴻則選擇中國古典寫實繪畫為西方古典寫實主義相融合,以中法為主,以西法為輔。
其次,郎世寧古典審美中的“靜”,體現的是一種優美、和諧、靜止的感覺,并且更側重馬這一客觀事物的描繪,更有客體性;而徐悲鴻近代審美中的“動”,體現的一種崇高、瀟灑、動態的感覺,更加側重主題情感和情緒的表達,因此更具有主體性。
五、郎世寧與徐悲鴻中西融合繪畫的影響
郎世寧的新體畫可以說是中西繪畫交流史上的第一次實踐,可以說郎世寧的藝術成就也就是中西方文化之間一次成功的交流融合。
與郎世寧新體繪畫的尷尬地位相比,從20世紀20年代到70年代,徐悲鴻的寫實主義改良論和美術教學體系影響了中國半個多世紀的美術教育和美術創作。他的“中西結合”沖擊了中國畫壇萎靡不振的風氣,拓展了中國繪畫的藝術語言,建立了系統科學的美術教育體系,也首次強調了素描在繪畫中的重要性。
郎世寧和徐悲鴻雖然所處的時代不同、環境不同、立場不同,一個是西體中用,一個是中體西用,在他們的畫馬藝術中,一個通過極度寫實,以一種客觀的表現方法,來表現清代優美的馬的面貌;另一個通過一種主體化水墨的形式表現馬崇高的內在精神,在中國畫中貫穿了西畫的科學與寫實。中西文化的碰撞是當下時代的發展趨勢,也必然是未來繪畫的發展趨勢,兩位畫家對于中西文化融合做出了不容小覷的成就。因此,只有將中西的理論、技法、畫風相互交流,有選擇性的選擇、融合,才能使中國繪畫得到真正的發展,才能使世界繪畫風格與特點呈現更多風貌。
參考文獻:
[1] 徐悲鴻.徐悲鴻談藝錄[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44.
[2]馮佳.論郎世寧的中西融合之路[J].文教資料,2011,10:75-76.
[3]吳夷.中西繪畫審美觀的差異共生性[J].北方美術,2009,04:50-51.
作者簡介:牛睿婷(出生年份:1997),女,民族漢,籍貫山東濰坊,職務/職稱無,學歷碩士在讀,單位:山東師范大學,研究方向學科教學(美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