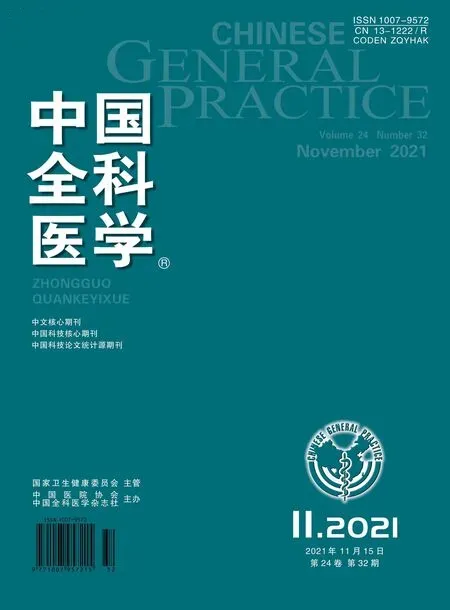雙相Ⅰ型障礙首發躁狂患者復發情況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基于7年的隨訪研究
蘆云平,崔偉,于超,鄭冬瑞,嚴保平,崔利軍
本文價值:
通過對雙相Ⅰ型障礙(BP-Ⅰ)首發躁狂患者進行為期7年的追蹤觀察,了解BP-Ⅰ首發躁狂患者7年內復發情況,并分析影響復發的相關因素,為減少復發、制定干預措施,提供理論依據。
本文局限性:
本研究結果只能反映完成7年隨訪患者的特點,因受研究因素影響,只納入了成年患者,未納入未成年患者,此結果不能代表未成年期患病人群復發特點,有待今后擴大研究對象,進一步闡明不同年齡人群的BP-Ⅰ復發特點。
雙相障礙是以躁狂發作和抑郁發作循環交替出現的一類心境障礙[1],易反復[2],具有高患病率、高復發率的特點,終生患病率為2.4%[3],終身復發率達90%以上[4]。國內外研究共識認為疾病反復發作,可導致人格改變和社會功能受損[5-6],預防或延緩復發已成為雙相障礙的研究焦點[7]。目前有關復發風險的研究多基于橫斷面調查,長期追蹤研究相對較少,結論缺乏一致性。因此,本研究擬通過對雙相Ⅰ型(bipolar disorder-I,BP-Ⅰ)首發躁狂患者進行為期7年的追蹤觀察,了解BP-Ⅰ首發躁狂患者7年內復發情況,并分析影響其復發的相關因素,為減少復發、制定干預措施提供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1年10月至2013年10月在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門診就診和住院的BP-Ⅰ首發躁狂患者。納入標準:年齡18~60歲;符合《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8](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ourth Edition,DSM-Ⅳ )BP-Ⅰ單次躁狂發作的診斷標準;楊氏躁狂量表(Young Manic Rating Scale,YMRS)評分≥20分。排除標準:有腦器質性疾病和嚴重軀體疾病者;癡呆、精神發育遲滯、疑似或確診為癲癇者;精神活性物質依賴和濫用者;哺乳期和妊娠期婦女;色盲或色弱者。本研究經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編號:冀精倫理(科)201809號〕,并經患者或家屬知情同意。根據隨訪7年的復發次數[9]分為兩組,復發次數<4次的患者為低復發組、復發次數≥4次的患者為高復發組。
1.2 研究方法
1.2.1 首發時資料 人口學特征:包括性別、年齡、體質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婚姻、職業、受教育水平;心理認知評估情況:威斯康星卡片分類測 驗(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WCST)、Stroop色-詞關聯測驗(Stroop Color-word Association Test,Stroop)、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疾病特征:陽性精神疾病家族史、發病前有無應激性生活事件、是否伴攻擊特征、是否伴精神病性癥狀、YMRS總分;治療情況:急性期治療時間、接受維持期治療情況。
1.2.2 隨訪資料 于2013年10月開始隨訪,分別于第2年、第4年、第7年進行隨訪,共3次。由經過統一培訓、熟悉研究方案的主治及以上精神科醫師采用DSM-Ⅳ-TR軸Ⅰ障礙定式臨床檢查患者版[10](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Axis I Disorders Patient Edition,SCID-I/P)對患者進行診斷復核。根據患者7年間門診和住院的病歷資料及患者或知情人的訪談完成調查問卷和量表評估。隨訪內容主要包括:第1年內復發情況、只有躁狂發作情況、是否伴精神病性癥狀,計算7年間不同特征發作次數與總發作次數的比值,分別為伴精神病性癥狀發作占比(伴精神病性癥狀發作次數/總發作次數)、抑郁發作次數占比(抑郁發作次數/總發作次數)、躁狂發作次數占比(躁狂發作次數/總發作次數)、維持治療次數占比(接受維持期治療次數/總發作次數);第7年末次隨訪時采用藥物依從性評定量表(Medication Adherence Rating Scale,MARS)評估患者對藥物治療的依從性、采用整體功能評定量表(Global Assessment Function,GAF)評估患者的功能水平。MARS總分為8分,<6分為依從性差,6~8分為依從性中等,>8分為依從性好;GAF總分>70分為社會功能良好,GAF總分≤70分為社會功能不良。隨訪截止時間為2020年10月。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以相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非正態分布計量資料以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檢驗;采用二分類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探討復發的影響因素,Hosmer-Lemeshow檢驗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低復發組與高復發組首發時人口學特征、心理認知評估情況、疾病特征和治療情況比較 共入組147例,完成7年隨訪101例,隨訪完成率68.7%(101/147),其中男49例,女52例;低復發組45例,高復發組56例。
首發時,兩組性別、年齡、BMI、婚姻、職業、受教育水平、WCST中各因子分、Stroop(單字正確閱讀數、顏色正確閱讀數、色詞正確閱讀數)、SSRS總分及各因子分、陽性精神疾病家族史比例、發病前有應激性生活事件比例、伴攻擊特征比例、伴精神病性癥狀比例、YMRS總分、急性期治療時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低復發組干擾量正確數(stroop interference ensues,SIE)低于高復發組、接受維持期治療者比例高于高復發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BP-Ⅰ首發躁狂患者首發時人口學特征、心理認知評估情況、疾病特征和治療情況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psychological cognitive level,diseas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details between two groups at first episode
2.2 兩組隨訪情況比較 低復發組中第1年內復發者比例低于高復發組,只有躁狂發作者比例、維持治療次數占比高于高復發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伴精神病性癥狀發作占比、抑郁發作次數占比、躁狂發作次數占比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BP-Ⅰ首發躁狂患者隨訪情況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follow-up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2.3 兩組依從性、社會功能情況比較 兩組依從性差、社會功能良好比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BP-Ⅰ首發躁狂患者依從性、社會功能情況比較〔n(%)〕Table 3 Comparison of compliance and social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BP-Ⅰ first-episode mania
2.4 BP-Ⅰ首發躁狂患者復發情況影響因素的二分類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 以7年后復發情況(賦值:低復發=0,高復發=1)為因變量,兩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SIE(賦值:實測值)、是否首次接受維持期治療(賦值:是=0,否=1)、第1年內復發(賦值:是=0,否=1)、只有躁狂發作(賦值:是=0,否=1)、維持治療次數占比(賦值:實測值)為自變量,進行二分類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只有躁狂發作為高復發的保護性因素(OR=0.170,P<0.05),見表4。Hosmer-Lemeshow 檢驗結果顯示,χ2=4.751,df=8,P=0.784,提示該模型擬合度好。

表4 BP-Ⅰ首發躁狂患者7年后復發情況影響因素的二分類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Table 4 Unconditional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possibly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ce at 7 years after first-episode mania in patients with BP-Ⅰ
3 討論
BP-Ⅰ是最常見的情感障礙,躁狂首發的患者復發情況有別于抑郁首發患者[11]。長期反復發作會導致家庭和社會疾病負擔嚴重[12-14]。KESSING 等[15]在綜述中提到成人雙相障礙患者第1年內復發率為31.0%~42.0%,而GIGNAC等[16]研究發現首次躁狂發作患者第1年內復發率高達58%。本研究通過對BP-Ⅰ首發躁狂患者進行7年的隨訪研究發現,第1年內復發率為40.6%,表明需關注這部分人群,采取干預措施以降低復發率,從而有利于減輕家庭和社會負擔。
有研究報道,首發認知功能低下的雙相障礙患者后期復發率高,并且提出認知功能低下是造成患者多次復發的原因之一[17]。SIE反映執行功能的優勢抑制成分,SIE愈大,干擾抑制控制能力愈低[18]。本研究結果顯示,低復發組中SIE低于高復發組,提示首次SIE低的雙相障礙患者,今后可能復發率相對低。但SIE在Logistic回歸方程中未被篩選出來,以上研究結果不一致,原因可能與神經認知功能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有關。
中國雙相障礙防治指南(第二版)未明確提出躁狂首發時是否需要接受維持治療,只提到多次發作者,維持期治療時間可為病情穩定達到既往發作2~3個循環的間歇期或2~3年[4]。本研究結果顯示,低復發組中首次接受維持期治療者比例高于高復發組,提示接受維持期治療者后期復發率低,所以首發時也建議進行維持治療,維持期治療時間有待后續研究進一步闡述。此結果與指南不一致,原因可能為研究人群及樣本量不同。本研究結果顯示,低復發組中1年內復發比例低于高復發組,提示第1年內復發者,以后復發率相對高。與GIGNAC等[16]研究結果一致,所以第1年內復發對雙相障礙的結局有一定影響。
國外學者研究發現,首發躁狂的患者在病程中仍以躁狂發作為主,其頻率是抑郁發作的2~3倍[19]。單純躁狂發作的患者復發較少,預后相對較好[11,20]。本研究結果顯示,只有躁狂發作為7年后BP-Ⅰ首發躁狂患者復發情況的影響因素,提示只有以躁狂發作臨床相的患者,以后復發率相對低。所以,BP-Ⅰ首發躁狂患者之后復發時的主要臨床相可作為復發風險和預后評估的重要指標,單純躁狂發作可能有別于躁狂和抑郁交替發作。
有學者提出有效維持期藥物可降低復發率[21],主張維持治療,但也有學者提出是否進行維持治療,應綜合風險和獲益的結果才能決定[22]。本研究結果顯示,低復發組中患者維持期治療次數占比高于高復發組,提示接受維持期治療能夠有效預防復發,本研究結果與中國雙相障礙防治指南(第二版)一致。所以BP-Ⅰ首發躁狂患者應堅持維持期治療。
綜上所述,BP-Ⅰ首發躁狂患者首次發病后執行功能相對良好的、接受維持期治療的、間期只有躁狂發作的、維持期治療次數占總發作次數比例高的患者,后期復發率低;首次發病緩解后第1年內復發的患者后期復發率高,因此在減少復發干預中要考慮到上述因素進行提前干預。其中只有躁狂發作為影響因素,可能只有躁狂發作患者有別于躁狂抑郁交替發作者。
作者貢獻:蘆云平進行研究設計與實施、文章的可行性分析和撰寫論文;于超、嚴保平進行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數據分析;鄭冬瑞、崔利軍進行研究實施、評估、論文的修訂;崔偉進行質量控制及審校,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