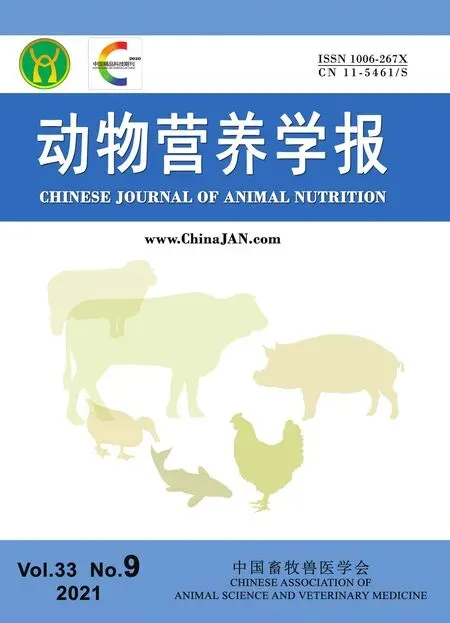間接法測定反芻動物甲烷排放量的研究進展
賈 鵬 董利鋒 屠 焰 刁其玉*
(1.中國農業科學院飼料研究所,農業部飼料生物技術重點實驗室,奶牛營養學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81;2.蘭州大學草地農業科技學院,蘭州大學草地農業生態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蘭州大學農業農村部草牧業創新重點實驗室,蘭州 730020)
1999—2006年,全球范圍內大氣中的甲烷摩爾比例相對穩定,但從2006年開始,大氣中甲烷(CH4)的比例以每年4~12 nmol/mol的速率持續增加。對環境中CH4進行同位素分析表明,2006年以后CH4排放量增加的源頭主要為微生物源CH4。微生物源CH4由產甲烷菌產生,可來自自然界和農業,主要包括沼澤地、水稻田和畜牧業(反芻動物)[1]。2016年,胃腸道CH4排放量為9 870萬t,乳制品行業是全球胃腸道CH4的主要生產行業,CH4排放量為1 860萬t[2]。反芻動物尤其是奶牛將是研究重點,反芻動物CH4的排放除了標志著飼糧能量的損耗,也將加劇全球氣候變暖。在維持反芻動物健康及其瘤胃正常發酵功能的前提下,降低動物機體CH4排放量,既有利于提高飼糧能量利用,又有助于緩解全球氣候變暖。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于反芻動物CH4排放。
反芻動物CH4排放量的檢測方法具有多種,適用范圍不同。檢測方法的選用是研究的基礎,關于反芻動物CH4排放量檢測方法中的直接檢測方法已有報道[3],本文將對間接測定方法進行論述。
1 間接測定法
檢測方法可分為直接法和間接法。直接法主要包括呼吸代謝室法、SF6示蹤法和GreenFeed系統法。直接法具有測量準確的優點,呼吸代謝室法更是被作為“黃金標準”。但直接測定法也具有弊端,如造價高、操作復雜等。間接法具有成本低、操作簡單、短時間內可重復測量和適用范圍廣的優點,因此間接法也是一種選擇,其主要分為二氧化碳(CO2)示蹤法、嗅探器法和激光檢測器法等。
1.1 CO2示蹤法
Madsen等[4]提出了用估算的CO2排放量和測量的呼出氣體中CH4∶CO2的比值來測算動物CH4排放速率的方法。CO2的排放量可以基于能量代謝、產熱和呼吸熵或碳平衡來估算,呼出氣體中CH4∶CO2的比值可通過便攜式設備測量。計算公式為:
CH4(g/d)=CO2×([CH4]M-[CH4]BG/
([CO2]M-[CO2]BG)。
式中:CO2是估算的動物生產量(g/d);[CH4]M和[CO2]M分別為測定的呼出氣體樣品中CH4和CO2的濃度;[CH4]BG和[CO2]BG是背景空氣濃度。

表1 反芻動物CH4排放量的間接測定方法及其應用特點Table 1 Indirect methods of CH4 emission from ruminants and its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CH4∶CO2比值對結果至關重要,CH4和CO2的排放量與干物質采食量(DMI)密切相關。另外,動物CO2的排放量即使在DMI相同的情況下,也會受到消化和代謝活動變化以及飼料利用率差異和瘤胃發酵變化的影響[5]。因此,CO2示蹤法與GreenFeed法相同,應當有足夠的采樣次數和時間點。樣品氣體的來源(呼出氣體、直腸排氣、糞便或臥床墊料的發酵等)以及由于動物活動、飼糧顆粒大小、飼喂頻率相關的發酵速率的差異而導致的CH4∶CO2比值的日變化,都會影響此方法的準確性[4]。
CH4∶CO2比值的應用在某些方面與SF6示蹤法相似,但與SF6示蹤法相比,其示蹤氣體(CO2)的排放量為估算值,而SF6示蹤法采用瘤胃內滲透管中的示蹤氣體(SF6)的釋放率為已知并經校準。另外,此方法估算的CO2產量只能代表某個時間點,并不是全天綜合測量。Haque等[6]分別用此方法估算和用呼吸室法測量的CO2產量計算CH4產量,結果表明,與呼吸室法相比,此方法的CH4產量的組間差異較小并改變了組間的顯著差異性。Hellwing等[7]將此方法與呼吸室法相比,此方法顯著低估了CH4的排放量(降低了17%)。需要改進對動物因素引起的CO2排放量的日變化的預測,以獲得更加準確的個體動物CH4排放量估算值。雖然CO2示蹤法不及“黃金標準”的呼吸代謝室法準確,但其操作簡單也不受場地限制,具有更強的靈活性。
1.2 嗅探器法
Garnsworthy等[8]提出了另一種間接法—嗅探器法,通過估算動物的噯氣頻率和噯氣中的CH4含量,進而算出CH4排放量。在自動擠奶系統的喂料槽中安裝取樣口,每隔1 s對料槽空氣中的氣體濃度進行連續取樣、分析和記錄。程序識別和量化CH4濃度峰值(噯氣)和峰值頻率(噯氣頻率),計算每只動物每次擠奶時的CH4排放速率(MER),即每分鐘噯氣次數乘以噯氣峰面積。使用經校準的氣體釋放量,在每個采樣周期結束時估算噯氣稀釋率。計算公式如下:
CH4(mg/L)=(噯氣峰面積×噯氣頻率)×
稀釋因子[9]。
對于測量呼出氣體中氣體濃度的嗅探器技術,動物頭部距采樣點的距離對CH4和CO2濃度的影響巨大。即使是頭部位置的微小變化也會在測量的氣體濃度上產生很大的差異,CH4濃度的變化與頭部移動和位置的差異以及喂料槽幾何形狀產生的可變空氣混合狀態相關聯,而不是CH4排放量[5]。Wu等[10]還提出了牛只呼氣速率之間的差異也可導致系統誤差。呼出氣體中CH4濃度的重復性與每次擠奶過程中頭部位置和行為的重復性具有簡單的關聯性。比如測得牛只的CH4排放量較低,其實質原因可能是牛只在擠奶過程中不安寧或者習慣將頭部遠離采樣管。另外需要關注的是,單個牛只在每次擠奶時由于產奶量、胎次、同時擠奶的奶牛數量和社會優勢等因素造成的行為差異,采食量和飼喂方式的差異[11],以及采樣時間的差異,將影響結果的重復性和準確性。牛只呼出氣體中的CH4相對于CH4總產生量的比例,在動物之間有一定的變化范圍,這也將對試驗結果造成影響。
有研究表明,同一動物在牧場擠奶期間的MER與在呼吸室內測得的每日總CH4排放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8]。但Huhtanen等[5]發現,在2項奶牛試驗中其可變性均較大,并且與GreenFeed法的結果沒有相關性。Van Engelen等[12]在自動擠奶系統中使用嗅探器法測出空氣中CH4∶CO2的比例平均值和變異系數分別比Aubry等[13]的結果高出約2倍和5倍,在生物學上都是不現實的,其原因有待進一步探究。該方法遺漏了呼氣中的CH4排放量;另外,奶牛間CH4排放量的真實變化太小,嗅探器方法精度較低,所以需要進一步改進以得到可靠的測量值。但是嗅探器法在長時間條件下,只需較少的費用就可進行數百次的重復測量。
1.3 激光檢測器法
激光CH4檢測器基于CH4的紅外吸收光譜原理,在距動物1~3 m內,可以測量出裝置與動物間的空氣中的CH4濃度。數據采集程序為連續2~4 min的短時間測量,結果由一系列代表動物呼吸周期的峰值組成。僅使用由于呼氣或噯氣導致CH4濃度增加的峰值進行分析,測量的氣體濃度根據采樣距離和背景濃度進行調整[14]。
激光檢測器法沒有采集氣體樣品,而是對動物呼吸的實時測定。結果為由于呼吸的生物力學和測量裝置的正常波動而產生的自然波動,波動除了正常的呼吸周期外,還包括陣發性的反芻片段以及微小的波峰和波谷。呼吸周期從最大峰值中獲得,微小的波峰和波谷不會影響測量結果,完整呼吸周期內的波動可以用滾動平均法或數據平滑方法來調整[15]。雖然激光檢測器法可以很容易地獲得CH4濃度的平均值,但為了改進激光檢測器法數據與呼吸室數據之間的相關性,并提高檢測單個動物之間CH4排放差異的技術靈敏度,需要將收集的數據分為呼氣和噯氣CH4[16]。可用每個測定周期的標準差作為閾值,從而將反芻片段從呼吸周期中分離。風向會影響測量結果,導致測量值由大到小的風向分別為順風、側風和逆風,并且風速與測量值呈顯著逆相關。
激光檢測器法與呼吸代謝室法之間只存在較弱的正相關關系[14,17]。其準確性受溫度、風速、濕度和鄰近動物等因素的影響,并且研究人員需要頻繁地接觸動物也將帶來差異。但是該方法不受頭部位置影響且測量速度快,可以在飼養場和大群試驗動物條件下應用,只要動物保持足夠時間的靜止,在擠奶和采食等情況下均可測量。
2 間接預測CH4指標
2.1 DMI
在全球網絡數據庫中顯示,CH4預測模型中的變量越多,其結果越準確。然而,僅含DMI的簡單預測模型與較復雜模型相比,預測能力無差異[均方根百分比誤差(RMSPE)=15.2%~21.4%][1]。因此,僅僅需要DMI就足以預測胃腸道CH4排放清單[18]。
Appuhamy等[19]使用包含實測的DMI和飼料特征屬性的數據評估了40個預測方程。然后再使用估測的DMI重新評估每個區域(北美、歐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中表現最好的模型,并與使用實測DMI得到的預測值進行比較。對于北美地區,DMI估測值可以一樣能夠很好地預測CH4排放量;對于歐洲,使用DMI估測值比DMI測量值能夠更好地預測CH4排放量;而對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DMI估測值預測CH4排放量的效果不佳。可能因為預測模型是根據北美地區數據得到的,無法適用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采食牧草較多的放牧牛只。結果表明,只要能夠合理準確地估測出DMI,將其帶入模型得出的CH4排放量與實測數據一樣準確。
但是CH4排放量實測值與DMI之間的決定系數是高度可變的,受DMI數據值范圍和CH4排放量檢測方法等因素的影響。DMI數據值范圍方面,Charmley等[20]選擇來自澳大利亞的肉牛及奶牛共1 033個測量數值作為數據集,研究表明CH4排放量和DMI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當DMI數據值范圍為2~28 kg/d時,截距接近于0;當DMI數據值范圍縮小為>15 kg/d時,CH4排放量和DMI之間決定系數(R2)降低至0.41,RMSPE增加至68.2。DMI數據值范圍越廣,它們之間的關系越強[20-21];DMI數據值范圍越窄,關系越弱[22]。CH4排放量檢測方法也會影響R2,Grainger等[23]對奶牛數據進行了Meta分析,采用SF6技術測量的CH4排放量和DMI之間的R2=0.56,而采用呼吸測熱室測量的CH4排放量和DMI之間的R2=0.39。在Hristov等[22]的奶牛試驗中表明,GreenFeed系統與SF6技術之間具有差異,得到的CH4排放量和DMI之間的R2分別為0.47和0.08。Niu等[24]年發現,與呼吸測熱室相比,采用GreenFeed系統與SF6技術得到的CH4排放量和DMI之間的相關性較弱。
2.2 CH4排放因子
目前,一些國家通常使用IPCC Tier 2方程來評估動物胃腸道CH4排放量:
CH4=Ym×GEI。
式中:CH4是胃腸道CH4排放量,單位為MJ/(頭·d);Ym為CH4轉換因子,定義為GEI的百分比。
雖然GE可以用氧彈法測定,但這種分析方法繁瑣。IPCC(1997)指南通過確定機體維持凈能來估算GEI,然后使用估算的能量消化率和可消化能量利用效率將其與DMI聯系起來。確定GEI和Ym所涉及的步驟在估算胃腸道CH4排放量時會引起誤差。將Ym作為恒定值是主要原因,因為它隨著DMI和DM消化率的變化而發生較大變化[20],它可以是3%~10%的任意值[25]。飼糧質量、生產水平(與DMI相關)和飼糧結構等因素均影響以CH4形式造成的能量損失比例[26-27]。因此,設定一個常數Ym可能會導致CH4排放量估算中相當大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在具有不同生產系統的地區。如北美奶牛的平均Ym為5.4%~5.7%,歐洲Ym為6.0%~6.9%,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該值(6.6%)更接近IPCC建議值[1]。近年來國內已有相關研究,王貝等[28-29]試驗表明,泌乳中期荷斯坦奶牛的Ym高于泌乳高峰期荷斯坦奶牛;董利鋒等[30]和李斌昌等[31]研究表明,飼糧結構顯著影響荷斯坦泌乳后備牛的Ym。
因此,應該在各個區域而不是全球的基礎上建立估算奶牛胃腸道CH4排放量的模型。
2.3 血液胰島素及乳中脂肪酸濃度
反芻動物CH4排放量和血液代謝產物均受到飼糧類型和DMI的影響,所以CH4排放量和血液代謝產物之間可能存在某些相關性。在奶牛試驗中表明,甲烷產量高組牛只與甲烷產量低組相比,其具有較高的血液胰島素濃度和較低的葡萄糖/胰島素比值[2]。在隨后的相關性分析中顯示,牛只CH4產量與血液胰島素濃度和葡萄糖/胰島素比值均具有中等強度的相關性,R2分別為0.54和0.52。研究證明,血液胰島素濃度具有作為奶牛CH4排放量標志物的潛力,具體關系還有待進一步探究。
瘤胃中的發酵還導致產生VFA,VFA是乳腺中合成短鏈和中鏈脂肪酸的前體物質。此外,某些VFA(如乙酸或丁酸)產生途徑會導致氫氣(H2)的產生,而丙酸產生途徑會使用H2,產甲烷菌也會利用H2產生CH4。因此,瘤胃發酵和CH4生成與牛奶脂肪酸成分之間存在直接的相互作用。Van Lingen等[32]采用Meta分析法得出牛奶脂肪酸成分與瘤胃CH4排放量之間呈中等強度關系;Bougouin等[33]也使用Meta分析法,共搜集了來自5個國家825頭荷斯坦泌乳牛的數據,結果表明牛奶中脂肪酸可以較好地預測CH4產量。
3 預測模型
測定反芻動物CH4排放量,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生產實踐中也無法對所有動物進行測定,可通過CH4預測模型解決。預測模型是根據反芻動物CH4排放量的實測數據,應用統計方法建立的統計模型。總的來說,胃腸道CH4預測模型是基于各種動物或飼料的特征,但以某種形式受DMI支配[1]。因此,準確預測DMI是準確預測反芻動物CH4排放的關鍵。預測模型已被廣泛應用于各種用途的CH4排放量估測,比如預測CH4排放清單,模型類型包括從簡單的排放因子和經驗模型到更詳細的機理模型。
3.1 經驗模型
經驗模型是根據大量的測量數據結合能量平衡的原理,建立在飼糧攝入量、飼糧成分和其他動物因素與胃腸道CH4排放之間的數學或統計關聯基礎上的。自Kris等[34]建立統計模型以來,已經發展出多個經驗模型。經驗模型可以相對容易地從觀測數據中建立,并不需要輸入大量數據,所以常被用來估算全國或全球動物胃腸道CH4排放量清單,以評估CH4對溫室氣體的作用。
Demarchi等[35]和顏志成等[36]分別在肉牛和奶牛上進行了研究,用不同季節的DMI和CH4排放量建立了CH4預測模型,結果表明春季模型的R2均高于冬季。Demarchi等[35]模型:
春季CH4(g/d)=36.31×dDMI(kg/d)-
3.9(R2=0.92);
冬季CH4(g/d)=18.11×dDMI(kg/d)+
53.64(R2=0.53)。
式中:dDMI為可消化的干物質采食量。
顏志成等[36]模型:
CH4(g/d)=22.4×DMI(kg/d)+26.4(R2=0.90);
CH4(g/d)=17.0×DMI(kg/d)+11.1(R2=0.30)。
使用DMI作為單一變量,忽略了飼糧的特性對動物CH4排放量的影響。因此,Moe等[37]使用攝入飼糧的中性洗滌可溶物、纖維素和半纖維素含量與奶牛CH4排放量,攝入飼糧的瘤胃可消化的中性洗滌可溶物、纖維素和半纖維素含量與奶牛CH4排放量分別建立了預測模型。Moe等[37]模型:CH4(g/d)=61.7+9.25×NDS(kg/d)+48.0×Cel(kg/d)+31.5×Hemi(kg/d) (R2=0.67);CH4(g/d)=33.3+20.7×dNDS(kg/d)+106×dCel(kg/d)+38.8×dHemi(kg/d)(R2=0.73)。
式中:NDS為中性洗滌可溶物;Cel為纖維素;Hemi為半纖維素;dNDS為瘤胃可消化的中性洗滌可溶物;dCel為瘤胃可消化的纖維素;dHemi為瘤胃可消化的半纖維素。
此后,馮仰廉[38]使用肉牛CH4排放量、粗飼料來源中性洗滌纖維和瘤胃可發酵有機物質建立了預測模型,進一步提高了R2(0.97)。馮仰廉[38]模型:
CH4(L)=0.297×FNDF(kg)+60.46×
FOM(kg)(R2=0.97)。
式中:FNDF為瘤胃可發酵中性洗滌纖維;FOM為瘤胃可發酵有機物。
在肉用綿羊上,周艷等[39]進行了全面研究,對不同生長階段分別建立了一元和多元方程。生長早期分別為:
CH4(L/d)=-26.58×NFC/NDF+92.7
(R2=0.772);
CH4(L/d)=2.71×DNDF-2.45×
DDM-0.97×DCP+124.46(R2=0.846)。
生長后期分別為:
CH4(L/d)=-57.00×GE(MJ/kg)+
1 076.0(R2=0.581);
CH4/BW0.75(L/kg0.75)=-0.013×
NDFI(g/d)-0.13×CPI(g/d)+0.02×DMI(g/d)+
0.84(R2=0.652)。
生長期整體為:
CH4(L/d)=-26.94×NFC/NDF+90.71
(R2=0.655);
CH4/BW0.75(L/kg0.75)=0.005×
DNDFI(g/d)+0.011×dDMI(g/d)-0.097×
DCPI(g/d)-4.78 (R2=0.722)。
理想的經驗模型,應該從包括1 000個以上動物或處理組平均測量值中建立,并有影響動物CH4排放量的飼糧和動物信息。目前,CH4排放數據主要來自歐洲、北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全球數據來源并不均勻。
3.2 機理模型
與經驗模型相比,根據營養代謝建立的機理模型數量有限,其通過預測動物消化道的營養物質吸收以及VFA產量,并且通過增加氫的計算來改善對胃腸道CH4排放量的預測。
機理模型預測CH4排放量的基本原理相似。均建立了瘤胃或后腸發酵過程中營養物質的消化、吸收、微生物生長和發酵的化學計量法,以確定VFA的類型和數量、產氫量以及最終的胃腸道CH4排放量。這些模型的主要區別在于所含微生物的數量、飼料的來源和顆粒度、生產VFA的底物以及VFA化學計量法。
在所有的模型中,CH4的排放量都是通過計算瘤胃中的氫平衡得出,并假設所有的氫都轉化為CH4。然而,由于飼糧成分的不同將造成動物產氫量較大的差異,并且產氫量具有全天變化,在采食后不久即達到峰值。王榮等[40]的研究對此進行了改進,根據VFA代謝產生的80%的氫用于CH4合成建立的模型與所有的氫用于CH4合成建立的模型相比,大大提高了預測精度。機理模型中CH4排放量的預測精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用化學計量模型的準確性及其預測VFA摩爾比例的準確性。Alemu等[41]評估了幾個化學計量模型,得出RMSPE為5.2%~43.2%,表明它們的性能差異較大。很少有人研究測量VFA的產生率,因為這需要使用同位素來區分在瘤胃中觀測到的VFA濃度和生產速率。研究人員使用機械模型Tier 3應用于全國奶牛CH4排放清單,使用這種方法,能夠解釋由于飼草青貯質量和DMI的變化而觀察到的胃腸道CH4排放量的部分變化[42]。
機理模型能夠獲得更加準確的估算值,但其需要應用與生物化學相關的數學參數,對數據要求較高制約了它的廣泛使用。
4 結 論
間接法的測定儀器和預測模型均具有簡單快速的優點,可根據各個地區硬件條件和可獲得數據,選擇合適的測定儀器和預測模型。任何一個特定的模型在預測CH4排放量上都有優缺點,多模型集成方法學已成為一種廣泛可接受的方法,可利用互補的單個模型并調整各種偏差來改善預測準確度。適用性廣且穩定性高的預測模型必須基于大數據的采集與分析,從眾多的因果參數中歸納他們之間的關聯,目前我國數據量仍然不足,加大動物的測定數量,建立適用于當地的預測模型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