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獵者”與“虔信者”:在粉絲文化的“兩副面孔”之間
□王玉玊
【導 讀】本文通過回顧21世紀以來中國網絡粉絲文化與粉絲文化研究的兩個階段,分析粉絲之為“文本盜獵者”與“迷狂的虔信者”這兩副截然相反的面孔背后,粉絲文化一以貫之的核心訴求與本質特征——作為粉絲文化“中心物”的偶像不過是“泡沫塑料制成的濕婆神像”,勾連起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共同體代償實踐。
回顧21世紀以來中國的網絡粉絲文化和粉絲文化研究,可以以2015年前后“內娛飯圈”(大陸真人偶像粉絲圈)的崛起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各式各樣以粉絲文化為基礎的青年亞文化在中國的網絡空間中生長起來,新的網絡文藝形式和網絡文藝作品隨之大量出現,中國的互聯網粉絲群體開始以“文本盜獵者”的正面形象進入學術研究視野。到了第二個階段,隨著“飯圈化”現象在網絡空間各個圈層普遍發生,對于粉絲社群與粉絲文化的憂慮與批評再度占據了絕對主流,粉絲作為偶像的非理性的狂熱信徒的形象重被加強。在粉絲文化的這兩個階段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我們又該如何理解粉絲群體“盜獵者”和“虔信者”的兩副面孔之間的割裂?剝除時代整體氛圍的變遷不可避免地帶給粉絲文化的一系列影響,我們或許才能在粉絲文化“兩副面孔”的夾縫間,理解其固有本質。
一、商業化與版權之爭:“飯圈化”的前奏
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初,或許是粉絲文化在中國的學術研究中聲譽最好的時期,以約翰·費斯克和亨利·詹金斯等為代表的英美粉絲研究理論為解釋今天中國的粉絲文化提供了新的理論資源,研究者寄希望于粉絲文化社群以“過度的消費者”和“文本盜獵者”的身份進行參與式文化生產,帶來新的文化創造,以及具有活力的文藝生產新形態。
楊玲在其2012年的著作《轉型時代的娛樂狂歡——超女粉絲與大眾文化消費》(以下簡稱“《轉型時代的娛樂狂歡》”)第一章第三節“一個學者粉的告白:研究身份與方法”中明確提出“將遵循英美粉絲研究的傳統,以一個學者粉的身份對超女粉絲群進行民族志研究”[1],以糾正那種將“粉絲”簡單建構為“學者”的對立面,定義為“著魔的個體和歇斯底里的群眾”[1]60的研究范式。《轉型時代的娛樂狂歡》始終有意無意地強調超女粉絲群體的精英面向:
超女粉絲的文化層次和經濟地位都比傳統粉絲要高……超女節目“比較受到中、高SES(經濟和社會地位)階層的關注”,是一種超越了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二元對立的“混合文化”。[1]3
這種對于粉絲群體精英特質的強調,指向了對粉絲創造消費時代新文化之可能性的肯定。全書第四章整個章節都用來描述超女粉絲小說的發展情況,并用了大量篇幅對超女同人小說做了詳細的文本分析,也即將把粉絲創作的同人小說等同于一般文學作品進行分析,從而肯定了超女精英粉絲的文學創作與文化生產能力,肯定了同人創作本身的文學價值,這在此前的研究之中是非常罕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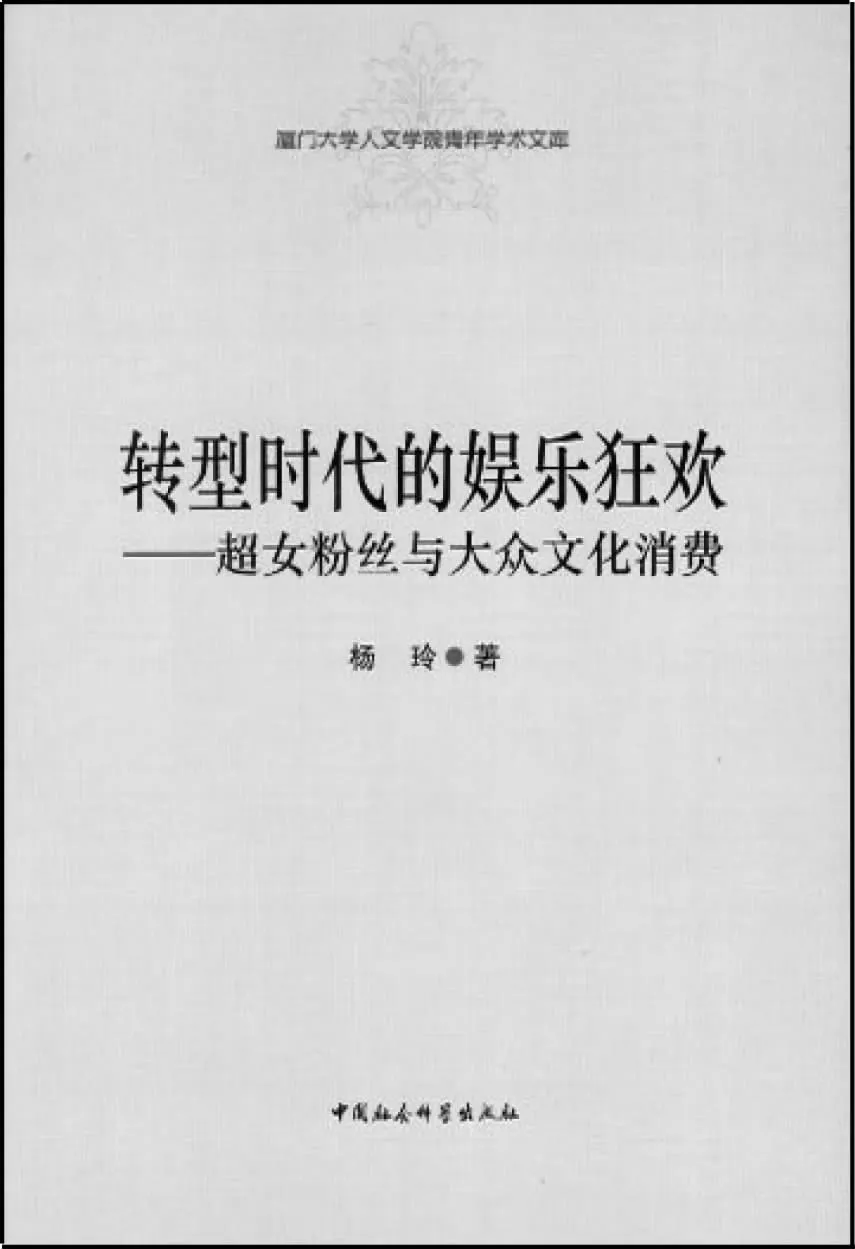
2015年,網絡文學研究者邵燕君在《網絡文學的“網絡性”與“經典性”》一文中提出,網絡文學的“文學性”要從其“網絡性”中重新生長出來,而網絡文學的“網絡性”是“根植于消費社會‘粉絲經濟’的”:
粉絲既是“過度的消費者”,又是積極意義的生產者。他們不僅是作者的衣食父母,也是智囊團和親友團,和作者形成一個“情感共同體”……這不但是一種文學生產模式,也是一種文學生活模式。[2]
毋庸諱言,我也與上述學者持有相似的立場。關于網絡文學領域作者與粉絲社群的關系,我曾做出過更激進的表述,強調網絡文學作者與粉絲之間的共創關系:
讀者從單純的閱讀者變成了“粉絲”,進而成為與作者平等共創的生產者。可以說,讀者身份的演變,是網絡文學區別于傳統紙質文學的最突出特征之一,也是網絡文學的生命力所在。[3]
在這一階段,研究者所強調的粉絲文化中的優秀特質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參與式文化與新型文藝生產、“有愛”的共同體、自由共享的互聯網精神。
這些特質的存在本身是毋庸置疑的。實際上,21世紀以來中國互聯網中勃興的林林總總的網絡青年亞文化社群,大多發源于粉絲文化(比如說,網絡文學與同人文化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網絡古風音樂脫胎于網絡翻唱,等等),并在從同人創作走向原創之后,仍舊保持著粉絲文化社群的基本信念與基本結構:因愛而相聚,因愛而創造,因愛而分享;圈地自萌、劃壁而治,通過創造對外區隔,強化自身共同體歸屬感。隨著網絡文學主流化、“國產動畫崛起”“二次元破壁”,這些孕育出成熟原創能力的粉絲趣緣社群已經充分證明了它們的想象力和文藝生產能力;與此同時,以粉絲趣緣社群為單位的人類社會“再部落化”的美好愿景似乎正在實現。
但到了2015年前后,隨著商業資本大規模進入網絡亞文化領域,隨著網絡亞文化越來越頻繁地進入主流文化視野,隨著偶像工業帶來龐大的偶像粉絲群體,粉絲文化再一次成為輿論的眾矢之的,“著魔的個體和歇斯底里的群眾”似乎再次歸來。
每一種網絡亞文化面對商業化與主流化的趨勢,都必須做出自己的抉擇。2015年,我曾在《古風:關于商業化的博弈》[4]一文中詳細討論了古風音樂圈,以及作為對照的中文廣播劇圈面對商業化的態度與抉擇。誕生于2004年的古風音樂圈于2008年開始了商業化的進程。
2008年2月23日,古風圈的著名音樂團隊“墨明棋妙”發行了《墨明棋妙一周年歌詞集》,開啟了一條具有古風圈特色的商業化道路。在這一階段,可以出售歌曲周邊,但音樂作品本身必須免費分享,一度成為古風圈商業化的底線。2009年,隨著古風圈歌手河圖古風專輯《風起天闌》的發售,這一底線隨之發生了變化。全部歌曲免費傳播與專輯有償銷售并行,成為古風圈商業化趨向和反商業化傾向之間長期博弈的最終結果。這樣一場充滿著各式各樣的丑聞和罵戰的激烈商業化論爭也終于在2015年落下帷幕。與古風圈明顯相反的是,中文廣播劇圈選擇了徹底拒絕商業化的道路,由此產生了完全免費的“網配”(網絡配音中文廣播劇)與完全商業化的“商配”(商業配音中文廣播劇)之間的分裂。
從今天的視角回看這一段紛繁復雜的網絡亞文化社群商業化進程,其最深遠的影響,或許是將“版權”這個詞帶入了所有互聯網的青年亞文化群體之中。版權爭端本該是商業化引發的連帶問題:由于大多數互聯網青年亞文化都脫胎于粉絲文化,所以早期文藝作品往往帶有明顯的同人創作特征,在營利過程中自然會出現版權糾紛。但實際情況是,無論是支持商業化的人還是反對商業化的人,都將尊重知識產權、要求授權明晰視作金科玉律。為了保護知識產權而反對商業化的人,與為了維護商業利益而反對抄襲的人奇妙地成了同仇敵愾的戰友,完全無視了版權神圣化的過程本身,恰恰證明了在粉絲文化的領域中,商業邏輯徹底驅逐了自由分享的互聯網精神。
免費與付費、同人與原創,圍繞版權產生的爭端在諸網絡亞文化社群中相繼爆發。以網絡文學粉絲社群為例,實際上在網文讀者中,閱讀盜文(盜版小說)的不付費讀者數量始終遠高于付費讀者數量,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2010年前后百度貼吧興盛時期,貼吧中存在大量被免費分享的網絡文學資源,只要不與正版更新同步發出,基本上都會被認為是合理的,發布精校手打版的吧友甚至還會得到其他吧友的感謝。當時,“盜文”一詞雖然存在,但其含義與今天并不相同,基本指向轉載不注明出處,或經作者許可,與付費正版同天發布等情況。閱讀免費版本的讀者毫無疑問也是網絡文學粉絲社群中的成員,他們同樣參與著網絡文學的評論、催更、評分等活動,付費讀者和盜文讀者之間并不存在明確的等級關系。但隨著版權概念的普及,特別從2016年百度貼吧開始大規模清理免費資源、整肅盜版后,對盜文讀者的聲討成為此后網絡文學粉絲社群的持續議題,盜文讀者漸漸不再持有對網文作品進行評論、打分的權力,起點中文網作者貔蚯的說法代表了一種普遍的觀點:“對于盜版讀者,態度大概就是‘你就算夸我,我都覺得惡心’。”[5]
標志著圍繞知識產權的道德爭論塵埃落定的,或許是2013年前后,“白嫖”這個帶有極強貶義色彩的詞,理所當然地在幾乎所有互聯網亞文化社群廣泛使用。“白嫖”本意指嫖娼不給錢,在2008年前后被偶像粉絲圈用來指“宣稱喜歡某位愛豆或某個愛豆團體,但只觀看免費或盜版資源,不為該愛豆/愛豆團體花錢的行為”[6],隨后開始代指所有使用免費(或付費)盜版資源,不為正版資源(或官方周邊產品)付費(或做數據)的行為。看盜文是白嫖,追星不花錢投票是白嫖,使用破解軟件也是白嫖。“白嫖”一詞以其強大的概括力跨越圈層,因而“反白嫖”不再是某一社群的局部圈規,而成為互聯網空間中的共識與主流。楊玲在《轉型時代的娛樂狂歡》中曾提到,粉絲強烈的情感投入能夠在粉絲社群中“引起普遍共鳴,并且成了判斷粉絲身份真偽的標準之一”[1]44。如今,情感的真摯與否已經不再是判斷粉絲真偽的標準,至少不是首要標準,“白嫖不是粉”成了粉絲文化社群的第一準則。
秦蘭珺在《論青年亞文化與互聯網生產方式的互動》一文中提到,黑客文化中作為技術需要的合作開發、作為倫理立場的自由分享精神和作為生產機制的開源模式,隨著Web2.0商業模式的普及進入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中國網絡空間。[7]這也形構了當時具有較強精英傾向的早期網民對互聯網烏托邦的基本想象,自由分享的互聯網精神因此成為早期中國互聯網中的普遍倫理。換言之,自由共享的互聯網精神勢必深刻地滲透進建基于互聯網空間之中的粉絲社群的結構與理念,而正如黑客文化中的合作開發必然需要開源模式的支持,粉絲社群中的參與式文化,也以資源共享、知識共享為前提進入了野蠻生長期。直到Web2.0模式本身的擴大再生產能力趨于飽和,將用戶變為數字勞工的“流量變現”模式開始被放在臺面上討論,為了以最高的效率吸納下沉市場的用戶群體,網絡平臺的用戶們不再被期待生產內容,而是被期待生產流量。以知識產權之名,內容生產的權力正在被重新壟斷,“飯圈化”的時代到來了。
二、從“粉絲”到“飯圈”:抵抗—收編模式歸來
到了2020年,當研究者再次試圖表述粉絲文化中的積極面向時,往往不得不使用更加審慎的表述,或者更直白來說,就是將偶像粉絲文化從抽象的粉絲文化概念中分割出來單獨考察。“飯圈”代替“粉絲圈”,成為對于偶像粉絲社群的代稱,圍繞這一群體產生的種種事件和爭議,似乎正在摧毀曾經被寄托在粉絲文化身上的一切厚望。
“粉絲”與“飯”,都是對英文單詞“fan(fans)”的音譯,這種音譯選擇上的變化,明顯受到了日韓偶像工業的影響。與用詞的變化方向相一致,今日中國的偶像經濟與偶像粉絲文化,也更多是仿照日韓偶像工業建立起來的,而日韓偶像工業批量生產的產品就是“愛豆”。
“愛豆”的詞源是英文詞idol,后經日韓傳入我國國內,音譯為“愛豆”。在日本和韓國,愛豆是區別于歌手和演員的一種特殊的演藝類職業,與演員、歌手有著不同的職業分工和職業素養要求。“人設”與“養成”是日韓偶像工業的兩大核心概念,也是愛豆區別于演員、歌手等傳統意義上的明星的顯著特征。
“人設”是“人物設定”的縮寫,這個概念最早出現于日本動漫領域。人設本身并不是靜態的人物描述,而是規定了角色面對不同情境、事件時將會做出何種反應的指令合集,因而人設最終將在故事之中顯現自身、完成自身,或者簡單來說,一個人設就是一套敘事。人設與愛豆的結合,是愛豆區別于此前的明星偶像的重要特征,愛豆的本職工作與其說是唱歌、跳舞、演戲,不如說是扮演好他的人設。
每個愛豆都在扮演自己的人設,這個人設可能與其作為一個自然人的本來性格有相似之處,也可能大相徑庭。對于一個理想愛豆而言,他唱的歌、跳的舞、出演的影視作品,在鏡頭前的每一次發言,他被媒體捕獲到的所有行為舉止都應該符合他的人設。對于愛豆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擁有人設,而是人設本身開始具有自反性。[8]
愛豆擁有人設這件事成了“公開的秘密”,愛豆可以在鏡頭前公開談論自己的人設,不少粉絲知道愛豆擁有人設,甚至還有一些會意識到自己喜愛的就是那個人設,而非作為自然人的愛豆本身。
對于“人設”的自覺意識,或許在CP粉[9]和RPF[10]粉那里體現得最為清晰:
翡翠,在不是玻璃的前提下,越像玻璃越值錢;rps,在不是真的前提下,越像真的越好嗑[11]。[12]
RPF不是真的,而是故事,那么相應地,圍繞這一段CP關系而存在的愛豆人設自然也是虛構的。粉絲一邊高喊“我的CP是真的”,一邊清醒地知道CP恰恰因為不是真的才可以嗑得毫無負擔。對待愛豆也是同理,只有故事才能美得像個童話,只有人設才能美玉無瑕。
愛豆的本質是扮演一套人設/敘事,這一事實提醒我們反過來重新關注“成為粉絲”這件事的敘事性特征。成為一個人的粉絲,與成為一部作品的粉絲之所以可以被等同視之,就是因為明星作為粉絲社群的中心物,是被當作一個故事來消費的。劉明洋在《“粉圈化”:權利販售的游戲規則——從“全職圈”麥當勞代言事件說起》一文中提到的網絡文學作品《全職高手》中主人公葉修的粉絲為葉修這一角色爭取麥當勞代言的抗議行動[13],生動地說明了愛豆粉絲社群的整套行為模式并不一定要應用于一個真人愛豆的身上,任何有資格成為故事主人公的人、虛擬角色,抑或非人的國家、動物、物品,都可以成為(類)偶像粉絲社群的“中心物”。這是非偶像粉絲文化社群的網絡亞文化社群能夠普遍“飯圈化”,復制飯圈行為模式和思維邏輯的重要基礎。
敘事性并非愛豆粉絲的獨有特征,而是粉絲文化的必然屬性,或者說是人類敘事天性的本能操演。只不過,由于愛豆是最晚近的一種偶像類型,它過度成熟以至于開始走向媒介自反,它將造星工業與粉絲文化的敘事屬性暴露出來,反而使得粉絲與運營方、粉絲與粉絲之間爭奪愛豆人設/敘事決定權的戰爭變得公開化了。只不過,即使是“過度的消費者”,歸根結底也還是消費者,在知識產權神圣不可侵犯的消費社會之中,粉絲的抵抗在開始之前就已經被標定了限度。
“愛豆養成”的神話,則更直接地服務于偶像工業的營銷模式,其基本預設是:粉絲花錢投票,將決定愛豆的未來,愛豆從出道之前的稚嫩新人練習生,到出道后的成熟優質偶像,每一點成就都是在粉絲的陪伴和幫助下達成的,粉絲被許諾成為愛豆的供養人。以韓國愛豆團體EXO的四位華人成員相繼歸國及國產養成系男子偶像團體TFboys的出現為標志,中國也開始仿照日韓建立自己的偶像工業,而以2018年的《偶像練習生》為代表的“101系”選秀[14],就是中國偶像工業的典型產物。“愛豆養成”的粉絲賦權神話也被復制到中國,極大調動了粉絲的積極性,打榜[15]、應援、控評、刷銷量,努力彰顯自己的存在感和消費力,并把這些當作籌碼站上運營方設置的談判桌,為自己心儀的愛豆爭取更多的出鏡機會(也即更多的敘事素材),同時爭奪對愛豆人設/敘事的主導權。
為何“愛豆人設化”疊加“愛豆養成”,能夠帶來如此強大的吸引力,并將這種吸引力高效轉化為粉絲的行動力與消費力,以至于“飯圈”文化前所未有地成了一種全民議題?如果說“人設”概念的流行使得偶像明星作為粉絲社群“中心物”的敘事性特征顯在化,那么“愛豆養成”就使得這種敘事動能最大化,從平凡青澀的少年,到閃閃發光的愛豆,從低谷到巔峰,陪伴愛豆成長的道路上濃縮了關于傳奇人生、關于成長與成功的一切最美好的故事,粉絲還能夠以花錢投票的方式,成為這些故事的親身參與者。而故事作為一種虛構物,并不受現實時間的約束,無論是對一個參加選秀的練習生傾注一個夏天的愛,還是在一個愛豆的人氣巔峰才遲遲“入坑”[16],都不影響這個宏大、曲折、是非分明而又閃閃發亮的故事本身的完整性。
經由前文對于中國粉絲文化發展階段的極簡梳理,可以得出結論: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中國網絡空間及其中各個亞文化社群的整體性的“飯圈化”進程,實際上包含兩個方面——以知識產權絕對正義性之確立為核心的互聯網大資本其控制之下的亞文化圈層的商業化進程在文化上的表現;以愛豆為代表的粉絲文化“中心物”之敘事性特征的自我暴露,以及整個網絡空間受此啟發涌起的將一切信息“故事化”的狂熱風尚。
我在《“故事社會”與后現代的散布——從網絡文藝的新敘事形態說起》一文中曾以“故事社會”一詞,描述“飯圈化”之后的互聯網空間,也即一種應對于宏大敘事崩潰的后現代困境的應激性生存形態:
無論是進步信念消退帶來的迷茫感,還是個體境遇落差帶來的失落感,都不是人類生活的常態,可以說,人類是無法長期生活在這種狀態中的。既然重新被宏大敘事完美包裹在短期內已不可能,那么價值共識與社會共識的代替品就不可或缺。[8]
不斷創造局部小故事,或者不斷將同一個故事結構套用在不同的對象上,都能有效設定出臨時錨點,暫時錨定某種價值或信念,強化它、鞏固它,甚至將它放大為絕對真理。人設只是無數種錨點命名裝置中較為高效的一種,它毫無遮掩地預先展示了自己的虛構屬性,反而可以無所顧忌、隨心所欲,把每一個故事講到極致。于是,清華和北大有了人設,大熊貓有了人設,國家和省市都有了人設,萬事萬物無往而不能人設化,人們在故事里分成敵我雙方,在故事里論證是非黑白。
三、“泡沫塑料制成的濕婆神像”:粉絲文化的“中心物”
以“飯圈化”為界,重審粉絲文化及粉絲文化研究的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詹金斯的“參與式文化”與“文本盜獵”成為解釋粉絲文化積極面向的有力理論資源,那種完全將粉絲視為“著魔的個體和歇斯底里的群眾”的觀念被隱隱撬動。但到了“飯圈化”愈演愈烈的2020年以后,粉絲似乎“自甘墮落”地再度成為“著魔的個體和歇斯底里的群眾”。將明星視為特殊的卡里斯瑪型領袖的解釋方法再度得到廣泛的接受,似乎粉絲與偶像之間的關系就如同領袖與門徒,偶像的感召力帶來粉絲無窮的非理性忠誠。
粉絲在這樣的兩個階段中好像分別具有“盜獵者”與“虔信者”兩副面孔,但事實遠非如此簡單。如果仔細甄別,實際上詹金斯對“盜獵”這一概念的描述更接近于“飯圈化”之后的粉絲文化狀態,或者更具體來說,接近于粉絲與運營方爭奪愛豆人設/敘事權的對抗狀態:
德塞杜的術語“盜獵”迫使我們意識到制作方和消費者、作者和讀者之間潛在的利益沖突……粉絲必須積極同他們所借用的原材料中強加給他們的意義做斗爭,他們只能在極為不平等的地勢上遭遇對手。[17]
媒體粉絲圈的歷史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聯合起來試圖影響制作方對節目的決定的斗爭史。[17]26
而在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的那十余年中,由于粉絲文化實際上常常以歐、美、日、韓等國流行文化為其“中心物”,大多數時候并不與主流文化、商業資本直接碰撞,所以恰恰缺乏這種“盜獵”的緊張感。詹金斯《文本盜獵者》一書的副標題是“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而電視媒介作為一種毫無疑問的主流媒介、大眾媒介,本身就宣示了其粉絲群體與主流文化間的對抗和互動關系。這種對抗關系的存在,意味著粉絲與粉絲文化“中心物”之間絕不是簡單的熱愛、效忠關系,甚至恰恰相反:

粉絲明白自己與文本的關系很薄弱,他們的樂趣往往只能處于原文的邊緣地帶,且與媒體制作方約束規范文本意義的努力處于正相對的位置。[17]23
媒體粉絲文化,就像其他流行閱讀行為一樣,并不該理解成對某部電視劇或文類的排他性愛好,相反的是,媒體粉絲十分樂于在大范圍內的媒體文本之間建立聯系。[17]35
在借用詹金斯的“文本盜獵者”理論進行的中國粉絲文化粉絲中,粉絲與“中心物”之間關系的薄弱性以及“中心物”的可替換性總是或顯或隱地被忽略了。研究者們更感興趣的是粉絲文化中無功利的熱愛,以及這種熱愛帶來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大爆發。而正如前文所說,中國互聯網粉絲文化中自由分享的無功利性,或許并不來自粉絲文化的固有品質,而來自Web2.0產業模式中的黑客文化精神遺產。因此,等到“飯圈化”的進程開啟,當“無功利的熱愛”中的“無功利性”被商業邏輯所取代,產生的后果是人們始料未及的。
那么2020年以來偶像粉絲文化中的“熱愛”就真的是一種絕對的忠誠、是著魔一般的歇斯底里嗎?作為偶像粉絲文化“中心物”的愛豆們,是否和他們的粉絲建立了深厚的、穩固的、絕對的單向關系呢?
顯然不是。
在以《偶像練習生》為代表的國產“101系”選秀中,一撥一撥的愛豆被批量生產出來,無論是哪一檔選秀節目,最終都能帶動巨大的經濟效益,選秀粉絲或者簡稱“秀粉”,因而成為今天中國互聯網飯圈中最有存在感、最具行動力和消費力的群體之一。但與此同時,在“秀粉”中還有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叫作“全網秀粉三千”,其含義為,實際上中國互聯網空間中追“101系”選秀的粉絲數量是有限的,而且人員是相對固定的,同一批粉絲追完了《偶像練習生》,追《青春有你》,如此往復,每次開始追看一檔新的選秀綜藝,自然就會中意于新的選手,于是開始新一輪的集資和打榜,節目層出不窮,愛豆常換常新,而粉絲永遠都在。如果只是這樣,我們還可以解釋說,粉絲的愛來得快、去得也快,至少在為某一個愛豆打榜、集資的那一段時間,她對這位愛豆的愛是絕對的、無條件的、非理性的,在這一段時間內,那個愛豆是一個不可替換的“中心物”。但“101系”選秀不僅可以用來追星,還能用來“炒股”。當然,這里所說的“炒股”,不是真金白銀的股票交易,而是在一檔選秀綜藝開播之前通過選秀的宣傳照或者極其簡短的宣傳視頻來決定自己要在節目中應援哪位選手,于是,在節目開播之前,選手超話乃至后援會都已經成立。
在這樣的追選秀綜藝的流程之中,相比于作為“中心物”的愛豆,顯而易見,粉絲行動和粉絲組織是處于絕對的優先地位的。不是因為對一個愛豆一見傾心,才加入粉絲后援會,為他打榜,而是因為一整套選秀綜藝的應援模式已經成為“秀粉”們娛樂生活的組成部分,所以才需要愛豆去充當那個“中心物”。愛豆是可替換的,但粉絲社群生活和粉絲日常活動不是。
“粉絲文化”,這個構詞天然地包含著“粉絲”與“中心物”兩者之間的關系,于是所有關于粉絲文化的理論,都理所當然地為“中心物”預留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即使在詹金斯的“文本盜獵”理論中,作為“中心物”的文本也不是不存在,只不過其與粉絲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但或許正如后結構主義的普遍信念那樣,在結構之中,中心作為一種功能而存在,其實指總是缺席的。冒領了粉絲文化中心這一位置的“中心物”,并不真的具有中心性。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各式各樣的網絡亞文化社群如雨后春筍般生長起來,這些亞文化社群中的文化產品逐漸從粉絲同人文化形態轉向原創形態,社群文化“中心物”也隨之轉變為社群內部的原創者和原創作品,但社群本身的粉絲文化結構并沒有發生改變;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轟轟烈烈的“飯圈化”進程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粉絲文化社群的風貌和生態,但批量生產的年輕愛豆,從一開始就被設計為可替換的標準化“中心物”。流水的愛豆鐵打的飯圈,粉絲在愛豆身上尋求的,難道真的是獨一無二的夢想與熱愛嗎?
即使不討論粉絲文化的問題,日本文化研究者宇野常寬在《00年代的想象力》一書中也給出了一個用在粉絲文化“中心物”上非常貼切的比喻:
……對于日常而言,“外部”究竟是否存在呢——說到底,后現代狀況不就是身處一切都可以被替換,無論做出怎樣的選擇都不會發生改變的世界之中嗎?在這樣的世界中,每個人都只能依賴于自身所屬的小共同體中通用的小敘事和與之相連的超越性。但這種地域化的神明,對于其他共同體(小敘事)中的人而言不過是如同泡沫塑料制成的濕婆神像一樣的東西罷了。[18]
“泡沫塑料制成的濕婆神像”,這就是對粉絲文化“中心物”的最恰切描述,“中心物”不是神明,而不過是使用廉價材料制作的并不稀缺的堅固的神像而已。甚至“人設”的概念進一步拆除了“神像”與“神”之間的關系,無所謂“地域化的神明”,一切神像/故事都在人間制作完成。
那么,既然粉絲在粉絲社群中尋求的并不是(至少首先不是)對某一個具體的“中心物”的愛(無論是無功利的熱愛,還是非理性的迷戀),他們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說,粉絲社群的本性與存在意義是什么呢?
回顧前文所提及的兩個階段的粉絲文化研究,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研究者們強調的粉絲文化的積極品質是:參與式文化與新型文藝生產、“有愛”的共同體、自由共享的互聯網精神。正如前文已經反復說明的,自由共享的互聯網精神不是中國網絡粉絲文化的固有品質,而是當時的中國互聯網空間的普遍倫理。參與式文化是“有愛”的共同體的運轉邏輯,新型文藝生產則是參與式文化的文藝產品。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飯圈”亂象中最受人詬病的是粉絲對于偶像的瘋狂迷戀,以及粉絲社群強大到令人不安的組織力和動員力。由于作為“中心物”的偶像不過是可以替換的“泡沫塑料制成的濕婆神像”,所以瘋狂迷戀的表象之下,實際上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粉絲社群強大的組織力和動員力。對照來看這兩個階段,粉絲社群的共同體操演始終是粉絲文化的核心問題。
楊玲曾經對超女粉絲的共同體做出這樣的描述:
超女粉絲群比較類似一個賢能體制,粉絲可以依靠自己的學識、才華以及對自身網絡形象的有效駕馭脫穎而出,成為所謂的“名ID”(有名的網絡ID)。[1]48
這樣的賢能體制在今天的粉絲社群中仍舊發揮著作用,擁有寫文、剪輯視頻、拍照修圖等技能的粉絲會在粉絲社群中被稱為“大大”或者“太太”,將自身文化資本成功兌換為圈內地位。只不過,在今天的飯圈文化中,更受矚目的已經不是這一套賢能體制,而是由官方后援會、數據組、(職業)大粉/粉頭層層控制的等級明確的類集權體制。粉絲社群曾經趨向于實現一種近似于古希臘城邦民主政治的共同體操演,憑借去中心化的、任人唯賢的、以興趣為紐帶的、友善的小型網絡社群,對抗原子化的現代性孤獨,而研究者們則在這樣的共同體之中,看到了民主參與模式的小規模演練,看到了在高度去政治化的一代人身上重構政治參與能力的可能性。隨著互聯網大資本的強有力滲透,隨著互聯網用戶市場下沉,隨著逆全球化的到來與國際局勢的變化,隨著國人對西方代議制民主政治的普遍幻滅,粉絲社群的組織形式也發生了迭代,一種更加激進的權力集中的層級化的,更強調忠誠、服從和戰斗性的,因而也更容易帶來凝聚力和參與感的共同體模式開始占據主導。相比于自由零散而又精英化的文藝生產,限時集資與集中控評的數據游戲確實更簡單、更高效,也更像是一場讓人熱血澎湃的戰爭。在這樣的轉換中,粉絲社群的成員變了,“中心物”變了,行事風格變了,對理想共同體的愿景也改變了,但粉絲社群的基本功能并沒有改變:“泡沫塑料制成的濕婆神像”暫代神職,將人們迅速聯系在一起,因而他們可以假設彼此間天然具有共同話題,至少在某一方面心有靈犀,他們完成集團性儀式,說著一樣的圈內“黑話”,創造共同的記憶與歷史,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共同講述一個關于共同體的故事,排演并重溫那種我與一群人無條件地站在一起的激情時刻——無論這個共同體是民族國家的微縮翻版、城邦政治的限時復刻,還是集權帝國的黃粱一夢。
對于一部作品、一個明星、一種文化現象的愛從來不足以成為人們參與或創造一個同好共同體的原因,實際的情況是:正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高效便捷低成本的局部社群來代償公共社會參與中的迷茫與無力,“泡沫塑料制成的濕婆神像”才有了用武之地。
注釋
[1]楊玲.轉型時代的娛樂狂歡——超女粉絲與大眾文化消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63.
[2]邵燕君.網絡文學的“網絡性”與“經典性”[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143-152.邵燕君文中提到網絡文學的“網絡性”包含三個方面,粉絲經濟是其中一個方面,另外兩個方面分別為“超文本”和與ACG文化的連通性。這兩個方面與本文關系不大,故不贅述。
[3]王玉玊.從讀者到“粉絲”,從受眾到作者——網絡文學中讀者角色的轉換[N].中華讀書報,2015-7-15(11).
[4]王玉玊,肖映萱等.古風:關于商業化的博弈[OL].“媒后臺”微信公眾號,2015-5-19/2021-8-26.
[5]引自貔蚯在知乎對“對于小說創作者和讀者來說,創作者是否特別厭惡看盜文小說的讀者?”這一問題的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0931711,2019-02-01。
[6]邵燕君.破壁書:網絡文化關鍵詞[M].“白嫖”詞條,該詞條編撰者為王玉玊,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133.
[7]秦蘭珺.論青年亞文化與互聯網生產方式的互動[J].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4):73-85.
[8]王玉玊.“故事社會”與后現代的散布——從網絡文藝的新敘事形態說起[J].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1):70-80.
[9]CP(Coupling,人物配對)粉一般指特別喜歡某一對真人偶像CP的粉絲,這些真人偶像CP往往不是真正的情侶,但粉絲會想象他們之間的親密關系。
[10]RPF(Real-Person Fiction),即真人同人,是以真實存在的人為主人公進行的同人寫作。為偶像明星寫作RPF,特別是以真人偶像明星CP雙方為主人公寫RPF是非常常見的粉絲行為。RPS(Real-Person Slash)是RPF的一種,其主要特征之一是以真人偶像CP的親密關系為主要表現內容。
[11]嗑,指CP愛好者們或RPF愛好者們如同“嗑藥”一般在CP的親密關系想象或RPF作品中獲得巨大的滿足和快感,是一種夸張和戲謔的說法。
[12]引文來自眾生之門菜雞表演藝術家宋引于2021年8月8日發布的微博。
[13]參見劉明洋.“粉圈化”:權利販售的游戲規則——從“全職圈”麥當勞代言事件說起[J].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3):140-148.
[14]“101系”選秀,即仿照韓國綜藝節目《PRODUCE 101》制作的一系列選秀節目。《PRODUCE 101》是一個女團出道選拔綜藝,101名來自不同經紀公司的女練習生進行唱跳舞臺比賽,最終成績由國民制作人(節目受眾)投票產生,最優秀的前11名練習生會組成一個愛豆團體,發行單曲,并進行為期一年的團體活動。
[15]打榜,即通過投票等方式使愛豆本人或相關作品、產品位于榜單前列。
[16]入坑,粉絲文化社群常用語,指因對某部作品或偶像明星的喜愛而加入對應的粉絲社群。
[17][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M].鄭熙青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31.
[18]宇野常寬.ゼロ年代の想像力[M].東京:早川書房,2011:74.譯文為筆者翻譯。引文中的“小敘事”指宏大敘事衰落后局部增生的小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