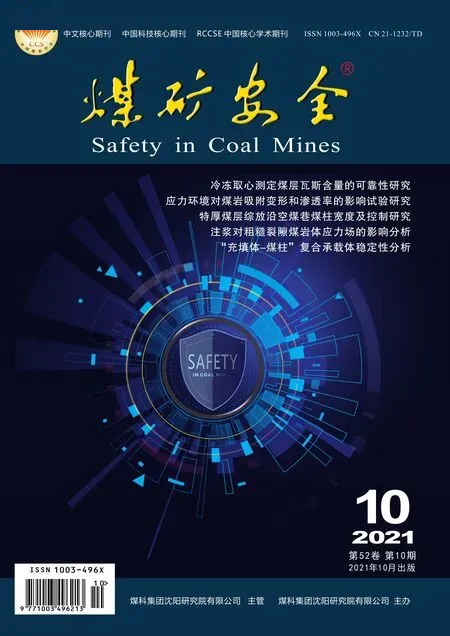雙孔膨脹致裂堅硬巖體裂隙擴展演化試驗研究
李團結,牟文輝,易瑞強,肖 曲,華 軍
(陜西陜煤黃陵礦業公司,陜西 黃陵 727307)
巖體作為礦井生產的基礎單元,隨煤炭資源回采呈現不同的演化特征[1]。隨著煤層開采尺寸和范圍的加大與堅硬巖體的共同影響,易造成懸而不垮。一旦垮落,垮落面積大并釋放巨大能量。為了保證“隨垮隨落”,不僅要考慮巖體的強度指標,而且結合堅硬巖體致裂的裂隙擴展方向,進一步保障安全開采。
礦井常用爆破致裂、水力壓裂等技術進行致裂堅硬巖體[2-5],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逐漸引入CO2預裂、膨脹致裂技術[6-10]。其中膨脹致裂以“無振動、無飛石、無噪音、無污染”的特點,更多的應用于地下空間工程領域[11-14]。近年來,眾多學者對膨脹性能及其工程應用進行了豐富的研究。謝益盛等[15]分析影響膨脹壓力的“三大”因素,得出膨脹劑的最佳水灰比和水化反應的“四個”階段;唐烈先等[16-17]在膨脹劑對混凝土的數值模擬中,提出了雙孔加壓下的合理孔間距;來興平等[18]利用膨脹劑對煤巖體試件進行弱化致裂試驗,發現試件破碎軟化過程中會產生明顯的膨脹壓力,同時對試件內部裂隙擴張具有促進作用。針對巖體物理力學特征,通過單軸循環加、卸載過程中的巖體演化力學特征和巖體損傷特征,逐步向三軸加載下的巖體實驗研究轉變,探索巖體受力下的應力傳播路徑、巖體微裂紋的擴展條件和斷裂準則等,更好地反映工程擾動下的巖體演化的真實性[19-21]。Peng K 等通過分析巖石的儲能系數和能量耗散系數與巖石中裂紋角的關系,揭示混合壓力對砂巖變形特征的影響,發現巖石中裂紋角越大,巖石的儲能系數越大,能量耗散系數越小[22]。
上述學者針對巖體這一層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但通過“聲-波”檢測手段對模擬現場巖體膨脹致裂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為此,以某礦21209 工作面懸頂為背景,以深部堅硬頂板巖體膨脹致裂為切入點,通過地質普查、膨脹劑確定、實驗室試驗等方法,憑借聲發射(AE)、微震實時動態監測巖體裂隙演化發展規律及破壞特征,為靜態膨脹致裂切頂提供實驗依據。
1 工程背景
1.1 礦井概況及生產條件
陜西中部地區隸屬于陜西煤業化工集團公司的某礦位于黃隴煤炭基地,核定生產能力8 Mt/a。礦井主要開采2#煤層是近水平煤層(傾角約1°~5°),屬于侏羅系中統延安組,為穩定~較穩定煤層。礦井主要開采二盤區,其中主采的21209 工作面采深在395~699 m 之間,西南緊鄰207 采空區,東北部緊鄰211工作面,東南至北一1#輔運大巷,其余為未采煤層。工作面地表標高+1 175~+1 424 m,井下標高+723~ +784 m;地面為中-低山林,周圍無建筑物和其他設施。工作面分布及覆巖特征如圖1。2#煤層上部普遍有1層12~25 m 的粉砂巖,其天然狀態抗壓強度普遍在58.35~76.7 MPa 之間,抗剪強度一般在4.22~6.4 MPa。

圖1 工作面分布及覆巖特征Fig.1 Distribution of working face and overburden characteristics
21209 工作面圍巖特性見表1。工作面設計走向長度約4 238 m,傾向長度約300 m,平均煤厚3.5 m,平均日推進12 個循環,每循環約0.85 m。采煤法選用走向長壁后退式一次采全高;采空區頂板進行全部垮落法處理。進、回風巷道尺寸(寬×高)分別為4.6 m×3.8 m、5.4 m×3.6 m,巷道頂部錨桿錨索聯合支護方式支護,錨桿、錨索預應力分別不小于150、260 kN。
1.2 隅角頂板致裂現狀
通過21209 工作面頂板巖石力學實驗測得,單軸抗壓強度為68.8 MPa,抗拉強度為3.99 MPa,黏聚力C 為20.74 MPa,內摩擦角φ 為35.56°,彈性模量E 為6.68 GPa。受工作面更替、巷道支護及頂板自身的共同影響下,導致工作面端頭頂板懸長在15~20 m 之間,不易垮落。突然垮落易把采空區內的有毒有害氣體突然涌入工作面,極大威脅了礦井的安全生產。
為了解決此項問題,工作面采用膨脹致裂技術。在工作面前方50 m 的2 條巷道進行切頂,根據工作面兩巷寬度,分別設計10、12 個切頂鉆孔。以運輸巷設計切頂孔為例,孔徑60 mm、鉆孔間距為0.4 m、孔長為6 m,并向采空區方向傾斜10°左右;為了保證致裂效果,采用封孔器進行封孔。
2 致裂材料性能
2.1 致裂材料參數
為了得到選用致裂材料的配比參數,將4 種不同配比下的膨脹劑放入統一規格量筒內,并干燥攪拌均直至無塊狀顆粒。為保證膨脹試驗的可靠性,將4 個燒杯放入統一環境中;所需純凈水提前24 h放置試驗室內,保證初始水溫與室溫一致。4 種膨脹劑配比下的膨脹特征見表2。

表2 不同膨脹劑配比的膨脹特征Table 2 Expans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expansion agent ratios
初始狀態下,1∶1~1∶3 水灰比的漿液具有較好的流動性,1∶4 的流動性明顯不足且攪拌過程中阻力較大。靜置約10 min 后,漿液出現分層現象;持續靜置后,沉淀物表面逐漸干涸并開始凝固。水平膨脹呈現的龜裂變化,隨水灰比的增加而加劇。1∶1 的漿液表面干涸并凝固后不再有任何變化;1∶2 的漿液中間隆起,龜裂明顯;1∶3 時的漿液龜裂平緩且塊狀增大;1∶4 的漿液過于濃稠,燒杯脹裂無法觀測其膨脹后的體積形態。縱向膨脹特中膨脹體積發生明顯變化。其中1∶3 的漿液體積膨脹率最大,增大了約290%,體積膨脹了將近3 倍;1:4 時體積膨脹率達到了250%。因此,最佳水灰比選擇1∶3。
2.2 靜態破碎劑特性
選用致裂劑的膨脹力是決定致裂技術的一項重要性能指標,現通過自主研發的膨脹力測試儀對其膨脹性能進行測試。將致裂劑按照水灰質量比1∶3攪拌均勻后倒入膨脹力測試儀中。受膨脹效應影響,裝藥量約為測試容積的3/5。共進行3 次測試,3次的徑向應力結果均大于軸向應力,雙向應力測試結果如圖2。

圖2 雙向應力測試結果Fig.2 Two-way stress test results
膨脹致裂劑的水化反應過程中分為3 個階段:①0~70 min 內,無明顯反應特征;②70~100 min 內,徑向和軸向應力迅速增加到最大,反應到最大值約需要20 min;③100 min 后,雙向應力基本穩定。加速期內,徑向應力和軸向應力發生到最大值所需要的時間基本相同。結合致裂材料水化反應現象,初期的致裂劑由流動性的膏體狀態逐漸轉變成具有一定彈性模量的固體,硬化固體與孔壁膠結約束了膨脹致裂劑軸向的應變,從而使軸向應力小于徑向應力,徑向應力反應的更為劇烈。
水灰質量比1∶3 的3 次測試致裂劑膨脹產生的平均徑向、軸向應力為30.47、19.8 MPa,遠大于巖石的抗拉強度。
3 致裂堅硬巖體的“聲-波”特征
3.1 物理模擬試驗搭建
根據現場頂板巖體力學特性、致裂參數的基礎,設計尺寸為1.2 m×1.2 m×1.3 m 的混凝土模型,實現水灰比1:3 的膨脹材料致裂下的效果。巖塊中間布置2 個間距為40 cm 的鉆孔,孔徑為40 mm、孔長120 cm。膨脹致裂堅硬巖體下的“聲-波”的檢測方案如圖3。巖塊四周分別布置微震10 個,四周探測點距頂、幫10 cm,正面的Ⅱ、Ⅴ探測點分別距兩幫和頂部60、10 cm。聲發射探測共布置4 個探測點,分別布置在前后左右4 個面的中部。

圖3 “聲-波”的檢測方案Fig.3 Detection scheme of“acoustic-wave”
根據所測得巖石抗壓強度為68.8 MPa,根據文獻[23]以0.8σc即55.04 MPa 進行混凝土配比,按照所需強度查找相應的混凝土模型配比見表3。該配合比所得強度為55 MPa,與設計強度相符。將水灰質量比1∶3 的漿液裝入致裂孔中,并至液面距離孔口10 cm 處,采用錨固劑進行封孔。

表3 混凝土模型配比Table 3 Concrete model ratio
3.2 致裂巖體微震分布特征
封孔后,膨脹致裂巖體進行連續24 h 實時監測,直至混凝土模型斷裂且裂縫不再發育。沿致裂孔水平方向,巖體一分為二,側面裂隙形成貫通。最后裂隙由巖體頂部向兩側延伸至底部,頂部裂隙寬度達到25 mm,膨脹致裂的巖體致裂特征如圖4。試驗動態微震分布特征如圖5。

圖4 巖體致裂特征Fig.4 Fra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mass

圖5 試驗動態微震分布特征Fig.5 Dynamic microseismic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st
動態微震數據分析可知,大事件發生主要在前11 h 內,隨后裂隙發育伴隨的微震事件數及其能量較小。通過分析前11 h 和整合11 h 以后的微震數據,膨脹致裂動態過程中的微震發生位置、能量大小等的分布特征。事件基本發生在鉆孔長度的中心周圍附近。
前4 h,事件總個數為43 次,能量均小于500 J。第5 h 內發生過1 次能量為794.78 J 的事件;第6 h 發生3 次能量大于1 000 J 的事件,其中最大能量值為2 015.45 J;第7、8 h 微震事件降低,且每次發生的能量均小于500 J;第9 h,共發生微震事件41 次,占總數量的68.33%,且微震大能量事件最多,其中大于2 000 J 的為6 次;隨后9 h 后的微震事件的數量及能量開始減少。由此可知,致裂兩鉆孔中間的巖體部分開始發生裂隙并向外擴展貫通,膨脹致裂的第9 h 巖塊出現整體斷裂現象。全程微震事件能量-頻次特征如圖6。

圖6 全程微震事件能量-頻次特征Fig.6 Energy-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whole-process microseismic events
全程致裂巖體的微震事件能量及頻次特征大體上分為3 個階段:
1)初始階段。在該階段鉆孔為攪拌均勻的膨脹劑沉淀及初始的水化反應過程,其中有少量微震事件產生且單次事件的能量均小于500 J。隨著時間的推移,此階段膨脹劑并未持續反應而是逐漸降低了反應速率,且微震事件及能量也隨之減少。
2)膨脹階段。第9 h 內發生的能量級頻次驟然增加,共釋放35 003.73 J 能量。其中大于2 000 J 的事件數持續時間約30 min,極大程度促進了混凝土模型的脹裂,并使裂紋沿著兩鉆孔連線方向貫通。
3)殘余階段。膨脹劑反應后期的膨脹劑持續反應但反應速率明顯降低。期間雖有大于500 J 的較大事件發生,但相隔時間較長,可知本階段膨脹劑的反應逐漸加大混凝土模型的脹裂尺寸。
3.3 致裂巖體聲發射分布特征
整個聲發射監測試驗過程中,第4~第18 h 接受到聲發射信號,巖體致裂過程中聲發射的能率和振鈴計數的分布趨勢基本相同,聲發射監測數據圖如圖7。

圖7 聲發射監測數據圖Fig.7 Acoustic emission monitoring data
第7、第8 h 時間內聲發射事件信號減弱,第9 h 聲發射事件能率突然增加;第18 h 后,聲發射事件數及能率大幅度降低;第6 h 和第9 h 聲發射分別出現了峰值,第6 h 和第9 h 對應的能率及振鈴計數分別為4.76×105mV·μs、2.13×103個,10.58×105mV·μs、3.23×103個。
4 致裂巖體的應力及聲發射特征
4.1 RFPA 模型搭建
擾動應力及AE 特征能夠充分揭示致裂巖體的變形特征。通過采用RFPA 軟件,建立堅硬巖體致裂的數值計算模型,達到致裂堅硬巖體應力分布和聲發射分布特征的目的。設計模型尺寸為130 cm×130 cm,模型基元取1 cm×1 cm,數值模型總基元數共1.69×104個。模型邊界設為不透水邊界,模型側面限制水平移動、底面限制垂直移動,RFPA 數值模型如圖8,數值模擬物理參數見表4。

圖8 RFPA 計算模型設計Fig.8 RFPA calculation model design

表4 數值模擬物理參數Table 4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physical parameters
試件圍巖施加0.5 MPa 應力,模擬巖層賦存條件下的圍巖壓力。模型中心對稱開挖2 個直徑為60 mm 的圓形鉆孔,孔間距為40 cm。整個加載過程中,通過水壓力加載方式模擬膨脹致裂,孔內注水的初始壓力為1 MPa,注水孔壓每步增量0.2 MPa,控制步數為50 步,實際計算過程中出現大量裂紋停止運算。模型設置2 條應力監測線,監測線Ⅰ位于鉆孔連線水平方向,監測線Ⅱ位于鉆連線垂直方向。通過計算圍壓作用下雙孔巖石水壓致裂過程,分析鉆孔中心到邊界的裂紋發育、應力分布、聲發射等分布情況。
4.2 裂隙發育特征
裂隙演化分布特征如圖9。初始狀態下在兩鉆孔周圍出現應力增高,但未未達到破壞強度極限,無明顯裂隙產生。隨計算步數的增加至34 步時,鉆孔內膨脹壓力達到7.8 MPa,基元體在開始破裂。

圖9 裂隙發育特征圖Fig.9 Characteristic diagrams of fracture development
第34 步節點下的裂隙沿鉆孔連線的水平方向發育。第34 步8 節前,各鉆孔的膨脹力致使各孔水平演化;第34 步8 節裂隙貫通。受孔間距40 cm 的影響,裂隙在達到模型邊界之前,內部出現貫通,形成“一”字空腔結構。裂隙的進一步發育,對其發育方向有較好的控制作用。
4.3 裂隙發育過程中應力分布特征
4.3.1 監測線Ⅰ應力曲線特征
膨脹致裂巖體的裂隙發育沿水平方向,產生較長裂隙直至破壞。監測線Ⅰ巖體的應力變化特征如圖10。

圖10 監測線Ⅰ的應力變化特征Fig.10 Stress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n the monitoring line Ⅰ
初始狀態下,x、y、xy 方向的應力幾乎無變化,僅在鉆孔周圍出現集中現象,如圖10(a)。隨著計算步數增加至34 步時,即鉆孔內膨脹壓力達到7.8 MPa,應力分布總體呈現y 向>x 向>xy 向,如圖10(b)~圖10(f)。34 步各節點的x、y 向應力分布具有相似對稱性,且無應力區范圍由鉆孔向模型兩側逐漸增大,兩側的應力值逐漸減小。xy 向的應力整體變化較小,不會影響裂隙發育的方向。
裂隙不斷演化,7 節、8 節鉆孔外側的應力峰值明顯較大,且左側大于右側;中間位置的應力峰值具有疊加趨勢。由此表明:裂隙由鉆孔向兩側逐漸發育、擴展,無應力區范圍擴大且向中心靠攏,兩鉆孔裂隙易出現貫通,形成空腔。
4.3.2 監測線Ⅱ應力曲線特征
模型監測線Ⅱ的初始狀態及34 步各節點的應力分布特征如圖11。
初始狀態下3 個方向的應力擾動基本無明顯變化;鉆孔內膨脹壓力達到7.8 MPa 時,x、y 向應力變化趨勢相似,且y 向>x 向,xy 向應力在0 MPa 附近震蕩。
34 步各節點的應力分布中,y 向應力變化比較劇烈。第34 步的2 節、4 節、6 節點下的y 向應力呈出“V”型分布特征。模型上側邊緣,y 向應力在垂直應力作用下呈正值,基元體處于壓縮狀態,模型中部的應力最大,一直處于拉伸狀態。隨著計算增加,模型中部拉應力持續增大。7 節點下的y 向應力鄒然增加,表明兩鉆孔之間裂隙發育、擴張,8 節點下y向應力峰值出現波動且應力峰值范圍擴大,此時模型裂隙逐漸擴大,并于兩鉆孔之間交匯貫通。
4.4 聲發射動態分布特征
致裂過程中同時伴隨裂紋不斷發育、擴展并向外發射出聲發射信號。產生聲發射的位置、數量與破裂之間的關系如圖12。致裂過程中聲發射信號可以直觀的發現其主要分布在鉆孔周圍,與裂紋的發育路徑基本吻合,且由裂紋由中心向兩側擴展,以鉆孔連線中心呈對稱形狀分布。

圖12 致裂過程中的聲發射圖Fig.12 Acoustic emission diagrams during the cracking process
初始狀態下兩鉆孔周圍并未出現明顯裂隙區,聲發射信號顯現不明顯。膨脹壓力的持續增加,裂紋數量不斷增加的同時向外發射出聲發射信號逐步增強,聲發射信號集中出現在鉆孔兩側。第34 步的4 節、6 節的聲發射信號(圖12(c)~圖12(d)),在鉆孔附近呈現“∞”形態分布特征。由于兩鉆孔間距相距40 cm,隨著持續增加,如圖12(e)。兩鉆孔中心處的聲發射信號形成疊加,兩端小中間大的“一”字長條形結構;鉆孔外側沿裂隙擴展方向發射信號密集。
由此可知,在第34 步7 節處的鉆孔裂隙貫通。之后隨著計算步的增加聲發射信號繼續向模型邊界擴展,直至模型破壞失穩為止。
5 結 論
1)膨脹劑水化反應后,最佳水灰比為1∶3。致裂劑膨脹產生的平均徑向、軸向應力為30.47 MPa 和19.8 MPa,遠大于巖石的抗拉強度。
2)雙孔膨脹致裂下,巖塊最終沿雙孔水平連線位置處斷裂,破裂過程中產生的微震事件多集中在巖體中心位置。其中微震在第9 h 事件數及能量級最大,事件數約占總數量的68.33%,能量值大于2 000 J 的為6 次。
3)通過RFPA 可知,鉆孔內膨脹壓力達到7.8 MPa,基元體在開始破裂。裂隙由鉆孔向兩側逐漸發育、擴展,內部出現逐步貫通并形成“一”字空腔結構。鉆孔出現的無應力區范圍擴大且向中心靠攏,隨裂隙貫通形成空腔。
4)裂隙發育、擴展下的聲發射初始呈現“∞”形態分布特征,RFPA 計算中第34 步7 節處的鉆孔裂隙貫通,聲發射信號在鉆孔內部形成疊加,呈現“兩端小中間大”的“一”字長條結構,同時鉆孔外側裂隙擴展方向的發射信號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