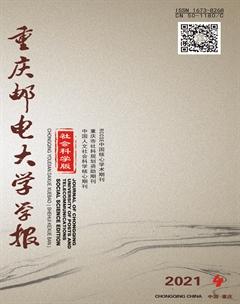虛擬財產保護路徑之探析
阿迪力·阿尤甫,秦文豪



摘要:對已公布的350個案件的研究顯示:虛擬財產認定標準不明確;類型劃分不清晰;價值評估方法選擇機制不合理;格式條款對網絡用戶權利的限制過多;案件審理過程中缺乏專業技術人士的配合;對重點罪名研究不足;配套法規不完善,給保護工作帶來了實際困難。其背后既有技術層面的原因,也與司法結構層面未予重視和配套措施不到位等相關。對虛擬財產的保護要調整思路,以價值和價值實現方式的抽象性作為認定虛擬財產的重要標準;區分網絡和非網絡虛擬財產;強化對部分案件的雙向教導功能;構建價值評估方法的合理選擇機制;減少格式條款對網絡用戶權利的限制;引進有專門知識的人士參與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討論;加強對重點罪名的預防和研究;盡快出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27條配套的司法解釋。
關鍵詞:虛擬財產保護;區分標準;評估方式;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D913?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21)04007316
如何推進虛擬財產的保護制度改革,是近年來理論界和實務界高度關注與熱烈討論的重要問題。而虛擬財產保護不僅被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是推進我國財產權保護的重要內容,也被中央認為是推進數字化經濟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虛擬財產的保護涉及的領域和方面卻無法一言道明,比如,有學者認為,虛擬財產究竟是物權還是債權,抑或是一種新型的權利類型值得商榷和討論[19];還有學者認為,虛擬財產的價值能否被合理評估,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10];在刑事立法層面,不少學者主張加強虛擬財產保護方面的刑事立法工作,以充實和完善現有的規定[1114];而在民事立法層面,基于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快速發展新形勢下財產權保護的新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與時俱進,在第127條中對數據和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做出了規定,但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無法適應實際需要《民法典》第127條規定:“法律對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無論在立法層面還是在實務層面,都迫切需要與之配套的特別法規盡快出臺[15]。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法學界各領域學者在理論層面進行了熱烈的探討,也為相關實證研究的開展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思路。虛擬財產保護制度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考察已公布虛擬財產案件的實際狀況,分析其中的問題,總結其中的規律,歸納其中的方法,可以為深化虛擬財產保護制度改革乃至司法體制改革提供理論參考。
一、研究樣本的選取
本項研究所關注的虛擬財產案件(以下簡稱“案件”),為20092019年全國范圍內公布于中國裁判文書網的焦點型案件由于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案件一直在不斷更新,本研究所收集的樣本均截至2020年4月10日。。中國裁判文書網是我國司法領域重要的法律文書搜索平臺,自2013年7月上線運行以來,各級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在中國裁判文書網集中統一發布生效裁判文書,各項工作扎實有序推進,取得了突出成效。2018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發布的《全國司法公開第三方評估報告》顯示,該平臺裁判文書上網率總體較好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2018年12月發布的《全國司法公開第三方評估報告》。,抽樣研究結果表明,截止到2018年10月24日,在樣本包含的160家法院中包括32家高級法院、32家中級法院和96家基層法院。,有19家法院的案件上網率超過80.0%,另外有129家法院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了不上網裁判文書的案件號、案由等信息項,占84.6%。這說明,該平臺公開的虛擬財產案件在所有可能的樣本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對該部分案件進行探討,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研究意義。有鑒于此,筆者對與虛擬財產相關的案件的審理和裁判情況進行了整理,通過對有關虛擬財產案件的法律文書進行全文關鍵字檢索,發現361個可供分析的實證樣本,通過對有效樣本的篩選和對無效樣本的剔除,共留下350個有效樣本。鑒于研究樣本中裁判文書的內容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為確保研究材料特別是數據的全面性和可比性,本文的分析對象主要集中在文書內容齊全或者主要變量數據基本符合要求的案件上,剔除了研究樣本中一些不符合要求的案件。質言之,本節下文各部分數據的統計基數可能略有差異,但整體上不會對分析結果產生顯著影響。通過對案件的變量編碼,收集整理了我國近年來各地法院審理的案件中涉及的虛擬財產案件的區域分布、時間分布、類型分布、訴訟標的種類分布、侵權者與被侵權者社會角色分布、案件爭議焦點類型、裁判效果以及刑事罪名最終認定狀況等數據,并對部分虛擬財產在市場上的作價方式進行了梳理和統計。通過以上方法,獲取了較為充分的實證材料,基本能滿足研究的需要。
基于這些文書材料和數據,本研究以“實務中,有關虛擬財產案件的審理存在多領域、多方面問題未被及時發現和解決”為假設,對我國各地三審法院有關虛擬財產案件的審理情況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考察,重點關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有關虛擬財產的案件在實務中是否存在未被解決或者未被發現的問題;二是在前一個問題成立的前提下,應當如何應對和解決。
二、財產虛擬化趨勢下虛擬財產案件的審理實踐
(一)種類分布
在實際案件中,虛擬財產是不是如《民法典》總則編第五章第127條規定的只有網絡虛擬財產一個類型?哪些財產被法院界定為虛擬財產?在這些類型中,又有哪些經常面臨糾紛?為了弄清楚這些問題,對樣本案件中涉及虛擬財產的類型和數量進行了統計。
1.網絡虛擬財產和非網絡虛擬財產
從表1中可見,網絡虛擬財產占比86.6%,種類為22種,而非網絡虛擬財產占比13.4%,種類為12種。這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坊間對虛擬財產的認知,即虛擬財產并非僅指網絡虛擬財產,非網絡虛擬財產在其中也占據著重要的位置,根據長尾理論[16],只重視多數而忽視少數,會導致解決問題的機制發生系統性效率問題,從而徒增成本,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在區分網絡虛擬財產和非網絡虛擬財產的問題上,仍有一些錯誤的認識需要糾正。譬如,手機號是網絡虛擬財產還是非網絡虛擬財產?在法律上,手機號和手機是兩個可以分離的客體,手機號不一定非要搭載在特定的手機上,一個沒有手機卡的手機也可以用來上網、下載應用等。通過對實際案件的分析和整理發現,單純就手機號碼的歸屬問題發生爭議的案件較多,占樣本數量的3.4%(見表1),但是,當事人之所以想要獲得涉案手機號碼,并非出于不同手機號之間效用之差異,而是“身份”之差異,即該手機號為“靚號”,能夠彰顯使用人的地位、身份及資金實力。手機即便沒有網絡,但只要帶有固定號碼的手機卡,在不欠費的情況下,一樣可以實現其撥號和通話的功能[17],也即手機靚號不通過網絡便可以實現“靚號”之價值。再譬如,購物券屬于網絡虛擬財產還是非網絡虛擬財產?購物券是店家在顧客再次購物時給予優惠的承諾書,代表著顧客可以享有的一種權益,該種權益的價值和價值的實現方式是抽象的,故無論是何種購物券,實務中多將其認定為虛擬財產。通過對實際案件統計發現,涉案的購物券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網絡購物平臺發放的購物券參見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2019)浙0106刑初522號刑事判決書。,有在線購物折抵的功能,但是該購物券必須在線購物時才能使用,也就是說,必須依賴網絡才能發揮其功能,這類購物券可以被界定為網絡虛擬財產;另一種是線下商店發放的紙質購物券代表性案件為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人民法院(2018)鄂0111民初8170號民事判決書中的民間借貸糾紛一案。在該案件中,一審法院直接將線下購物券識別為虛擬貨幣,筆者認為不妥,因為案件所涉購物券本質上是用來兌換禮品,雖然能夠部分兌現,但是,也僅限于發放購物券的商家一方,其并不具備貨幣的流通性這一基本屬性。,其不依賴于網絡而存在,也并非貨幣,只具有線下購物時的折抵功能,可界定為非網絡虛擬財產。對網絡虛擬財產和非網絡虛擬財產進行準確劃分,有利于在立法和實務層面對不同類型虛擬財產的保護采取適宜的應對措施。部分知識產權學者主張“現有法律能夠涵蓋所謂的新興事物出現的問題,沒有必要事事呼吁立法”[18],但虛擬財產,尤其是網絡虛擬財產有自己新型的存在方式,在財產保護方面,也應當有自己的特點,若不能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想要對其進行合理保護并不現實。
2.數據和網絡虛擬財產
《民法典》第127條將數據和網絡虛擬財產并列于法條之中。在實際的案件中,由網絡店鋪訪問量和網頁訪問頻次等網絡數據引發的糾紛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比如,網絡店鋪違規刷單或者刷網頁的訪問流量。而在此類案件中,相關網絡數據均被一審法院認定為網絡虛擬財產,在樣本案件中,有3件(見表1腳注)由于網頁訪問流量產生的糾紛,將網頁訪問流量認定為網絡虛擬財產,當事人均無異議。但如果線上的訪問流量可以被認定為網絡虛擬財產,那是不是意味著線下店鋪的客流量也可以認定為虛擬財產?線下店可以通過口碑營銷,熟人口口相傳,通常無法直接體現為數據,但是網絡購物環境是陌生人組成的空間,網絡店鋪首頁所顯示出來的訪問量對消費者的最終決策影響較大。游戲裝備和網絡店鋪訪問量同樣以數據的形式存在于網絡,又同樣對于使用者具有一定價值。在市場上,游戲裝備和網絡店鋪訪問量又有可以參考的市場價格,所以,既然游戲裝備可以被認定為網絡虛擬財產,網絡店鋪訪問量為什么不行?故當實踐已經走在前面,且學界理論上無充足之理由證明其錯誤時,將網絡數據認定為網絡虛擬財產并無不妥。而一旦以網絡店鋪訪問量為代表的網絡數據被認定為網絡虛擬財產,網絡數據又是數據的主要存在形式,則《民法典》第127條將數據和網絡虛擬財產并列,其合理性似存在一定繼續探討的空間。
3.虛擬財產與無形財產
虛擬財產不等同于無形財產。從表1可以看出,在實際案件中,被認定為虛擬財產的財產類型中很大一部分是無形財產。但是無形財產不等于虛擬財產,因為“虛擬”二字其特征之一便是抽象,而“無形”之事物在價值和價值的實現方式上不一定是抽象的,誠然,“有形”之事物也不一定是具體的。例如,銀行存款體現在當事人的賬戶余額上,其表現形式是一串數字,在形態上是“無形”的,通過銀行賬號進行盜竊從而導致賬戶余額發生變化是常見的財產糾紛案件。在財產屬性方面,其價值和價值實現方式均不存在抽象一說,就不能認定為虛擬財產。經營權、股本權益等,雖然可能有合同或者認股書記載其權益,但是因為很多權益自身的價值和價值的實現方式是抽象的,故實務中多將其認定為虛擬財產。實際案件中,將股本權益認定為虛擬財產的案例占總樣本的2.0%,經營權占1.1%(見表1)。基于以上分析,就虛擬財產的概念和范圍在學界爭議較大的情況下,部分學者主張《民法典》應當更加關注無形財產并不現實[1920],因為相關民事立法中并沒有對無形財產做出具體規定,如果把無形財產的概念引入《民法典》,將會出現兩方面的問題:首先,無形財產更多的是一個經濟學上的概念,一旦引入民法,那么,民法上的無形財產和經濟學上的無形財產怎樣進行區分?其次,在民法內部,無形財產這一概念作為后來者,和虛擬財產又怎樣劃分界限?所以,在虛擬財產能夠涵蓋大部分無形財產的情況下,沿用民法對虛擬財產概念的使用可能更為合適。目前,《民法通則》《民法總則》以及已經出臺的《民法典》均未對無形財產進行規定。此外,在樣本案件中,亦未發現有將虛擬財產認定為無形財產的情形。
(二)區域分布
以往的實證研究表明,地域的差異性會對案件的審理工作產生較大影響[21]。具體到虛擬財產案件,發達地區、發展中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在案件審理方面同樣存在一些差異。
1.民事案件的上訴率
從案件的區域和案件終審層級的交叉分布來看(見表2),無論是在經濟發達地區、發展中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此處之欠發達地區,具體包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在一審即審結而當事人又沒有上訴的比例較低,其中,發達地區基層法院審理虛擬財產案件的上訴率為60.4%,發展中地區為81.0%,欠發達地區為44.4%,均超過40%,三地區平均上訴率為65.9%。這說明,基層法院在處理虛擬財產這類新型財產案件的過程中并不得心應手,其裁判結果亦不能讓大多數案件的當事人滿意。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首先,虛擬財產作為一種新型的財產權利,在理論上,其權利屬性未被明確,在實務中,可能會影響法官對整個案件屬性的認知。其次,相關立法并不完善,導致實務中處理案件時缺乏法條依據,進而影響法院審判結果的公信力和各方對案件裁判結果的滿意度。但是同樣應當注意到,發達地區案件的上訴率比發展中地區低20.6%,考慮到欠發達地區由于只有13個樣本,所以偶然性較大,若單從發達地區和發展中地區一審案件上訴率來看,案件的上訴率與法院所處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呈負相關關系,即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上訴率就越低。對此,推測性的解釋是:在經濟發達地區,當事人經濟能力較強,對小額標的的虛擬財產可能并不那么上心。再次,其對虛擬財產的認知能力較強,更能理解和相信一審法院裁判結果的公平公正性。最后,法官的整體素質和業務水平較高,其更具能力解決案件處理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而在經濟發展中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當事人經濟能力和對虛擬財產的認知水平相對有限,法官的業務水平也參差不齊,在辦案質量方面可能與經濟發達地區有一定差距。
2.刑事、民事案件數量
從案件的區域和案件類型的交叉分布來看(見表3),無論是在經濟發達地區、發展中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民事案件所占比例都顯著大于刑事案件。其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幾點:首先,虛擬財產人身依附性較小,即虛擬財產一般儲存在計算機網絡或者其他形式的介質中,具有“無形性”,在作案手段上,直接對財產的持有者進行人身攻擊獲利的可能性不大,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許多嚴重暴力型犯罪在虛擬財產案件發生的可能性。其次,虛擬財產面臨作價難的問題,例如,當一起虛擬財產盜竊案件發生后,能否將其界定為刑事犯罪,對虛擬財產價值的認定就十分關鍵,但在實務中,對涉案虛擬財產進行合理評估并非易事,根據刑事訴訟過程中的“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則,涉案金額模糊的刑事案件可能無法達到立案要求。再次,當用戶注冊成為某游戲公司旗下的玩家后,雙方就形成了服務合同關系,游戲公司若對玩家采取了不當的凍結賬號、沒收裝備等行為,涉及的是民事違約,玩家想恢復權益就要提起民事訴訟。最后,對虛擬財產尤其是網絡虛擬財產作案一般需要一定的技術能力和專業知識,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作案設置了更高的門檻。
(三)時間分布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虛擬財產而引發的糾紛數量逐年增加。通過對樣本中典型案件的數量進行統計后發現,20092019年間,虛擬財產案件的絕對數量在整體上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樣本案件在數量上年平均增加97.50%(見表4)。如果考慮到未公布于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樣本案件,則可推測出該類案件增加的絕對數量應該比表4中所示有增不減。除了科技方面的原因,在經濟層面,資產虛擬化的趨勢也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因素,傳統介質不但攜帶不便,也容易產生較高的交易和流通成本,以互聯網和區塊鏈技術為代表的新型財產存儲和流通手段開始逐漸獲得青睞。
(四)案件類型分布
由表5可見,在三級法院的案件類型分布狀況中,均以民、刑兩類案件為主。除此之外,統計結果還發現,管轄權異議案件和法院執行案件也占據一定的比例,分別占總樣本比例的7%和2%。在管轄權異議案件中,同級自行移送管轄的案件僅1件,但是報請上級進行指定管轄的案件為23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兩極分化。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執行00.020.651.4首先,虛擬財產的“無形性”特點使得對其侵權行為發生地的認定較為困難,例如,一款游戲的服務器可能放置在全國任何一個地方;其次,對于虛擬財產管轄權確定的問題,由于是新型財產案件,問題相較于常見案件更為復雜,各法院之間可能出現相互推諉的現象,故相關法院可能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而直接向上級法院申請指定管轄。出現一定比例的執行案件,可能的原因是虛擬財產的查封和執行涉及技術壟斷的網絡技術提供商,如果相關公司不能高效配合,很可能導致虛擬財產案件在判決之后無法被順利執行。
(五)侵權者和被侵權者社會角色分布
無論是預防犯罪還是懲治犯罪,研究哪類人群易成為該類案件的高發群體都有其必要性。通過研究和分析高發群體的普遍特征,不僅有利于對可能發生的犯罪進行前期干預和在案件偵查、審判過程中對其進行合理引導,也便于在案件審結之后對其進行個性化改造。那么,哪些人群容易成為虛擬財產案件的高發群體呢?通過對樣本案件的侵權者和被侵權者的數量系統梳理后發現,被侵權者的一方中,游戲玩家居于榜首,占到了總樣本比例的近四成(37.1%,見表6),緊隨其后的是游戲服務的買家該類人士一般也是游戲玩家,但是玩游戲的人不一定非要購買游戲服務,硬性地將購買游戲服務的人理解成游戲玩家,可能有不妥之處,所以,這里對二者還是進行了區分。、游戲公司、財產共有人、電信用戶、虛擬貨幣持有人和直播平臺的主播等。在侵權者中,游戲公司同樣占比近四成(38.0%),其次是游戲服務的賣家、網絡平臺、游戲玩家、直播平臺、虛擬貨幣發售平臺和虛擬貨幣銷售中介。在提起訴訟的主體中,排名前三的類型均與游戲有關,占到總樣本比例的55.7%,在被起訴的主體中,這一比例為56.7%。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幾點:首先,青年群體是網絡用戶的主體,網絡游戲又是最吸引該類群體的產品之一,根據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止到2020年12月,我國網民總數為9.89億,其中,手機網絡用戶9.86億;網絡游戲玩家總數為5.18億,占全部網民總數的52.4%;手機網絡游戲用戶規模達5.16億,占手機網民的52.4%[22]。在龐大的人口基數下,與游戲有關的案件占虛擬財產案件總樣本比例最大也可以理解;其次,資產虛擬化仍處于逐漸推進的過程之中,近年來,除游戲之外的許多新型虛擬財產案件涌現出來,但是類型較為分散,所占比例并不高。例如,虛擬貨幣持有人與虛擬貨幣發售平臺、虛擬貨幣銷售中介之間的矛盾,直播平臺的主播與直播平臺之間的利益沖突,甚至是購房積分的持有者和購彩積分的持有者與盜用者之間的糾葛,這些新興的虛擬財產案件豐富了法院所接觸到的虛擬財產的類型。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實物資產轉化為數字化的形式進行儲存,也使得傳統法律規定和理論界、實務界對財產權的古板認識面臨巨大挑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貨幣的虛擬化。我國并未承認民間流通虛擬貨幣的合法地位參見2017年9月發布并實施的《中國人民銀行、中央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等關于防范代幣融資風險的公告》。,但是,貨幣數字化的大趨勢迫使上層建筑進行改革。自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啟動相關研究以來,區塊鏈接技術應用于數字貨幣的技術已經逐漸成熟。2020年4月,央行法定數字貨幣DCEP在農行內測的消息更是引起軒然大波。所以,可以預見的是,一旦央行法定數字貨幣正式落地發行,今后有關法定數字貨幣的虛擬財產案件可能會快速增加。
(六)案件爭議焦點類型
虛擬財產案件之所以面臨上訴率高、發改率高的尷尬局面,與其審理過程中需要認定的難點多聯系密切。通過對樣本案件的裁判難點的整理和分析,發現在案件的裁判過程中,案件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虛擬財產能否構成侵權客體、能否被合理定價、能否被認定為物權、能否入股和轉讓這四個類型的問題上。
1.能否構成侵權客體
關于虛擬財產能否構成侵權客體,涉及該類型爭議焦點的107個案件全部支持構成侵權客體(見表7),相關法律依據的適用也較為集中
例如,大多數民事案件都引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的規定:民事主體享有物權、知識產權,法律規定網絡虛擬財產作為物權客體的,依照其規定。,說明實務界對該問題有著較為統一的認識。此處不再做過多討論。
2.能否被合理定價
關于虛擬財產能否被合理定價,涉及該類型爭議焦點的85個案件中,有70個被合理定價,占總樣本的82.4%,但也有15個無法被合理定價,占比17.6%。涉案虛擬財產無法被合理定價將導致一系列程序和實體問題,甚至導致案件無法審理。學界一般認為虛擬財產定價的方法大體有市場法、重置成本法、收益法和綜合法四種,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除市場法外,重置成本法和收益法并不具有廣泛代表性,部分學者所提及的綜合法也缺乏具體標準和步驟[2324]。虛擬財產想要被合理定價,首先要弄清涉案虛擬財產的類型,其次再選擇實用性較強的評估方法。從表8中可以看出,市場法、拍賣法和法院認定法的適用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成功率上,都具有顯著優勢。相比之下,當事人協商法和第三方機構評估法不但適用案件數量少,而且成功率也較低。但是,以市場法為手段對虛擬財產進行價值評估的成功率較高,并不意味著所有類型的虛擬財產都適合用該種方法進行價值評估。譬如,手機靚號就不適用該法進行評估,因為手機號是“獨一無二”的,市場法的適用需要以同種類產品在市場上的價格為參照物,而手機號的特殊屬性使其很難在市場上找到合適的替代品。但是“獨一無二”的東西卻很適合拍賣,手機號通過司法拍賣來評估其價值,已經成為各級法院常用的價值評估手段。實證研究表明,游戲賬號和游戲服務用市場法進行評估成功率較高,除了游戲公司自身的報價之外,很多購物平臺上的游戲賬號相關服務的出售價格也可以作為參考。對常用的三大電商平臺上344個游戲店鋪的交易狀況進行數據統計發現該三大平臺分別為:天貓(淘寶)、京東、拼多多。,其平臺上所出售的服務,即游戲賬號的出售、出租、代練和找回,都有較為詳細的報價,基本涵蓋了網絡游戲案件可能的救濟途徑類型(見表9)。法院直接定價法與第三方專業機構評估法相比,雖然在評估技術上可能略顯粗糙,但在實際案件中卻有著不俗的表現,成功率為88.2%(見表8),即當涉案虛擬財產既不適用市場法和拍賣法進行評估作價,當事人之間亦無法達成共識且涉案虛擬財產價值又不足以引進第三方評估機構進行評估,抑或是第三方評估機構亦無法合理進行評估時,直接由法院綜合考慮相關因素進行價格認定。在評估虛擬財產的眾多策略中,該方式通常可兜底適用。
3.如何確認權利屬性
關于如何確認虛擬財產的權利屬性。由表7可見,有19.1%的樣本案件法院支持虛擬財產物權說,但也有15.7%的案件法官認為將其認定為物權缺乏法律依據。從數據上看,兩者平分秋色,說明實務中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對該問題所持觀點分歧較大。已經人大表決通過的《民法典》總則編第五章第127條規定:“法律對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這一規定的實際應用價值十分有限,只是為虛擬財產的相關立法起總的引領作用,相比于2017年3月15日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在立法層面并未進行創新。實際上,該規定出臺后,反而在學界和實務界引起更為激烈的爭論,至今,有關虛擬財產屬性的問題仍未形成一種較為一致的觀點,相關立法也離完善相距甚遠。那么,虛擬財產應不應該被認定為物權呢?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將其認定為物權似乎更有利于案件的順利解決。在樣本案件中,也僅有一個案件當事人提起了上訴,因為一旦其被認定為物權,相關民事案件便可以適用原《物權法》和《民法典》之物權編的相關規定進行處理。可是,從理論上來說,一旦將虛擬財產視為財產上的“物”,那么,基于物的屬性,它的權利就應當是完整的。具體地說,民事主體對物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而虛擬財產有時會面臨無法進行收益,甚至無法處分的困境。關于虛擬財產屬性,學界仍在進行激烈討論,有物權說、債權說、知識產權說和新型財產權利說等,目前,物權說和債權說逐漸占據上風,但是,究竟哪種學說最為合適目前尚無定論。對虛擬財產的權利屬性這個問題,筆者主張,根據虛擬財產利益存在的法律關系的性質確認虛擬財產屬性。
4.能否入股和轉讓
實證研究表明,多數法院認定虛擬財產不能入股和轉讓,占樣本總數的17.1%,相比之下,只有9.1%的樣本案件對此表示肯定。該問題主要發生在網絡虛擬財產上,通過對裁判文書的整理不難發現,解決該問題的關鍵是弄清楚使用者在注冊賬號時所勾選的格式條款是否全部有效。而此類格式條款中一般規定,賬號、店鋪、點券等網絡虛擬財產的所有權歸屬于網絡公司,禁止贈與、借用、租用、轉讓或者售賣。比如,騰訊公司在游戲玩家開通游戲服務時,會明確告知注冊方游戲賬號及其裝備的所有權屬于騰訊公司,玩家只有使用游戲賬號和裝備的權利;再比如,杭州淘寶網絡有限公司在商家注冊淘寶店鋪時,明確告知該店鋪所有權屬于淘寶公司,商家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且未經淘寶公司同意,相關店鋪使用權不得轉讓。但筆者認為,該格式條款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之處。
首先,該格式條款對案件的審理造成了困難。在實際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法院時常根據該格式條款認定虛擬財產的使用人沒有處分該虛擬財產的權利,基于民法的自愿原則,很少有法院主動審查該條款本身是否存在問題,但若嚴格依據該格式條款,會對實際案件的高效、公正處理造成一定阻礙。以研究樣本中一個典型案件為例參見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滬02民終7631號民事判決書,尹某某、袁某某與趙某某合伙協議糾紛一案。該案件為全國首例微信公眾號虛擬財產分割案。,原告和被告原本是一微信公眾號的合伙經營者,但是由于相互間缺乏信任而決定對微信公眾號的財產權益進行分割,然而,騰訊公司的《微信公眾平臺服務協議》中載明:微信公眾號的所有權歸騰訊公司所有,用戶完成注冊后只有使用權,賬號使用權禁止贈與、借用、租用、轉讓或者售賣。根據這一條款,雙方當事人中最先注冊該微信公眾號并通過審核的,應該是該公眾號的使用權人,但是,實際運營人卻是包括三名原告和一名被告在內的四人,這明顯是違反該條款的。另外,法院在審理過程中,認定以微信公眾號為基礎的合伙協議成立,已經是對上述格式條款的突破,更引人注目的是,原注冊方已經不再掌握涉案微信公眾號的使用權,而是轉移到了被告一方,法院最終判決被告給予原告以經濟補償。這一判決結果起碼認可了兩個事實:第一,法院間接認可了微信公眾號使用權可以轉移的事實;第二,微信公眾號并非僅屬于注冊者一方,而是屬于合伙人全體,且其他合伙人的微信公眾號使用權可以折價,即能夠對各自的份額進行價值評估并售賣,此兩點均是對騰訊公司《微信公眾平臺服務協議》格式條款的直接突破。若完全按照網絡公司和用戶之間生效的格式條款進行審理,那該案件將會變得較為繁瑣,有畫蛇添足之嫌。
其次,很多法院支持該格式條款的部分理由
也很難讓人信服。大多數法院之所以對該格式條款表示支持,除了民法中的自愿原則以外,還認為網絡用戶是為了獲得“體驗”才進行賬號的注冊,既然用戶獲得了體驗(如游戲體驗),就不應當再奢求虛擬財產的所有權參見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終10897號民事判決書、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742號民事判決書、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區人民法院(2017)贛0502民初718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58326號民事判決書等相關法律文書。。但細以析之,該理由并站不住腳,僅僅因為游戲玩家和微信訂閱號等網絡虛擬財產的使用者獲得了體驗就認為其不具有虛擬財產的所有權未免匪夷所思。比如,某人買了新的電腦,既獲得了驚喜又獲得了玩電腦的體驗,難道因為這種體驗就能認為電腦的所有權不屬于他而屬于電腦的生產商嗎?網絡技術提供商之所以讓用戶免費注冊,是為了打開市場,一旦用戶注冊成功,用戶就開始在該平臺上消費“注意力”,另外,一些功能要付費才能使用。與此同時,公司并不會為每一特定主體開發新的技術,這類似于產品的標準化生產模式,不過,在網絡空間內更為簡單和便捷。是故,在網絡公司與用戶之間,理解為買賣合同關系可能更為恰當。而一旦用戶支付了對價,虛擬財產的所有權也應當相應地歸用戶所有,用戶基于該財產產生的收益,自然也歸其所有。
最后,該格式條款的內容不符合實際需求。除了處分權之外,其內容還包括網絡虛擬財產的所有權歸網絡公司所有。事實上,無論是游戲賬號還是網絡店鋪,數據作為一種載體,本身并沒有價值,價值由誰挖掘、創造,所有權就應歸誰[25]。如游戲玩家可能需要幾年時間才能打出一套頂級裝備,微信訂閱號的使用者也需要長時間的積累才能發展出數量龐大的粉絲群體。網絡虛擬財產的價值通常在使用過程中被使用者創造,其所有權也應歸屬于使用者。有的學者或者實務界人士不禁要問,網絡公司完全控制著網絡虛擬財產的產生和消亡,而使用人卻無法基于其所有者的身份對虛擬財產進行任意處分,從這個角度來看,還算有所有權嗎?筆者認為,這可以解釋為部分財產權的一種委托管理,在委托的過程中,所有者并不對自己的財產完全占有,即所有權人雖無力掌控網絡虛擬財產的產生和消亡,但是仍可以依法對網絡虛擬財產進行處分,要求將自己投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轉化為財富。若網絡公司基于技術壟斷優勢對用戶應有的權利設置諸多阻礙,既不利于用戶利益的保護,也不利于市場正常交易的進行,甚至會在訴訟中影響案件的公平公正處理。一種可能的解決方式是,網絡公司可以在要求獲得一部分傭金的情形下對用戶提供幫助,但不得對用戶的處分行為在技術上設置阻礙。
部分知識產權學者主張,網絡公司技術的開發者擁有版權,受著作權法保護,若片面地認為網絡虛擬財產的所有權歸用戶所有,可能有失偏頗[26]。但是,對數據的所有權并不代表對專利擁有所有權,如產品和其上的知識產權,用戶可以使用數據,可以向網絡公司申請對數據進行注銷,但不能對開發者編寫的原始程序進行改寫絕大多數網絡公司也不允許,只有極少數公司的虛擬社區允許用戶參與編寫,如第二世界。,故對數據的所有并不代表對知識產權的侵犯。另一部分知識產權學者主張,此處使用者所創造的“價值”,體現為使用“新數據”的權利,這些數據先前已經被網絡公司開發出來,對網絡公司來說,用戶的“升級”無法體現價值的增加。但是,由于“晉級”“獲得裝備”“獲得粉絲量”需要“做任務”,在網絡公司設置門檻和規則的情形下,一旦用戶通過努力達到了要求,網絡公司同樣應當依照規則使用戶享受使用“新數據”的權利,在該權利可以轉讓的情況下,價值就能體現出來(見表9,有的游戲賬號甚至價值百萬)。所以,知識產權說所主張的用戶“不創造價值說”,要區分具體的情形和所針對的對象。
(七)案件裁判效果
在所有的終審案件中,未經過改判或者發回的案件共236件,占所有樣本的67.4%;發回重審的共38件,占10.9%(見表10),全部由基層法院一審,由中院發回重審;而改判的為76件,占所有樣本的21.7%(見表10),一審法院包括初審法院為基層法院的案件和初審法院為中級人民法院的案件,數據收集過程中未發現有虛擬財產案件直接由高級人民法院或者最高院進行審理的情況,所以,此處不涉及對后二者的討論。為基層法院,由中院進行改判的為75件,一審法院為中院,由高院依法改判的案件僅1件。其中,改判和發回的案件數量共占樣本案件的33.6%,這也進一步說明,一審法院在審理該類案件時在事實、證據的認定以及法律的適用方面存在困難,除了立法不足和對虛擬財產的屬性了解不夠之外,以下原因也可能是導致該種情形的重要因素:首先,審判委員會未充分發揮作用,對案件的討論不足,對于新興的案件,當面臨立法不足及法律適用不明確的情形時,應當提交審判委員會進行討論,但是,在實際案件中可以發現,審判委員會存在效率低下、責任彌散、運行封閉等固有的問題,這使得其在處理新型虛擬財產案件時不能夠及時、準確地對難點進行處理;其次,法官對互聯網和區塊鏈等新型技術手段缺乏了解,在實際案件中,不能對虛擬財產的類型及其作案手段準確識別,從而在案件事實、證據認定方面困難重重,不利于其對案情的精確把握。
(八)刑事案件罪名分布
虛擬財產刑事案件應當如何定性在學界曾一石激起千層浪[2735],在實際案件中,有關法院對此究竟如何認定,是否與學界所探討之問題及解決方式有所不同,值得進行實證上的探究。由表11可見,在刑事案件罪名的最終認定上,盜竊罪占40.5%,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占18.9%,詐騙罪占9.9%,排名前三的犯罪占據總樣本的近七成(69.3%)。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在作案手段上較為相似,若將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也歸入最為集中的罪名中,那么排名前四的犯罪將占據總樣本的76.5%。這說明,在因虛擬財產引發的刑事案件中,相關罪名呈現出較為集中的趨勢,這有利于為有關犯罪的預防和審理工作理清重點端口。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首先,虛擬財產具有一般財產的價值性,有些虛擬財產的價值巨大,譬如,一些游戲賬號的網售最高價竟達到百萬元(見表9),在利益的引誘下,犯罪人可能會鋌而走險,故如盜竊、詐騙等傳統的犯罪手段在虛擬財產案件中頻繁出現;其次,與傳統財產權相比,虛擬財產有著自身的特點,其最大的特點是價值和價值的實現方式具有抽象性,對于網絡虛擬財產來說,還具有儲存方式上的虛擬性,故此類侵權案件中直接侵害人身的暴力型犯罪較少(譬如,搶劫罪案件只有3件,僅占比2.7%),相反,其手段一般比較隱秘,需要借助互聯網或者區塊鏈等新型技術進行,于是,與互聯網犯罪緊密相關的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便占據著相當一部分的比例(26.1%)。
三、虛擬財產保護的因應之策
(一)以價值和價值實現方式的抽象性作為認定虛擬財產的重要標準
研究表明,以是否存在于虛擬空間和是否“無形”來作為虛擬財產的判斷標準可能都不恰當。但在無形財產和財產性權益等概念未引入民法的情形下,越來越多的無形財產和財產性權益被法院認定為虛擬財產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否則,相關案件將無可適用之法條,不利于當事人權益的保
護。從樣本案件來看,被認定為虛擬財產的32個類型中,有的是“有形”財產,有的是“無形”財產,盡管存在形式各異,但它們卻有著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價值和價值的實現方式上具有抽象性。是故,以價值和價值的實現方式是否具有抽象性來認定一種財產是否為虛擬財產,更符合案件實際審理的需要。第一,與常見的財產類型不同,虛擬財產的價值具有抽象性,體現在其價值無法被直接“量化”,也即在是否具有價值這一問題上,很多人都能給出肯定的答案,但該虛擬財產究竟有多少價值,對不熟悉的人來說常常無法一言道明。第二,虛擬財產價值實現方式的抽象性首先體現在需要通過新的方式去實現,如作為新型的營利方式,直播博主需要將其獲得的直播打賞幣與直播平臺進行兌換,才能最終獲得收入。另外,這一過程多數情況下還需要借助新型的載體,如線上購物券作為網絡虛擬財產,其價值的實現需要借助于網絡。而軟件激活碼作為非網絡虛擬財產,其價值的實現需要借助電子設備和軟件程序。故當虛擬財產越偏向于以新的方式和新型的載體實現其價值時,越會顯著提高人們對其價值實現方式抽象性的感知。第三,虛擬財產還具有流動性,某一類虛擬財產價值和價值實現方式的抽象性可能不會一直存在,隨著技術和商業模式的創新和發展,新的虛擬財產類型也會涌現出來。所以,筆者認為,將虛擬財產種類看成一個動態區間比較合理,當知識更迭的速度小于等于人類認知能力的時候,能夠顯著減少此類財產的種類和數量,但如果技術和商業模型的創新速度更迭太快,則會正向促進其種類和數量的增加。
另外,對于部分有實物作為載體的虛擬財產來說,直接認定為常見的財產類型即可,根據上述標準將其劃分為虛擬財產豈不弄巧成拙?對于上述可能存在的疑惑,筆者認為,這是對實際案件缺乏實證考察所產生的錯誤認知。單純從概念去推導概念可能會導致理論與實際相距甚遠,在缺乏實證研究的情形下,片面地從概念上推斷法院在認定虛擬財產方面存在瑕疵可能會遺漏關鍵變量。由實證研究可知,有形虛擬財產的案件為11件
線下購物券(2)、股本權益書(4)、購房積分卡(2)、購彩積分卡(2)、經營權證書(1)。,有5種類型,占所有非網絡虛擬財產案件總樣本的27.7%。由表4可見,虛擬財產案件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可以料想,在未來,有形的虛擬財產案件將會越來越多。雖然司法裁判中對虛擬財產的認定可能不一定準確,但直接把紙質購物券、購房積分卡等“有形的虛擬財產”認定為常見的財產類型恐怕也難以服眾。在虛擬財產的相關概念未進行準確定義的情形下,法院從結案息訴和讓相關當事人滿意的角度出發,將一些價值和價值實現方式具有抽象性的財產認定為虛擬財產并無不妥,否則,相關當事人的權益將無法及時得到保護。
(二)區分網絡虛擬財產和非網絡虛擬財產
在虛擬財產的類別上,可劃分為網絡虛擬財產和非網絡虛擬財產。事實上,在網絡虛擬財產概念已經頻繁使用的情況下,學界和實務上對網絡虛擬財產與其他虛擬財產之區別的認識仍比較模糊。在有些案件中,甚至有法院直接將手機號視為網絡虛擬財產進行裁判參見山東省臨沂市莒南縣人民法院(2019)魯1327執異60號執行裁定書,臨沂聚豐典當股份有限公司、陳某某典當執行糾紛案。,在對涉案虛擬財產的基本屬性缺乏明確認識的情況下,法院判決的公信力和說服力一定程度上受到質疑。另外,區分網絡虛擬財產與非網絡虛擬財產的意義還在于兩者保護方式的側重點可能有所不同,對于網絡虛擬財產來說,應注重線上保護,并強調技術支撐,對于非網絡虛擬財產來說,應加強線下保護,強調傳統財產權保護方式和新型技術手段并用。非網絡虛擬財產案件不依賴網絡而存在,其存在形式多種多樣,既可以由簡單的一張紙記載其權利,也可以是沒有任何記載憑證,但事實上被相關當事人認可的一種事實狀態。所以,對于非網絡虛擬財產來說,強調其線下保護就尤為重要。當然,不完全依賴于網絡并不代表不能以網絡為介質,所以,對于某些可能會使用網絡作為介質的非網絡虛擬財產,不但要通過傳統方式對侵權行為進行規制,而且還要注重新型技術手段在保護非網絡虛擬財產方面的應用。
(三)強化對案件起訴方為游戲玩家案件的雙向社會教導功能
研究表明,隨著財產虛擬化趨勢的延伸,近年來,有很多新型的虛擬財產侵權案件進入公眾視野,但是,必須注意到的是,游戲玩家訴網絡游戲公司的案件在比例上仍然占據著榜首。處理該類案件的一個常見的方向是,對侵權者(比如網絡游戲公司)進行懲罰,使其恢復游戲玩家的虛擬財產。但是,僅從這一個方向出發并不能使問題得到很好的解決。游戲玩家一般屬于年輕群體,一旦作為勝訴者的游戲玩家不能把時間、精力轉移到實際的生活、工作中來,那么,法院在維護其利益的同時也等于變相地對其利益進行了損害。一種可能的解決方式是,在處理虛擬財產案件時,對癡迷于網絡游戲的玩家進行口頭教育,引導其理性走向社會。
(四)構建虛擬財產評估方法的合理選擇機制
除傳統的市場法、重置成本法、收益法外,涉案虛擬財產的評估可以加強對第三方專業機構評估法和法院直接認定法的使用,并在評估方法方面構建合理的選擇機制。實證研究表明,虛擬財產不同的評估方法適用于不同的虛擬財產類型和評估階段,比如,手機靚號就適合用拍賣法而不是其他方法,而大多數游戲裝備適合用市場法。對于一些既可以使用市場法又可以使用拍賣法進行價值評估的虛擬財產來說,可以優先考慮市場法,因為司法拍賣充滿不確定性,而且容易徒增成本[3637]。除市場法外,有關學者主張的重置成本法、收益法雖不常見,但卻像市場法一樣擁有便捷性,而綜合法則較為籠統,缺乏適用的具體步驟和規范[38],所以,在虛擬財產評估方法合理的選擇機制中,不再對綜合法進行采用。構建虛擬財產評估方法合理選擇機制的具體思路為:在選擇具體的評估方法之前,應當允許雙方當事人就虛擬財產的價值和評估方法進行協商,當協商不成時,則以市場法、重置成本法、收益法、拍賣法為主,加強對法院直接定價法的使用。第三方評估機構具有專業性強的優點,但實證研究發現,其也有評估速度慢、失敗率高的弊病,所以,只有在特別需要時才建議使用第三方機構評估法。具體步驟為:雙方當事人無法就虛擬財產的價值和評估方式協商一致時,若涉案虛擬財產能夠適用市場法、重置成本法、收益法、拍賣法進行價值評估,則根據不同的虛擬財產類型選擇合適的評估方法,不再考慮其他方法,但是,如果不能順利進行評估,則應當看涉案虛擬財產的價值。一種情形是,涉案虛擬財產價值巨大,則可以引進第三方專業評估機構,若第三方評估機構依法依規評估成功,則不再考慮其他方法,若失敗,則由法院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直接進行認定;另一種情形是,涉案虛擬財產為一般價值的財產,則可直接由法院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后直接進行認定。
(五)減少格式條款對網絡用戶權利的限制
減少格式條款對網絡用戶權利的限制,明確用戶擁有網絡虛擬財產所有權和處分權。以游戲賬號為例,若所有權歸于賬號的使用者,就要突破注冊賬號時格式條款對虛擬財產使用者收益、處分權利的限制,若所有權歸于網絡公司,則對于賬號用戶來說明顯不公平。數據載體本身是沒有價值的,其價值通常是在使用過程中產生,如游戲賬號附帶的裝備和微信公眾號附帶的粉絲量,都是用戶付出一定的時間和精力換來的成果。所以,應當禁止網絡公司限制用戶虛擬財產所有權的格式條款。另一個問題是,由于網絡公司完全有能力隨時將賬號進行回收、凍結,事實上,即便用戶擁有所有權,也無法對賬號進行實際上的管控。一個可能的解決方式是,將其視為財產的一種委托管理,即用戶將數據載體的所有權委托給網絡技術平臺進行管理,并通過關注和使用該平臺為網絡公司創造價值,相應地,網絡平臺應尊重用戶對其網絡虛擬財產的所有權。由于該數據載體與使用者創造之價值具有不可分割性,網絡技術平臺通過格式條款將數據的處分權控制在自己手里,使用戶在賬號上付出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難以轉化,不但不利于用戶權益的保護,而且也不利于市場交易的進行,甚至會給相關案件的審判設置難以解決的障礙。所以,在禁止網絡公司使用限制用戶虛擬財產使用權的基礎上,一種可能的解決方式是,網絡公司可以在要求獲得一部分傭金的情形下提供幫助,但不得對用戶的處分行為在技術上設置阻礙。網絡平臺應尊重用戶對賬戶的處分權,不得干涉其贈與、借用、轉讓或者售賣虛擬財產。
(六)引進有專門知識的人士參與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討論
虛擬財產案件的一審案件上訴率高
通過對裁判文書的檢索可知,一審民事案件總數量為51 570 270件,二審民事案件的總數量為5 736 152件,由此可見,民事案件的平均上訴率大約為11.1%;一審刑事案件總數量為6 322 845件,二審刑事案件數量為764 354件,上訴率大約為12.1%。而虛擬財產民事案件的上訴率大約為70.5%,刑事案件的上訴率大約為21.5%,所以,無論從民事案件的上訴率還是從刑事案件的上訴率看,都遠高于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平均上訴率。,與審判委員會未對相關案件進行充分、有效的討論有密切關系。在新型虛擬財產案件的審判過程中,審判委員會面臨固有弊病和新生問題的雙重挑戰。首先,審判委員會存在效率低下、責任彌散、運行封閉等固有的問題,會使其在處理新型虛擬財產案件時反應遲鈍,不能迅速、準確地對難點進行處理;其次,對互聯網和區塊鏈等新型技術手段缺乏了解,審判委員會中缺乏有技術背景的人員,不能對案件類型及其作案手段準確識別,從而在案件事實、證據認定方面出現困難,不利于其對案情的精確把握。解決上述問題可能的思路是:首先,應當在既有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審判委員會改革試點工作,強化其對新型案件的協商和討論功能;其次,進一步提升民事訴訟法中的“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制度,建立有互聯網、區塊鏈等新興技術背景的專門知識的人士進入審判委員會制度,在簽訂保密協議的前提下,可以向社會公開招聘有新型技術背景的專業人員參與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討論工作,必要時給予其一定的報酬。
(七)加強對重點罪名的預防和研究
研究發現,虛擬財產的刑事案件主要集中在盜竊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詐騙罪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四類犯罪上,這為與虛擬財產有關案件的預防和審判理清了重點端口。關于預防犯罪:首先,盜竊罪和詐騙罪是比較傳統的財產類犯罪,應加大宣傳力度,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識,以免犯罪分子乘虛而入;其次,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屬于隨著互聯網經濟的產生而出現的新的罪名,應強化技術層面的監管,督促電信企業和網絡公司加強自身防火墻的設置,定期排查系統安全漏洞,以防患于未然,還要加強對接受過網絡技術培訓的畢業生以及相關從業者的普法宣傳力度,引導其將自己掌握的網絡技術應用于經濟社會需要的領域。關于犯罪的偵查、審理工作:首先,應當認識到即便面對盜竊罪和詐騙罪這種傳統的財產犯罪,對其犯罪手段的認定也可能會成為難點,隨著技術的發展,當事人掩蓋犯罪證據的手段也會隨之增加,所以,面對狡猾的犯罪分子,如果用傳統的眼光審視財產虛擬化背景下的盜竊罪和詐騙罪可能會使案件無法被偵破,最終導致其無法被公平公正審理。一種可能的解決方式是,在對有關虛擬財產的盜竊案和詐騙案重點關注的同時,對相關作案手段以及與之有關的新技術進行及時梳理,并公之于眾。其次,實證研究表明,對于新興的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來說,此類犯罪的當事人學歷較高,一般接受過較高程度的教育,且多數屬于計算機領域的專業人士,在偵查和審理時,應當引進比其更為優秀的技術人才,對其犯罪手段和經過進行技術層面的全面解讀。此舉不但有利于使當事人盡快認罪認罰,也有利于法官對案件的性質和嚴重性程度進行合理評估。
(八)盡快出臺與《民法典》第127條配套的相關解釋
我國法學研究和立法實踐受大陸法系國家影響頗大,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遠超傳統的大陸法系國家
“電通安吉斯網絡”與英國經濟咨詢公司牛津研究院共同發布的《數字社會治理指數2019》,調查了24個國家的4.3萬人,最終,新加坡、美國、中國位列前三,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只有德國進入前十,而且是前十名的最后一名。。當意大利的部分學者還在關注無形財產的時候,新型的虛擬財產已經在我國財產保護方面激起不和諧的浪花。由實證數據可知,我國《民法典》物權編僅對有體物和部分權利進行保護
《民法典》第115條規定:“物包括不動產和動產。法律規定權利作為物權客體的,依照其規定。”,無法涵蓋無形的虛擬財產(如網絡虛擬財產和手機號),知識產權法也只能對部分無形的虛擬財產進行保護,而無法涵蓋很多有形的非網絡虛擬財產(如紙質購房積分卡)。但正如一位著名的意大利法學家所說:教條式概念既違反了普遍的法律認知,又容易導致其在財產規范的技術層面與法律、社會,尤其與經濟發展的需求相脫節[39]。因此,在虛擬財產保護方面應突破傳統思維限制,結合我國發展實際需要積極進行立法創新。實證研究表明,鑒于《民法典》第127條本身的規定較為籠統,可能無法適應案件審理的實際需要,法條本身可能也存在概念的瑕疵
首先,在以網絡店鋪訪問量為代表的網絡數據是否為網絡虛擬財產等問題不明確的情況下,《民法典》第127條將數據和網絡虛擬財產并列并不妥當;其次,實證研究表明,虛擬財產也不只有網絡虛擬財產這一個類型。,所以,出臺與該條配套的相關解釋已迫在眉睫。除文中已列舉的建議或能為完善相關立法提供一些思路外,還應注意的是,僅就網絡技術提供商內部來說,職務侵占也較為常見(約占刑事案件的4.5%,見表11)。隨著技術的發展,普通民眾對技術的理解可能越來越困難,而網絡技術提供商內部發生自利行為卻越來越便捷,這種技術、信息上的不對稱為虛擬財產侵權案件的出現提供了溫床。所以,既要重點加強對網絡技術提供商的監管,也要督促網絡技術提供商加強對其內部工作人員的監督,必要時,對相關機構或個人處以懲罰性賠償。
參考文獻:
[1]沈健州.從概念到規則:網絡虛擬財產權利的解釋選擇[J].現代法學,2018(6):4353.
[2]張明楷.非法獲取虛擬財產的行為性質[J].法學,2015(3):1225.
[3]楊立新.民法總則規定網絡虛擬財產的含義及重要價值[J].東方法學,2017(3):6472.
[4]程建華,高鋒志.侵犯“網絡虛擬財產”的行為如何定性[J].人民檢察,2005(12):3536.
[5]王洪用.網絡游戲虛擬財產案件的裁判思路[J].人民司法,2019(22):7583.
[6]馬一德.網絡虛擬財產繼承問題探析[J].法商研究,2013(5):7583.
[7]孫山.網絡虛擬財產權單獨立法保護的可行性初探[J].河北法學,2019(8):218.
[8]許可.網絡虛擬財產物權定位的證立——一個后果論的進路[J].政法論壇,2016(5):4956.
[9]李佳倫.網絡虛擬人格保護的困境與進路[J].比較法研究,2017(3):193200.
[10]陳如良,胡瞻智.游戲虛擬財產的執行[J].人民司法,2014(5):4750.
[11]臧德勝,付想兵.盜竊網絡虛擬財產罪名的認定[J].人民司法,2017(7):2730.
[12]姚萬勤.盜竊網絡虛擬財產行為定性的教義學分析——兼與劉明祥教授商榷[J].當代法學,2017(4):7285.
[13]張金鋼.竊取網絡虛擬財產的行為宜認定為盜竊罪[J].人民檢察,2019(7):7576.
[14]劉明祥.竊取網絡虛擬財產行為定性研究[J].法學,2016(1):151160.
[15]瞿靈敏.虛擬財產的概念共識與法律屬性——兼論《民法總則》第127條的理解和適用[J].東方法學,2017(6):6779.
[16]克里斯·安德森.長尾理論[M].喬江濤,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12.
[17]羅春燕.電信網間主叫號碼傳送規范探討[J].中國新技術新產品,2009(2):1920.
[18]鄧社民,李炳錄,韓金山.再論網絡虛擬財產的法律性質——以玩家對網絡游戲裝備享有的權利性質為視角[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5):3137.
[19]馬俊駒,梅夏英.無形財產的理論和立法問題[J].中國法學,2001(2):102112.
[20]吳漢東.無形財產的若干理論問題[J].中國法學,1997(4):7783.
[21]左衛民.審判委員會運行狀況的實證研究[J].法學研究,2016(3):170.
[22]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R/OL].(20210203)[20210204].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23]陶信平,劉志仁.論虛擬財產的法律保護[J].政治與法律,2007(4):96100.
[24]張元.談網絡虛擬財產價值之確定[J].人民司法,2006(11):7475.
[25]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迪·庫克耶.大數據時代[M].盛楊艷,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2125.
[26]侯利宏.論虛擬財產若干法律問題研究[J].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2):177.
[27]陳興良.虛擬財產的刑法屬性及其保護路徑[J].中國法學,2017(2):147172.
[28]梅夏英,許可.虛擬財產繼承的理論與立法問題[J].法學家,2013(6):8192.
[29]侯國云.再論虛擬財產刑事保護的不當性——與王志祥博士商榷[J].北方法學,2012(2):145160.
[30]臧德勝,付想兵.盜竊網絡虛擬財產的定性——以楊燦強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案為視角[J].法律適用,2017(16):6974.
[31]米鐵男.刑法視角下的網絡數字化財產問題研究[J].東方法學,2012(5):100108.
[32]田宏杰,肖鵬,周時雨.網絡虛擬財產的界定及刑法保護[J].人民檢察,2016(3):5458.
[33]孟璐.網絡虛擬財產的刑法保護——以謙抑刑法觀為分析視覺[J].法學雜志,2017(11):3946.
[34]葉慧娟.網絡虛擬財產的刑法定位[J].東方法學,2008(3):96106.
[35]徐彰.盜竊網絡虛擬財產不構成盜竊罪的刑民思考[J].法學論壇,2016(2):152160.
[36]張元華.論網絡司法拍賣的制度優勢與未來選擇[J].法律適用,2020(3):5970.
[37]芮晨宸.司法網絡拍賣疑難問題研究[J].中國拍賣,2019(11):1011.
[38]鄒政.盜竊虛擬財產行為的刑法適用探討——兼論虛擬財產價格的確定[J].法律適用,2014(5):7376.
[39]保羅·格羅西.財產:“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發展路徑[J].烏蘭,譯.比較法研究,2019(4):188200.
On the Path of Vir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Published Cases
ADILI Ayoufu, QIN Wenhao
(Law School,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350 published cases shows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and type of virtual property are not clear; there is a big regional gap in the quality of judges;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virtual property is unreasonable; there are too many restrictions on the rights of network users; the coopera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is lacking in the trial process; the research on key crimes is insufficient; the suppor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not enough. The imperfection has brought practical difficulties to the protection work. There are not only technical reasons behind it, but also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judicial structure and the lack of supporting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virtual property, we should adjust the way of thinking, take the abstraction of value and the way of value realization as the important standard to identify the virtual property, distinguish the network and non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strengthen the twoway teaching function of some cases, construct the reasonabl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evaluation methods, and reduce the restrictions of standard terms on the rights of network users. It is suggested that people with special knowledge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of cases by the judicial committee,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and research of key crimes, and formulate special laws and regulations corresponding to Article 127 of the civil code as soon as possible.
Keywords:
vir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distinguishing standard; evaluation method;? empirical research
(編輯:劉仲秋)
收稿日期:20200821修訂日期:2021020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知識產權獨立成編立法問題研究(18AFX021)
作者簡介:
阿迪力·阿尤甫(1975),男,維吾爾族,新疆拜城人,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主要從事民商法、知識產權法研究;秦文豪(1995),男,河南周口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民商法、網絡信息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