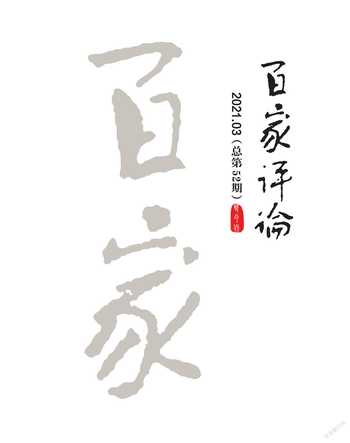來自生命深處的苦汁釀就的清酒
何志鈞 王心月
內容提要:在第三代詩歌運動的親歷者和參與者中,溫恕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作為大學時代投身詩歌熱潮的青年詩人、曾經的制藥廠工人、文學博士和人文學者,他將自身復雜坎坷的人生際遇發酵出的悲劇性人生體悟、詩人的敏銳與靈動、大學教授的文學素養和批判思維、海外訪學經歷和長期英文文獻研讀鑄就的跨文化視野與洞察力、對國際詩歌創作動態的了然于心,都融入了自身創作中。他的多面人生使他的詩作題材豐富,不拘一隅。他天性的灑脫、率真使他即使身歷坎坷曲折,他的詩歌卻并不悲沉凄苦,相反,多數的詩作輕靈淡雅,舉重若輕,散發出清思的芬芳,讀后令人心中靈動,心意久久難平。而他的英年早逝又使他創作的180首詩成為了凝定的遺存,為他頗有天分的詩歌創作斷然劃下了休止符。
關鍵詞:溫恕 詩歌 生命 悲劇
一、關于歷史與藝術的超越時空的對話思考
在他創作的詩歌中,溫恕或是肆意灑脫地表達文學作品所引起的無際遐想,或是超越時空,與歷史上的知名藝術家進行心靈對話,將自己的沉思和感悟外化為詩語。或是將自我代入特定歷史人物,帶領讀者漫步于歷史長河。或是深入內心,剖析自我的詩歌創作歷程……歷史與藝術作為其詩歌的重要主題,令其詩歌呈現出濃厚的學者情懷和人文氣息。溫恕把歷史與藝術當作橋梁,并通過二者將自己的獨到見解生動地呈現在了詩歌中。在寫作于1988年11月的《想起〈瓦爾登湖〉》(全文中所引詩歌出處均為《溫恕詩集》,重慶出版社,2017年5月版,不再一一注明)中,他通過回憶文學來表達對人生的獨特理解:人既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小我”,卻終將歸入“大我”,作為個體,人既可以擁有“去尋找、去放肆、去搖動”的追尋熱情,也可以懷抱“微笑著、退讓著”的安寧心境;在《致安德魯·懷斯》中,“棲身于窮鄉的房屋和冷僻的書中”是同為創作者的詩人和“我”都曾有過的艱難處境,“你不斷暗示、呼喊”是同為創作者的詩人和“我”對于藝術真諦的執著追求,相同的感受與經歷使作者能夠跨越藝術種類、無視時空距離與遠方的安德魯.懷斯進行深入交流并產生精神上的共鳴。他將自己關于藝術的看法在詩歌中和盤托出,認為藝術既是“果實中最堅硬的內核”,又是“凌駕了卻又空無所有的無邊的網”,結尾的詩句“我僅僅要求表達,你卻給了我真實”與其說是對安德魯·懷斯的崇敬與歌頌,不如說其中蘊涵著溫恕本人對于藝術本質和價值的追求與向往。
《寫作的問題》是溫恕創作的又一首靈動的短詩。
差不多成了鬼魂
由于近年來沒有敵人和朋友
我幾乎把你們當作活物
白天黑夜的傾訴
直到今天大風吹去樹梢
和一切幻想
在爽朗的空氣中
讓我嘲笑青春期的瘦子
過分寬大的制服
在《寫作的問題》中,溫恕點明了詩歌在其生活中充當著傾聽者的角色,“我幾乎把你們當作活物,白天黑夜的傾訴”,詩歌一方面被作者看作是靈犀相通的知音,因此他帶著自己的全部熱忱步入其中,他大可以將自己的荒誕、幻想、希望與感受寫入其中,天馬行空,任性肆意,為其詩歌增添幾分浪漫與夢幻色彩。
溫恕的詩浸染著靈性與活力,對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他看似信筆寫來,但在他的筆下卻都被點鐵成金,閃爍著金色質感。在《奧斯卡王爾德的最后時光》中,他寫道:
不列顛終于來到我頭腦中
女王、國教、見習修女
她們不斷指出:嗨,王爾德
向左轉,通過倫敦西區
奔流的泰晤士河水
教會你領悟永恒的人生……
聽啊,整個國家的腳步
多么轟然向前
當累丁獄憂傷的回憶
給我送來羅敦道、冥想中的甜點
同志們仍在指手畫腳
小個子比亞芝萊、陰謀家佩特
如今功德圓滿、奔赴天國
可是給我撂下一副怎樣的爛攤子
整整一個世紀的重擔
全都找上我,生活、藝術
良心、道德、人類的疾病
在我衰亡的余生反復發作
懸而未決。是的,到底是哪一個環節
我、奧斯卡·王爾德
經歷了懲罰和監禁
擁有良好的舉止、言行
這還不夠嗎?懺悔不足以
彌補過錯,又讓我趕上未來
新世紀的曙光
對于今天,我來得太早
昨天正是時候,然而
一個王爾德反對另一個王爾德
主啊,我知道這樣的時刻已經來臨
“讓邪惡拋棄邪惡”
難道罪過在我,抑或是別的
英俊少年、華麗的馬車
馳過狂熱的街心
當時我干得多么漂亮
一個世紀在驅使
一個世紀在呼喚
但現在我必須說:再見,奧斯卡;再見,倫敦
在詩中,虛擬幻想與歷史真實交錯重疊,讀者跟隨作者腳步邁入特定歷史時期,“女王、修女、倫敦西區、泰晤士河水”作者用簡單幾個詞語便構建出濃郁的異國風調,令讀者的感受更加逼真,生活、藝術、良心、道德、人類的疾病“在我衰亡的余生反復發作”這些詩句更讓讀者重新審視與思考王爾德這一偉大人物的在歷史中所應擁有的地位與價值。
在這類以歷史與藝術為主題的詩歌中,作者仿佛締造了一場存在著多元角色的對話與思考,過程精彩紛繁卻不喧囂,歷史和藝術既作為載體傳達著作者的感受與思考,也引發了讀者關于二者自身的價值與意義何在這一問題的思索與追尋。“Art for art’s sake(為藝術而藝術)”,這是溫恕執著追求的藝術目標,他身體力行,不斷嘗試在詩歌中與歷史、藝術、文學進行對話,以期發現詩歌自身的獨立價值并找回詩歌本應具有的尊嚴和力量。
二、回眸自然與童年的隱含在平凡中的
生活哲學
溫恕的創作并未拘泥于一種形式,在以深奧、淵博為特點的學者氣質濃厚的詩歌之外,他的詩歌還表現出另外一種風格:明麗、輕松、溫馨。這類詩歌以自然和童年為出發點,給其詩歌帶來一抹亮色。這首先表現在群山、群星、河流、飛鳥、花瓣、無花果等自然景物大量出現于詩中,如果說“群山、群星、山峰”等靜態景物為詩歌奠定了浪漫與莊重的基調,那么,“河流、飛鳥、落日”等動態景物又為其詩歌增添了幾筆靈動與活潑的色彩。自然既是一種可供我們觀賞的美的形式,又是一種我們可深入其中感受的生命。人類永遠是自然之子,也唯有在自然中,我們可以躲避都市生活的沉悶、機械與人際交往的繁瑣、虛偽,重新審視生活與自身,重新回歸最初的寧靜本心。
在寫于1994年4月2日的《我的房屋永遠在田野上》中,他寫道:
我的房屋永遠在田野上
在時間、飛翔的玫瑰花瓣上
我的靈魂在無花果上
在妥巴樹、小圓石
在所有干燥的和潮濕的物質上
看啊,陽光金色的蜜蜂圍繞它
風的女兒吹拂它,面向著永遠的田野
與其說作者在想象中將自己的房屋置于了田野上,不如說他將自己的靈魂安妥在了清新、曠遠的自然中,詩人盡情生發,在他的暢想中,他所向往的生活境界如金色的陽光一樣鋪灑,這是一個心性自由飛翔、陽光、清風、蜜蜂、樹木與花果盡情綻放的理想化境,詩人用全部身心投入其中,歆享這和諧、愉悅、安然、閑適、靜謐的意境。
作者在欣賞、沉醉于大自然的秀麗風光之余,也因其內心的細膩而敏銳感知著季節的轉變。在《跟隨春天》中,作者將可感卻抽象的四季轉化為具體實在并一一進行“跟隨、擊碎、訴說和孕育”,自然事物完全被擬人化了——“陽光編織的幻象”“群星燃燒”表現了春日的浪漫與激情,“糾纏的水草”“云朵的尖叫”點明了夏日的躁動與喧囂,“生命瀉空后的虛無”道出了秋天的寂靜與緩慢,“時光的魔法溺死飛行的物體和天空”的冬天卻迎來屬于自己的蕭條與沉寂,四季在這篇詩歌中完成了一個輪回。初讀這類以自然為主題的詩歌似乎并無特別之處,但細細品味,卻不難發現作者將自己的生活哲思隱匿于其中,或是在詩歌中通過描寫自然景物來表達對自然的喜愛,從而不言自明地展現自己的淡泊心境和對閑適、寧靜生活的向往,或是在詩歌中大膽抒寫自己的內心獨白,如《遙寄秋天》的結尾詩句:“上帝,我厭倦了虛假”以及《再致向日葵(二)》的詩句:“請你以不變的本性暢飲”,“從此你僅存了智慧”,“去度過、去歷盡漫漫余生”等。
童年記憶對每個人來說都彌足珍貴并難以忘卻,它同樣成為了溫恕創作的重要主題。在寫作于1997年的《空氣——童年紀事》中,他寫道:
十點,燈光熄滅
城市像一本識字課本
被黑夜吞沒
自鐵皮屋頂下
父親、母親在搓洗衣服
院子里曬衣繩滴水的聲音
像平原上的大河流動
教導愛與關懷
我們是吞食空氣的孩子
穿藍布衣服,蔑視肉體
在一個安詳的時刻
燕子飛翔的聲音可以傳出很遠
在這個星球上孤零零的一點
它遠離大陸,靜靜地向前
在《空氣——童年紀事》中,寫實部分如“白鐵皮屋頂下 父親、母親在搓洗衣服”,這是一幅極日常卻又深深烙印在所有人腦海中的畫面,正是這些平常事物與簡單動作的日日重復構成了我們自認不凡卻又時時懷念的童年回憶,也影響著我們對于溫馨生活的理解與定義。夸張部分如“院子里曬衣繩滴水的聲音,像平原上的大河流動,教導著愛與關懷”,個人所擁有的美好本性從不是與生俱來的,血脈中擁有的良好品質,來自于他人在生活中的點滴給予和善良。在童年時期我們最信任、最依賴、給予我們最多的便是與我們朝夕相處的父母,從日常生活的一蔬一飯到心理精神的一寸一土。院子里曬衣繩滴水的聲音雖微小,然而它的影響力量卻如平原上遼闊的大河,不斷滲透于我們的生命之中,教導著我們學會關懷與愛。想象部分如“燕子飛翔的聲音可以傳出很遠 在這個星球上孤零零的一點 它遠離大陸 靜靜地向前”,在結尾處,我們的思緒也跟隨著這只向前飛行的燕子進入浩瀚無垠的宇宙,展開無限的遐想。紀實的童年回憶與無稽的童年幻想在詩歌中前后聯結,能夠激起讀者的雙重情感:既有昔日溫馨回憶帶給我們的感動,也有如今的我們對于童年天真的懷念。“我們是吞食空氣的孩子”這一詩句聯結前半部分的回憶與后半部分的幻想,將的孩童的自由靈魂與天性表現得淋漓盡致,為整篇詩歌注入了童趣與靈性。以童年與自然為主題的詩歌創作雖平凡常見,然而溫恕卻將自己的人生智慧以及獨特回憶與其相融,形成其詩歌特有的韻味。
三、游刃技藝與詩心間的詩歌語詞煉金術
溫恕的詩歌運思精細,他對詩語有著天然的敏感,但他又不是純然放任自己詩思自然迸流的性情化詩人,他又很注重文句的精工打造。在他的詩作中,詞語及意義的對立非常引人注目,這構成了溫恕詩歌的一個重要結構特點。其中一種表現為單層對立,占比較大的為動詞的對立,如《想起〈瓦爾登湖〉》中“去尋找、去放肆”與“微笑著、退讓著”;《聲音》中“他們要繼續夢游他鄉”與“多舛的書本遺世獨立”;《再致向日葵(二)》中“暗自接近”與“深刻別離”“在潰散、在集結”;《別樣的方法》中“要么永遠背棄”與“要么立刻緘默”,這些對立詞語或表示人可擁有的雙向選擇,或是運用反襯手法,突出所描寫的對象與主題。或通過描寫選擇的猶豫彷徨來表達內心的掙扎與痛苦。除動詞外,也有名詞的對立,如《致安德魯·懷斯》中的“果實中最堅硬的內核”與“一張凌駕了卻又空無所有的無邊的網”,用堅硬實在與輕盈無邊來形容某一共同體,既從不同方面表現出共同體的特有價值,也加深了讀者對這一共同體的理解。在單層對立之外,一些詩句中也蘊涵著多層對立。在《黃昏》這首小詩之中,既有著浮現于詩歌表層的忙碌與疲倦的對立——“日出我忙于行走、忙于勞作”與“現在,很疲倦,我搖搖晃晃”,也有著更為深層的精神與肉體、期待與現實的對立。溫恕在詩歌創作中常常將相反或相對的詞語置于同一天平的兩端,雖看似矛盾,卻能夠將事物表現得更為完善深入,讀者讀來不能不被其超凡的聯想能力、深厚的文學功底以及獨到的目光所折服。作者雖頻繁使用對立詞語,卻并未破壞詩歌自身邏輯與完整性,加之其他藝術手法的運用,詩歌整體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和諧之感。藝術手法的運用其中之一便是結構的勻稱,如《跟隨春天》以“跟隨春天、擊碎夏天、訴說秋天、孕育冬天”作為每一段詩節的開篇,既著重點出了詩歌的分層結構,也令詩歌讀來節奏鮮明、朗朗上口,加之各段詩節篇幅相當,特色鮮明,不可或缺,全詩便形成一種擁有著內在張力的和諧。在《黃昏》中,“期待的畫面”與“現實的處境”兩段詩節著墨相當,平分秋色,同樣是這一手法的體現。形成和諧之感的另一因素便是頂針手法的運用。在《是否有過那么一天》中,“大海的心臟永遠不變”“當群山駛過瘋狂的夏天”以及“直到喧囂的時辰終止”等詩句既是上一段詩節的結尾,也是下一段詩節的開篇,不僅起到了推動詩歌主題層層深入的作用,也使得密切聯系的詩節之間環環相扣,全詩形成整齊的句子結構。整體和諧包容著部分對立,部分對立反而造就了別樣的和諧,就這樣,和諧與對立在溫恕的詩歌中相輔相成、共生共存,為其詩歌贏得了獨特的光彩。
溫恕的詩歌創作,想象天馬行空,文思汪洋恣肆。相較于平淡的詞語,他在詩歌中更偏愛于選用那些具有強烈表現效果的詞語,并令其承載著自己全部情感與思索的重量。名詞如“遙遠的風暴”“可怕的戰栗”“碎裂的血肉”“喧囂的時辰”“遍地驚魂”等,這類冷色調詞語的頻繁使用為其詩歌披上了一層冷峻與悲涼的色彩;動詞如“轟然突破”“驟然消失”“倏忽即至”“奔突四散”“勇敢焚燒”等,這些詞語不僅使詩歌表層詞句間充盈著跳動的力量,似乎也在詩歌深層積蓄著能量,以期在適當的時候噴薄而出,震撼人心;形容詞的恰切、精當使用既加深了詩歌內容的深廣度,有時也在其中氤氳升騰起作者的期許與希冀。濃墨重彩的詞語地大量使用,既標明、調節著詩歌的段落、節奏,也使得詩歌整體風格更為激蕩、悲壯。
以己觀物、物我靈犀相通似乎是詩人的特長。溫恕在創作時也非常擅長將自我屬性與情感移植于自然和其他事物,因此,其詩歌中蓬勃的各種無生命的事物如同人類一樣有情思有感喟,能獨立思考,有鮮明個性,并遵從其自身意志采取行動。
在寫作于1987年10月13日的《聲音》中,他寫道:
沉寂的秋天降臨窗外
我熟悉了這種遷移
像夏天的光輝驟然消失
他們很難再次歸來
他們要繼續夢游他鄉
在漸漸昏暗的光線中
我看見這些去年的家具
多舛的書本遺世獨立
我還會不會一如既往
潮濕而微弱的空氣啊
請讓我凝神傾聽
一種聲音帶我遠去
作者將夏末初秋的季節轉換看作夏天將要離開此地的一場出游,夏天這一季節在作者筆下成了鮮活靈動的生命體,作者把用來形容超凡脫俗意境的“遺世獨立”一詞用于形容“多舛的書本”,昏暗的光線、去年的家具,寂靜、冷清的環境氛圍更有力地凸顯了“聲音”這一主題。夏天的光輝選擇夢游他鄉,家具與書本選擇繼續遺世獨立,視角隨之轉移到了“我”的身上,“他人”的選擇有遠方,也有當下,那么在見證“他人”做出選擇后,“我”還會不會以一種一如既往的姿態來繼續存在?在作者筆下,萬物被賦予靈性、精神與情感體驗,與不同詩歌各自的獨特基調融合在一體,孕育在詩歌中的生命力如一條涓涓細流緩緩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