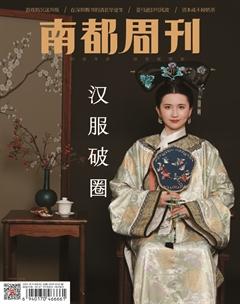“讀了這個熱門專業后,我卻發現是天坑”
詹丹晴
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你還會報考大學那個專業嗎?
近日,武漢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鄧紅兵為“天坑專業”正名,呼吁“高等教育不是教我們謀生,而是教我們創造生活”,很多網友對此并不買賬。
所謂的“天坑專業”,指的是生物、化學、環境、材料專業,因為學習難度大、就業缺乏競爭力得此戲稱。網友們指責鄧紅兵,“站著說話不腰疼”。
除了“生化環材”,一些被視為香餑餑的熱門專業,有人讀了同樣后悔。
高考后,社區網站豆瓣上幾個“大學后悔學xx專業”小組變得異常活躍,按照小組人數排名,后悔學法學、會計學的小組人數最多。他們在枯燥的法律條文、會計公式泥沼里掙扎,看著灰蒙蒙的職業前景,悔不當初。
那些自認為讀了“天坑“專業的人,當初為何會報考,后來又怎么樣了?南都周刊試著找到其中一些人。
名牌大學畢業變身打雜的律師助理
2009年,陳曉敏如愿被錄取為廣東一所211院校的法學專業本科生。
這是她填報的第一志愿,更準確地說,是她母親的第一志愿。
母親覺得,丈夫那在某省檢察廳當檢察長的同學和他那擔任法官的妻子,是活得最成功的典范。她希望女兒以后也能有這樣一份體面的工作。
陳曉敏并不抗拒,她對法學有過天真的想象。她以為學了法學,就會像電視劇里演的那樣,變成光鮮的律師、體面的公務員或者是站在鏡頭前的法制記者。
法學一直是高考考生報考的熱門專業。根據中國教育網的報考指數,2021年,法學專業在所有專業中人氣排名第8,位列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之后。法學專業也在不斷擴招。1977年,我國只有3所大學開設法學專業;到了2020年,這一數字變為619所。
而且,陳曉敏發現, 學法學性價比不高,“法學很難學,就業競爭激烈。
想要學好,并且把知識變現, 過好自己的生活, 難上加難。”
但事實是,陳曉敏開始修讀法學時就后悔了。她很快就因為法條的繁瑣、現實案例的豐富以及法條和現實間的盤根錯節而倍感折磨。
而且,陳曉敏發現,學法學性價比不高,“法學很難學,就業競爭激烈。想要學好,并且把知識變現,過好自己的生活,難上加難。”
這也是“大學后悔學法學”小組成員最沮喪的地方——法學就業口狹窄。
法學畢業生的就業方向一般有律所、司法機構、企業法務部。僧多粥少的司法機構不好考,想要成為光鮮亮麗的律師也沒有那么容易。
要拿到律師執業證、獨立代理案件要闖很多關,最難的是要通過司法考試,還要在律師事務所實習一年。整個周期最快也要一年半將近兩年。
除非是名牌律所,在這不算短的時間里,畢業生們連養活自己都很困難。
“每個月2000元。”在廣州某檢察院工作的陳悠米回憶起8年前當律師助理拿到的工資。但8年過去了,律師助理的待遇并沒有得到多大改善。南都周刊從招聘網站了解到,以廣州為例,律師助理每個月的薪酬多在3000-6000元之間,上萬元的很少。
在薪資待遇不如意的實習期,很多人連律師真正的工作都摸不到邊。陳悠米就告訴南都周刊,“我當時跟的律師不是很容易信任人,凡事喜歡親力親為。我做的事會比較瑣碎,比如把律師手寫的文書打印進電腦文檔、跟當事人見面、跑法院、去立案,主要是打下手。”
“有些律師害怕被搶飯碗,不愿意傳授職業技巧,導致很多律師助理都在打雜。”在上海一家律所工作了10年的奚海麟告訴南都周刊,“但是如果實習不滿一年就拿不到執業證,這由不得你。如果想做律師,就要接受前幾年都要‘啃老的現實,還要熬得下去。”
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李莉就不想去律所,比起待遇低、工作強度大,更主要是因為通過實習真正接觸這一行后,她明白自己不適合。
“在律所,能說會道的實習生很受歡迎,我也很羨慕這種能夠在很多人之間游刃有余的人,但我自己就是做不到。”李莉稱,“有時候給帶教老師發消息,三行的消息我能琢磨10分鐘,害怕用詞有誤。想到以后做訴訟律師要開庭、做非訴律師要不停熬夜就覺得很痛苦。”
奚海麟介紹稱,“大多數律師的執業狀態都是單兵作戰,從銷售到售后,一個人包圓了。除了專業能力外,律師非常看重經驗、開拓資源能力和情商。”
李莉很后悔當初的選擇,“性格對于法學專業真的很重要,不擅長溝通交流的人要遠離法學,不然會很痛苦。”
陳曉敏就沒有考慮過做律師,她覺得“在廣州,律師助理的收入還不如餐廳服務員”,她也不向往司法系統,“基層工作人員的工作量相當多,壓力也大,性價比不高。”
對后面這一點,陳悠米則深有體會。去檢察院工作幾年,她幾乎沒有試過準點下班,經常要加班到晚上9點甚至更晚,除了辦案外,她還要兼顧一些行政性的工作。
熱門專業變冷門
如果考生報考法學時或多或少被它正義的光環吸引,那報考會計學的考生更加直接,是為了畢業后好就業。
每日在題海里奮戰的考生對專業前景又有多少認識呢?
許寬是一名小鎮做題家,高考后,他考慮過修讀上海交通大學的經濟學專業,但是,老師和父母認為經濟學比較寬泛,不如會計來得實際。
許寬不懂。在貧窮的縣城里信息閉塞,忙于備考的他對大學專業、行業前景幾乎一無所知。他聽從長輩們的建議,報考了一所財經類大學的會計學專業。
畢業于某985院校的王萌會選擇會計,則是因為高三時家里經濟出了點問題,想著要早點出來工作、減輕家庭負擔,而會計則被家里長輩視為好就業的專業。
但是,曾經被視為“好就業”的會計專業,如今收入卻很難跟游戲策劃、計算機編程等相比。好就業的專業隨著產業變遷在不斷更迭。
數據管理咨詢機構麥可思發布的《中國2010屆、2019屆大學畢業生培養質量跟蹤評價》顯示,2010年畢業本科生月收入排名前五的是互聯網開發員、財務分析員、管理咨詢師、信貸經紀人和個人理財顧問。到了2019年,排名前五的是游戲策劃員、互聯網開發員、網絡設計員、計算機程序員、計算機系統軟件工程技術人員。
根據麥可思研究院的數據,2010年本科生畢業后薪資最高的行業是金融、銀行、保險、證券業,到了2019年則是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指出,“從現實的供求關系來看,經管類專業其實已經屬于人才培養供給超過社會需求的‘冷門專業。盲目追求所謂的‘熱門,反而會掉進‘冷門的坑里。”
今年5月,網易數讀統計了微博上與“專業勸退”有關的話題,在“專業勸退”榜單上,會計學排名第一。
上大學前,王萌只聽說會計好就業,卻不曾想,好就業不意味著待遇好。她所在的新一線城市,企業掛出來的會計崗招聘啟事經常是這樣的:要求工作經驗5年以上,擁有cpa(會計注冊師)證書,月薪7000-9000元。
王萌透露,有同班同學寧愿去當銷售也不愿意做會計,同樣是辛苦和有壓力,銷售待遇會好一些,“業績好時,銷售崗一個月能拿2萬元,會計的月薪則不到8000元。”
2021年6月,東方數字財稅研究院發布的《稅務會計人才發展白皮書》顯示,稅務會計從業人員中基層員工數量較多,整體薪資較低,有59.4%的從業人員年薪在8萬元以下。
許寬并不討厭學會計,但真正從事相關工作后,他對會計的厭惡與日俱增。
“財務工作需要花費很大精力去核對數據、整理憑證,確保每個數字、每個小數點沒有差錯,可是這種費勁的過程不會給我帶來多少成就感,每次做完月報、季報、年報只會有一種解脫的感覺,領導也很少認同我的工作。”許寬告訴南都周刊。
從事財務工作后,許寬基本告別了元旦、清明、國慶等假期,別人在休息玩樂時,他在加班加點編寫企業的財務季報、年報。
在豆瓣上,“大學后悔學會計”的小組人數有21501人,僅次于后悔學法學小組。人們后悔的點主要在于會計門檻低、工作枯燥、天花板低、沒有就業前景。
“會計是最不需要高學歷的崗位之一。會計瑣碎、知識量大,本身難度不算大。用人單位更關注應聘者的實操能力經驗和證書,而這方面只要大專生努力就不比我們差”。王萌說道,“我們還會被用人單位反向歧視,他們覺得學歷差一點的候選人穩定性更好、成本更低。”
“就像凱恩斯的那句名言:‘從長期看,我們都將死去。會計行業的飽和及易替代性就意味著它未來總體悲觀。”許寬補充道。
把他們推向困境的手
南都周刊在跟十幾位畢業生交流后發現,這些后悔大學修讀某門專業的學生,當年高考后幾乎都是依據長輩建議填報志愿的。
在熊丙奇看來,這些遺憾本可以避免。“我國基礎教育階段,不少學校不重視對學生興趣的培養。新高考改革的出發點,就是讓學生根據興趣選科、發展興趣,可這依舊被功利對待,很多學校仍然只抓應試。等到填報志愿時,能夠明確說出自己的專業興趣的學生很少。”
事實上,在國外,針對學生興趣、能力等的認識、引導早被納入教育系統。1971年,時任美國教育署署長的西德尼·馬蘭正式提出“職業生涯教育”概念。1989年,美國《國家職業生涯發展指導方針》提倡要從6歲開始生涯規劃。英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家也有很成熟的做法。
“生涯規劃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導學生認識自我,分析自己所處的環境,確定適合自己的發展目標,并制定計劃去完成、實現。我國已要求高中進行生涯教育,大學把就業指導作為必修課,但真正重視的學校和學生不多。”熊丙奇告訴南都周刊。
這種教育的缺失,使得少數有自己興趣的學生無法明確自己的選擇,在對專業就業前景一知半解的情況下,他們最后很容易聽信長輩的意見。
在“大學后悔學會計”小組,一位叫“x柴”的網友就發帖稱:“我真應該遵從我心愿學歷史專業……但是爸爸覺得我學歷史沒發展,高中稀里糊涂學理科,理科學得稀爛,高考分高不成低不就,稀里糊涂學財務,結果會計越來越卷,根本不是越老越吃香。”
在“大學后悔學商科”小組里,一位名為“釘某野薔薇”的網友發帖稱,“我更喜歡建筑學或者園藝相關的專業,但是被家里人勸說,工地根本不需要女生……”
熊丙奇指出,“對于那些迷茫的學生而言,職業生涯教育是必須補上的一課,要認真思考自己究竟適合干什么、怎么去改變。每個人的路是不一樣的,要有自己的人生發展規劃。”
除此之外,還有這樣一些人,本來是不討厭自己修讀的專業的,甚至報讀的就是感興趣的專業,但在就業過程中后悔情緒不斷滋長。
在“大學后悔學小語種”小組里,有網友發帖詢問,“如果論愛好,大家會選什么語種學。”點贊數最多的答案是:“計算機語言。”
這一定程度道出了現在就業市場的真相——信息技術類專業才是香餑餑。明明他們當年同樣是高分考進的專業,最后就業時卻只能望著別人的高薪哀嘆。
彷徨、轉型、和解
王萌想要逃離會計行業。在校時她考慮過轉化學專業,不被家里人支持,畢業后她花了兩年時間考研,想要換道到哲學專業,但沒有成功。
7月5日,王萌去了一家國企的會計部門報到,開始上班。自從學了會計后,她感覺人生處于一種停滯和倒退的狀態。眼下,她正在吃藥對抗抑郁癥。
許寬剛剛從房企辦理了離職手續,他準備參加公務員考試,逃離會計崗位。
許寬勸報考會計的考生要想清楚,要了解會計的就業前景。“如果真的要讀,一定要和別的專業結合。比如會計+python、會計+金融等等。會計就業范圍很廣,但如果想要有一個比較好的結果,一定要和別的技能相結合,提高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后悔報讀法學的李莉才剛剛大三,在人大法學院上進、狂熱的氣氛烘托下,不參加模擬法庭、不參加辯論賽、不加入學生會的她,在整個專業里顯得格格不入。
“周圍同學對法學的熱愛,對我而言,更像是一種可悲的諷刺。”李莉說。李莉還在等,等待兩年后通過考取研究生、修讀中文專業,脫離苦海。
剛上大一就后悔讀法學的陳曉敏,大學四年都沒有認真聽課,就連對法學生最為重要的司法考試,她都隨便應付,結果自然沒有通過。直到第二次備戰司考,陳曉敏花了三四個月時間認真備考后,才真正感受到了法學的魅力。
熊丙奇指出, 對于那些迷茫的學生而言, 職業生涯教育是必須補上的一課, 要認真思考自己究竟適合干什么, 怎么去改變。
每個人的路是不一樣的,要有自己的人生發展規劃。”
陳曉敏不討厭法學了,但也不向往法律行業、司法系統的工作。
那些后悔讀了某些專業的人,沒辦法坐時光穿梭機回到過去,再做一次選擇,但他們中也有一些人,正在積極地尋求改變,與過去的自己和解。
畢業后,陳曉敏在二線城市一檢察院工作了一段時間。再后來,她去佛山開了一家咖啡館,實現文藝青年的夢想。
陳曉敏那些后悔學法學的情緒早已釋懷,“我是那種適合經營生活的人,種種花、做做美食比較適合我。雖然我沒有從事法律相關的工作,但法學其實很有趣。法律獨特的邏輯思維,看待社會、歷史問題的角度,都令我在學習其他東西時得到不少啟示。”
像陳曉敏一樣,因為后悔而轉行的人并不少。在豆瓣,有不少“過來人”傳授經驗,例如在大學時期讀多個第二學位,有讀工商管理的第二專業是法學專業,也有有討厭小語種的人轉去學會計;畢業后厭惡會計的畢業生轉行做了新媒體運營,也有不喜歡法學的人轉行當記者。
如果還有一次選擇的機會,陳曉敏不會讀法學,她會遵從內心報考文學、心理學專業。
但是,陳曉敏也沒有覺得選了法學就很可惜,“我學的東西都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我的生活里。人生沒有什么東西是白學的。”
(應受訪者要求,李莉、陳悠米、許寬、王萌為化名)
編輯_林意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