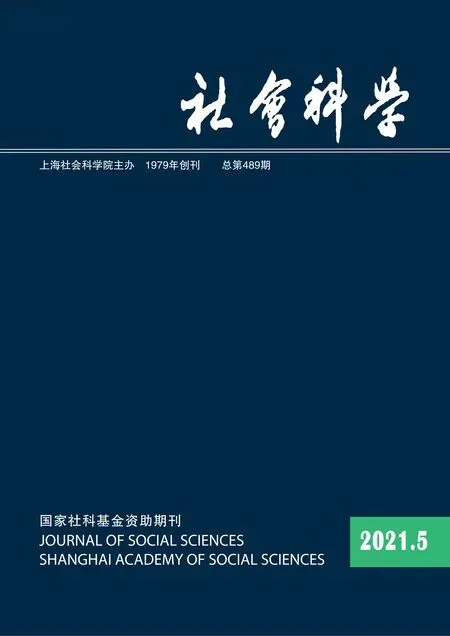全球價值鏈治理、政府能力與中國國際經濟權力提升*
劉洪鐘
當今世界,國際權力正在自西向東、由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快速擴散與轉移。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大國的崛起,冷戰后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世界開始受到挑戰,多極化趨勢不斷加強。在這場大變革中,中國國際權力的快速提升具有尤其深遠的歷史意義(1)不過,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變化并非是國際體系中的“權力轉移”,而只是有限的“權力變遷”(power shift)。參見江憶恩、陳喜娜《中國崛起:對概念運用的探討》,載王緝思主編《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1》,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版,第70-88頁;Chen Dongjin, “Examining the Rising Dragon:A Review of Foreign Affairs and Foreign Policy’s Article on China in 2008”, 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Vol.1, No.4, 2009。。根據英國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CEBR)的估計,2028年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CEBR, “World Economic League Table 2021: A World Economic League Table with Forecasts for 193 Countries to 2035”,https://cebrcom/service/macroeconomic-forecasting, 2021-01-11.。果真如此,那將意味著一個多世紀之后世界經濟的領頭羊將不再是美國。二戰之后,蘇聯和日本的經濟總量曾先后接近過美國,但最終都功虧一簣,隨后陷入“大國趕超陷阱”(3)張宇燕:《跨越“大國趕超陷阱”》,《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1期。。當今的中國經濟也正在沿著趕超的路徑持續增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是否能夠跨越“陷阱”并順利實現國際經濟權力的躍升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經成為國內外諸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關心的核心命題。本文希望基于全球價值鏈治理這一全新的視角對上述問題展開討論,并詳細分析中國前行道路上的重要優勢、主要障礙以及突圍方略。
一、全球價值鏈時代的經濟權力與現實悖論
(一)經濟權力轉移
所謂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通常是指由于國家實力發展不平衡而導致的國際權力結構中原有主導大國地位下降、后崛起大國地位上升并逐漸獲得主導大國權力的變化過程(4)朱鋒、[美]羅伯特·羅斯主編:《中國崛起:理論與政策的視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權力轉移可以從多個視角來觀察,其中經濟權力轉移是最重要的維度,因為它是大國間政治、軍事等權力變化的基礎(5)[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陳景彪等譯,國際文化傳播公司2006年版,第35頁。。從權力的內涵引申開來,經濟權力一般是指在國家間政治經濟交往與互動過程中,一國運用自身經濟實力,使用經濟或金融政策手段,通過使用或威脅使用打擊、給予或承諾給予好處的方法從經濟上削弱或增強他國,強迫他國改變意志從而使自身獲益的能力(6)Klaus Knorr, The Power of Nation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79; 轉引自常璐璐、陳志敏《吸引性經濟權力在中國外交中的運用》,《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與軍事權力通常被認為是銳利權力(sharp power)不同,經濟權力一般被認為是一種粘性權力(sticky power),它包含一系列經濟制度和政策以吸引他者進入,進而將其困在其中(7)Walter Russell Mead, “America’s Sticky Power”, Foreign Policy, No.141, 2004; 轉引自常璐璐、陳志敏《吸引性經濟權力在中國外交中的運用》,《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這種經濟權力往往與雙方在國際利益博弈中不對稱的相互依存所造成的不對等地位有關。經濟權力的基礎是經濟實力(8)達巍:《從權力的“三張面孔”看美國的地位走勢》,《現代國際關系》2010年第2期。,盡管二者并不直接相等,但經濟實力是一國經濟和政治權力的主要支撐,因此可以轉化為經濟權力而在外交中使用(9)常璐璐、陳志敏:《吸引性經濟權力在中國外交中的運用》,《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學者們通常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它被認為是關鍵的“旗艦指標”(10)Michael Beckley, “The Power of Nations: Measuring What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3, No.2, 2018.。
經濟權力既具有宏觀特征,體現為一國經濟總量增加而帶來的政治和軍事能力的提升,也具有微觀屬性,表現為該國企業競爭力的增強而形成的迫使他國企業按照本國意愿采取某項行動的能力,比如,在全球價值鏈治理中本國企業由于產業升級而形成的討價還價、議程設置等能力的提高。就目前而言,對于經濟權力的微觀屬性,國內外學者們仍然關注較少。
(二)全球價值鏈治理與經濟權力分配:發達國家的優勢
通過重塑生產與貿易,全球化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國際競爭時代(11)Gary Gereffi最早用全球商品鏈這一概念來分析國際貿易和生產網絡的重組。此后,學者們多用全球供應鏈來進行分析。自21世紀初以來,全球價值鏈(GVC)和全球生產網絡(GPN)概念作為分析當代供應鏈的國際擴張和地理碎片化的方法開始受到普遍歡迎。在本文,如果不是特別說明,我們使用全球價值鏈來泛指全球商品鏈、全球供應鏈和全球生產網絡。參見Gary Gereffi,John Humphrey,Raphael Kaplinsky and Timothy Sturgeon, “Introduction: Globalisation,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 IDS Bulletin, Vol.32, No.3, 2001;Peter Dicken,“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The Automobile Components Industries”, GPN Working Paper No.7, 2003, http://hummedia.manchester.ac.uk/schools/seed/geography/research/workingpapers/gpn/gpnwp7.pdf, 2021-01-11;Jeffrey Henderson, Peter Dicken, Martin Hess, Neil Coe and Henry Wai-Chung Yeu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9, No.3, 2002。。在各類產業全球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全球價值鏈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的支柱和中樞神經系統”(12)Olivier Cattaneo, Gary Gereffi and Cornelia Staritz,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Crisis World: Resilience, Consolidation and Shifting End Markets”, in Olivier Cattaneo, Gary Gereffi and Cornelia Staritz(eds.),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Crisis World: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0, p.7.。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的估計,目前全球80%左右的貿易是通過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進行的(13)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Geneva, 2013, p.135.。
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是本文分析的核心和重點。全球價值鏈治理可以被定義為在價值鏈上形成包容或排斥門檻以及參與模式的行動、制度和規范,這些行動、制度和規范反過來又決定了價值的增值、分配、獲取條件及區位(14)Mark P.Dallas, Stefano Ponte and Timothy J.Sturgeon, “Power in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6, No.4, 2019.。它展示了企業權力如何影響一個行業的利潤分配和風險分擔,并確定了行使這種權力的行為體(15)Gary Gereffi,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1, No.1,2014.。在全球價值鏈治理過程中,權力主要被主導企業所擁有,它們有能力調動和利用自身與其他企業之間不對稱的權力關系,來決定整個價值鏈生產過程中價值創造的模式、地點、時間以及最終的價值在不同行為體之間的分配(16)Nicola Phillips, “Power and Inequalit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3, No.2, 2017.。這些主導企業通常都是來自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它們既可以是生產商,也可以是采購商。
參與全球價值鏈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提供了獲取知識、市場和其他有價值的競爭性資產的途徑(17)Daria Taglioni and Deborah Winkler, Making Global Value Chains Work for Development, Trade and Development Ser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6, pp.11-13.。它們可以通過成為發達國家大型企業的供應商而進入由這些主導企業所控制的全球市場。然而,后起國家企業的權力往往受到極大限制,因為主導企業有能力通過采取不同類型的治理模式和設定參與供應鏈的條件對其形成制約(18)Marion Werner, Jennifer Bair and Victor Ramiro Fernández, “Linking Up to Development?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Making of a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45, No.6, 2014.。比如一項有關東亞汽車產業價值鏈的研究就發現,后起國家的企業要想進入該生產網絡,必須向主導企業開放其財務報表。主導企業權力大小通常取決于它們制定的各類條款(19)John Humphrey and Hubert Schmitz,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Regional Studies, Vol.36, No.9, 2002.。此外,這些主導企業還能夠利用其技術壟斷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在技術設計、生產工藝、營銷網絡等方面設置障礙,阻止東道國企業的技術汲取,進而將后起國家的企業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主導企業與非主導參與者之間的不平等權力導致了全球價值鏈上價值分配的不公平(20)Nicola Phillips, “Power and Inequalit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3, No.2, 2017.。以2010年蘋果手機生產為例,在整個生產過程中,超過一半增加值都被蘋果公司作為利潤獲取,而流向中國的利潤則微不足道(21)Kenneth L.Kraemer, Greg Linden and Jason Dedrick, “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 Apple’s iPad and iPhon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5187229_Capturing_Value_in_Global_Networks_Apple%27s_iPad_and_iPhone, 2020-06-14.。該結果的產生根源于蘋果公司能夠利用自身的權力設施等多種條件以迫使供應商形成激烈的競爭,并攫取了價值鏈上大部分的價值(22)Nicola Phillips, “Power and Inequalit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3, No.2, 2017.。
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全球價值鏈上對權力的俘獲既是企業在全球競爭中依靠資金、技術和管理優勢而勝出的結果,也是各國政策支持的產物。它們通過各種貿易、稅收、競爭政策等,與本國跨國公司通過全球價值鏈的構建與治理,共同獲得了主導性的國際經濟權力(23)Sklair使用“跨國資產階級”來形容這一松散的聯盟,認為他們主要由高級管理人員、專業人員、學者和國家官員組成,他們共享一種意識形態。Gill則用“跨國歷史集團”來描述這一壟斷聯盟,認為其核心主要由七國集團的國家機構和跨國資本以及與之相關的部分特權工人和小企業組成。參見L.Sklair,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Political Actor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3, No.2, 1998; Stephen Gill, “Globalisation, Market Civilisation, 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 Mille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4, No.3, 1995。。以美國為例,從1890年通過第一個反托拉斯法——《謝爾曼反托拉斯法》開始,美國政府就一直對國內大型壟斷企業的經濟權力保持高度警惕,然而,國外則是另一番情形:只要不影響美國國內市場,本國跨國公司在境外采取聯合行動獲取壟斷地位通常都會得到政府的默許(24)[英]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楊宇光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20世紀80年代以后,美歐發達國家政府以“新自由主義”為口號,在全球推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以此打開新興市場的大門。當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為吸引FDI而普遍采取寬松的競爭政策和對領先企業的市場勢力采取更大的政治容忍時,全球財富日益集中到西方國家的少數寡頭企業手中就成了一種普遍現象(25)比如1992年最大的300家跨國公司控制了世界20萬億生產性資產存量的25%,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的全球銷售額達到5.5萬億美元,幾乎與美國的GNP相當。1992年全球商品和服務出口額大約是4萬億美元,其中1/3都是在跨國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間進行的。參見Nicola Phillips, “Power and Inequalit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3, No.2, 2017; Stephen Gill, “Globalisation, Market Civilisation, 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Mille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4, No.3, 1995。。這種經濟權力的分化構成了全球政治經濟不平等的核心特征。
(三)后起大國的“經濟趕超悖論”
在理論層面上,經濟權力失衡的全球價值鏈體系將使發展中國家永遠無法趕超發達國家,而只能保持“雁型”的狀態跟隨。但現實情況是,近三十年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通過加入全球價值鏈,推動了本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和國際經濟權力的不斷提升,尤其中國經濟的崛起所帶來的經濟權力的轉移更是無法用上述理論進行解釋。
快速崛起的中國是當今世界權力擴散與轉移的一個重要案例。在全球化迅速發展的背景下,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采取與西方國家隔離的發展戰略,而是實施了大膽的現代化和全球化戰略(26)[美]布蘭德利·沃馬克、林民旺:《中國崛起與美國:權力持平與文明的磨合》,《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7年第6期。。中國通過融入世界經濟而與東亞及西方國家構建起了復雜的生產網絡。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抓住時機積極參與全球分工,從簡單的低端加工開始,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產業聚集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逐步從全球產業鏈的低端成長為東亞區域生產網絡乃至全球價值鏈的中樞,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權力也隨之不斷提升。
中國及其他新興經濟體借助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崛起似乎形成了如下悖論:在全球價值鏈的總體價值分配中,來自發達國家的主導企業勢必攫取更大的份額,同時利用規則、條款等方式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鎖定在低端位置。然而,現實卻是全球價值鏈已經成為新興經濟體崛起的重要渠道。在學術視域下我們應當如何解釋這一悖論?進一步,全球價值鏈縮小新興大國(中國)與守成大國(美國)經濟權力差距的機制有哪些?此外,面對相同的歷史機遇,不同國家的命運也呈現出鮮明的對比:在東亞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實力不斷提升的同時,拉美國家卻為何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非洲國家則持續迷失在世界經濟的邊緣。對于這些重要的現實問題,學術界目前仍然缺乏系統性研究和邏輯自洽的分析框架。接下來本文將以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治理下的地位變化為視角,通過討論政府能力在這一變化過程中的作用,分析未來中國經濟權力變遷的前景與約束。
二、政府能力與后起國家的全球價值鏈治理參與:一個解釋框架
(一)后發優勢:內涵與特征變化
“后發優勢”理論最早是由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的,他通過對俄國、德國、意大利等國經濟追趕的歷史研究,探討了相對落后國家如何利用“落后的優勢”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實現經濟趕超的經驗(27)參見[美]亞歷山大·格申克龍《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張鳳林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林毅夫指出,一國經濟增長潛力取決于生產要素、產業結構和技術創新等三個主要條件,三者當中,技術創新最重要。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技術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水平與發達國家有差距,可以利用這個技術差距,通過引進技術的方式,來加速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變遷,從而使經濟發展得更快(28)林毅夫:《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經濟學(季刊)》2003年第4期。。后發優勢具有多維性,不但包括技術的后發優勢,而且還包括資本、人力、制度以及結構的后發優勢。充分發揮上述優勢,后起國家就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羅斯托所說的經濟起飛(29)郭熙保、胡漢昌:《后發優勢研究述評》,《山東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郭熙保、胡漢昌:《后發優勢新論——兼論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后發優勢論為后起國家實現經濟趕超提供了“理想的范本”,并且理論上后起國家的相對落后程度越高,與發達國家經濟收斂的速度也將越快。然而,這種思路容易給人造成一種假象,即發達國家的今天就是后起國家的明天,只要發展中國家沿襲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通過技術和制度模仿,就能以更快的速度實現經濟的趨同。但事實證明,起點基本相同的諸多后起國家(比如拉美國家和東亞國家,前者在自然資源、資本、人口壓力等方面甚至優于后者),在開放的背景下結局卻相去甚遠,拉美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后就再也沒有重啟經濟繁榮,而東亞國家則形成了“四小龍”追趕日本、東盟和中國追趕“四小龍”的“多層次趕超”動態空間格局(30)轉引自劉洪鐘、崔巖、佟蒼松《東亞轉型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頁。。
筆者認為,導致上述后發優勢理論無法解釋東亞與拉美國家趕超結果差異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忽視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分工的重大變化對后起國家趕超方式和政府作用形式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使得傳統以技術模仿和產業結構模仿為基礎的后發優勢無法得到有效發揮。新的以全球價值鏈為主要特征的國際分工形態,要求我們超越簡單地以國家作為生產和貿易分析單位的研究范式,在一個由全球價值鏈推動的一體化全球經濟中,將國家與企業、國內和國外相結合,重新思考后起國家的后發優勢及現實約束,進而在此基礎上分析其經濟發展與趕超的戰略選擇。
全球價值鏈的構建是以全球產業的多樣性為前提,產業是后起國家進入全球經濟的主要切入點(31)Gary Gereffi,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1, No.1, 2014.,也為后起國家提供了利用后發優勢追趕發達國家的機會。后起國家可以通過加入全球價值鏈啟動本國的工業化進程,而不需要像工業化前期的意大利、俄國以及二戰后的日本那樣,從零開始在國內建立完整的產業鏈。這些國家可以專注于價值鏈上的特定環節,從而降低工業化發展的門檻和成本。在增加就業的同時,通過技術引進和模仿、“干中學”等,后起國家可以從全球價值鏈上的主導企業獲得專有知識,提高組織管理和市場營銷技能,從而釋放生產潛力,促進整個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上述“捷徑”就構成了全球價值鏈治理下后起國家發揮后發優勢的重要基礎。
然而,潛在的后發優勢并不會自動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觀察拉美和東亞國家趕超的歷史進程,可以發現,從空間距離來看拉美地區離美國和歐洲更近,理論上本應更具區位優勢,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拉美各國雖然融入了全球價值鏈,但基本上淪為西方跨國公司的原料供應地,形成事實上的依附性經濟。與其相反,東亞各國卻在大規模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基礎上,不斷提升本國比較優勢,其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也隨之不斷上升。對于上述差異,丹尼·羅德瑞克(Dani Rodrik)提出,對世界經濟的開放能夠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利益的來源,但這些只是潛在利益,只有當國內存在相應的互補性政策和制度時才能最終實現經濟的騰飛(32)[美]丹尼·羅德瑞克:《讓開放發揮作用:新的全球經濟與發展中國家》,熊賢良等譯,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頁。。為此,政府的作用和能力就顯得尤為關鍵,它們需要有能力采取適當的政策在充分利用全球價值鏈所提供機會的同時,也能有效化解與之相關的風險。
(二)政府能力與后起國家的全球價值鏈治理
20世紀90年代,學術界曾一度出現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所說的“國家的制度中心地位與全球化不相容”的論調,認為在全球化的新世界中,政府會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或至多扮演一種被動的行動者角色,在私人治理無法觸及的角落履行“剩余職能”,通過提供法律和政治基礎為多維的全球治理保駕護航(33)Frederick W.Mayer and Nicola Phillips, “Outsourcing Governance: States and the Politics of a ‘Global Value Chain World’”,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22, No.2, 2017.。在這些學者眼中,東亞奇跡甚至也被描述為是“企業脫嵌”(firm dis-embedding)的結果,即東亞企業“逐漸擺脫政府管制的束縛,重新嵌入由競爭性公司治理的各類全球生產網絡中”(34)H.W.C.Yeung, “Governing the Market in a Globalizing Era: Developmental State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Inter-Firm Dynamics in East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1,No.1, 2014.。
受到上述觀念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有關全球價值鏈治理的研究也忽視政府的角色。大多數學者的研究都集中在價值鏈內部治理形式的多樣性,而非國家行動和政府政策的作用上(35)Shengjun Zhu and John Pickles, “Bring In, Go Up, Go West, Go Out: Upgrading, Regioalisation and Delocalisation in China’s Apparel Production Net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44, No.1, 2014.。即使有些研究關注政府的作用,通常也都將其視為“外部”因素,主要討論貿易政策如配額、關稅和自由貿易協定等相關問題(36)Rory Horner, “Beyond Facilitator? State Rol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eography Compass, Vol.11, No.2, 2017.。近年來隨著學界對全球生產網絡關注度的提高,政府作用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37)Neil M.Coe, Peter Dicken and Martin Hes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8, No.3, 2008; Rory Horner, “Beyond Facilitator? State Rol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eography Compass, Vol.11, No.2, 2017; Julia Tijaja and Mohammad Faisal, “Industrial Policy in Indonesia: A Global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411, 2014.。新的研究表明,國家政策、制度和政治環境對一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成功至關重要(38)Victor Kummritz, Daria Taglioni, and Deborah Winkler, “Economic Upgrading Through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Which Policies Increase the Value Added Gain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8007, World Bank Group,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6348/WPS8007.pdf?sequence=1&isAllowed=y, pp.1-45, 2021-01-10.。加里·格里菲(Gary Gereffi)和弗雷德里克·梅耶(Frederick W.Mayer)最早分析了政府通過制定和實施國家政策來充當全球價值鏈推動者和監管者的作用,他們認為政府政策有助于價值鏈的平穩,監管活動則旨在限制市場交易的負外部性(39)Gary Gereffi and Frederick W.May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Governance”, in Gary Gereffi (ed.), The New Offshoring of Job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2006, pp.39-58.。后來有學者將這些政策進一步細化為三類:經濟層面的“水平”政策,特定產業的“選擇性”或“垂直”政策,以及全球價值鏈導向的政策,即利用國際聯系向價值鏈上更高價值的方向轉移(40)Gary Gereffi and Timothy Sturgeo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ndustrial Policy: the Role of Emerging Economies”, in D.Elms and P.Low (ed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Changing World,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3, pp.329-360.。
沿著上述邏輯,從促進本國經濟融入全球價值鏈并不斷提升地位的角度,后起國家政府可以通過三種方式實現本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后發優勢,如果該國同時又是一個大國,則額外還具有作為潛在最終消費市場的優勢。
1.積極推動本國企業和經濟融入全球價值鏈。融入全球價值鏈是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全球分工推進本國工業化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政府可以從兩個方面發揮促進作用:一是創造條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二是采取有效政策支持本地企業參與到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當中(41)Rory Horner, “Beyond Facilitator? State Rol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eography Compass, Vol.11, No.2, 2017.。
低工資通常是落后國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和進入全球價值鏈的最主要優勢,但如果缺乏配套和完善的有形或無形基礎設施,勞動力成本優勢就很難體現出來。因此,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匹配措施,如提升基礎設施質量、外資促進與保護、職業培訓等。隨著本國企業逐步加入全球價值鏈,隨后的政策考慮就必須確保全球價值鏈盡可能融入國內經濟。盡管全球價值鏈敞開了大門,但是它們并沒有魔力。大部分關鍵性的工作仍然需要在國內完成,包括支持投資、提升技能、增加工作、促進增長的改革,否則就無法使全球價值鏈與國內經濟形成緊密聯系,從而也就難以使外國投資企業的技術和專有知識產生更大的擴散效應。為了防止技術外溢或保持技術領先,外國投資者實際上往往缺乏融入國內經濟的動力,為此,政府就需要努力為通過FDI進入本國的外國有形和無形資產創造良好的全球價值鏈連接環境,使得國內勞動力能夠有效地與外國投資相匹配。
2.經濟與技術升級。融入全球價值鏈為發展中國家的本地企業學習發達國家主導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知識提供了機會(42)Elisa Giuliani, Carlo Pietrobelli and Roberta Rabellotti,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clusters”, World Development, Vol.33, No.4, 2005.。通過全球價值鏈體系購買的高質量國際中間投入品而產生的技術和知識擴散,可以刺激下游部門的生產;將與全球價值鏈有關的本地中間產品銷售給國際買家,其對產品質量的高標準要求可能會刺激各上游部門生產力的提高;全球價值鏈的發展還可能通過知識和技術溢出而對當地其他企業產生示范效應。此外,還可以通過勞動力培訓提升人力資本,并通過勞動力市場流動而將內含在勞動力身上的技能和知識轉移到本地其他企業。
但是全球價值鏈仍然由主導企業掌控,它們不愿看到后起國家的經濟升級,更可能通過與后起國家的供應商保持穩定的技術差距,進而形成等級結構。如何突破低端鎖定,就成了后起國家實現價值鏈升級的關鍵。在全球價值鏈框架內,存在著四種類型的經濟升級:一是產品升級,即進入更復雜的產品線,能夠以更高的技術和質量提供超越競爭對手的高附加值產品;二是流程升級,就是通過重組生產系統或引進先進技術,使投入轉化為產出的效率更高;三是功能升級,即通過整合或轉移到更復雜的任務,提高本國在現有全球價值鏈生產過程中的增加值份額;四是鏈的升級,就是企業借助現有產業鏈中的知識和技巧進入新的具有較高增加值份額的產業鏈(43)John Humphrey and Hubert Schmitz,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Regional Studies, Vol.36, No.9, 2002.。
為達到上述四個目標,政府可以通過提升勞動力技能、提高資本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勞動力技能是提升競爭力的關鍵要素,它影響著參與全球價值鏈以及利用全球價值鏈實現本國經濟升級的能力。為此,政府可以通過建立特殊工業園區和培訓基地等方式形成或提升針對特定產業的勞動力技能。比如,新加坡政府通過專門的高等教育項目、有針對性的稅收減免和創建與航空相關的特殊工業園區,成功實現了本國在商用飛機行業的價值鏈深度嵌入和地位提升;同樣,日本政府也通過專門的技術培訓,使得本國制造商在最新的波音787飛機生產所依賴的復合材料領域獲得超越美國的優勢(44)John T.Bowen Jr.,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Asia Pacific Economies in the Commercial Aircraft Industry”,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48, No.3, 2007.。提高資本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則需要提高企業的吸收能力和技術水平。為此,政府可以通過鼓勵引進新技術、加速折舊、產學研合作、研發投入稅收抵扣等方式推動綜合或特定行業的投資,以此保證企業產品質量和企業持續高水平的創新能力。
3.推動創新。與全球價值鏈相關的創新活動大多都是由發達國家的龍頭企業完成的,這也是他們經濟權力產生的一個重要根源。由于后起國家的企業在規模、技術等方面處于劣勢,人們往往懷疑它們的創新能力(45)Tilman Altenburg, Hubert Schmitz, Andreas Stamm, “Breakthrough? China’s and India’s Transition from Production to Innov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36, No.2, 2008.。然而,在現實中,21世紀以來新興市場經濟體開始越來越多地在各個行業發揮領導作用,這意味著后起國家的企業在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同時,能夠通過創新實踐和價值鏈構建轉變為主導企業,最終實現全球價值鏈上經濟權力的逆轉(46)Keun Lee and Franco Malerba, “Catch-up Cycles and Changes in Industrial Leadership: Windows of Opportunity and Responses of Firms and Countries in the Evolution of Sectoral Systems”, Research Policy,Vol.46, No.2, 2017.。
后起國家企業可以從簡單的代工(OEM)開始加入由主導企業控制的全球價值鏈,通過“干中學”獲得相關運營知識和技能。隨著資本的積累和能力的不斷提升,這些企業就可以從簡單的工作(如裝配)中脫身,開始參與生產設計、研發和營銷等,以此通過面向委托設計和制造(ODM)的轉型進而實現價值鏈參與能力的提升。最后,一旦這些企業具備獨立完成生產、設計、營銷、渠道管理和研發的所有能力,他們就可以通過對研發活動的大量投資促進自身技術、產品和工藝的發展和創新,完成向自主品牌制造(OBM)的轉型。這種OEM-ODM-OBM三階段理論常被視為理解后起國家實現全球價值鏈功能升級的關鍵框架(47)Mike Hobday, “Innovation in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A Gerschenkronian Perspective”,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1, No.3, 2003.。
然而,實現上述升級,尤其是從ODM向OBM的“驚險一躍”卻是極其困難的。首先是較高的進入門檻。與早期英國與葡萄牙之間“羊毛-葡萄酒”式的分工與貿易模式相比,如今在許多產業中,由于在位企業具有先發優勢,任何新進入者都必須在相似的初始規模起步,這需要大規模的前期投資,同時還需要擁有高效經銷商和支持網絡(48)[美]拉爾夫·戈莫里、[美]威廉·鮑莫爾:《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沖突》,文爽、喬羽譯,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頁。。以半導體產業為例,20世紀80年代用5000萬美元建起來的裝配廠,到2008年時所需前期投入則要超過30億美元(49)[美]小理查德·埃爾克斯:《大國的命脈》,程海榮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頁。。在此背景下,完全聽憑市場力量的引導,后起國家的企業進入發達國家控制下的全球價值鏈并與主導企業展開競爭就像一場曠日持久、成本高昂而且異常艱難的戰役(50)[美]拉爾夫·戈莫里、[美]威廉·鮑莫爾:《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沖突》,文爽、喬羽譯,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頁。。但政府卻可以扭轉局勢,通過合理的產業政策,后起國家新進入企業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必要的生產能力和規模優勢,從而改變該產業的世界分工與貿易格局,各國企業競爭形成新的均衡。第二個挑戰是如何從一個簽約制造商轉變為一個自有品牌和營銷公司。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最初可能沒有顧客愿意購買他們的產品(51)Keun Lee, Jaeyong Song and Jooyoung Kwak,“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Transition from OEM to OBM: Case Studies of SMEs in Korea”,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Vol.22, No.5, 2015.。最后,還有一個重大風險是來自主導企業的干擾甚至攻擊(52)Keun Lee, Marina Szapiro and Zhuqing Mao, “From Global Value Chains (GVC) to Innovation Systems for Local Value Chainsand Knowledge Cre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30, No.3, 2018.。他們可能會通過取消OEM/ODM訂單、知識產權訴訟、價格戰或傾銷等方式,對這些以前的合作伙伴實施打擊。因此,從ODM向OBM的“驚險一躍”就好似跨過一條寬闊的“OBM河”(OBM river),只有實現真正的跨越,后起國家的企業才能真正成為一家OBM公司。
因此,政府的支持至關重要。與推動本國企業和產業融入全球價值鏈而采取的外資優惠政策、基礎設施建設等措施不同,在本國企業轉向自有品牌跨國公司階段,政府需要提供的是扶植和援助。政府可以幫助國內企業尋求獨立,通過產業政策安排、創新體系構建、公私合作研發、市場信息提供、教育和培訓體系完善等措施,扶植和促進本國趕超型企業的升級與轉型。至于援助,由于后起國家的企業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比普遍規模較小、技術水平相對落后,在競爭時必然處于下風,特別是當后者發起知識產權訴訟等行動時,本國企業往往會由于資金、能力和經驗不足而輕易落敗。因此,政府的任務就是為企業預防涉及專利的知識產權糾紛或在其遭受糾紛時提供必要的服務和支持,比如針對可能出現的知識產權訴訟出售商業保險,為可能發生的法律糾紛提供調查服務,以及當本國企業面臨外國企業知識產權訴訟時提供一攬子咨詢服務等。在上述政策激勵下,后起國家就有希望擺脫低端鎖定的困境,推進本國企業從全球價值鏈的中間“洼地”向兩端“高地”轉移,實現全球價值鏈上經濟權力的轉移。
4.國內市場。權力并不只是意味著羅伯特·達爾(Robert A.Dahl)經典定義所說的迫使其他行為體服從的能力,它還包括議程設置和改變其他人偏好的能力,即為結構性權力(53)Robert A.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2, No.3, 1957.。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賦予了本國重要的結構性權力(54)Susan Strange,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4, 1987.,而現有全球價值鏈治理研究通常沒有考慮后起國家規模的異質性。這些國家的企業加入由發達國家主導企業控制的全球價值鏈,本國國內市場規模的大小以及產品銷售市場的特征都被假定為同質的。在此背景下,后起國家的產業升級會沿著一條相似的路徑逐步完成。但在現實中,國內市場的規模大小及其作為最終產品銷售市場的能力實際上會對本國企業的升級和創新產生顯著的影響。如果代工或委托生產的產品都是銷往西方發達國家的,那么參與其中的后起國家企業在與龍頭企業的博弈中通常都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發達國家品牌零售商(買方)會不斷向工廠(供應商)施壓,要求他們降低成本和價格。
然而,隨著后起國家國內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并逐漸成為發達國家主導企業不可或缺的最終需求市場,他們在全球價值鏈上的議價能力也將隨之提升。相對于主導企業,后起國家企業對本國的法律法規、市場環境、消費者習慣等更為熟悉,如果主導企業希望利用本地企業的在地優勢更快地嵌入東道國市場,則后起國家企業在與主導企業博弈時就會形成更強的討價還價能力(55)Y.H.Dennis Wei and Felix H.F.Liao, “The Embeddednes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ese Cities:Strategic Coupl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40, 2013.。比如,基于巨大的國內市場優勢,中國國內汽車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就形成了比較緊密的戰略耦合關系,主導企業往往會賦予中國國內汽車企業更多的自主權。
同時,巨大的國內市場也有助于后起國家的國內企業構筑自己的價值鏈。當本土企業嘗試從ODM向OBM轉型時,除了產品質量和價格競爭力本身,能否打開市場把自有品牌銷售出去,決定著企業是否能夠最終形成屬于自己的全球價值鏈。如果本國市場規模過小,那么轉型企業就需要從其他后起國家的市場積累經驗,逐步形成品牌優勢,這無疑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本國市場規模足夠大,后起國家本國企業則具有了天然的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在本國市場的開拓逐步壯大企業規模,累積組織和營銷能力,擴大自有品牌影響力。為加速本土企業的升級,減少轉型進程中的摩擦成本,后起國家的政府無疑能夠起到有力的引導作用,政府可以通過實施各種金融、稅收政策以及其他產業政策,激勵本土企業加大研發和創新力度,努力形成自有品牌,從本國市場開始,逐步構建以自身為核心的價值鏈。
三、價值鏈治理視角下的中國崛起與經濟權力的演進
(一)全球價值鏈治理與中國經濟趕超
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為節點,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進程根據特征差異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此進程中,中國的經濟權力也實現了快速的躍升。
第一階段(1992-2008年):中國從全面融入全球價值鏈到成為“世界工廠”。1978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20世紀80年代,港澳外資以“三來一補”“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國際代工模式試探性地進入內地。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及隨后“十四大”上中央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標志著中國開始由政策性開放向制度性開放轉變,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中國大規模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元年。從1992年到2008年,中國在不斷融入全球分工體系的過程中,逐步成為“世界工廠”和制造大國。這一階段有兩個關鍵性事件:一是1992年中國向市場經濟的制度轉型以及隨后兩年以人民幣匯率改革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為代表的一系列市場化改革。這些改革充分釋放了中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極大鼓勵了外商進行直接投資的信心,此后,外資迅猛增長,進出口貿易規模明顯提升。經由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中國得以成功切入全球產業鏈的分工體系,搭上世界經濟發展的快車。在這一階段,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釋放出來的勞動力,是我國將潛在的資源稟賦等后發優勢轉化為參與全球化比較優勢的最大的“人口紅利”(56)蔡昉:《中國改革成功經驗的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二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兌現入世承諾,中國不斷深化改革,除了大幅降低關稅水平,還重點清理了大量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法律法規,同時,中國還逐步健全貿易促進、貿易救濟法律體系和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等,推動對外經濟貿易法制化建設。這些制度性紅利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推動中國經濟加速融入全球分工體系(57)洪俊杰、商輝:《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四十年回顧與展望》,《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為了加強與完善對加工貿易的管理,鼓勵企業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價值鏈并擴大外貿出口規模,中國政府自2000年4月開始成立了一系列由海關監管的出口加工區。除了對加工區內企業生產所需的機器、設備等實施免稅政策,以及對區內為加工出口產品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提供服務的企業實施保稅政策之外,國家為促進當地形成產業集群,還在每一個出口加工區設定了主導產業,從而形成了出口加工區扶持“主導產業”的政策(58)張鵬楊、朱光、趙祚翔:《產業政策如何影響GVC升級——基于資源錯配的視角》,《財貿研究》2019年第9期。。其結果是,一方面出口加工區成為中國進出口貿易的主要平臺,其進口和出口貿易額分別占到全國進口總量的1/3和出口總量的近一半(59)Gary Gereffi,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Vol.21, No.1, 2014.;另一方面,各地區依據中央政策和本地區特點形成的供應鏈,完美地將規模驅動的專業化轉變為一種可持續的國家競爭優勢。從珠三角地區專門從事零部件生產以及將其組裝成各種最終產品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到長三角地區專門從事汽車、半導體、手機和計算機等產品生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都是中央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作出戰略規劃,并在地方層面快速、大規模實施的結果(60)Gary Gereffi,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The Antitrust Bulletin, Vol.56, No.1, 2011.。這些專業集群一方面與東亞關鍵零部件供應商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與全球買家聯系在一起,將中國產品推向世界市場(61)Gary Gereffi, “Development Model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and Mexico”,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5, No.1, 2009.。
由于上述一系列政策的實施,中國最終在21世紀初成為“世界工廠”,主要表現為:一是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總額快速增加,國際貿易當中外商投資企業占比很高。從1992年到2008年,中國貨物出口總額從849億美元上升至14307億美元,提高了16.9倍;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從110億美元上升至1083億美元,提高了9.8倍(62)根據CEIC數據庫計算得到,https://insights.ceicdata.com/Untitled-insight/myseries,2021-01-10。。在出口總額當中,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占比從1996年的41%提升至2008年的55%(63)根據CEIC數據庫計算得到,https://insights.ceicdata.com/Untitled-insight/views,2021-03-23。,說明這一時期中國對通過外商投資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的依賴度不斷提高。二是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后向聯系不斷加強,說明中國仍然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這是中國主要依靠低成本勞動力融入世界經濟的結果。1995-2007年,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后向參與度從14%快速上升至20%(64)所謂后向參與度是指一國出口當中其他國家生產的中間產品所占的比重,用來反映出口對來自其他國家進口的依賴程度。根據對外經貿大學全球價值鏈數據庫相關數據計算得到,https://v2.fangcloud.com/share/a26979974d538c7e5aeb24b55a?lang=en,2021-01-10。,表明在這一階段,中國主要是通過大量進口中間產品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再出口的方式快速、全面地融入全球產業鏈當中,由此形成的生產和貿易分工網絡被一些學者稱為“新三角貿易”(65)李曉、丁一兵、秦婷婷:《中國在東亞經濟中地位的提升:基于貿易動向的考察》,《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5年第5期。。
第二階段(2009年至今):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不斷提升地位和實現創新。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于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發展來說是一個“重大拐點”(66)Gary Gereffi,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Vol.21, No.1, 2014.,同時也是中美經濟權力轉移的一個分水嶺。危機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開始顯著下降,而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則保持了強勁的發展勢頭,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據世界銀行的估算,2013-2017年間,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超過30%,超過了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貢獻總和(67)侯露露、管克江:《五年來中國經濟貢獻率超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總和》, 人民網,http://m.people.cn/n4/2018/0416/c3515-10831798.html,2020-06-14。。
在經濟強勁增長的同時,幾個關鍵性的因素變化促使中國政府開始調整經濟增長和發展戰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全球貿易額斷崖式下跌,外需減少迫使中國實施經濟再平衡戰略;中國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成本優勢開始下降;早期“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政策并未獲得顯著成效,同時導致許多產業的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所壟斷,本土企業卻被鎖定在價值鏈的低端環節;等等。由此,我們可以觀察到,危機后中國政府的發展政策在兩方面發生了重大的戰略轉變:一是實施經濟再平衡戰略,推動經濟增長方式從外需主導向內需主導轉變;二是實施技術升級與創新戰略,提升本土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以及構建我國跨國企業的全球價值鏈。
增長方式的轉變意味著中國開始改變以往對出口拉動的過度依賴,真正邁入后重商主義時代。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2008年最終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44%,大大低于投資的53.3%。但從2012年開始,最終消費逐漸超越投資,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2014年消費貢獻率達到56.3%,2018年進一步升至64.0%(68)數據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1-01-10。。
增長方式轉型的同時,中國政府對于通過引進技術推動本國創新發展的思路也開始發生變化。人們逐漸認識到,功能升級和鏈的升級已經成為中國產業和企業擺脫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困境的刻不容緩的戰略任務。為此,就必須改變以往將外國直接投資視為發展本國創新能力的主要渠道,將注意力集中在打破對外國技術的依賴和創建自我持續的、以創新為導向的經濟上。
2006年中國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被認為是中國向創新經濟轉型的標志(69)陳燕玲、朱孔來:《中國自主創新政策的演進及未來發展趨勢》,《社會科學前沿》2017年第6期。。大會提出了“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并發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產業政策更為注重創新驅動發展、新興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應用。圍繞創新驅動、新興技術(產業)及先進制造業發展,中央政府又陸續出臺多個政策文件,其中2015年頒布的《中國制造2025》是集中體現。從政策措施來看,在繼續秉持政府引導的基本原則下,中國開始更加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與健全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等功能性產業政策,則成為政府新的政策著力點(70)江飛濤、李曉萍:《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產業政策演進與發展——兼論中國產業政策體系的轉型》,《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2016年12月,中國商務部、國家發改委等七部委聯合下發《關于加強國際合作提高我國產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指導意見》,該意見指出未來我國產業發展的三個方向:繼續支持企業融入全球分工合作體系,不斷提高我國出口增加值,主動打造互利共贏的全球價值鏈。為此,政府從產業基金支持政策、財稅政策、人才政策、貿易投資便利化政策、金融政策、創新政策等多個方面提出了實現上述目標的政策框架。
上述一系列產業提升和創新政策的實施正在顯現成效。2009年至今,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不斷升級,從低端制造向先進制造和先進服務邁進,中國也由此開始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從“世界工廠”向“全球價值鏈樞紐”轉變。
首先,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不斷攀升。這主要表現為越來越多的企業能夠進入全球價值鏈上更復雜、增加值更多的生產環節,實現所謂的產品升級、流程升級和功能升級。這種變化可以從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后向參與度的下降得以體現。從2009年到2015年,中國制造業產品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占比從79.0%上升至81.3%;相應地,外國增加值從21.0%降至18.7%,減少了2.3個百分點(71)根據CEIC和OECD的TiVA數據庫數據計算得出,CEIC數據庫,https://insights.ceicdata.com/Untitled-insight/myseries,2021-01-11;TiVA數據庫,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TIVA_2018_C1,2021-01-11。。這意味著中國通過產業鏈升級,替代和減少了對中間產品的進口,制造業正在升級到先進制造產業。張斌等人基于制造業出口產品增加值率的計算也發現,全球金融危機后制造業的升級要快于危機前,而且對出口增加值率提高貢獻最大的是行業內效應,而不是行業間效應(72)張斌、王雅琦、鄒靜嫻:《從貿易數據透視中國制造業升級》,《國際經濟評論》2017年第3期。,也就是說,中國制造業企業的技術升級路線主要來自對所進口中間產品的替代。后向參與度下降的同時,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上的前向參與度則在危機之后穩步上升,從2009年的1.5%提升至2015年的2.4%(73)根據CEIC數據計算得出,https://insights.ceicdata.com/Untitled-insight/myseries,2021-01-11。,說明中國作為全球中間產品供應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數據顯示,從2009年到2018年,中國出口中的中間產品占比從36%上升至63%,而中國在世界中間產品出口中的占比則從8.9%升至15.7%,增加了6.8個百分點(74)根據RIETI-TID 2018數據計算得出,https://www.rieti-tid.com/,2021-01-11。。上述現象表明中國已經成為多數國家中間產品進口的主要來源國,中國開始在全球價值鏈上扮演關鍵的“樞紐”角色。
其次,越來越多參與全球價值鏈的中國企業努力通過技術創新和價值鏈重構實現“鏈的升級”。通常人們將創新等同于突破性技術,但事實上,正如阿瑪爾·畢海德(Amar Bhidé)所言,創新是一個復雜過程,除了高水平的突破性技術,還包括許多中等水平和低水平的應用性技術創新,它們是對突破性技術創新的有益補充,也是一種同等重要的創新活動(75)Amar Bhidé, “Where Innovation Creates Value”, McKinsey Quarterly, February 2009.。何少偉等人借鑒畢海德的思想,從結構創新(architectural innovation)和嫁接創新(grafting innovation)(76)所謂結構創新,是指重新配置已建立的系統,以新的方式將現有組件連接在一起,以便生產和銷售滿足客戶需求的產品。這使后發企業有機會獲得比先發企業更大的優勢,但要求后發企業了解組成部分如何相互聯系成一個整體,還需要獨特的管理和組織技能。所謂嫁接創新,是指發現現有技術的新用途和應用,從而根據其核心技術在其他行業的應用情況開發新產品和提供解決方案。兩個方面討論了中國企業的鏈的升級活動與績效后發現,華為(結構創新的代表)、比亞迪、中國南車(嫁接創新的代表)都已顯示出強大的創新能力。為了進一步升級和追趕,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還在政府“走出去”和“自主創新”政策的支持下,開始在發達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或是設立海外研發中心。根據中國政府2012年對數百家中國領先創新企業的調查,其中70家企業已經在海外設立了137個研發中心,其中大部分位于發達國家(77)比如固態物理學的突破只有伴隨著新的微處理器設計,才對半導體產業有價值,如果沒有工廠層級的調整使大量生產這些組件成為可能,那么新的微處理器設計本身是毫無用處的。而如果沒有新的主板和計算機,新的微處理器的價值也可能無法實現。參見Shaowei He, Grahame Fallon, Zaheer Khan and Zhong Wang, “The Rise of Chinese Innovative Firms and the Changing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Brunel Business School Research Papers, https://bura.brunel.ac.uk/bitstream/2438/15400/1/Fulltext.pdf , 2021-01-20。。由于上述鏈的升級活動,大量中國企業開始向主導企業轉變。比如華為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電信設備制造商,聯想是最大的個人電腦制造商,海爾是最大的家用電器制造商,中國中車則是世界最大的機車制造商等。中國在創新方面的新趨勢正在導致全球創新和研發活動的所有權、控制權和地理區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些新的企業開始在全球生產網絡和市場中塑造自身的領導地位(78)BCG, “Redefining Global Competitive Dynamics”, 2014 BCG Global Challengers,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https://image-src.bcg.com/Images/Redefining_Global_Competitive_Dynamics_Sep_2014_tcm9-74264.pdf, 2021-01-20.。
最后,中國快速擴張的國內市場大大提高了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上的討價還價能力,這成為中國結構性權力的重要來源。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國內需求停滯,全球價值鏈的最終需求開始轉向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在中國生產的目的是為滿足中國國內需求。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統計,2010年到2017 年間,全球汽車銷量增長的 50% 來自中國。2017 年美國企業通過對華出口和在華子公司的業務,共計從中國獲得了 4500-5000 億美元營收(79)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中國與世界:理解變化中的經濟聯系》,https://www.mckinsey.com.cn/wp-content/uploads/2019/12/中國與世界:理解變化中的經濟聯系-中文全文-Final.pdf/,第83、85、93頁,2021-01-13。這種轉變也深刻改變了中國本土企業(合同供應商)與全球價值鏈主導企業(合同購買方)的關系,并使得前者的議價能力不斷提高。因為生產目的從出口到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轉變意味著中國的制造商必須將其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作用從制造擴大到采購、銷售和分銷,而這些功能原本都是由價值鏈上的主導企業控制的。除了本土企業議價能力的提高,中國的地方政府在與跨國公司談判中的地位也在不斷上升,由于國家創新發展戰略的實施,地方政府特別是來自沿海地區的地方政府更加歡迎能更大程度融入本地經濟、有助于促進本地產業技術升級的跨國投資。
(二)中國國際經濟權力的提升
21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實力大幅躍升,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2019年則達到美國的2/3。那么,如何客觀地比較和評價中美的經濟實力呢?學者們通常采用GDP總量來討論中國的經濟崛起,盡管學者們對于用名義匯率計算的GDP還是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GDP更能反映一國的經濟實力的看法并不一致。另一方面,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認為,GDP指標會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人口大國的實力水平,而忽略國家的成本和效率,為此,他提出了以“GDP×人均GDP”作為衡量一國經濟實力的指標,前者代表一國經濟和軍事產出總規模,后者則反映該國經濟和軍事的效率,二者綜合即可囊括凈資源的規模和利用效率這兩個重要維度,從而更加準確地測量出該國的總體經濟實力(80)Michael Beckley, “The Power of Nations: Measuring What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3, No.2, 2018.。格倫·哈伯德(R.Glenn Hubbard)、蒂姆·凱恩(Tim Kane)則進一步把經濟增長率納入衡量范圍,提出了如下計算公式:經濟實力=國內生產總值×生產率×增長率1/2(81)如果一國某年的經濟增長率低于0.2,作者的處理方法是按照0.2來計算。此外,為了使結果更加合理,作者采用了增長率平方根的計算方法。參見[美]格倫·哈伯德、蒂姆·凱恩《平衡:從古羅馬到今日美國的大國興衰》,陳毅平、余小丹、伍定強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頁。。如果分別用名義匯率和PPP方式按照上述三種衡量方法計算中國的相對經濟實力(占美國的百分比),會發現六種結果差異巨大。以2018年為例,按照名義匯率方法下的“GDP×人均GDP”公式計算,中國的經濟實力只有美國的10.3%,而按照PPP方法計算,中國的經濟實力則已達到美國的123.6%。
考慮到上述方法各有優劣,筆者對六種方法計算的結果進行加權平均,以此計算出來的結果能更好地避免極端情況的出現,更加真實地反映中國的綜合經濟實力(見表1)。從2000年到2018年,中國的綜合經濟實力占美國的比重從9.3%上升至50.9%,提高了4.5倍。如果把歐元區、英國、日本和印度也納入考察范圍,2000年中國的經濟實力僅僅超過印度,分別只有歐元區、日本和英國的16%、26%和73%,但到2018年,中國的經濟實力則幾乎與歐元區持平,分別為日本、英國和印度的2.9倍、4.8倍和3.7倍(見表2)。不過,盡管中國的經濟實力上升很快,但截至2018年中國經濟實力仍然只有美國的一半。

表1中美經濟實力比較(中國占美國的比重) (單位:%)
加權平均:方法1-6的簡單加權平均之和。

表2主要經濟體經濟實力比較(各國占美國的比重) (單位:%)
由于全球化背景下大量的跨國公司在全球經營,而一國的GDP并不包含本國跨國公司的國外增加值,因此,作為一種補充,筆者借鑒肖恩·斯塔爾斯(Sean Starrs)的做法,通過考察中美跨國公司的規模與績效,來進一步衡量和比較兩國的經濟實力差距(82)Sean Starrs, “American Economic Power Hasn’t Declined-It Globalized! Summoning the Data and Taking Globalization Seriousl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7, No.4, 2013.。出于可比較的角度,筆者以2019年《財富》世界500強中的企業上榜數量和發展質量來考察中國企業(與美國企業比較)的相對實力。從2000年至2019年,中國世界500強的企業數量從9家增至129家(含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其中,中國大陸500強企業數量從8家增加到119家。同期美國的500強企業數量則從175家減少至121家,2019年較中國少8家,這是自世界500強榜單誕生以來,美國500強企業首次在數量上退居全球第二位。中國企業與美國企業在數量對比上呈現一升一降的趨勢。
與此同時,進一步考察企業的競爭力,可以發現中美之間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從行業分布看,中國上榜企業主要分布在能源、銀行等具有壟斷性質的行業,而在高端制造業、信息技術等行業,中國則明顯處于下風,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仍處于中低端地位。從營業收入來看,中國企業與美國企業相差不大,2019年中國上榜企業營業收入總計7.9萬億美元,平均為614億美元,分別占美國的84%和79%。但從企業利潤來看,中國企業的盈利能力要顯著低于美國,總利潤與平均利潤分別相當于美國企業的56.2%和52.7%。如果不算銀行業(中國全部上榜企業中銀行數量僅占8.5%但利潤占比卻高達50.8%),那么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僅相當于美國的32.4%,其中高新技術產業利潤僅為美國的31.5%(83)根據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相關數據計算得出,https://fortune.com/global500/,2021-01-12。。
四、國際秩序轉型、全球價值鏈重構與跨越“大國趕超陷阱”
(一)國際秩序轉型背景下全球價值鏈重構與大國博弈
近年來國際秩序進入劇烈的震蕩期。英國脫歐、特朗普民粹政府上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黑天鵝事件”此起彼伏,導致全球政治經濟陷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雙重危機,國際秩序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其中,中美兩國因特朗普政府發起的對華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而擴大的分歧,無疑是當今緊張、動蕩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縮影。在未來數年中,各國都將在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作出艱難的政策選擇。
國際秩序轉型的背景下,全球價值鏈因為全球化逆流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加強而開始發生深刻調整。事實上,這一變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就已經出現,主要特征是全球價值鏈呈現出顯著的區域化轉變態勢,大量研究表明,北美、東亞和歐洲正在逐漸向彼此“脫鉤”的方向發展(84)Christophe Degain,Bo Meng and Zhi Wang,“Recent Trends in Global Trade and Global Value Chains”,in World Bank (eds.),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gvcd_report_17_e.htm,2021-01-11;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亞洲的未來:亞洲的流動與網絡正在定義全球化的下一階段》,https://www.mckinsey.com.cn/insights/mckinsey-global-institute/,第39頁,2021-01-11。。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巨大影響則可能加速這一進程。為了避免美國對華征收的高額關稅,一些價值鏈主導企業已經開始減少從中國的采購,或者把服務于美國市場的產能從中國撤回,或轉移至第三國。比如,蘋果公司已經要求它在中國的加工企業把10%到15%的產能轉移到東盟。根據科爾尼公司發布的美國制造業回流指數報告,2019年美國制造業從中國進口減少了900億美元,其中有310億美元被東盟低收入國家所替代,而越南是最大的受益國,獲得了其中大約50%的份額(85)Kearney, “Trade War Spurs Sharp Reversal in 2019 Reshoring Index, Foreshadowing COVID-19 Test of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https://www.kearney.com/operations-performance-transformation/us-reshoring-index/full-report,2020-06-14.。中國美國商會發布的商業環境調查報告也顯示,特朗普執政以來,有20%左右的公司已經或正在考慮將產能轉移至中國境外,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戰(86)中國美國商會:《2019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https://www.amchamchina.org/white_paper/2019-american-business-in-china-white-paper/,第33頁,2021-01-20。。2020年突如其來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則進一步暴露了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脆弱和安全問題,美國、日本、法國等發達國家的政府紛紛采取措施激勵本國跨國企業回歸本土,疫情之后這些國家必然會進一步采取措施,努力通過價值鏈調整和重新布局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企業撤離中國的規模、范圍和速度,將主要取決于企業自身和集體所感知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大小。一些受到高度安全審查的技術型企業,特別是美國企業,可能被迫選擇徹底退出中國,并根據新的市場環境重新設計其技術生態系統;另外一些企業不會選擇徹底離開中國,但可能會縮小在華經營規模,同時采取“中國+1”的發展戰略以分散風險。
新形勢下大國博弈的加強,預示著中國正在接近“大國趕超陷阱”,不過正如張宇燕所說,“陷阱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參與大國博弈的國家必然會墜入陷阱,而是意味著大國間的趕超在達到一定層次后難度會陡增,其中就包括美國及其盟友對華態度與政策的大角度轉變”(87)張宇燕:《跨越“大國趕超陷阱”》,《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1期。。那么,中國最終能夠跨越這個“陷阱”,從而實現國際經濟權力的躍升嗎?
(二)中國跨越“大國趕超陷阱”的能力與制約
二戰后蘇聯和日本是最接近于趕超美國但最終功虧一簣的兩個國家,縱觀兩國的失敗趕超歷史,美國的遏制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不過,筆者認為,美國的壓力只是給趕超大國設置了很難跨越的“陷阱”,蘇聯和日本最終掉入“陷阱”歸根結底還是國內政策失敗的結果。蘇聯趕超失敗可歸因于體制僵化,大規模政府主導的國內投資在無法避免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作用下導致經濟陷入停滯,市場活力和創新能力始終未能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廣場協議”后日本所實施的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及由此導致的泡沫經濟則成為日本經濟迷失的根源。
與蘇聯被美國稱為“極權主義國家”類似,中國如今也被美國政府稱為“修正主義國家”,中蘇與美國的競爭不僅是經濟的競爭,而且也是兩種制度的競爭。不同的是,美蘇對抗是在兩個“完全平行的世界”中進行的,兩國經濟基本沒有交集和合作,因此,雙方的博弈更類似于零和博弈,一方的失敗就意味著另一方的勝利。中美競爭則不同,兩國共存于同一個國際經濟體系之中,全球化高速發展下,兩國經濟深度融合,雙方的競爭并非你死我活的斗爭,而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非零和博弈,雙方均無法在完全擊垮對手之后全身而退。
從同一國際經濟體系的競爭角度看,中美競爭與日美競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當中日經濟實力接近于美國時,美國采取的施壓政策主要以經濟和貿易手段為主,并未涉及政治和軍事層面的直接對抗和極限施壓。背后的原因在于中日都是依靠戰后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成長起來的,除了在治理層面尋求邊際上的調整與改進之外,兩國從未試圖顛覆和推翻該國際體系,相反,還都努力維護和加強現有國際組織在全球治理中的權威和有效性,同時也都承認美國在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中的領導角色。
以中國為例,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加,中國對現有國際體系投入了大量資源以維護其正常運行:中國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第二大出資國,目前在全球部署有2500余名維和人員,超過其他幾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派出人數的總和;中國提前還清世界銀行的借款并向其進行了捐款,中國還從支持法治、打擊腐敗、開放數據系統等方面為世界銀行的諸多倡議提供支持;同時,中國還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資以增強該機構的資金實力。中國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并非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組織的替代,相反在政府管理、采購和環保等方面采納了已有的全球標準,同時還為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項目提供資助。中國如期兌現了入世時關于關稅、配額等方面作出的承諾,并將貿易壁壘降至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此外,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中國竭力維護美國在國際組織中的權威:從2000年至2018年,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積極推動了190項與“制裁違反國際規則的國家”有關的決議,中國對其中的182項投了贊成票(88)《世行前行長佐利克:中美仍互為“利益攸關方”》,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0/0227/2403154_6.shtml,2020-06-14。。因此,總體上中國是把自己的利益與全球自由經濟秩序的利益鎖定在了一起,這一目標與美國高度一致,美國把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的做法更多體現為霸權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
然而,中美競爭又不同于日美競爭。2017年底美國政府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把中國定位為“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對手”,這與歷史上美國對日本的態度完全不同(89)拜登上臺后,雖然其對華戰略比特朗普政府更為理性,但依然視中國為“最嚴峻競爭對手”。而2021年4月8日美國參議院拋出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草案,則是一部匯聚兩黨共識的專門針對中國的綱領性文件,如果法案得以通過,無疑將全面拉開未來幾十年中美新一輪競爭的序幕。。日美是一個同盟體系內領頭羊與跟隨者之間的競爭,中美則是經濟與政治制度均存在巨大差異的新興崛起大國和在位霸權國之間的競爭。除了這種制度性差異,崛起的中國與日本還存在諸多重要的不同,這些不同可能奠定中國跨越“大國趕超陷阱”的堅實基礎。
首先,豐富的勞動力供給。經濟高速增長期,豐富的勞動力供給變成了趕超的“紅利”,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資源。此外,人口眾多也意味著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在面對愈發明顯的外部壓力時,為后起國家從外向型經濟向內需型經濟轉型提供有力支撐。其次,當前中國具有更顯著的后發優勢。1994年,當日本GDP超過美國的2/3時,人均GDP已達到美國的1.4倍;而中國在2018年GDP達到美國的2/3時,人均GDP還僅僅只有美國的15.6%(90)數據來源于CEIC數據庫,https://insights.ceicdata.com/Untitled-insight/myseries,2021-01-13。。1995年日本的城鎮化比率已達到78%,中國2017年的比率僅為58%(91)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中國與世界:理解變化中的經濟聯系》,https://www.mckinsey.com.cn/wp-content/uploads/2019/12/中國與世界:理解變化中的經濟聯系-中文全文-Final.pdf,第22頁,2021-01-13。。再次,當今中國與美國經濟深度融合的同時,本土已擁有全套型產業鏈,這使得中國具有更大的回旋空間。20世紀80年代日美之間盡管雙邊貿易規模很大,但彼此經濟聯系并不緊密。美國一直指責日本市場對外封閉,1994年美國對日本直接投資只有18.7億美元,僅比對中國的12.3億美元多6.4億美元,而該年日本的GDP是中國的8.7倍。日本對美國大量的貿易順差中,增加值所得基本上都被日本企業攫取。相反,由于美國在中國的大規模直接投資,中美兩國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當中并高度相互依賴,這也使得美國難以真正與中國經濟全面“脫鉤”。最后,中國具有堅定的復興信念、顯著的制度優勢和強大的政府能力。當前,西方發達國家正面臨一系列嚴峻的經濟、政治、社會挑戰,而中國則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引領下,持續推進國民經濟高水平、高質量發展。同時,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支持。中國跨越“大國趕超陷阱”存在諸多有利條件。
但在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上,仍然存在著許多內部和外部制約。從內部因素來看,從外需主導向內需為主的增長模式轉型困難重重,外需大幅下降的同時,內需卻由于社會保障缺失、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問題而難以快速提升;向高質量市場經濟方向發展的過程中仍存在大量的體制性障礙,過度管制性傾向在經濟運行過程中仍廣泛存在;積極的產業政策和債務投資驅動模式仍是政府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但傳統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已面臨債務負擔、金融風險和產業空間的極大限制,政策的邊際效果不斷下降;新舊動能轉換任重道遠,舊結構、舊動能開始衰退,但新結構、新動能仍然發育不足;政府扶植型新動能過剩而政府服務型新動能不足;等等。從外部制約看,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外部需求持續回落,出口增長面臨巨大壓力,這成為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中美貿易戰影響逐漸顯現,對經濟預期和市場信心產生巨大沖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使得全球貿易和投資突然停擺,世界經濟陷入深度衰退已成定局,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更加悲觀。特別重要的是,全球價值鏈受到中美貿易戰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沖擊,以市場為基礎的國際分工風險日益暴露,全球化發展正加速回潮,而危機當中西方發達國家政府乃至民眾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大幅上升,這可能成為后疫情時代西方國家推動全球價值鏈重構的重要民意基礎,需引起我國的高度警惕。外部環境的動蕩與惡化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正步入一個不確定性風險更大的新階段,開放戰略和模式的調整勢在必行。
結 論
縱觀人類發展歷史,大國之間的權力變化與更迭是國際關系中不變的規律,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可以在國際權力結構中始終保持主導地位(92)袁偉華:《權力轉移、相對收益與中日合作困境——以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反應為例》,《日本學刊》2018年第3期。。在新興大國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進程中,中國走在了最前列。與歷史上的蘇聯和日本不同,中國在全球化深入發展、全球價值鏈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中不斷成長。在此過程中,具有顯著東方特征的政府權威和國家能力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對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干預和激勵模式與高速發展時期的日本、韓國大同小異,其利用后發優勢采用產業政策推動經濟增長和保護國內幼稚產業的戰略舉措,甚至與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成長初期的做法也無二致。不同的是,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其他大國崛起時面臨的時代環境存在巨大差異。與早期的全球化發展不充分、各國產業處于分離狀態不同,中國面對的是一個全球價值鏈深度融合的國際環境。中國抓住了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和推動的經濟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和技術進步所提供的機遇,利用自身龐大的勞動力供給、市場化轉型紅利和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等優勢,把本國經濟有機融入全球價值鏈當中;同時,依靠強大的政府能力,通過“摸著石頭過河”“大膽試驗與謹慎推進”“干中學”等方式,保證國內經濟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穩步前行的同時,一步一個腳印地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
然而,隨著經濟的迅速增長,中國對世界經濟和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在此背景下,中國的發展模式和與其他國家的互動模式就成了世界各國重視的焦點問題。盡管我們從未謀求徹底改變國際體系現狀,但無論是出于擔心被趕超而形成的防范心理,還是因為中國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不同而產生的疑慮,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也在預期之中。未來發展過程中,如何優化我們的發展模式,消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疑慮,如何調整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互動方式,讓世界各國更加容易接受中國,都需要成為我們戰略制定和政策考量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考慮到西方社會收入不平等加劇、民粹主義泛濫等問題的出現很大程度上與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迅猛發展有關,未來為更好地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我們在重視國內經濟增長和解決內部問題的同時,就需要更加關注中國對世界各國的外溢效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更好地維護有利于我們的發展環境,在安全和平的世界秩序演變中最終實現對“大國趕超陷阱”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