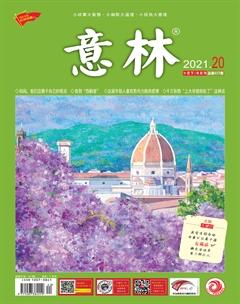為什么你朋友圈里的打工人,都在學街舞
李放鹿
以前一說健身,標配就是全套運動裝備、一眼望去各類器材應有盡有的健身房大廳,以及一張極大概率只會使用一次的會員年卡。
而如今,朋友圈里規規矩矩去健身房的人越來越少。
他們看重“有趣”甚于健身目的,從大而全的健身房,流向了小而精的街舞班、攀巖館、拳擊館、擊劍館。
1.“我不是去健身,是去合法打人”
前兩年健身房遍地開花的時候,“健身”二字是最讓社畜又愛又恨的東西。
27歲的木木就是這股健身泡沫的親歷者,她辦過年卡,試過跳繩、跑步,還在家里買了一輛動感單車放在家里。
無一例外,都是三分鐘熱度。
直到后來被同事拉著去了泰拳館,第一次打靶的時候她還有點不好意思,但教練跟她說:“你就把我當作你老板,踢我。”
木木瞬間就來勁了。
泰拳課比一般健身房還貴,但木木覺得特別值。
上班上得一身火氣,回家拎著拳套就會往拳館沖:“去打人泄火。”
對她來說,以往的運動方式,跑步跳操什么的,都只是單純地折磨自己;而泰拳讓她感受到了反擊別人的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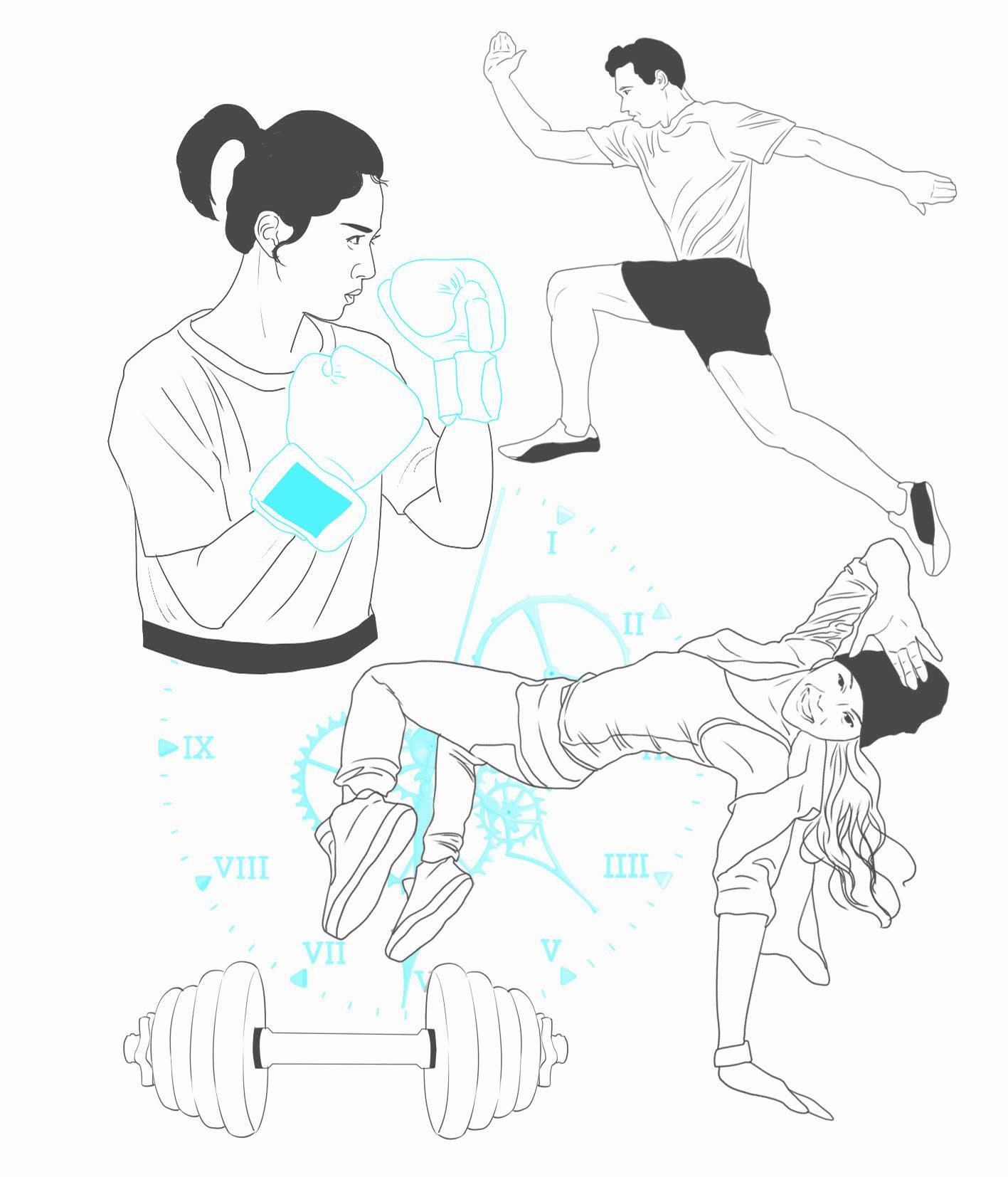
至于打拳的運動強度有多大、減重塑性效率有多高,反而成了這個過程中得來的意外收獲。
帶她入坑的那位同事,揍人的欲望沒這么強烈,她一開始練拳是想要學習防身技巧。看多了獨居生活不安全的新聞,總覺得千防萬防,最有用的還是武力值夠高。
拳館里抱著這種心態來的姑娘挺多,盡管大家都知道,在外面跟人動手的概率其實很小很小,但“練拳本身就給人安全感”。
這種非典型的健身項目,在城市青年人群中越來越流行。
個子小膽子大的阿弈,每年雷打不動,冬天滑雪、夏日攀巖。
她運動的目的同樣不是通常認為的減肥、塑身,純粹是因為上班用腦過度,一放假就想用用別的地方,協調一下。
阿弈不喜歡一直重復的狀態,而滑雪和攀巖恰恰都是需要不斷學習新技巧的運動。
每學會一個新動作,就是一份新的成就感;有時候第二天胳膊酸腿疼,都覺得真棒,身上又有一塊肌肉調動起來了。
因為女朋友喜歡一檔街舞綜藝,Allen在她的帶動下,報了一萬多塊錢的街舞培訓班。
每學會一個好看的動作,他們倆就會給彼此錄個小視頻,發到社交平臺上,收獲一堆點贊。
這些項目的運動量,并不比泡在健身房里玩幾小時機械少,毫無基礎的人剛開始入門,也時常會出現腰酸背痛、怎么還不結束的疲憊感。
但成就感來得很快,從不得要領的菜雞階段到徹底入坑,也許只需要一瞬間:
第一次把一個動作做完整,或是第一次實戰贏了,那種巨大的成就感跟跑步到終點不同,它意味著你完成了一件專業的、別人做不到的事,能讓人很快上癮。
跟傳統健身方式比起來,這些項目,似乎沒那么“難熬”。
2.比起苦哈哈的“鍛煉”,他們更想“爽一把”
之前健身房刮起倒閉大潮的時候,網上很多人嘲諷,“健身卡就是智商稅”“年輕人已經放棄運動了”。
去健身房的人的確越來越少,根據統計,去年傳統健身房倒閉率達到50%。
疫情固然是重要的誘因,但傳統健身行業的衰落在疫情前就已有征兆。
并非大家都不愛運動了,相反,整個體育行業熱度很高,尤其是擊劍、攀巖、拳擊、街舞、滑板這些非典型的運動項目。
拿最出圈的街舞來說,目前,全國有超過5000家街舞工作室,每年報名街舞培訓的學員累計500萬人次。
就連看似小眾的擊劍,全國注冊的各類俱樂部、培訓中心等也早已有數百個,參與人數在2018年就超過了10萬。
究其原因,健身市場其實一直都在,一坐就是八小時的打工人,“動一動”是永恒的需求。
只是傳統的健身方式,在越來越細致的運動需求面前,越發跟不上節奏。
另一個常見的誤會是,這些看起來比較“小眾”的運動,好像都是年輕人去圖個新鮮熱鬧。
事實上,這些運動的愛好者或許并不在互聯網“年輕人”的范疇里,而是這樣一群人:
工作幾年薄有積蓄,但年齡逼近三十歲,壓力越來越大,頸椎和腰間盤咔咔作響,各項指標搖搖欲墜。
這大概也是他們運動興趣大于目的的原因,年輕人的腹肌焦慮,肥胖焦慮,在三十歲的煩躁和壓力面前,都得往后靠。
被他們喜歡的運動,無論拳擊還是街舞,都需要傾注全部的注意力。
要凝神聽教練糾正動作,要跟對手發生對抗,或是要注意每個動作的節奏。
在健身房里一板一眼地擼鐵不會有這種效果,沒有對手、沒有交流,人在機械地重復某個動作,就會忍不住胡思亂想。
年輕網友暢想的那種一邊看電視、一邊做運動也不行,這個年紀的人,平時想的事越多,就越需要一段什么也不用想的時間。
我有個隔三岔五去沖浪的朋友,從來不指望這項運動能減肥塑身,每次去的時間也都不長。
他去的原因很簡單,工作日每天都在加班,每天都很累。
一到周末,就是不想看手機、不想打開電腦,就愿意去海里待那么幾小時。
在海浪中,他必須全神貫注,沒有任何余力去思考下周的工作、沒完成的KPI。
“只想浪的事,刺激一把,爽一把。”
爽完照片曬出去,收一波“生活好精彩”的彩虹屁,就收拾東西回家,繼續憋屈著加班干活,去掙下一次沖浪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