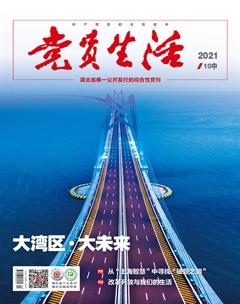當外國大衛 到中國農村掰起了玉米
metro
中國嶺南超過36℃的高溫,落在每一個人的頭頂。大衛來我們家那幾天,氣溫達到一個新高峰。我們打算把地里的玉米收完就回家。此時,他的T恤衫被汗浸透,濕噠噠地貼在身上,有幾只螞蟻,正艱難地往衣袖里鉆。“你幫我翻譯,”我媽對我說,“問他要不要先回去,外面太熱了,怕他受不住。”大衛聽聞,疑惑地望過來,我媽喊道:“你,OK不OK?”
“還可以。”他用生硬的中文回答,擠出笑容。
1
七年前,我和丈夫把北京的家搬回廣西的一個小村莊,和女兒、父母住在一起。城里的朋友們偶爾來住幾天,幫我們干點農活。
有位朋友,跟我們割了一天水稻,說回去后再叫朋友來,在健身房運動的人,力氣大,干活派得上用場。被忽悠來的那人,就是大衛。
愛爾蘭人,四十出頭,上海一所國際學校的老師。他在中國三年,去過北上廣幾個大城市,著名景點也打過卡。因為疫情無法出境,六月份學校放暑假,他計劃去昆明報了個給外國人開的語言學校,一邊旅游一邊學中文。上海的夏天太悶熱了,總得找個什么理由跑出來。
朋友建議他到我們這里——“你為什么不住進真正的中國人家里去?每天都能學中文,還可以看到中國年輕人、中國農村家庭不一樣的生活。”
但是,朋友又嚇唬他,“農村肯定沒你現在的條件好,萬一,做飯不合你胃口,哪兒有讓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得忍著,不能提前哭著跑回來。”
“我們這里條件哪有那么差?”我媽有點生氣,“叫大衛別怕。”怎么招待國際友人,成了那段時間我們家飯桌上天天討論的議題。
“我們家還沒招待過外國人呢,”我爸說:“雞鴨是肯定要抓來吃的,第一天吃雞,最后走那天吃鴨。”“不用那么隆重吧,家常菜就好了。”我說。
“那是必須的。這個代表中國農村的生活水平,我們這里招待客人就是這樣的,最高水準。”我爸說,“對了,大衛家在農村還是城市?看樣子,可能也是進城打工的,都不容易。”
唯一讓我媽發愁的,是不知道該怎么跟大衛溝通。我媽拜托外孫女那那:“你幫我們翻譯。”那那大驚:“我才四年級,我也聽不懂。”
2
第一天,大衛被接進家門,恭恭敬敬地跟我們走。他左看右看,禮貌地說:“哇喔,good。”“他什么意思?”爸媽問我。“就是好。”“顧得、顧得”,他倆笑逐顏開。面對我們說的中文,大衛一概報以專注的神情,并附上神秘的微笑,似乎鼓勵我們繼續說下去。等我們滔滔不絕說完,問他:“聽懂了嗎?”此人立刻換上一副呆滯的表情:“對不起,你說什么?”
吃飽飯,大衛說:“今天農場安排什么活兒?”我不得不糾正他,我家不是農場,只是幾塊地而已。他在城市長大,沒做過體力活,費力氣的事,除了在健身房舉鐵,他想起來就是大學畢業那年在倫敦當警察,把街邊的醉漢拖到診所去。
第二天,我們到山坡的樹林里,那兒有一大片成熟的玉米。剛下過雨,小路被沖出一道道溝壑。離玉米地還有幾百米遠時,三輪車無法前行,我爸開始用鐵鏟修路。再往上,只能一步步撥開野草叢,探身前行。
天地沉默,惟有鳥鳴和微風偶爾發出響動,一個人把玉米棒子掰下,剝去外皮,露出金黃色的顆粒,后面跟上一個人,把玉米桿砍倒。摘下的玉米,裝進竹筐里,背下山。
大衛一身行頭穿戴整齊,長袖長褲,另外從腦袋到脖子,裹了一塊花花綠綠的圍巾,一戴上鴨舌帽墨鏡,就像花枝招展的007。我們看著他大笑,他不解地問:“有什么奇怪的嗎?”
007出門前往全身上下噴了一通。“我特別招蟲子。”他說,“噢,螞蟻又咬我。”玉米搬回家,吃完飯大家邊看電視邊剝玉米粒。大衛很快繳械投降,舉起手指報告:磨破皮了,同時抱怨無聊。他不解,這份工作,為什么不交給機器做?我爸笑嘻嘻地說:“反正看電視也是閑著嘛。”
能引起大衛感興趣的農活,是傍晚時將曬了一天的玉米粒收回家。慢慢掃攏成堆、裝袋、用手推車運回家,頭幾天,他略微欣慰地說:“我喜歡做這個,什么也不用思考,太好了。”如此重復了三天。到最后一天,干活時我們已不再聊天,空氣中是長久的沉默。機械化、無意識地勞作,在太陽落山之前系緊最后一個袋子。
3
這座少數民族聚集的村落里,至少一個世紀沒出現過外國人。“聽說你們家來了個外國人?”從地里回來的屯委,打電話問:“他不是剛入境的吧?防疫要求……”“他這兩年都在國內,沒出境,也打了疫苗。”我說。
橫貫村子的是一條淺淺的水渠,那里擠滿洗衣服、熱鬧聊天的婦女。看到大衛,她們停住手中的棒槌,強裝鎮定。大衛說:“嗨,你好。”大嬸立刻吃驚地將頭扭到一邊,向姐妹宣告:“他真高啊!他跟我說話了!”“說什么了?”“我不知道!”
作為一名老師,大衛最擅長交往的,還是孩子。下午2點半,大衛準時給孩子們上英語課。教材是書柜上隨便找的一本幼兒園英語繪本。作為語言交換,她們教會了他打中國的撲克牌,他的中文在牌局上得到飛速提高,像孩子們那樣說話:“不要不要不要……”他意識到當自己說出這句中文后,會引起一陣哄堂大笑,便一次又一次抓住機會把它甩出來,再也沒有學會別的中文。
住在我家的這些天,大衛帶了咖啡豆和便攜咖啡機,一邊喝咖啡,一邊用kindle讀《瓦爾登湖》。他說自己不太喜歡上海,因為工作節奏太快,“你們這里跟金邊很像,大家慢悠悠的,享受生活。”
離開前的最后一天,我爸抓了一只鴨子。吃完最后一頓飯,大衛到客廳去稱重,我們聽到他發出一聲慘叫。“不可能!我不應該選在這個時候稱重的。”他跑過來向所有人說。不知什么時候起,那個拘謹的、只顧埋頭吃飯的人,會在飯桌開玩笑,會在吃飽后心滿意足地坐在座位上,看看這個,再看看那個,甚至會說:“一個大家庭一起吃飯,我家以后也要這樣。”
農村勞作想必給大衛留下難忘的印象。回到上海后,他時不時給我們發一些隨手拍的照片,超市貨架上的玉米罐頭、玉米廣告……“我今年恐怕都不會再吃玉米了。”他笑著說,他這個夏天為玉米流過的汗,見過的玉米粒,比一輩子加起來的還多。
熟悉以后,大衛曾問我們“你們為什么要離開北京住到村子里?”也許他是在問自己,為什么我會在這個夏天來到一個與我完全沒有聯系的中國小山村里?
看見他,就像看見幾年前剛搬到鄉下的我們,經歷窘迫、熟悉后的欣喜、疲乏和困惑。“值得嗎?”我問他。“當然值得。”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