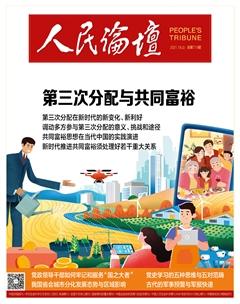古代的軍事預警與軍報快遞
李智君
【關鍵詞】烽火 驛傳 軍事情報 羽檄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五原烽火急:古代軍事預警系統
交通和通信系統,不僅是平衡國土資源空間分布不均的主要手段,也是維持國家大一統的基礎設施,及時準確的軍事情報預警和傳遞尤其如此。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導致自己被犬戎所殺的故事,家喻戶曉。
烽火是中國歷史上傳遞速度最快的軍事預警信號系統。漢代烽火傳遞的速度是每漢時不得低于一百漢里,即每小時不能低于三十公里,實際傳遞速度,遠高于最低速度。烽火報警的信號是以不同數量的火光、煙、標志物等的組合來實現的。“其煙看放時,若無事,盡一時;有事,盡一日。若晝放煙,至夜即放火,無事盡一夜。若夜放火,至天曉還續放煙。從烽放訖,前烽不應,煙盡一時,火盡一炬,即差腳力人走問探知。失堠或被賊掩捉,其腳力人問者即亦須防慮,且至烽側遙聽,如無消息,喚烽師姓名,若無人應接,先徑過向前烽,依式放火。仍錄被捉失堠之狀,告所在州縣勘當。”不僅失堠或被賊掩捉時需要鄰近烽師勘察情況并銜接,遇到惡劣天氣也是。據《居延新簡》載,漢代“匈奴人入塞,天大風、風及降雨不具烽火者,亟傳檄告,人走馬馳,以急疾為[故]。”唐代也有類似的方法,“若晝日陰晦霧起,望煙不見,原放之所即差腳力人速告前鋒;霧開之處,依式放煙。”唐代時,烽火預警信號已大體能傳遞入侵者的規模信息。
盡管如此,烽火也只能是軍中之耳目,豫備之道,且易受敵人干擾,如匈奴人經過多年的觀察,掌握了漢代邊塞烽火信號的規律,不時地釋放假烽火,干擾正常信號傳遞,讓邊塞將士虛驚慌亂一場。因此,準確詳細的戰爭情報,只能憑借政府運營的驛傳系統來傳遞。
六郡羽書催:軍情快遞制度與速度
驛傳,作為傳統中國的主要交通通信系統,不僅集客貨運輸和通信于一體,而且軍政合一。驛傳動力主要以人力和畜力為主,而人畜每行走一段路程,都需要補充能量和休息,因此,歷代都在驛路上每隔十里、三十里、五十里等不同距離的節點,設置了驛、站、塘、臺、所、鋪等機構。無論慢行的客貨,還是急行的官軍、糧草,又或是加急傳遞的最高軍事情報,都屬驛傳業務。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漢晉時期,最快的軍事情報是由持“羽檄”的使者傳遞的。漢高祖劉邦曾以羽檄征天下之兵,未果。可見羽檄是皇帝征召軍人和快遞軍情的憑證。“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取其急速若飛鳥也。烽火與羽檄從漢代起就成了邊塞戰事的代名詞。因此,“胡馬不窺于長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國”就成了國家無戰事、和平安寧的象征。羽檄為征兵之書,軍情緊急,通常是快馬不分晝夜接力傳遞,因此,傳遞速度比每漢時十里的“書檄”要快很多,即日行五百里。五百里是漢晉時期驛馬接力長跑的距離,也是羽檄傳遞的最快速度。
西周時已建有交通通信系統,但將其轉變為大一統國家的驛傳,無疑是秦始皇的功勞。《睡虎地秦墓竹簡》載秦時驛站設置是:“三十里一傳,十里一亭。”即每相隔十里,就要設一亭,為往來驛傳人員與馬匹提供完備的食宿。盡管秦始皇憑借馳道和郵驛,建立了完整的國家交通運輸和通信系統,但秦的國家命運最終還是栽在符璽和驛傳上。秦時,管理國璽、羽檄之類印信的官員為符璽令。李斯和趙高,正是利用了符璽令這個職權,私自截留秦始皇的遺囑,置太子扶蘇和蒙恬于死地,將胡亥扶上了皇位,導致嬴秦二世而亡。正如后人所言:“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殞身,一奸愆命,七廟為墟。”當然,作為國家管理人員,有人借符璽謀權篡位,還有人不惜用生命保護符璽,主持正義。漢因秦制,置符節令丞。《漢書·循吏傳序》云:“昭帝幼沖,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符璽郎取璽,郎不與,光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光壯之,增秩二等。”一正一反兩個案例,可見國家印信正確使用與否,對國家命運有重大影響。
隋置符璽郎,唐承隋制,后因武后惡“璽”字,“改為寶。其受命傳國等八璽文,并改雕寶字。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又改為符寶,從璽文也。”唐的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于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其中符節與驛傳密切相關。“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辨其左右之異,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而在諸多的符節中,“所以給郵驛,通制命”的傳符,無疑是驛路常見的符節。與“所以起軍旅,易守長”的銅魚符不同,傳符是銀牌。《宋史·輿服志》載:“符券。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敕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為竅,貫以韋帶。其后罷之。”
宋初,繼承了唐代的銀牌制度。如太平興國三年所制新牌中的飛龍符和麒麟符,顯然繼承了唐代雙龍符和麟符圖案。有宋一代,始終沒有平定邊疆的割據勢力,戰爭壓力日甚一日,因此建立了軍事快遞業務——急腳遞。急腳遞所用的傳符是檄牌。金字牌為檄牌之一種,也是傳遞速度最快的一種。據《宋史·輿服志》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紅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郵置之最速遞也。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由內侍省發遣焉。干道末,樞密院置雌黃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里,軍期急速則用之。淳熙末,趙汝愚在樞筦,乃作黑漆紅字牌,奏委諸路提舉官催督,歲校遲速最甚者,以議賞罰。其后尚書省亦踵行之,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久之,稽緩復如故。紹熙末,遂置擺鋪焉。”
“御前金字牌,一日數十置。冠蓋何紛紛,排日遣郎吏。”廣泛使用的金字牌,應用效果如何?宋人李心傳云:“余在成都,見制帥楊端明有命召,以丁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降旨,而戊辰正月末旬方被受,是日行才百余里耳。”可見金字牌快遞,在該制度運行的后期,傳遞速度下降很快,只相當于初時的四分之一。紹興末年,擺鋪應運而生。“紹興末邱宗卿為蜀帥,始創擺鋪。以健步四十人為之,歲增給錢八十余緡,以初三、十八兩遣平安報,至行在率一月而達。蜀去朝廷遠,始時四川事朝廷多不盡知。自創擺遞以來,蜀中動搖靡所不聞,凡宗卿劾疏中所言,皆擺遞之報也。”盡管后來因有大量的私人信件托擺鋪傳遞,影響了速度,但也能日行四百里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