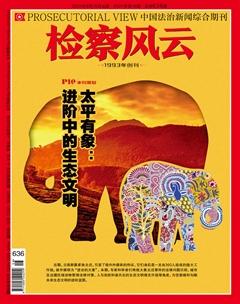劉醒龍的現實主義
直面現實
《檢察風云》:1981年,您是怎么創作自己的第一篇小說《派飯》的?
劉醒龍:《派飯》不是我寫的第一篇作品,在這之前還寫過一兩篇表現青年工人對異性情感的文字。那些文字從未公開過。當年的手稿,有一陣曾經失散,前些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又失而復得。反而是《派飯》,雖然刊登在縣文化館油印的《英山文藝》上,自己卻沒有保存下來。只記得當年寫“國家干部”到生產隊,每天輪流到各家吃飯。某農戶很窮,又趕上青黃不接,輪到他家做“派飯”時,什么菜也沒有,幸好孩子下河玩水抓到一條小魚,好不容易做好一道菜,放在桌上時,一不小心讓貓給吃了,惹出女主人的一番呼天搶地。“派飯”本意是讓干部能更加接近群眾,但有時反而讓干群關系不如人意。
《檢察風云》:您的代表作中篇小說《村支書》《鳳凰琴》和《秋風醉了》都是1992年發表的,之后又創作了引起很大反響的《分享艱難》,再往后又有三卷本的長篇小說《圣天門口》和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天行者》,您因此被批評界認為是新現實主義作家。你是怎么看待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您覺得新現實主義和傳統的現實主義有什么不同?
劉醒龍:我所理解的傳統現實主義作品,往往較喜歡下結論、作預測、好指引,在有意無意間流露出指點江山舍我其誰的味道。我的這種判斷不一定對,但也有許多現成的例子擺在那里。從20世紀90年代起,世界變化的節奏突然加快,而好一點的文學作品是必須將歲月做一番沉淀才能形成的,更不用說經典文學了。那些一見到風浪過來,就急于用文學來表態的,比如“詩歌將死”“小說將死”“鄉村和鄉村文學將死”,結果正好相反,小說和詩歌還在,鄉村更是以“綠水青山”的面貌寓意其恒久綿長。凡是指舊東西的不足比較容易看得清,一種新生的創立自然是對不足的破解,人與現實的不和諧,會是文學新勢力的基本出發點。
《檢察風云》:《鳳凰琴》寫鄉村教師,《天行者》也寫鄉村教師,小說是否有原型?
劉醒龍:當代文學與當代現實發生碰撞時的情景,很難預料,也很難控制。武漢封城戰疫,讓我對早期經歷有了新的認識。如果沒有這段特殊的日子,關于《鳳凰琴》《天行者》原型的問題,不知將來會不會做出明白的回應。作為代表作的《鳳凰琴》,發表之初,在我生活過的故土,相關反響卻不甚愉快。武漢解封之后,回英山縣城給已故作家舉辦逝世三十周年紀念座談會,我才坦承,當年寫這兩部作品,其原型地為英山縣孔坊鄉父子嶺小學。同行的於可訓先生,聞之欣然提筆寫了一篇隨筆記錄這件事。武漢大學的劉早博士還專門寫了一篇《〈鳳凰琴〉〈天行者〉》原型地考》。兩篇文章各有其妙,都令人不勝唏噓。
《檢察風云》:《蟠虺》寫的是湖北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曾侯乙尊盤,寫這樣一部小說是想以此來反思楚文化嗎?創作《黃岡秘卷》是為自己生活的土地樹碑立傳嗎?黃岡和湖北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感覺這兩部作品,冥冥之中與湖北武漢的抗疫斗爭存在某種預兆式的關聯,是不是這樣?
劉醒龍:湖北武漢從地理人文上講,有點曾侯乙尊盤的意味。在2018年4月28日“東湖敘談”和2016年4月出版的《蟠虺》之前,只有相關專業人士才曉得曾侯乙尊盤在青銅重器中的頂級位置。2020年的戰疫行動,讓許多人曉得了湖北武漢在中國地理人文中的重要性。全世界也從湖北武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決戰決勝中,認識中華民族之所以偉大的關鍵所在。在所有人擔憂疫情時,黃岡率先實現感染人數“清零”。如果了解黃岡的民風民情,就不會覺得意外。鄂東黃岡幾百個將軍同一故鄉,黃岡向來有“賢良方正”之說傳世。立世之人,僅有高雅才學是不夠的,還得有很強的戰斗力才行,才能做到治大國如烹小鮮。
“武漢抗疫日記”
《檢察風云》:這次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最新作品《如果來日方長》,寫那段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武漢抗疫過程。您是什么時候決定要寫這樣一本書的?可不可以將這本書視為您本人的一本“武漢抗疫日記”?
劉醒龍:武漢封城初期,也是我們這些城中人感覺最艱難之時,多家雜志和出版社約我寫點相關文字,當時我明確拒絕。一方面因為自己正患眼疾沒地方就診,另一方面也是氣氛太緊張,想要成為文學所能抵達的真正現場,光靠一點腦細胞是不行的,還需要打開門,走出去用自己的神經末梢進行感知。那段時間里,家里也發生了一些事情,最令人揪心的是母親重病,既不能就醫,也無法探視,只好一點點地寫些文字。偏偏這樣的文字是最可靠的,還能像種子一樣,生根發芽,一點點不斷生發開來長成一棵樹,成為一部與眾不同的作品。《如果來日方長》不是由“專業”的記者、作家所寫,是由一千一百萬普通市民中的一個親自寫成,是身陷疫情險境中的一個普通市民為應對萬一而寫的與妻書、與兒女書和致慈母書,也是一個普通武漢市民、普通中國人寫給他所熱愛的城市、他所熱愛的祖國、他所熱愛的時代的致敬書。
《檢察風云》:《如果來日方長》原本是寫給抗疫的一首歌,當時是怎么會創作這首歌曲的?最后又怎么決定用這個標題作為自己這部長篇散文的題目?
劉醒龍:2020年2月中旬,一個朋友受托打電話給我,希望我能寫一首像表現“九八抗洪”的《為了誰》那樣的歌曲。我答應下來,然后寫了。但封城中人所感受的,與封城之外的人感受太不一樣了。事實上,那一陣子,在武漢人的理智中,無論愿意或不愿意,都在做各種“如果”中最壞一種的準備。別人都說來日方長,封城中人只能在來日方長前面加上使人雙淚暗流的“如果”。
《檢察風云》:武漢封城期間,您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樣的?你的一位同行說他非常焦慮,讀不進書,除了關心疫情之外,您日常還做些什么?
劉醒龍:封城的那段日子,是自己人生中最本色的時候,既要做好兒子,關心老母親的狀況;又要做好父親和爺爺,關注孩子們的身心變化;還要做好丈夫,傾聽夫人的聲聲咳嗽,何為相同,何為不同。在做好每個角色的同時,竭盡全力讓被認定為“高危人群”的自己,不給家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從做飯、吸塵到滿世界找消毒用品,到審時度勢給家里換換空氣,到想辦法消滅從馬桶中鉆出來的老鼠,所有這些平時都不是事的事情,都是家里的大事。
《檢察風云》:您的人生中和小說中已經經歷和書寫過很多生老病死,這一次經歷新冠肺炎疫情,再加上您的母親在疫情期間得了重病,您又有什么樣不同的感受?
劉醒龍:封城期間,我在《黃岡秘卷》中寫過的熊家老表悄然離世,曾經是浪漫愛情縮影的二叔也在次生災害中走遠了。老母親熬過了疫情,熬過了疫情之后接連三次病危,今年大年初五凌晨在睡夢中含笑大行。這些經歷讓自己對人生有了不一樣的體驗,說是不一樣,其實也是很普通與很常見的道理:無論我們是如何想、如何做的,這個世界都不可能為某一個人、某一種勢力、某一類文明所獨有,唯一能做好,也是唯一能夠做到天長地久的事情只有兩個字:陪伴!這也是《如果來日方長》所要表達的。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