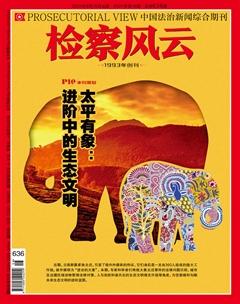大象的隱退與復現
吳凱

在環境史的敘事中,人類與野生動物在時間、空間與種群數量上的動態演化進程,一方面是人與自然關系史中極為重要卻又容易被忽視的一環;另一方面,在“天人合一”的傳統中國自然觀念中,人與動物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和諧相處,也是自然環境整體變化的直接反映。著名英國環境史學家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也有譯者將其翻譯為“象之隱退”)中考察了中國歷史中大象南撤事件。事實上,包括大象在內的眾多野生動物(熊貓、金絲猴、鱷魚等)都在歷史上與人類的博弈中不斷退卻,其棲息地逐漸由廣闊的區域退縮到狹小的空間。伊懋可教授指出“大象從東北撤到西南的這條長長的退卻之路,在時間和空間上與前現代中國經濟發展和環境變遷的情形相反相成”。然而,令眾多環境研究領域專家沒想到的是,在新世紀里祖國云南邊陲的大象又出現了。這次大象的登場,令這個邊疆省份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目光。
進擊的大象
2020年3月,我國云南省一群亞洲象從原棲息地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向北遷徙;2021年4月由普洱市再度向北遷徙,一度到達昆明市,沿途經歷折返、掉隊,時至6月28日,象群依然在峨山縣塔甸鎮附近林地內活動。亞洲象群的遷移,引發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也聚焦了全球范圍內動物愛好者的目光。為了穩妥應對此次罕見的大象遷移,云南北移亞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省級指揮部等多部門聯合工作機制先后建立起來,云南省地方設置食物儲存點,有意識投放大象尋覓的食物以引導其避開城市區域活動,及時調整當地村民分布以避免被象群誤傷,當地林業部門出動無人機對移動中的象群進行跟蹤監視以研判其未來走向。多種技術手段將隱秘在森林中的象群行為原原本本地擴散開來。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公眾一邊驚訝于象群遷移過程中當地政府回應之迅速、工作之細致,一邊也對象群移動給當地村民帶來的干擾、象群逼近昆明城區可能引發的城市管理難題以及象群未來將會向何處去表達了擔憂。
可以說,曾經在人類社會面前“隱退”的大象復現,甚至有日本媒體親切地將此次象群移動事件稱之為“進擊的大象”,象群重現的直接原因是象群所處的自然棲息地生態環境變化,間接原因與當地保護亞洲象的法律與策略緊密相關。而象群移動過程中當地政府部門的應急處置,也需要相應的法律依據支撐。為了將來亞洲象群走向一片真正適合它們生活、真正屬于它們的樂土,也需要更加完備、精細的動物保護法律制度與策略體系。其中,動物保護法律制度體系是象群保護機制的“骨骼”,其不僅僅以法律的形式將平時對于大象的可持續看護資源投入制度化,也為在諸如象群開始遷移等突發事件出現時及時組織力量回應提供了規則依據。管理策略體系則從另一個層面,在法律框架之內為亞洲象保護提供了微觀的、可操作的“工具箱”。兩者相互配合,密集編織出特定區域內特定野生動物保護的法網,為特定種類的野生動物提供制度化、彈性化的保護。
亞洲象群北遷事件中的法律問題識別
從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視角來看,以本次云南地區大象北移為典型代表的動物遷徙將大眾的目光吸引到原先未得到充分關注的人與動物在廣闊地理空間中的互動問題,并以“人象沖突”的形式突出表現出來,也令受關注較少的陸生動物跨境遷徙過程中的法律保護問題呈現在了全社會面前。這種吸引大眾眼球的、極具張力的新聞事件是人類制定的法律對于野生動物變遷的一個高能片段。對于野生動物甚至是植物的保護,在20世紀中葉以前僅僅是為了其經濟價值。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眾多國家過去都制定有狩獵法,以保持人類的狩獵對象——野生動物的繁殖與數量增加,來維護其正常的狩獵秩序,使得野生動物得到有效利用。到20世紀中葉,法律觀念有所改變,人類逐漸認識到野生動植物在作為人類資源為人類提供經濟價值的同時,對保持生物多樣性和維持生態系統平衡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因此,大量狩獵法被廢止或者實質更新,各類野生動植物保護法先后出臺,輔之以中央和地方林業部門的各種配套政策。
本次象群在其途經的云南各地的遭遇暴露了動物養護政策方面的兩重困難:第一重困難在于,很長距離的遷徙必然會跨行政管轄區域,包括越過市或者云南當地的民族自治州邊界、省界甚至是國境線,在此種情況下,脫離了國家設置的自然保護地的野生動物就被暴露在了力度不同的保護之下。在一個有著對于遷徙物種較強的保護力度的行政管轄區域中,遷移中的動物固然是安全無虞的,然而一旦遷徙動物進入一個只有較弱保護力度的行政管轄區域,其面臨的風險就會驟然增大。另一重困難在于,動物的遷徙很難在大規模種群意義上進行,這就意味著大部分的動物越境移動是中等規模或者小規模的,一如本次在云南一路北上的亞洲野象群。動物群落如果不大,未必能夠觸發《突發事件應對法》機制,可將依法應對此類事件的責任限制于各級地方政府;如果動物群落又不小,其活動對于公共秩序和居民私人空間的侵擾,便會產生來自財產法、公共安全法領域的法律后果。這兩重困境都要求我們迅速提煉有效的法律對策。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野生動物保護法》第十八條僅有寥寥數語可供此次象群北遷參照,即“有關地方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預防、控制野生動物可能造成的危害,保障人畜安全和農業、林業生產”。要知道,《野生動物保護法》制定時間較早,彼時對遷移中的動物加以法律保護還沒有引起立法機關的足夠重視。在《野生動物保護法》之外,國務院還制定了《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原林業部1992年發布;國務院2011年和2016年修訂),對具體的行政保護措施作出了規定,而這一部行政法規中,對于遷徙中野生動物的保護依然沒有作出規定。因此,此次亞洲象北遷事件后,動物遷移中的法律保護成為一個嶄新的法律現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法律發展的新的生長點。
亞洲象群北遷事件中的法律對策
在我國目前的立法工作機制背景下,對特定種類的動物提供專門法律保護的立法尚未被列入全國人大以及國務院的立法工作計劃,這種類型的立法也不符合我國既有的立法工作慣例。可以想象,在今后一個時間段內,寄托于從立法方向獲取支持與資源,得到成型的法律條文來使用,并不是一個現實的、可行的設想。這就要求法律工作者在一個特定的經濟社會領域暫時沒有法條供給的條件下,積極使用現有的規則體系來達到保護動物的法律目的。此時我們的考查重點,很可能是需要借鑒《民法總論》中對于人意思表示判斷的理論來營造圍繞以大象為典型代表的野生動物的保護規則體系。作出意思表示意味著對于自身需求的法律表達。此時,大量存在于林業等野生動物保護部門發布的規章、標準中對動物福利保障的要求,就成了可以使用的素材。
“進擊的大象”之所以能夠安然入睡,背后是“法律之手”遞出的橄欖枝
就自身的生理需求方面,大象等野生動物需要環境和食物兩方面的豐容。其中水資源對大象而言尤其重要,水池、瀑布、噴淋設施、塵土浴和泥坑都是重要的環境豐容內容,尤其是游泳可以使得大象獲得更加充沛的精力。在食物方面,和非洲象相比,亞洲象的食物更精細,對于新鮮飼料的需求也更大。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大象與人類一樣,能夠感知到痛苦與恐懼,也有其自身獨特的情感需求,大象的行為是其表達感覺的肢體語言。這些行為具體包括在各自的生活環境中尋找食物、隱身避難、追求配偶以及躲避天敵等。如果在我們對于象群的管理活動中,任何一種大象的自主行為被剝奪(或者說是無法表現),象群成員就無法實現其特定的功能,也無法滿足機體的需要,從而導致大象群體行為異常或者出現生理應激,更加嚴重的,象群本身的健康會受到威脅。就象群的社會特征而言,雄性大象由于性情反復無常,體型、力量巨大,維持社會關系的操作更加復雜,也更加容易對人類造成傷害,這一點在此次亞洲象北遷事件中也有體現。
如果我們希望能夠以對策的方式將現有的動物保護法律規則組合以形成合力,應該從如下兩個方面著手開展工作:第一個方面是需要向上尋求與基礎性、主干法律如《民法典》《野生動物保護法》以及我國加入的野生動物保護公約條文的接口,例如對《民法典》第1248條動物園動物侵權責任的規定,結合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對此問題的認識,可以明悉現階段我國在此議題上的政策導向與規則適用邊界,在可以被允許的范圍內組織法律策略,這是法律策略可能運行的上限和“天花板”;第二個方面是對于諸如《象圈養最低福利標準》等由專業領域人員總結出的行之有效的操作規程中將有利于遷徙中的動物保護的部分遴選出來,組合成符合當地自然環境和行政管理實際的對策體系,考慮到這一類規范大多是規定在象群處于動物園或者自然保護區中平和生活時加以保護,其可以作為對野生動物遷徙保護法律對策體系組織的基線。在此基線上,動物移動時變數多、情感波動幅度大,也需要在基線以上預留更多隨機應變的預備策略,這方面的支持主要來自當地政府的財政、應急管理與多部門協同機制的法律構建。
最后,我們還需要考慮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借鑒域外野生動物遷徙保護法律經驗的能與不能。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野生動物保護法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法領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在大象種群作為瀕危物種之一的整體保護方面,1978年,根據《美國瀕危物種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非洲象被列為受威脅物種。非洲象于1976年首次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的附錄III,并于次年移至附錄II。1990年,鑒于非洲象在近十年間數量下降了接近50%,其被升格列入附錄I之中。同時,美國法律體系中還專門有《非洲象保護法》,但這部法律主要針對的是管制象牙貿易。為了表明在政策上對非法象牙貿易零容忍,美國的幾個州政府實施了更嚴格的規定。在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他們這三次統一執法公開銷毀了從游客、貿易商和走私者手中繳獲的大量非法象牙制品。但是對于大型野生動物如象只在遷徙過程中的保護,美國法的規定同樣是相對模糊的。這也就決定了我們必須自己去探索如何在中國大地上保護我們自己的大象,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
以此次云南亞洲象群北遷事件為標志,我們可以發現自然變化再次早于法律變革,固然可以在當地組織村民自建屏障來阻隔大象,但無法阻隔人與動物、人與自然之間一體的緊密聯系。在這個動態變化的體系中,單純依靠立法機關的法條供給未必是最好的選擇。以上位法的規定及其變動趨勢為工作指針,以現有的動物福利保護的標準、規則中有益于遷徙動物保護的內容為主體,以地方政府和群眾積極應對、多部門配合協作的應急工作方案為背景支撐,中國的動物保護法律策略完全可以在未來更多在中國環境史上曾經“隱退”的動物“復現”之時,向它們伸出來自法律的溫和的橄欖枝。
(本文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學系講師、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