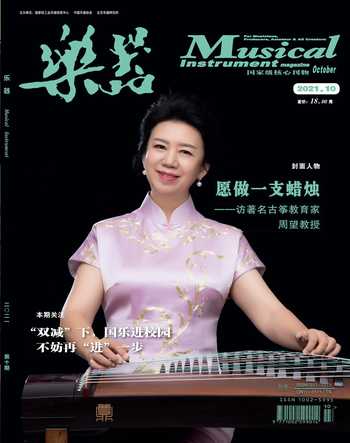音樂奇人李季達(dá)
舒鐵民


提起音樂界的李季達(dá),當(dāng)年延安的文藝界和“前魯藝”(晉東南魯迅藝術(shù)學(xué)校,校長李伯釗)的同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建國后,他卻默默無聞,甚至銷聲匿跡,其人、其事也鮮為人知,實(shí)令人唏噓不已。在耄耋之年,為緬懷這位音樂界的奇才、怪才,僅就半個世紀(jì)前個人的所見、所聞簡述于后,以饗讀者。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以李先念為首的新四軍五師(豫鄂皖邊區(qū)),和以王樹聲為首的八路軍河南軍區(qū)部隊(duì)、以王震為首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隊(duì)等三支隊(duì)伍,根據(jù)中央指令,于11月上旬在豫鄂皖邊區(qū)進(jìn)行合并,組建成“中原軍區(qū)”,下轄野戰(zhàn)軍和地方部隊(duì)6萬余人,駐防于鄂、豫交界的大悟縣境,以宣化店為中心,方圓不足百里,人口僅40余萬的貧瘠農(nóng)村。
隨后,軍區(qū)政治部以三部分人員:原五師少量文藝工作者、隨三五九旅南下的八位延安“魯藝”師生,以及數(shù)十名從大后方來的重慶劇專、育才的學(xué)生和院校文藝青年,共60余人,組建成“中原軍區(qū)文工團(tuán)”,這是邊區(qū)從未有過的如此規(guī)模、人才濟(jì)濟(jì)的文藝團(tuán)體。內(nèi)分戲劇、音樂、文學(xué)、演出等各組,“魯藝”的師生,便成了團(tuán)內(nèi)的領(lǐng)導(dǎo)與骨干。李季達(dá),原“魯藝”音樂系老師擔(dān)任了音樂組組長。我是五師干部,分在音樂組,跟他學(xué)習(xí)器樂。他個子不高,平易近人,一口地道的四川話,說起話來像放機(jī)關(guān)槍。雖是大家的老師,人們并不以老師稱呼,直呼其名,他也不在意。平時,他專心致志于音樂,不問政治。但凡召開黨的會議,都邀請他參加。有人問道:“你不是黨員,為何能參加黨的會議?”他不假思索地說:“我是黨外布爾什維克!”
文工團(tuán)成立后,為當(dāng)?shù)剀娒衽叛萘诵⌒脱砀鑴 斗蚱拮R字》《兄妹開荒》《牛永貴負(fù)傷》和大型秧歌劇《周子山》。演員陣容很強(qiáng),但樂隊(duì)太簡單,當(dāng)時團(tuán)里只有口琴、笛子、二胡、手風(fēng)琴和幾件打擊樂器。此外,李季達(dá)從延安帶出來一把小提琴,因隨軍南下,日夜長途行軍,為輕便,他將琴盒也扔了,自縫了一個布口袋裝著,演出中它是主要的伴奏樂器,代替了秧歌劇中必用的板胡。由于在這偏僻的農(nóng)村買不到任何樂器,李季達(dá)便提出自己動手,就地取材來制作樂器,人們半信半疑。
此后,李季達(dá)將要制作的樂器,一件件的都繪制出來(部分樂器制作圖,早已記錄在他的袖珍筆記本上了,如小提琴、大提琴、十一孔笛等),又親自去找來一個做細(xì)活的木工。再通過組織去四處購買需要的工具、配件,以及不同質(zhì)地的木材。在老鄉(xiāng)家的一間空屋內(nèi),他開起了樂器作坊,整天和木匠呆在一起。我們偶爾去當(dāng)小工,熬拌豬皮膠和打磨半成品。這時,大家才相信李季達(dá)要自制樂器并非夸口。在宣化店不到半年的時間里,他先后制作出板胡(原音瓢椰殼以木質(zhì)材料代替)、三弦、揚(yáng)琴、小木琴、十一孔笛、小提琴和和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大提琴(他曾說要用木頭制作小號)。在琴腹內(nèi)銘記:“中原軍區(qū)政治部文工團(tuán)制作于宣化店某年某月某日”,我們的樂隊(duì)壯大起來了。令人更為驚奇的是,每件樂器他都知道發(fā)音的原理和如何演奏。從此,他也備受大家的關(guān)注。
原來,李季達(dá)從小就聰慧過人,喜愛音樂,且心靈手巧。他童年在重慶,曾自制一把獨(dú)弦胡琴,在街頭奏出動聽的音樂,被一位音樂老師發(fā)現(xiàn)后,涉足樂壇,學(xué)會了鋼琴、小提琴和作曲,還熟悉多種樂器。他思想進(jìn)步,抗戰(zhàn)初期參加了由金滿成、肖崇素等人組織的“重慶文化界救國聯(lián)合會”及其演劇隊(duì),演出抗戰(zhàn)戲劇和音樂,他擔(dān)任指揮。1938年,李季達(dá)到我黨領(lǐng)導(dǎo)的“孩子抗戰(zhàn)劇團(tuán)”工作①,又去西北青年救國聯(lián)合會于陜西涇陽開辦的“安吳堡青年訓(xùn)練班”學(xué)習(xí),結(jié)業(yè)后,被分配到前方二團(tuán)工作。1939年春,經(jīng)中共北方局調(diào)到“前魯藝”任教。翌年,該校與抗大文工團(tuán)在紀(jì)念“五四”青年節(jié)的晚會上,聯(lián)合演出了《黃河大合唱》,為豐富樂隊(duì)的打擊樂,李季達(dá)親自設(shè)計(jì)“制作了一套由十面大小不一、高低音不同的鼓和一套由梆子、木魚、響板、鑼、堂鑼、小鑼等組成的組合式打擊樂器。他一個人,雙手雙腳并用,就能擔(dān)任這兩套樂器的演奏。”(摘自吳因:《唱出中華民族的呼聲——憶<黃河大合唱>在敵后的演出》)1942年5月,“前方魯藝”合并入“延安魯藝”。他在延安的時間不長,仍在各種場合大顯身手。在演出中,他以洋油桶制作低音樂器替代大提琴,用日常生活用品代替打擊樂器。在舞會上,他以鋼琴、小提琴、以及十一孔笛即興演奏等。1944年,他隨三五九旅南下支隊(duì)南下,直到返回中原軍區(qū)。
1946年春,國民黨在“和談、停戰(zhàn)”的幌子下,暗中調(diào)遣30萬大軍,對我區(qū)實(shí)行經(jīng)濟(jì)封鎖和軍事包圍,妄圖消滅我軍,制造另一個“皖南事變”。為此,“停戰(zhàn)三人小組”共方代表周恩來副主席,會同美國馬歇爾的代表白魯?shù)隆顸h徐永昌的代表王天鳴,以及中外記者共40余人,于5月8日從武漢前來宣化店視察。在軍區(qū)司令部舉行的歡迎晚會上,文工團(tuán)演出了音樂節(jié)目和秧歌劇,李季達(dá)用自制的大提琴,特意為周副主席獨(dú)奏了陜北民歌聯(lián)奏。演出完畢,周副主席和記者們到后臺看望大家。他對文工團(tuán)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制作出許多樂器,倍加稱贊,記者們也不斷夸獎這種自力更生的精神。周副主席注意到已經(jīng)是初夏天氣,但李季達(dá)身上還穿著延安特有的灰色粗呢子大衣,許多人還穿著軍棉襖;又問起文工團(tuán)的伙食,大家回答“吃粗糧和野菜”。他隨即對身邊的陪同人員說,要給文工團(tuán)發(fā)一些救濟(jì)(指1943年11月在美國成立的聯(lián)合國善后救濟(jì)總署)物資。不久,文工團(tuán)便吃到了美國白面做的饅頭,穿上了五顏六色的春夏裝。
“停戰(zhàn)三人小組”離開后,形勢并未改觀。國民黨軍對我區(qū)步步進(jìn)逼,修筑工事,搶占地盤,對物資、特別是糧食嚴(yán)密封鎖,已威脅到我軍的生存。又獲悉國民黨軍策劃于7月1日發(fā)動總攻,擬在48小時之內(nèi)全殲中原主力部隊(duì)。6月23日,黨中央指示:“立即突圍,愈快愈好!”26日深夜,文工團(tuán)奉命緊急集合,跟隨軍區(qū)機(jī)關(guān)的隊(duì)伍,靜悄悄地離開了宣化店。
突圍大軍分南、北兩路。司令員李先念和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震率領(lǐng)軍區(qū)主力約15000人為北路軍,從鄂中方向往西突圍,文工團(tuán)隨北路軍。由此,于抗戰(zhàn)八年之后,又拉開了三年解放戰(zhàn)爭的序幕。
突圍中,李季達(dá)的趣事一樁接一樁。
部隊(duì)日夜連續(xù)行軍兩天兩夜后,聚集在一個山谷中,大家席地而坐。神情嚴(yán)峻地李先念和王震站在一塊巨石上,向北路軍進(jìn)行了“認(rèn)清形勢、嚴(yán)守紀(jì)律、誓死也要突出敵人重圍”的戰(zhàn)前動員。王震舉起拳頭高聲問道:“蔣介石要消滅我們,你們答應(yīng)嗎?”“不答應(yīng)!”“你們有信心突出重圍嗎?”“有!”,回聲震蕩著山谷。隨后,為了部隊(duì)的機(jī)動性,所有非戰(zhàn)斗成員就地再度輕裝(出發(fā)前已輕裝一次)。在監(jiān)督人員的檢查和示意下,我們再將身上“多余”的衣物和書籍棄之于地。團(tuán)部還必須將那些心愛的自制樂器、幕布、服裝和燈光器材全部扔掉。這時,有人和監(jiān)督員發(fā)生了爭執(zhí),那是李季達(dá)。只見他雙手護(hù)著那只大提琴,堅(jiān)決不讓扔掉。就個人而言,李季達(dá)的輕裝是團(tuán)內(nèi)最徹底的,他身上沒有背包和掛包,只在肩頭背上那把小提琴,腰帶上掛著一個茶缸和一個自縫的比煙盒還小的皮包,內(nèi)裝一疊袖珍筆記本。這就是他的全部行裝,連被子、床單和衣物都扔了。但這把大提琴,他執(zhí)意要留下來。監(jiān)督人員說:“你現(xiàn)在不扔,到前面的檢查站也通不過的!”李季達(dá)喊道:“我要找王震同志講理……”團(tuán)領(lǐng)導(dǎo)和監(jiān)督員拗不過他,留下了大提琴,由民夫?qū)⑺持下贰9唬?dāng)隊(duì)伍走到檢查站,檢查人員瞅著這個“龐然大物”,要強(qiáng)行沒收!李季達(dá)不再爭執(zhí),一氣跑到司令部,竟然拿來了王震將軍親手簽發(fā)的“大提琴放行”令。
離開宣化店的第三天,隊(duì)伍直奔國民黨自詡為“銅墻鐵壁”的第一道封鎖線——平漢鐵路。蔣介石為防止我軍向西轉(zhuǎn)移,半年來在鐵路沿線的要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據(jù)點(diǎn)和碉堡。我軍為快速突破,分散敵人的注意力,決定北路軍一分為二,從左、右兩翼同時通過,李先念和王震各率一隊(duì)。文工團(tuán)隨王震率領(lǐng)的三五九旅等單位為左翼,從武勝關(guān)以北的李家寨突圍。29日午夜,我們急行軍來到李家寨附近的泥濘小路上,距離鐵路還有4、5華里的地方,隊(duì)伍就開始跑步前進(jìn)。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只看到前面戰(zhàn)友手臂上的一個白點(diǎn),那是為防止夜間掉隊(duì)而統(tǒng)一系上的白色毛巾。平漢鐵路兩側(cè)是一片水稻田,當(dāng)我們接近鐵路時,四周一片寂靜,大家加速向前奔跑。李季達(dá)護(hù)衛(wèi)著背大提琴的民夫,也緊跟著隊(duì)伍。突然,槍聲大作,據(jù)點(diǎn)內(nèi)的敵人發(fā)現(xiàn)我軍在穿越鐵路,向我軍瘋狂地射擊。事先埋伏在鐵路兩端的三五九旅指戰(zhàn)員奮勇還擊掩護(hù),大家不約而同地散開了隊(duì)形,冒著如雨點(diǎn)的槍彈和炮彈,沖上路基,跨過鐵軌,躍入稻田,三三兩兩、跌跌撞撞地沖出了敵人的火力封鎖圈,來到一片樹林中隱蔽。不久,后方傳來嘹亮的軍號聲,表明我左翼部隊(duì)已勝利突破國民黨所苦心經(jīng)營的“銅墻鐵壁”。文工團(tuán)無人傷亡,李季達(dá)和他的大提琴也安然無恙。一位大后方來的青年看著自己滿身的泥漿,風(fēng)趣地說:“我們經(jīng)受了一次戰(zhàn)爭的洗禮!”
李先念和王震的兩支隊(duì)伍,本打算在豫鄂陜交界處的荊紫關(guān)會合,再一同奔向陜甘寧邊區(qū)。當(dāng)我們被敵軍追擊和飛機(jī)的轟炸、掃射下,日夜兼程,在豫西搶渡唐河,險闖丹江,于7月13日夜抵達(dá)荊紫關(guān)時,蔣介石已知道我們的走向,事先派遣機(jī)械化部隊(duì)在荊紫關(guān)堵截我軍,致使兩軍未能會合,從此分開各自突圍。當(dāng)晚,我們被包圍在鮑魚嶺。王震向老鄉(xiāng)了解了敵情之后,決定所有非戰(zhàn)斗員,都準(zhǔn)備拿起槍和手榴彈,于次日凌晨從敵人的薄弱環(huán)節(jié)打出去。這時,同志們勸說李季達(dá),快扔掉大提琴吧,也解放那疲憊不堪的背琴老鄉(xiāng)。后來,我軍這只唯一的大提琴,被扔在山間的一條小河中,無奈地李季達(dá)望著他那“寵兒”孤零零地漂流而去。
18日部隊(duì)進(jìn)入陜南,由于敵方已知我軍的走向。我們是徒步走,敵人是機(jī)械化,故我們經(jīng)常處于被堵?lián)簟?cè)擊和追擊的狀態(tài)。敵強(qiáng)我弱,我們只能繞開走,每天的方位不定,時東時西,時南時北。從早到晚,走不完的路,淌不完的水,爬不完的山。有一天連續(xù)爬了11座山,一些同志掉隊(duì)了。李季達(dá)爬山也有學(xué)問,他杵著一根木棍,上山時走“之”字。大家問他,你為何這樣走?他答:“你們看,這座山的坡度,是30到45度,如直上直下,一定很累。我這樣走,坡度只有5度,如履平地,就不累了。……但我的步伐要快一點(diǎn),否則就會掉隊(duì)!”每到宿營地,李季達(dá)睡覺也不一般。因沒有行李,睡覺時,大家都在稻草上打開背包,鋪上床單,脫下外裝睡覺。他只脫下身上那件自己設(shè)計(jì)的、從右腋下面開扣的長筒夾袍,鋪開便是一床夾被,既可下墊,也可上蓋;再將兩只褲腿內(nèi)縫上的系帶解開,使上、下系帶連接在一起,兩條褲腿就成一只睡袋。當(dāng)氣候寒冷時,他在夾被上再堆放一些稻草來保暖。起床時只要把褲腿上的系帶換回來,穿上夾袍就可以出發(fā)了,動作比我們要快很多。突圍中,由于很少洗澡和換衣,身上都長了虱子,人們戲稱之為“革命蟲”。李季達(dá)連換洗衣服都沒有,自然他身上的“革命蟲”要多一些。每晚睡覺也只能集體地鋪,以稻草鋪地,相互擁擠在一起。某天早上,與李季達(dá)臨鋪的同志用四川話開玩笑地說:“李季達(dá),昨天夜晚,你身上的‘革命蟲’,都爬到我的身上喏!”李季達(dá)面帶歉意,急忙回答:“喔、喔,對不起,對不起,以后不會了,以后不會了。”大家疑惑他以后怎么不會哩?第二天夜晚宿營鋪地時,只見李季達(dá)在他鋪位兩邊,高高地壘起兩堆稻草,然后一本正經(jīng)地對相鄰的同志說道:“我計(jì)算了一下,在一個夜晚,我身上的‘革命蟲’,是爬不過這座高山的,你們可以放心地睡覺。”惹得眾人哈哈大笑。和李季達(dá)在一起,不僅能增長知識,也有無窮的樂趣。在嚴(yán)酷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他常常給我們帶來輕松與快樂。但突圍到陜南后,除了被敵人糾纏,日夜走路,又累又困外,在那窮山僻壤中,也沒有吃的了。雖是玉米成熟的季節(jié),但路旁田間的玉米,已被前衛(wèi)部隊(duì)吃光,我們只能去嚼玉米桿。隊(duì)伍已開始減員,文工團(tuán)團(tuán)長徐苓夫婦已掉隊(duì)被俘,指導(dǎo)員胡代偉也受傷離隊(duì),不知生死。王震將軍本想將文工團(tuán)這批“墨水瓶”(他對“知識分子”的稱呼)帶往延安,而前路會更加艱險。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他決定文工團(tuán)的同志可以自行離隊(duì),并發(fā)給衣物和路費(fèi)。此后不久,我們的李季達(dá)也掉隊(duì)了,幸好被李先念部隊(duì)收留。最后,文工團(tuán)隨三五九旅回到延安的,只有我和海嘯、杜利等6人。
新中國建立初期,李季達(dá)在北影作曲組工作。我因1949年在布達(dá)佩斯參加第二屆世界青年學(xué)生和平友誼聯(lián)歡會,看到匈牙利的民間樂器“欽巴龍”(Cylbalom)和我們的揚(yáng)琴一樣,但音域?qū)挘曇舸螅刑ぐ濉@罴具_(dá)曾教我學(xué)揚(yáng)琴,1950年春為借鑒“欽巴龍”來改革我們的揚(yáng)琴一事,曾幾次去北影請教,后來他給我設(shè)計(jì)了一個新式揚(yáng)琴,有半音,可轉(zhuǎn)調(diào),能奏和弦,有踏板。因工藝過于復(fù)雜,而李季達(dá)又調(diào)往長影,此改革未能繼續(xù)。我到他家時,又見到一件他的“作品”,一個活動的書架,約6層,呈圓柱狀,可整體移動和每層轉(zhuǎn)動。他將常用的書刊放在上面,置于座椅邊,需看哪本書刊,隨手可取。
自他去長影后,我們再無聯(lián)系,遺憾的是竟連他的生卒年月也不知道。近查網(wǎng)絡(luò),得知他先后為兩個制片廠寫了《呂梁英雄》《智取華山》《新局長到來之前》《人參姑娘》等8部故事片和木偶片的音樂。時間截至于1980年。又從網(wǎng)絡(luò)上發(fā)現(xiàn)他1979年2、3月份的手跡,這是寫給中國音樂研究所一位同志的兩封信,其中提到他在研究曾侯乙編鐘的銘文。又寫到:“我現(xiàn)把歷博(歷史博物館)Y332商代陶塤復(fù)制出來了,因測有尺寸,與錄音對證是一致的。現(xiàn)又在復(fù)制Y333小的陶塤,現(xiàn)基本成功了,正在修改音孔后第二次燒制中。”“我想把曾侯乙的磬全部復(fù)制出來,能合(和)編鐘演奏,已經(jīng)問得安徽歙縣制硯工廠之硯石即可制磬。復(fù)制的目的,是為了兩點(diǎn):一是從復(fù)制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問題;一是為了與編鐘合奏。”李季達(dá)寫此信時,應(yīng)已年近古稀,仍孜孜不倦地在音樂領(lǐng)域探索,不僅親手復(fù)制了商代陶塤,當(dāng)1978年震驚世界的我國最完整一套編鐘出土后,他又在研究編鐘和它的銘文,還打算復(fù)制曾侯乙編磬,并暢想有一天能鐘磬合鳴,讓全世界都能聽到2400多年前我中華文明的天籟之聲。
李季達(dá),一位生命不止,創(chuàng)造不息的音樂奇人。
注釋:
①見2014年5期《文藝?yán)碚撆c批評》劉鋒口述,李丹陽整理:“(孩子抗戰(zhàn)劇)團(tuán)里搞音樂的還有李季達(dá),他是個怪才,他一個人可以演奏幾種樂器。它會自己發(fā)明、制作樂器,做過西班牙舞的響板,還曾用木頭做成喇叭形,貼上一張紙,弄出火車嗚-嗚-開過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