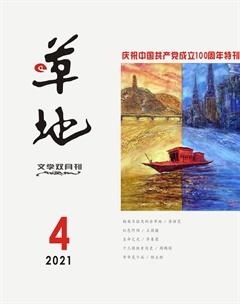我與紅軍“同時(shí)”過(guò)草地
孫貴頌
從西安走時(shí),氣溫?cái)z氏38度。
我和妻利用假期外出旅游。
茫茫夜色中,只感覺(jué)火車(chē)不時(shí)地穿過(guò)一個(gè)隧道,又穿過(guò)一個(gè)隧道;視線(xiàn)一會(huì)兒玄青,一會(huì)兒幽暗,一會(huì)兒又轉(zhuǎn)成鉛灰。這條鐵路,是中國(guó)鐵路史上的奇跡。沿途幾乎全是崇山峻嶺,地勢(shì)極為復(fù)雜,工程艱巨異常。共和國(guó)的鐵道兵和鐵路工人,硬是逢山開(kāi)道,遇壑架橋,在長(zhǎng)達(dá)1085公里的鐵路線(xiàn)上,打通隧道427個(gè),架設(shè)橋梁653座,在隧道里或橋梁上建造了幾十個(gè)“地下車(chē)站”或“空中車(chē)站”,整個(gè)工程歷經(jīng)12個(gè)春秋,1970年7月1日正式通車(chē)。于今我們身臨其境,卻因?yàn)槭峭砩希w會(huì)不到多大驚險(xiǎn),留下些許遺憾。
凌晨到達(dá)昭化火車(chē)站后,便馬不停蹄地趕往汽車(chē)站,坐上了去往九寨溝的汽車(chē)。一路上的勞頓非言語(yǔ)所能道盡。那時(shí)交通落后,我們坐的是一輛解放牌卡車(chē),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搖蕩,一邊是懸崖峭壁,另一邊是水流湍急的白龍江,人似在畫(huà)中游,心卻提到了嗓子眼。一天下來(lái),嘗盡“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的滋味。好在九寨溝的風(fēng)景迷人,算是將一路上的艱辛做了補(bǔ)償。
從九寨溝出來(lái),有人指點(diǎn),可以坐九寨溝至成都的旅游車(chē),途經(jīng)松潘草地,“走”長(zhǎng)征路。這一消息,使我倆陡添驚喜。一咬牙,每人花80元買(mǎi)了一張車(chē)票——這在當(dāng)時(shí)可是很昂貴的。
時(shí)值八月。出發(fā)時(shí)還是艷陽(yáng)高照,酷暑當(dāng)頭。我們這一車(chē)來(lái)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清一色夏裝裹身。我穿短褲背心,妻著短衫長(zhǎng)裙。進(jìn)入草地后,人煙逐漸稀少,頓有荒涼之感。偶爾可見(jiàn)到一些石頭堆,討教同行客方知,那叫“瑪尼堆”,藏語(yǔ)稱(chēng)“朵幫”,就是壘起來(lái)的石頭之意,類(lèi)似于蒙古族的“敖包”,說(shuō)明我們已進(jìn)入藏族居住地區(qū)。藏族同胞以碎石塊疊壘成堆,布上經(jīng)幡,每次路過(guò)時(shí),就在石堆上添加一些石塊,然后繞“瑪尼堆”順時(shí)針走三圈,祈求上蒼保佑。這里人煙稀少,天高地闊,間或出現(xiàn)幾頂帳篷,二三牧民,還有陪伴他們的牛馬。牧民見(jiàn)到汽車(chē),老遠(yuǎn)就招手,就喊叫,我們還之以禮,也揮手,也喊叫。雖然素不相識(shí),心卻在溝通交流。天空忽有蒼鷹盤(pán)旋,妻首先喊:“高山之鷹!”車(chē)廂里的人都伸出頭來(lái),對(duì)著天空大叫:“高山之鷹!高山之鷹!”車(chē)廂里,一派浪漫、歡樂(lè)景象。
不料,再往前走,氣氛逐漸冷卻下來(lái)。雖然門(mén)窗緊閉,但我們卻分明感覺(jué)到寒冷在逼近、壓迫過(guò)來(lái)。一步一步,一點(diǎn)一點(diǎn),令人漸漸招架不住。冷,徹骨的冷。又過(guò)了一段時(shí)間,天空中居然飄起了雪花。雪花紛紛揚(yáng)揚(yáng),似乎很溫柔,很耐心,輕輕地叩擊著門(mén)窗,無(wú)聲無(wú)息地陪伴著我們前行。同車(chē)中有幾個(gè)廣東青年,生平第一次見(jiàn)到真雪,不由激動(dòng)得大呼小叫。當(dāng)司機(jī)在一個(gè)地方停車(chē)讓大家方便時(shí),他們又是拍照,又是打雪仗,可樂(lè)壞了。路旁有青青的小草,小草中間有成群的牦牛,以黑色居多,毛長(zhǎng)長(zhǎng)的,在悠閑地吃草。
牦牛不怕冷,我們怕冷。在車(chē)廂里面坐著,又不能活動(dòng),大家一個(gè)個(gè)瑟縮著,戰(zhàn)栗著,紛紛從隨身的行囊中搜尋衣服御寒——實(shí)在也搜不到什么衣服,除了夏裝,還是夏裝。無(wú)奈之下,我將一件雨衣披在身上,妻子索性把一條裙子套在頭上。這時(shí)最艱巨的任務(wù),是抵御嚴(yán)寒。
在草地上共走了兩天。第一天傍晚到達(dá)松潘縣城。松潘西面,有個(gè)地方叫毛兒蓋。1935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lái)等率領(lǐng)中央紅軍到達(dá)這里。部隊(duì)一面籌糧準(zhǔn)備過(guò)草地,一面耐心等待張國(guó)燾率領(lǐng)的紅四方面軍到來(lái)。其時(shí),張國(guó)燾自恃兵眾槍多,已經(jīng)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他野心大發(fā),企圖篡奪領(lǐng)導(dǎo)權(quán)。8月6日,黨中央在毛兒蓋的沙窩召開(kāi)了政治局會(huì)議,對(duì)張國(guó)燾進(jìn)行批評(píng)教育,決定紅軍兵分左右,經(jīng)草地北上。然而張國(guó)燾竟拒不執(zhí)行黨中央的決議,主張西出阿壩,向青甘邊緣退卻。8月20日,中央又在毛兒蓋召開(kāi)政治局會(huì)議,反對(duì)張國(guó)燾的錯(cuò)誤,堅(jiān)持北上,實(shí)現(xiàn)創(chuàng)建川陜甘革命根據(jù)地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這兩次會(huì)議后,右路軍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lái)等的指揮下,戰(zhàn)勝?lài)?yán)寒和饑餓,勝利通過(guò)草地,到達(dá)四川巴西。而左路軍由于張國(guó)燾的倒行逆施,使紅軍兩過(guò)草地,遭受了巨大損失和痛苦。
第二天,我們開(kāi)始穿越草原腹地。或許由于氣候逐漸干燥的緣故,草原沒(méi)有我們想象得那樣遍地是泥濘沼澤。但天氣依然不好。天空仍不時(shí)飄著雪花。遠(yuǎn)處雪峰連綿,眼前野草茫茫,牛糞觸目皆是。顯然,這里已經(jīng)成了良好的牧場(chǎng)。而50年前不是這樣。當(dāng)年紅軍過(guò)草地時(shí),也是8月,氣候比現(xiàn)在惡劣得多。記得曾讀過(guò)周恩來(lái)的警衛(wèi)員魏國(guó)祿寫(xiě)的回憶錄:“草地是個(gè)氣候變化無(wú)常的地區(qū),有時(shí)天空無(wú)云,烈日曬得臉上火辣辣地疼;有時(shí)陰云密布,疾風(fēng)暴雨猛烈襲來(lái),一剎時(shí)就像到了嚴(yán)寒的冬天。在那越走越難走的草地上,長(zhǎng)滿(mǎn)了齊腰的水草,起伏不平,踏上去像是走在海綿上一樣晃蕩。”當(dāng)時(shí),紅軍后有川軍,前有胡宗南,還要攜帶武器和極少的干糧,又缺少御寒的衣服,在茫茫的草地上跋涉了十幾天。糧食吃完了,就挖野菜,吃草根,喝涼水,咽棉花,有許多同志沒(méi)有走出草地就累死、餓死了。先烈們沒(méi)有想到,在他們倒下14年之后,新中國(guó)就誕生了。半個(gè)世紀(jì)以后,又有一些人坐著旅游車(chē),來(lái)重踏他們的足跡。雖然我們的目的是為了玩耍,但也是出于緬懷和感恩。每一個(gè)人的心中,都對(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所領(lǐng)導(dǎo)的紅軍,懷著深深的崇敬和謝意。
是的,歷史不應(yīng)該忘記。就在第二天,我們到達(dá)了紅原縣。“紅原”二字是由敬愛(ài)的周恩來(lái)總理親自命名,意為“紅軍走過(guò)的草原”。
出紅原抵南,經(jīng)刷經(jīng)寺,直奔成都,離松潘草地漸漸遠(yuǎn)了。
又是艷陽(yáng)高照。
責(zé)任編校:鄔彥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