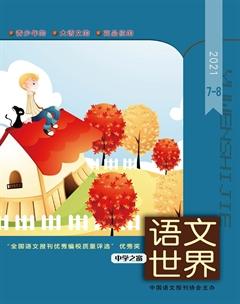原來你還在這里
艾略特有幾句很美的詩:我們不停地探索,所有探索結束時,都是物歸初始,都是此境初識,他依然還在探索。從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至今,我在上海中學的講臺上已經探索了十四年了,一直以為走上教師的崗位,不過是生命中的偶然,然而回首初高中的讀書生涯,又讓人不禁感嘆,冥冥之中自有一股力量,始終引導著我走向那三尺講臺。
我所就讀的初中叫里塘中學,這是一所鄉鎮初級中學,現已經被改成了中心小學。里塘,浙北的一個小鄉鎮,在上個世紀90年代,和絕大多數農村鄉鎮一樣貧窮落后。然而,這個小鄉鎮、這所鄉鎮初中卻以人才輩出在當地聞名遠近,每年都有六七人考上縣里的最高學府長興中學,這是當地人極為自豪的一件事。這里之所以重視文教、文脈綿延,我愿意將原因歸結于歷史上的一位名人——范蠡。傳說范蠡歸隱之后在此地開塘養魚,并撰寫了著名的《養魚經》,也正因此,此地取名為“蠡塘”。蘇軾在《書韓魏公黃州詩后》有這樣一段話:“《詩》云:‘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于用?”若把范蠡比作“金錫圭璧”的話,我們這些“瓦石草木”是受其恩澤的。
簡化字推行之后,“蠡塘”改成了“里塘”。我曾為此憤憤不平,還寫了一篇小文章。這篇小文章竟然得到初一語文老師施桂敏老師的垂青。施老師是學校的教導主任,字寫得很瀟灑,她在我的作文本上寫了八個字:實為佳作,孺子可教。為此,我得意了好一陣。自此,施老師似乎也把我當得意門生了。她不僅在課堂上朗讀我的文章,還多次讓我登上講臺給同學們講解習題與文章之法。這對我是極大的觸動,一向性格內向的我怎么敢站在講臺上給同學們上課!看著兩額出汗的我,施老師笑笑地向我點點頭。那笑容瞬間融化了我的緊張。
初三時,施桂敏老師不再教我們,我們迎來了一位年輕帥氣的語文老師陳偉忠老師。陳老師對文言文非常重視,他不僅讓我們背熟課本上的每一篇文言文,包括現在都還能成誦的《岳陽樓記》《小石潭記》等經典名篇,而且還印發《古文觀止》的一些名文拓展我們的視野。是陳老師,讓我第一次知道了《古文觀止》,帶領我逐步走進古典文學的世界。那時給學生印發課外文章真非易事。當時的里塘中學里并沒有現在司空見慣的打印機、復印機,唯有一臺老式的油印機。印給學生的學習資料,必須由老師親手刻寫蠟紙,然后在油印機上一張張印刷。有一次,華東師范大學的趙志偉老師說起年輕時刻寫蠟紙,我笑說我也刻過。趙老師很驚訝:新強,你這個年紀的人也刻過蠟紙?是的,我刻寫蠟紙的經歷,也與陳偉忠老師有關。初三畢業之前,我參加了長興中學的提前招考并被錄取,這樣就不用再參加中考了。在畢業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我賦閑了。這時陳老師交給了我一項光榮的任務,幫他出題目,并刻寫蠟紙。刻蠟紙,是要手頭功夫的,運力要適宜,太重容易破紙,太輕又印不出來。沒有經過什么訓練,我居然勝任了這份工作,不知道冥冥之中是否已經規定了我未來的方向。
進入長興中學讀書,是當地孩子的最大夢想。第一次走進長興中學,我就被震撼了,竟然是那么大的校園。后來我知道占地僅50畝。可惜當年的校園也不在了,學校在我畢業的次年整體搬遷到現在的新址,據“百度”上的信息看新校園占地216畝。值得欣慰的是,原校址內的大成殿還在。大成殿和其后的明倫堂是長興的孔廟,是歷代學宮。大成殿前有明清28通碑刻,在大殿的后墻墻基上鑲嵌石刻3通,分別為“萬世師表”碑、“至圣先師孔子贊并序”碑和字跡清晰可見的“康熙十五年”碑。引領我去認識這些碑刻的正是語文老師徐明學老師。在當時的縣城教育中,徐老師是比較開明的老師,他不只是要求學生做題,也鼓勵學生閱讀。正是在徐老師的指引之下,我把學校內的大成殿當作了一處私密的讀書之所。上學日的午休,我會跑到大成殿前的一個角落里讀書,記得當時正迷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看著《文化苦旅》,摩挲著一旁漫滅的碑文,不免激起少年人的激憤。周日,因為住校不回鄉下家里(那時六天上課,唯有周日休息,家離縣城較遠,一般一月回去一次),大成殿前的幾處角落更是我終日盤桓之所。
說起碑刻,記得徐老師在教授歸有光的《項脊軒志》時,自豪地告訴我們歸有光做過長興縣的縣令,長興縣博物館內有一塊碑刻寫了《項脊軒志》。但可能是我聽錯了,那個周末我在長興縣博物館內找了好久,并沒有找到《項脊軒志》的碑文。后來在館內老師的指引下,我倒是找到了一塊叫《圣井銘并序》的碑,碑是斷碑修補而成,碑文最后隱約可見“吳郡歸有光撰,淮陰吳承恩書”。“吳承恩”,不就是《西游記》的作者嗎?一塊斷碑竟然牽連著中國歷史上兩位偉大的文學家,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大發現。回校之后,我立刻興致勃勃地給大家講當天的發現。彼時的意氣,不知當年的室友們還記得嗎?
徐明學老師做了我三年的高中語文老師,也是我高二高三的班主任。高一升高二分文理科時,我毅然地選擇了文科班。高一時的班主任李建新老師知道后,遺憾地對我說:“怎么選文科呢,讀理科以后有更大的選擇面。你這次期末考試考了全年級第9名,選文科可惜了!”彼時的我正沉浸在歸有光、吳承恩等先賢的故事中,總覺得斯文不喪,我輩當有所作為。一個做著虛幻文學夢的男孩子哪里聽得進李老師中肯的建議。這樣,我就到了徐老師做班主任的文科班高二(12)班。
到了徐老師的班里,徐老師對我頗為看重,有一個場景至今依然清晰在目。初一開始,我爸媽就都在深圳的制衣廠打工,常年不在家,我是那個時代的留守少年。有一個周日,我回到了里塘會頭村的外婆家。那天臨近中午時,一個男人身穿帶著泥點的黑色皮夾克,戴著頭盔,騎著摩托車沖進了院子,大喊:樊新強在嗎?我出門一看,是徐老師!徐老師一看是我,滿臉笑容地說:“你爸媽不在家,我來看看你!”我呆在那里,邊上的二表哥趕緊請進家里,并囑咐大舅媽殺雞燒飯。徐老師揮手忙說:“不用殺雞,我肚子倒是餓了,有什么我就吃什么。吃完了,還要趕回去。”外婆家離縣城大約有35公里,不像城市有大路,有門牌,也不像現在有導航系統,農村歧路繁多難走,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徐老師是怎么找到我外婆家的。
徐老師對我的看重,還在于他期待著把我送進北京大學,因為當時的長興中學已經多年沒有文科生考進北大了。有一次,在校園里,遙遙地,有一個小個子男老師向我招手。走近一看,原來是肖惠康校長。肖校長拍拍我的肩,說:“你叫樊新強吧?我聽你們徐老師說起你,加油哦!”我點了點頭。這是我唯一一次與長興中學的校長對話,然而我竟然一句話也沒有說。徐老師還和各位任課老師商量著幫我補齊短板,英語顯然是的。于是,我走進了英語老師蔣亞琴老師的小班里,她免費幫我補課。每個周日的晚上,在蔣老師家的小閣樓里,我就跟著蔣老師學習《新概念英語》。蔣老師身材微胖,中氣很足,洪亮的聲音在小閣樓里回蕩,也回蕩在我永遠的記憶里。
雖然有各位老師的愛護加持,當時懵懂的我卻更愿意在文學的世界中游蕩。記得高三一次月考,我忘了參加上午的歷史考試,竟然在寢室里睡過頭了。因為前一天晚上,整個通宵看完了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打著小手電,縮在被窩里,翻到最后“維爾福發瘋,基督山實現了全部的復仇計劃”,心中竟然暢快得不能自已。
后來,北京大學自然是沒考上!我的中學時代結束了,我的文學夢也結束了。
到了杭州、上海念書之后,一會兒想做記者,在《文匯報》實習過;一會兒想做律師,在大學里輔修了法學的雙學位;一會兒想做公務員,曾去參加了香港中聯辦的公務員面試并進入最后一關。兜兜轉轉,似乎都不如意。
直到上海中學來校招聘,很隨意地投了一份簡歷,很隨意地參加了一次試講。試講的課文是諸葛亮的《梁甫吟》。站上講臺的那一刻,我忽然感覺自己回到了初中施桂敏老師的教室里,又好像回到了大成殿前石碑邊上。那一課應該是講得不錯的,上海中學選擇了我,我似乎又找到了自己。
十四年來,驀然再回首,你還在這里。
聽“生”說感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王國維將這句極美的詞引在《人間詞話》中,是為治學的最高境界。樊老師一篇《原來你還在這里》,似與這百年來的著作遙相呼應。時間與空間在此交匯。
人們總是感嘆物是人非。唐代的劉希夷寫下“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明代的歸有光在《項脊軒志》里寫“今已亭亭如蓋”的枇杷樹,不知是不是也和劉希夷的這句詩取得了跨越時空的共鳴。時間抓不住空間的維度,空間消磨成時間的碎片,感嘆時間之鏈與空間之鏈的脫節,是自古以來的情節。
然而,在樊老師這篇傳記式的敘事文章里,我卻看到了另一個感受時空的角度。十四年來,兜兜轉轉,那個“做著虛幻文學夢的男孩”回到了三尺講臺。冥冥之中時間得到了一場洗禮式的輪回,時空的流逝不再只是割裂的悲戚與感傷,卻恰在燈火闌珊中,在氤氳青煙中,輕輕叩響往昔的回音,升華到生命的禮贊。
樊老師是一位有故事的老師。
如今,他在講臺上給我們講歸有光寫《項脊軒志》,給我們講高三在長興中學苦樂并存的日子,比如,他用當時他一周六天上課,只有周日休息,一般一月回家一次來勉勵同在高三艱苦學習的我們。這一切細細想來,又何嘗不是對他曾經的中學時代星星點點的回應呢?一個人最真摯的生命體驗能夠經由文學的筆墨悉數記下,又融匯于語文教學的底蘊之中,何嘗不是一種傳承,對曾經赤誠初心的堅守與踐行?
我想,樊老師一定很珍視這些他自己中學時代的故事,甚至因為長時間文學性的、詩性的揣摩,他一定流連著這期間的片羽時光。最終,他回到了時空開啟的起點,回到了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三尺講臺。
這次,他掙脫了自古以來時空注定難以交匯的詛咒。這次,他成為了我們中學時代的啟幕人。
(上海中學 張詩穎)
物歸初始,此境初識。樊老師以這篇文字帶領我們跨越荏苒時光,回憶他求學年代的點點滴滴,深深觸動了我。文字是絕對誠實的東西,若非親臨體驗蘊含在文字中的真摯情感,是無法想象如今滿腹經綸、舉重若輕的樊老師少年時竟是一個因半夜讀書誤了考試的“非主流”學霸的。但正是這樣一個個生活中的小細節串聯起了樊老師完整的成長脈絡,使我能無意中撞破光陰的帷幕,一睹他少年時書生意氣的風采。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靜水流深,亦能昂揚。樊老師向我們分享的更多是他在少年時所遇見的老一輩教師們,他們當年在鄉鎮中學的生活處境與劉慈欣筆下的《鄉村教師》大抵類似吧。然而他們仍在治學上各具特色,并都以極大的熱情和關心呵護著學生的成長,在靈魂層面指引初出茅廬的他們走上人生的正軌。從樊老師深沉地流露于字里行間的對教師這一職業的熱愛,我們得以再次窺見樊老師在少年時就已深埋于心的那個關于傳承的承諾。而如今,樊老師也毫無疑問更好地擔當了這樣一份教書育人的責任。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他接過了老師們的期許,將教育的薪火繼續傳承。
平日在三尺講壇上侃侃而談、用三寸粉筆寫出一手好板書的樊老師,今天像朋友一樣分享了充滿書生意氣的少年事,也道出了教師之所以為教師的真諦。紅燭啊,莫問收獲,但問耕耘!
(上海中學 胡 迪)
樊老師是一登上講臺就可以抓住我們的心的,他的淵博、純熟、老練讓我們折服。我們卻更驚異于樊老師不時顯出的“少年氣”:是講述重耳人生選擇時的慷慨激昂,是評點乾隆“文人意趣”時的神氣,也是回憶通宵閱讀忘記考試時快意的容光。無數瞬間迸發出的少年人的活力,竟與樊老師一貫的深沉調和甚佳。讀罷樊老師的文章,我終于了解到這份情懷來自何處,也對樊老師獨特的人格魅力有了更深的了解。
樊老師的氣質與中國古典文學無疑是很契合的。“斯文不喪,我輩當有所作為”,在樊老師身上我們能看到古代士人的才情和氣節。他不只是教書的匠人,他的洞見總能在三言兩語中啟發我們,將我們引向考試之外更廣闊的天地。他在《困教錄》中的思索,這是他在教學上實實在在的追求,讓我們看見他的嚴格與細致,看見他的原則和要求,看見他把自己視為學人,孜孜不倦突破自我。樊老師少年時在大成殿讀書,在長興縣博物館尋碑文,文字的原始魔力為他搭起通往歷史、通往亙古的橋梁,承繼斯文的志向大概就此生根。綿延文脈的滋養造就這樣出色的老師,我們能如草木受老師恩澤,這是緣分,是我輩的幸事。
學校里掛有樊老師的書法作品,扇面兩幅,“清”“雅”二字,正如其人。正是這樣一位儒雅隨和的謙謙君子,將他少年的夢傳給了更多的人。
(上海中學 高培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