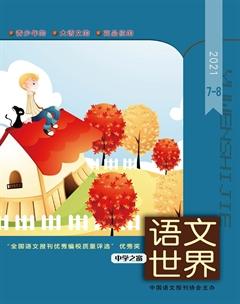成了知識分子的蘇東坡
鄭朝暉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
詩歌寫到宋代,對景物具體描摹的功能和目的都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以往的詩歌以能夠生動展現事情物態為能,如果偶有哲思之妙,也是自然天成。而宋人寫詩詞,似乎更在意細膩的哲理思索和人生體驗,其感人處常常不是展現出來的情境,而是言辭中所體現的哲思與體會,所以常常將對事情物態的描摹放到點綴的地位。宋代經濟發達,普遍的生活水準較高,衣食富足的時候,情感體驗往往細膩入微,也自然很容易打動后來的讀者。待到宋人之后,經濟的衰退,異族的入侵,文化的嬗變讓人很難如此從容細致,哲思體驗不如宋人,描摹情態之功又遠遜前人,所以整體上的詩歌創作,也就不免每況愈下了——當然這只是從大的趨勢上說,并不否認歷朝歷代都有天縱奇才、卓然出塵的詩人詞人。
蘇軾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一個不世而出的人物,他的高妙之處就在于,他的詩詞,如若專注摹情寫物,高處不遜前人,廁身唐人之中,自可顧眄生風,而一旦他開始表達人生感悟,似乎也就沒有別人什么事了,而所有這些又常常顯出不經意的輕松與隨意。
蘇東坡的人生經烏臺詩案一獄,就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以往他的人生追求似乎和別的文人差距也并不太大,烏臺詩案之后,尤其是他被流放黃州之后,他的內心對于“致君堯舜”似乎已經興趣不大,所思所為大概也就是求“安心”而已了。當然,這個變化也還是有一個過程,我們今天讀的這首《臨江仙》,大概就是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的。
東坡是蘇軾在黃州開墾的一片荒地,他還在那里修造了“東坡雪堂”,并從此自號東坡居士。這首《臨江仙》就是記錄了蘇軾從東坡雪堂暢飲之后回家的經歷。因為回家晚了,童子已經熟睡,怎么叫門也不開。這時候蘇軾就表現出了人格中那種通達坦然的特點——既然叫不開門,不妨就倚著竹杖聽聽大江濤聲吧。其實人們在自然里“極視聽之娛”常常是會產生人生之感慨的,這一點只要回憶一下《蘭亭集序》就知道了,東坡作為一個文人,自然也是如此,這一聽江聲,自然就引發了他深沉的人生感慨。他所感慨的是,自己不能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從仕卻被世俗的追求所困然,什么時候能夠像這平靜的大江一般,讓自己蠅營狗茍的心思平復下來,寄情山水,在自然的懷抱里度過自己的余生呢?
東坡這首詩,是以人格取勝,是以人生的感悟取勝的。直接寫自然景物的大概就是“夜闌風靜縠紋平”,而且這樣的景物描寫也只是作為作者抒發人生感喟的附庸而已。這首詞最吸引人的地方,應該是蘇軾所表現的人生態度。“長恨此身非我有”,這是哲學上所謂生命主體對于“自在自為”的期盼,是遠超當時時代的士大夫階層的認知的。自屈原以來,中國的士大夫都是將自己的人生意義寄托在了君王的身上,即便是像天縱奇才的李白,也曾經是想“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他們的人格價值是依附在君王身上的,即便有時候表面是為家國,內底里卻還是為君王。但是經歷了烏臺詩案的蘇軾似乎看清了人生的本質,提出了我身應該“我有”的觀點,這是一種人格上的自立的呼聲,非常了不起。
其實對獨立人格的追求,也并非是從蘇軾開始的,魏晉南北朝的時候,也有不少文人學者有著類似的態度,但他們常常是以破壞、反抗、高蹈的方式來體現自己的人生追求。東坡則不然,他江海度余生的暢想,堅守的是此生此地,這是難能可貴的。
所以,結合蘇軾后來的經歷,似乎也能從“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之中讀出了一點別的意思。
江海,或者江湖,在中國文人的語言系統中,是與“廟堂”相對立的地方。身在江海,心存魏闕(代指朝廷),是很多失意文人的心理狀態。歷史上固然也有文人在各種場合表現自己想要歸隱田園的意愿,其實無非是在君王面前惺惺作態而已。但是,東坡的這兩句,是和“長恨”“何時”相關聯的,是真切地希望人生不必以廟堂為指歸,而能夠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身份去實現真正屬于自己的人生。像蘇軾這樣有強烈的自我意識的封建士大夫,在那個時代是很少見的。更難能可貴的是,蘇軾不僅有強烈的自我意識,還積極以自己的才能扎扎實實地去做切實的工作,但不再是為君王,而是為實現自己的人格追求(“我有”)。從這個意義上說蘇軾可以說是一個具有現代知識分子氣質的傳統士大夫了。
從這個意義上就能夠很好地解釋,蘇東坡在此后的人生中雖仍然屢經躓踣,而猶劬勞殷勤的原因,因為在他的信念中,皇帝已經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