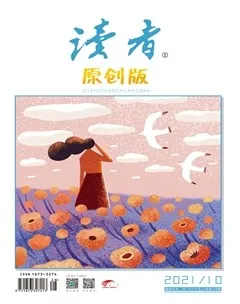江城涪陵
樊北溟
一
“你知道涪陵師專嗎?”聽我問起這個,司機大哥從后視鏡里驚訝地看了我一眼。如今的長江師范學院,其前身就是涪陵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但這是十幾年前的舊事,一個外鄉(xiāng)人似乎不應該知道。
汽車正在平坦的國道上快速通行,兩側便是連綿的群山。山勢很陡,夾著公路迤邐向前,只有置身其中,真真切切地走上那么一遭,才知“兩岸連山、略無缺處”絕非一句空言。山下即是浩蕩的烏江,水流滾滾,遠看有色,近聽有聲,似乎在為行進在這山、這路上的人,奏響激昂的背景音。時有大橋橫跨其上,巍然地屹立著,像在宣示其有不小的決心。
“涪陵師專很有名啊,被寫進過書里的。”
聽到我這么說,司機大哥滿意地勾了勾嘴角。
“我女兒就在涪陵師專讀書,哎呀,罵了她多少回,還是應該考到大城市去,見一見世面。”
伴著我們有一搭無一搭的交談,汽車穿過了好幾個隧道。手機屏幕亮起,信號仍然是滿格的,讓人覺得安心。我這才意識到,這里并不是山隨路轉,而是人們硬生生地將這山掏出了幾個洞。即使在今天,涪陵仍算不得一座大城市,許多人依然寄希望于能走出去,探索更廣大的世界。
二
涪陵古稱“涪水”,因巴國先王陵墓多葬于此而得名。現(xiàn)如今它以“榨菜之鄉(xiāng)”聞名于世,是一座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濱江城市。涪陵歷史悠久,早在2000多年前,涪陵為巴國都城,秦、漢、晉時設枳縣,自唐代以來一直為州所在地。
不過我第一次知道涪陵倒不是因為榨菜,而是因為作家何偉和他的那本《江城》。20世紀90年代,28歲的美國人何偉從重慶乘慢船來到涪陵。他在涪陵師專教了兩年英文,并將這段經(jīng)歷寫進了《江城》一書。
“涪陵沒有鐵路,歷來是四川省的貧困地區(qū),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會去。”
2001年,也就是這本書在美國出版的時候,重慶至涪陵的高速公路通車了,一條鐵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沒有人坐船去涪陵了。如今,眼前的景象顯然和書中的描述對不上了,而這一切只用了不到30年時間!從涪陵去重慶市坐動車只需半個小時,普快火車只消一個小時,它們可以幫助人們迅速實現(xiàn)城市間的自由流動。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周末驅車來到涪陵,參觀武陵山大裂谷、大木花谷和白鶴梁水下博物館。
《江城》一書中,何偉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專門描述白鶴梁周邊的風土人文。其中,一對石頭鯉魚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頭鯉魚起初的目的乃是功用,而非藝術性的。對江上的船只來說,冬天乃是最危險的。當危巖和淺灘因低水位而暴露出來時,駕船經(jīng)過涪陵的船長可以觀察白鶴梁,將水位和雙子魚相比較,從而預測出前方江面的情況。石頭鯉魚的位置不變,而江水總在波動;當?shù)厝死斫馑鼈兊南嗷リP系,而這成為長江每年的固定模式。”
過去,這對石頭鯉魚被刻在長江波動的水線位置上,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人們就是憑借這種樸素的方式,來判斷水位和水流的。而這一看,就是千年。如今,這對石頭鯉魚早在三峽大壩竣工前夕,就為防止被水流磨蝕而遷走,如今人們能在白鶴梁水下博物館里一睹它的風采。歷史滄桑千載,正是石頭鯉魚、《江城》以及更多的文字和文物,為涪陵的發(fā)展變遷添加了生動的注腳。
“我在這兒沒有過去,而我的工作至多只有兩年。可是這兒的語言是豐富的,既回響過去又預示將來;而且時時提醒我,對住在這兒的人來說,時間就像手風琴一樣,過去與現(xiàn)在是可重疊的。福克納曾經(jīng)說過,過去并沒有真正過去—仍然在一串串的語句中顯露出來。”
在涪陵,我感受到過去與現(xiàn)在的重疊。
三
“你小的時候知道這個地方嗎?”在車上時,我好奇地詢問司機大哥。我以為當?shù)厝藦膩矶际切恼詹恍刂獣?16工程的存在。
“怎么可能!都是2002年解密了以后才知道的。”
自從1966年涪陵白濤建造中國第二個核原料工業(yè)基地—“三線建設”進洞的原子能反應堆及化學后處理工程(代號“816工程”)—以來,白濤這個地名就從地圖上消失了。
“凡是以數(shù)字‘8開頭的代號,都和‘核沾邊。這個洞是沒建完、沒使用過的,所以才能帶大家來參觀。”這里的向導向我們解說道。實際上,“816工程”即為制造原子彈提供核原料的地下核工廠 ,是目前國內唯一對外開放的核工程。“816工程”主體洞體高79.6米,總長24千米。作為特殊時期的歷史產(chǎn)物,整個項目于20世紀80年代被叫停,20世紀90年代以后就被完全廢棄了。“816工程”是中國三線建設這段不可磨滅的歷史的重要代表性工程。
“我們現(xiàn)在在6樓,上下還各有6層。”向導帶領我們從路邊一個毫不起眼的洞口進入,從外觀來看,山體絲毫不見工程的痕跡,誰承想,內部竟然別有洞天!盡管向導的語氣顯得有些輕描淡寫,但是對置身其中的參觀者來說,已是難以描述的震撼了。
“大家跟緊,里面地形復雜,大小入口幾十個,千萬不要私自走開。”向導的聲音仍在繼續(xù),而我的心神早已飄遠了。洞內縱橫交錯不說,各種電機、水泵早已銹跡斑斑。洞內氣溫很低,濕度很大,盡管舉架很高,但仍讓人不自覺地感到瑟縮。
沿著長長的過水通道,我們參觀了工廠的核心區(qū)域—位于地下的核反應堆,向導還為我們介紹了整個洞體的通風設施。想不到,來的路上遠遠望見的一根毫不起眼的煙囪,竟然就是主要負責洞內通風的!這讓我由衷感嘆三線建設者的智慧和付出。
四
從“816工程”遺址出來,始終等不到回市區(qū)的公交車。眼看著太陽偏西,若再回不去可就麻煩了。情急之下,我攔住一輛過路的摩托車。騎車的是個當?shù)厝耍目谝襞梦乙活^霧水。他看出我當下的困窘,于是二話不說,一擺手就讓我上了車。
一路上,摩托車司機不停地向我介紹著什么,但由于風聲太大,他的口音又很重,我聽得十分含糊,只好一路“哦”“這樣啊”敷衍地應答。我一邊在心里對司機慷慨的行為由衷表示感激,一邊也在暗自盤算著等會兒要支付多少車資才算合理,而對于來時路上那些令人驚喜的群山、江水和大橋,再也無法分出精力來欣賞它們了。
“就在那兒,快跑幾步,那個車可以回涪陵市區(qū)!”摩托車忽然在路邊停了下來,司機指著不遠處的公交站臺,焦急地對我說。
“快跑!快跑!車快開了。”司機又沖那邊揚了揚手,我這才反應過來,急忙下了車。慌亂中,我甚至來不及好好道謝。我連忙掏出手機,回身沖著還在擔心我趕不上車的司機拍了幾張照片,并大聲感謝。我并不知道這位司機的名字,但是他的善意與溫情,卻作為涪陵這座城市留給我的記憶,被一并封存下來。旅途中,正是這些陌生人的善意幫助我們走得更遠。
青山高高、江水浩渺,難忘的涪陵,從過去到現(xiàn)在,這里的人們從未停止過書寫屬于它的精彩。
- 讀者·原創(chuàng)版的其它文章
- 搟面
- “躺平”時警惕發(fā)生“踩踏事故”
- 你被朋友背叛過嗎
- 詩人的世俗生活
- 開學日
- 那些“災難”真的會發(fā)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