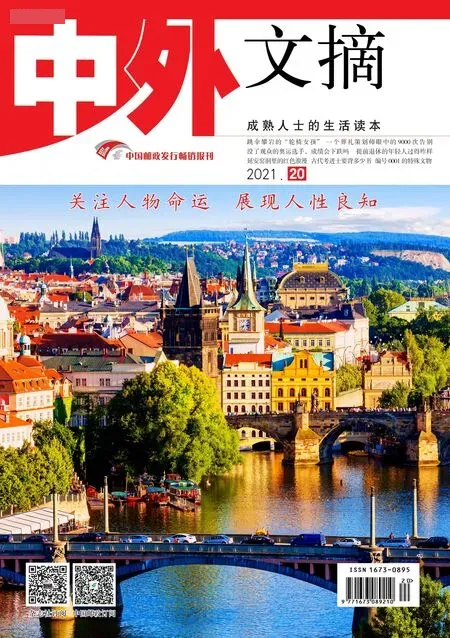我的同事不是“人”
□ 張 來
不想成為工作機器
干了半年后,周偉(化名)決定離開日復一日的流水線工廠。
2019 年初,因校企合作,周偉被派到廣州一家演藝設備制造企業的燈具組裝流水線上。“每天從早上八點半站到六點,晚飯后還需要干到十點,大小周的周六,也時常加班。”深思熟慮后,周偉繼續讀完了大專,并找到了一份電商企業的運營工作。每月5000 元的工資,僅比工廠多了幾百塊。但坐在寫字樓里的周偉,明顯比以前活潑開朗許多。
張玲(化名)是廣州一家制造業企業負責招聘的HR(人力資源),她說近幾年來的工作越來越難做。“年輕人都不太愿意做普工,覺得是廉價勞動力。”5000 元左右的普工工資,在珠三角制造業中已算比較高的,但對95 后、00 后來說,吸引力并不高。
而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招工難度又有差異。江林(化名)是東莞一家電子廠的負責人,手下管理著六百人。與鞋廠、服裝廠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不同,過半崗位的招聘要求并不低:大專學歷以上,同時具備設備維修經驗。收入也自然不低,通常可達萬元。但這些具備一定學歷和經驗的技術人才并不好找。更讓他頭疼的是,包裝、搬運、檢查等崗位的流動性更大。“現在招工人基本很難招到固定工人,多是臨時工,但臨時工平均下來也多是干一個月就走了。”他坦言,工人因為工作重復、枯燥、技術含量低就離職,但產品、工序是多年摸索出來的,短期不可能改變。
為什么現在的00 后不愿意進工廠了?在知乎的多個問答帖子下,回答基本類似:日子極其枯燥、無聊;時間長了就是個機器,如同行尸走肉。
機器人不會離職
一邊是逃離工廠、不愿成為工作機器的年輕人。而另一邊,流水線工廠里,永不疲倦的機器人開始取代了他們。
江林的工廠已開始使用機械臂,如果未來機器人的成本下降,并且能夠很好地適應現有產業,江林表示會優先考慮機器人:“不用擔心效率,不用擔心它會離職。”
楊思明(化名)是佛山一家汽車配件企業的負責人,早在2019年他便投入2050 萬元引入工業機器人,進行智能化生產線改造。巨大投入之后,他也收獲了可觀的回報。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間,部分外地員工一時難以復工。但由于生產線進行了智能化升級,人工依賴不高,企業業績逆勢上揚。
早在十年前,郭臺銘就在富士康提出“百萬機器人計劃”,即在5 到10 年 內裝配100 萬 臺機械手臂,取代生產線上的大量工人。2018 年,郭臺銘再次語出驚人:“富士康將于5 年內裁員80%,如果做不到,那么10 年肯定可以。”
富士康不是孤例。2015~2018 年《中國企業綜合調查報告》顯示,機器人占企業勞動力的比重,從2008 年的12%提升至2017 年的37%。

大廠不斷升級自動化流水線,無人即可運行的“黑燈工廠”早已不是新鮮事兒。2020 年,雷軍透露,小米科技“黑燈工廠”已實現全自動化,年產百萬臺手機,二期工廠建成投產后,年產值或達600 億元。2021 年,董明珠也宣布,格力全產業鏈都實現智能化,過去一萬人的工廠現在只需1000 人。
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階段,中國經濟未來將圍繞著智能創新不斷發力,搭建智慧工廠已逐漸成為制造業剛需。而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城市化進程加速,生活消費需求更加豐富多彩。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多勞多得的低門檻崗位,擁有著比車間更舒適的環境,和更可觀的預期薪資,吸納了許多從工廠一線退下來的工人。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互聯網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歐陽日輝認為,隨著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生活服務業承接了不少流水線工人,一方面可以緩和結構性失業造成的沖擊,同時也能增加就業、構建多層次的就業市場。此外,也給當地年輕人提供了更多就業選擇,不少年輕人在收入、自由、技能等多維度進行選擇,尋找滿足自己需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