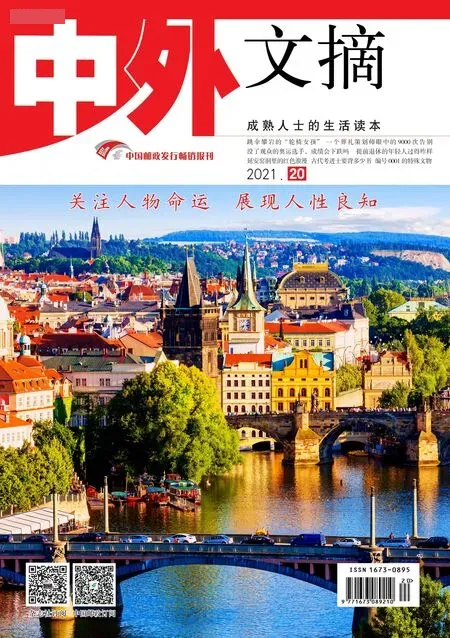在津和野,我看到了另一種生活
□ 李勝博

在日本鄉村旅居的起因是我看了一部日本電影《小森林》,故事講的是一個從小在日本鄉村長大的女孩子,去了大城市讀書之后最終又回到鄉村生活的故事。
大學時期因為有過一次休學搭車旅行中國的經歷,我有幸去過很多中國的鄉村,有過一些身臨其境的了解,所以當我第一次看到那部描述日本鄉村的電影時,感到非常驚訝,電影里面所描繪的日本鄉村,打破了“鄉村”這個詞在我腦子里的固有認知,它干凈、漂亮、舒適,富有美感和藝術感。
為了一探日本鄉村的真相,我索性真的找了一個日本鄉村,并由此過起了前后累計一年的旅居生活。
與津和野相遇
我旅居的日本鄉村叫做津和野,是日本一個非常不起眼的小地方,可能日本的老年人會知道它,但是大多數的年輕人并不了解。津和野位于山口縣和島根縣的交界處,四面環山,是一個坐落在山谷里的村鎮,自然環境優美,四季鮮明,常住人口3000 人(后來和附近的日原町合并,人口達7000 人)。這里是日本的大文豪森鷗外的故鄉,曾經也出過一個叫做西周的哲學家,后者和中國有一些淵源,把西方的一些哲學與社會科學術語翻譯成漢字傳入中國,比如“哲學”“科學”“理性”“主觀”“演繹”等。
在經濟泡沫時期的日本,津和野曾經是一個知名的旅游景點,人潮涌動。但是隨著經濟泡沫破滅以及國際旅游的興起,津和野慢慢地淡出了日本人的視野。
我和津和野的淵源源于一個叫couchsurfing 的沙發客網站,通過這個網站,你可以認識很多愿意把自己的家門打開、給陌生人提供免費住宿的人。當時一個女孩Saki 把津和野推薦給了我。Saki曾經在聯合國實習過,工作內容是協助制定公共政策,維護世界和平,但是最終她放棄了在國外高大上的工作機會,來到津和野做起了殺野豬的工作。
事情起因于2011 年日本那場聞名世界的大地震,當時她以一個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到救援工作中,在這個過程中,她說自己最感動的是通過自己的工作,可以收獲當地人對她表達的真誠的感謝,那種感覺和自己坐在辦公室里做一些書面工作的感覺非常不同,后者是一種更加抽象的、冰冷的、機械的感受。相比之下,人和人之間相處的感受更加打動她。所以她認為自己在那個時候至少應該先從一線工作開始做起。不同于中國把野豬定義為一種保護動物,在日本,野豬因為經常會在村子里毀壞莊稼、產生破壞而被定義為自然災害,很多農村都有獵殺野豬的習俗。Saki 吃過一次津和野的野豬肉,覺得肉質鮮美,調查之后又發現其營養豐富,所以考慮再三,決定把野豬肉做成一個更上規模的產業,如果可行的話,那么這個事業一方面可以幫助地方減少自然災害,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幫助地方增加經濟收入,在她看來是一個很好的方向。當我見到她的時候,正好是她野豬事業的第一年。
類似于Saki 這樣有著豐富背景經歷的年輕人,在津和野有不少,比如有在美國讀書之后周游世界然后回到日本鄉下種田的;有在美國畢業之后回到鄉下的高中做教育革命的;有從日本最好的大學畢業之后在鄉下做一些地方振興嘗試的;也有人有過很多的生命經歷之后在鄉村找到生命答案的……
在日本,近些年開始選擇去鄉村生活的人逐漸增多。追其原因,當地人分析說可能是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以及大型自然災害的經歷,給社會整體帶來了新的思潮,很多新一代的年輕人開始對生命意義有更多的思考:我為什么而活?我想要什么樣的生活?好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其中一些人思考出自己的答案之后,就把移居鄉村作為一種實踐的方案去嘗試。
另一方面,日本的政府也出臺了一些相關的政策進行宏觀調控來影響人口的遷移,比如我在日本鄉村里認識的不少年輕人就是經過一個叫做“地方協力隊”的項目過來的。這個項目是由日本總務省發起的,撥出一些預算給到一些帶有技能的年輕人,以地方協力隊成員的身份來解決地方政府提出的課題。政府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在解決地方問題的同時也能夠增加地方的年輕人口。
而這些政策的背后,暗示的是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日本和大多數國家一樣,大城市的虹吸效應使得小地方的人口衰減十分嚴重,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年輕人結婚生子的意愿下降,普遍造成了鄉村少子高齡化的現象,地方活力下降,經濟衰退。如果你有機會去日本鄉村探訪的話,第一個直觀的感受肯定就是清凈,路上沒什么人,也會經常看到一些閑置的空屋。比如我的朋友就用1 萬日元(相當于人民幣600 元)的租金租下了一個六室一廳的大房子,同時還包括前面一片田和后面的一座山。雖然他已經40 出頭了,但是笑稱自己是這片區域的年輕人。
雖然中國和日本的鄉村都面臨著人口減少的問題,但是,日本鄉村更有一種清凈的與世無爭的感覺。因為日本整體的社會福祉、醫療以及飲食健康方面都在世界上非常領先,所以就造就日本成了全世界平均壽命最長的一個國家。不僅如此,村里的老年人也不是每天閑著沒事干,除了勞作之外,他們還會積極地通過參與所在地的文化活動以及公益活動來充實自己的業余生活:茶道、花道、音樂、閱讀、運動、舞蹈、歌唱、電腦……各種各樣的都有。曾讓我非常震驚的一個畫面是在小鎮的某個公共區域正在舉行一個公益的電腦培訓班,參加者是好幾位白發蒼蒼、目測有七八十歲的老奶奶,他們正盯著屏幕一個字、一個字認真地敲打著鍵盤,來學習電腦軟件。
盡管老年人的業余生活豐富多彩,精神生活充沛富足,但是因為沒有新生人口的介入,仍然掩蓋不了少子高齡化對地方可持續發展的影響,這是整個日本國當下都在面對的一個關于未來的嚴峻課題。
鄉村里的人生方向
不過,不同于中國主要由政府來主導社會議題的解決,日本社會以一種更全面細膩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除了政府會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之外,民間也會進行自發的努力。
比如我所在的津和野就有一所當地的高中在進行很有趣的教育嘗試。宏觀的人口衰減現象表現在具體的學校層面就是學生數量的減少,很多年前,學校的領導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且試圖去積極改變。
“千萬不能讓學校毀在我的手上”,這是津和野高中校長當時的心情,“所以,與其維持學校的現狀、任由其衰敗,不如做一些方針上的調整,放手一搏。”于是,學校開始改變自己的教學方針,從以前的“如何讓學生更多地進入到更好的學校里面去”轉變成了“如何讓學生在3 年的高中生活里盡可能地想清楚自己未來的人生方向”。
如果有學生想清楚了自己未來的方向,那需要上大學的就可以去上大學,不需要上大學的也可以去個技術學校,或者找一個師傅當學徒也很好。
正是因為這種教育方針的改變,使得學校開始吸引一些對此感興趣的年輕師資力量流入,學校也開始慢慢地有了自己的特色,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其他地區,比如東京、大阪的學生過來就讀,甚至還有一些國外的留學生過來交換。
同時,也是因為這樣的改變,很多學生在上學期間有非常強的動力去做自己的一些興趣的探索:有人喜歡釣魚,因為津和野自然環境優美,所以來到津和野高中就讀;有人喜歡火車,而這邊恰好有蒸汽火車SL,所以來就讀;有人不喜歡大城市的喧鬧,更希望接近清凈的狀態;有人有一些關于動植物的學術課題研究,所以跑到更接近自然的地方來。
學校的這種嘗試最終反而使得這里的學生升入名牌大學的數量大大增加,又變相地增加了學校的影響力,最近幾年的生源也一直在穩定地向上增長。
但是,不同于津和野高中希望通過教育方針的改變來避免學生人數減少的問題,附近的一所小學的考慮是:如果學生人口的減少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那在這個無法避免的未來的基礎之上,我們要做些什么呢?
當我訪問柚野木小學的時候,學校里一共只有7 個學生,基本是每個年級就1 個學生,有些年級甚至沒有學生。但是,盡管學生很少,每個學生獲得的教育資源卻是非常充沛的:有8 個常規和臨時的老師,學校的設備也都一應俱全,家政教室,物理、生物、化學實驗室,體育館和游泳池,應有盡有。

隨著更多的有獨立想法、活力、創造力的年輕人加入,鄉村生活日益豐富起來
雖然我聽說過日本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但是那個時候也還是很好奇,專門為幾個孩子建設這么好的硬件設施,是不是投入的成本過大?直到后來,我才了解到這個學校的設計之初就考慮到這個地方未來會沒有孩子使用,那個時候,這個建筑就可以直接投入到老年人的看護事業里面去,因此設計者在開始設計之前,就是以這樣一種復合功能的空間來做考量,所以,雖然現在的這個建筑是一個學校,但未來就會變成一個養老院。
在日本鄉村,少子高齡化問題已經衍生出了其他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政府也好,社會組織也罷,或是一些具體的個人,都為此在做出各自的努力。不過,這些努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解決鄉村衰退的問題,大家都說不好。有些人覺得在這些努力中看到了未來的方向,而在另外一些人眼里,這些努力只是不可避免的消亡過程中的垂死掙扎。
這兩種有差異的視角,主要來源于兩類不同的群體。在當地一些上了年紀的原住民看來,大家就都不要折騰了,好好過日子就行了,這個地方未來也是沒有什么希望的,過好現在的生活,未來安靜地消失就好了,比如前面提到的從事野豬產業的女孩Saki,在嘗試了幾年之后,因為勢單力薄,最終放棄了這個工作,選擇了結婚嫁人相夫教子;而在另外一些年輕的移居者眼里,這些地方具有不為人知的魅力,大有可為,比如一個叫Ushi 的男生,就是在津和野的高中里做教育改革嘗試,并且開始逐漸成為日本教育界的一個典范。
我特別理解這兩種視角的差異,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兩類生理狀態不同的群體,年長的人衰敗,年輕的人富有活力,與其說他們對鄉村未來的想象是一種理解與判斷,不如說他們對鄉村未來的想象是自己生理機能的一種投射。Saki 更多地是和當地的長者協作,會遇到很多的挑戰;而Ushi 更多地是和可塑的年輕人相處,可能就會產生更多的可能性。

柚野木小學學生在上音樂課
基于這樣的原因,在我看來,鄉村的希望其實在一些年輕的人口身上,尤其是一些年輕的外來移民身上。我經常強調用“移民精神”培育一個地方的文化,并以此為基礎作為地方振興的儲備。這個觀點就來源于我和當地的新村民的接觸。“移民精神”的內涵一方面是一種小眾獨立的想法:因為他們和主流的想法不一致,所以才想要離開,發生移民行為;另外一方面是飽滿的精神和能量:他們確實把想法付諸行動了,而不只是停留在嘴上,也不是停留在心里。
所以,一群帶有移民精神的人所孕育出來的豐富、多元、飽滿而富有活力的文化,是一個地方想要重新振興的基礎。而這樣的地方文化形成之后,轉而又會開始吸引更多的有獨立想法、活力、創造力的年輕人加入,從而進入一種正向的循環,先積累人群,然后孵化團隊,進而產生項目,擴大影響力,吸引更多的人群,如此反復。
但是,這些年輕人作為新文化的代表介入到鄉村的生活,勢必又會和當地年長的原住民產生交集,這種交集可能會是一種溫和的融合,但大多數時候也有可能成為一種激烈的沖突。
以我自己的個人經歷而言,從我大學休學旅行的那年到今天寫下這些文字的這一刻大概過去了十來年,通過這十來年的相處,我的家人才開始逐漸從拒絕過渡到接納,再到理解,然后才最終支持我的“乖張奇葩”的言行舉止和“不務正業”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一個鄉村,作為一個更加封閉的古老的文化的載體,需要多少時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外來的新生文化所激活,并且運營出可持續的生命力,大概是鄉村振興真正需要解決的課題吧。
我曾經給津和野的町長提過一個建議:如果能夠讓人一想到這個地方,腦子里就冒出來“這是一個讓人重新實現理想生活的地方”的話,也許就會有源源不斷的年輕人過來,那么地方也會因此更有活力。我自己后來也做了一個項目,理念是“讓每個人成為每個人”。在我看來,能夠正確地梳理個人、群體以及土地的關系,能夠實現一種互相協助的氛圍,這大概就是每個地方最終能夠振興的最重要的根基吧。